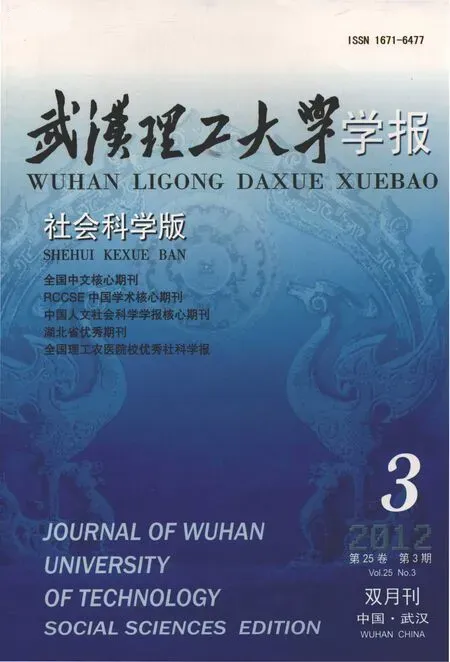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王 忠,程启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与职业健康安全规制*
王 忠,程启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职业健康安全的内在联系,并构建了一个产权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随经济增长而波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析。认为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策略应寻求对劳动力产权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市场中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均衡,并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
职业健康安全;经济增长;劳动力产权;协同规制
一、引 言
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劳动力产权的利用与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又是职业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基础。国内目前针对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研究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成果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经济贡献率,经济产出水平与生产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劳动力产权的形态与归属以及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来讲,职业健康安全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问题。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职业健康安全被视为是劳动力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对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协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政治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和管制经济理论出发,对影响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劳动力产权问题和规制政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产权改革和协同规制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
二、一个产权要素的分析框架
产权,是西方契约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它既可以是对物质资本(如,房屋产权)也可以是对非物质资本(如,知识产权)的占有与支配。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当权利规定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也往往会发生变化[1]。在产权理论看来,产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形成与他人进行市场交易的合理预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运行规则是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会影响到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市场交换活动的安全。按照巴泽尔的观点,产权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完全界定产权的成本太高。因而,产权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该项权利的“公共领域”[2],那么,类似职业健康安全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因健康和安全产权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领域”治理的问题。产权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规定来界定产权;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界定产权。前者是借助国家公权对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在干预,如国家所有制对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后者是借助个体自身力量对个体权益的私人捍卫,它取决于捍卫的结果对个体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如果预期收益大,捍卫的努力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产权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力产权;另一种是物质资本产权。这两种产权形态都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劳动力产权要素和物质资本产权要素关系的演进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实质,即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3]。在对人的依赖阶段,单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存在,人们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将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力产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自然的风险和外在的威胁,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劳动力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稀缺性,只有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联合才可以解决个人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间基于对物质的占有或交换形成了社会交往的行为关系,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资本要素”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具有稀缺性,通过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换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赖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又回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形式上,“劳动力要素”中的“收益权”具有稀缺性,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重新配置,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它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社会阶段,如,中级或高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劳动力产权是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要素。劳动力产权是基于劳动者全部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关系,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与发展权等[4]。劳动力产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其权利主张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同时也是不同经济社会人与物之间依赖关系相互演进的逻辑基础。职业健康安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交换所能实现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劳动力收益权和发展权的具体体现。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恶化会降低劳动者对劳动的供给和边际产出,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合乎逻辑的判断应该是,经济增长应平等考虑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因为这两者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是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没有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价值也无法实现。”[5]我们这里将生产资料要素与物质资本要素进行了概念的类化,实质上都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要素。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我们逻辑的判断相隔甚远,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货币等)和某些无形物(如商标、专利等)看作是产权,现有的和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社会制度法律都没有把人的劳动力当作产权来对待。
劳动力产权的残缺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伤害的制度根源。随着资本产权的发展壮大,劳动力产权的残缺不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最终会出现强资本产权而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结构[6],并进而发展演变为“资本雇佣劳动”与“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契约结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这种契约关系中劳动力市场平等交换掩盖下的资本产权与劳动力产权之间权利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有剩余劳动,原因在于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者在理性资本面前几乎不可能具有劳动契约签定和退出的自由,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较强,它则可以与雇主建立有利于其个体的契约安排;而如果劳动者个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的能力不足,劳动者便失去了与资本产权或雇主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劳动者的权益受损问题则不可避免。
三、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产权逻辑
按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是基于职业健康安全的市场失灵,劳动交换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作业场所风险和职业伤害外溢等问题,前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内部性问题,而后者是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问题[7]。无论其在劳动交换过程中是发生内部性问题还是发生外部性问题,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反映了劳动者所遭受到的额外损失或外在成本,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都可以放在统一的产权分析框架之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剧”,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成为嗜血的工具。当然,产权的归属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共有制形式,即产权由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各成员将权利联合起来交由共同体(如,国家)来实施[8];另一种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体将产权界定给私人所有,并承认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该产权的权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护下自由实施。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这类劳动力产权而言,其产权到底是属于公共所有还是属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职业健康安全的产权属性便成为我们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制度基础。
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从内容层次上来讲,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共同性产权,二是个性化产权。对于共同性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它是对劳动者为使生命延续而拥有的劳动权与使生命具有意义而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权的体现。洛克曾指出,人“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的自由”,“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9]。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拥有何种权利,我们都不能损害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产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应采取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实施供给,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正义和社会公平。而对于个性化产权而言,职业健康安全权是劳动者基于个人收入、地区差异、工作差异、身份差异等众多原因而衍生出来的更高层次权利的体现,它反映了劳动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个性化的健康安全权利在性质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与纯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性化产权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其供给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纯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门无偿提供的方式,因为它还体现了部分劳动者对职业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国家公权力依靠税收无偿供给的不公平。因此,应采用混合制的供给方式,主张私人供给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形式。
那么,对于职业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手段而言,我们不管是选择政府管制,还是应该选择自由市场或者两者皆有的手段,它都体现了我们对劳动力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种能够创设明晰、确凿及可让渡的且受私法保护的产权政策,私人谈判、私法执行都可以成为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虽然私人谈判、私法执行也是有成本的,但这类成本可以在较为清晰明确的产权体系的安排下得以内化。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决定谁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体现了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效率性和经济性的价值取向[10]。而在随后的管制经济理论中,职业健康安全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雇主比劳动者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如对工作环境、工作风险等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劳动者在与雇主订立劳动合约时常常成为被欺骗的对象,使得劳动者对劳动过程中职业伤害事件发生性的真实概率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者若需要通过自我搜寻的过程来获取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状况的充分信息,则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等等,劳动者需要权衡信息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并最终会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职业劳动的交换行为。因此,劳动力产权的有效实现则依赖于政府管制的保护,它体现了对职业健康安全劳动力产权保护公平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取向。
职业健康安全与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适应于私有制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政府也许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等问题,但通过政府干预所建立的管制机制,却并不能解决劳动力产权配置的效率性和经济性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个性化产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言“只要是因为排他性产权无法解决冲突性(或竞争性)使用的问题,其产权界定就永远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形成产权的“公共领域”,导致该产权的“公地灾难”。因此,对于劳动力产权而言,因“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模糊产权便成为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纳给出的方案,模糊产权的冲突性使用问题可以通过财产法和民法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前者可将使用权转让给最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团体,而后者则可使使用者承担义务[7]。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产权逐渐呈现出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产权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通过建立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应对健康安全产权保护的公平性和社会性;而个体性产权是个性化需求的体现,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对于这类产权需要建立相对明晰的个性化产权制度,让私权主体之间自由博弈相互调适,以形成有助于职业健康安全伤害成本消散的内部市场来应对健康安全保护的经济性和效率性。
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产权分析
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按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国家经济的发展须经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个阶段[11],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也会经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抛物线”的演进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健康安全效益的改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将不断恶化,在中期阶段会出现“拐点”,而在中期阶段以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状况将不断得到改进。当然,这只是我们一种经验判断上的假说,我们还需对波动出现的时间、形态进行实证检验,当然我们还希望这种经验判断是可以被证伪的,同时,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波动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因此,我们急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职业伤害从高发到低发的转折,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中某些内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动),还是因为某些外生性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如,政府规制)?如果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与劳动力产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劳动力产权的规制改革来成功跨越这一假说所揭示的波动“拐点”?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规制机制能够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产生影响的话,其具体的规制政策又应该是怎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实现条件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综合利用的结果,两者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不同经济阶段所采取的不同产业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产业模式或产业结构又是影响和制约职业健康安全的根源性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高风险特性的资本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安全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概率则较大;而如果产业结构中具有技术性、服务性特性的消费品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职业健康面临的风险和伤害发生的概率则较小,职业伤害事件发生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弱。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劳动要素的供给也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出现由粗放型供给到集约型供给的转变,劳动生产将从高风险、高强度的重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型、服务型的服务业,职业健康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将渐次降低。因此,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并进而引致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从职业健康安全倒U型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形态来看,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及其政府规制是实现其“拐点”转折的充分条件。劳动力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规制确权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础,他们之间具体的责、权、利关系都可以通过各行为主体间的自由谈判或外在的政府规制来确定,劳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非对称性信息、负外部性等问题都能够在双方合意的产权契约中得以解决。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劳动者捍卫自身劳动权利的谈判能力不足等现象时,劳动者便失去了与雇主在订立劳动契约中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契约机制便无法自发形成对劳动力产权的保护,从而形成强资本产权与弱劳动力产权的等级产权结构。在此产权结构中,资本要素便具有了剥夺劳动者权益的合理动能,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内生性的市场环境。当政府在寻求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保护时,若规制机制存在制度缺失、规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问题,职业伤害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波动出现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这则为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发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环境。
中国正处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职业健康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年均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单位GDP死亡人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伤亡水平[12]。按前所述,导致这样一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围绕物资资本要素而展开的,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产权改革还未开始。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物质财产得到了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国家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业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质财产产权为主导的单一产权制度,国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大量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足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农村劳动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毫无竞争优势,工作选择性小,只能选择脏、苦、累、毒的职业安全风险大的行业,劳动力供给有限过剩和劳动者进行个体权利捍卫的谈判能力不足是导致劳动力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内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偏在问题普遍存在,劳动力产权的责、权、利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职业伤害的频繁发生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又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一个社会劳动力产权的实现方式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它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均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13]。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引起的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实质上是对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对产权的改革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实现了生活资料异常匮乏的自然经济形态向物质供给日渐充足的商品经济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面对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通过实行干预程度最深,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公权对社会生产所赖以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其间职业伤害事件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波动,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尚未出现变革的需求。其次,伴随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国家单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渐演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产权逐渐明晰,市场效率不断提高,但其间职业伤害事件频发,社会逐渐出现资本产权强与劳动力产权弱的等级产权结构。劳动力产权的保护在国家优先经济发展的战略下,不断受到经济理性的越界干扰和损害。
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应对策略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劳动力产权面临着两种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规制对劳动力产权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个是源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这两种低效率本质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种低效率同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潜在风险,即物质资本产权的过分张扬与劳动力产权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分化,并进而撕裂社会系统的均衡,社会系统的失衡然后又会传导至政治市场,造成政治市场的失衡,并最终形成对国家现代化的阻碍。那么,对于中国职业健康安全所存在的这样一种低效率,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制度的重塑,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在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呢?
通常来讲,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对劳动力产权中的“模糊领域”进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种能有效促进劳动者与雇主之间通过自由谈判来订立劳动契约的产权规制机制,为劳动契约的产权纠纷和自我裁决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环境;二是通过对经济增长中具有高风险性的重工业、采掘业及建筑业等产业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性规制机制,并配合运用职业健康安全社会性规制的政策供给来形成产业进入的壁垒,为职业健康安全的改进提供内生性的市场环境。我们知道,劳动力产权的契约机制和政府规制是实现对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拐点”时间和“拐点”形态进行有效调节的外在性条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点”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的规制与变动是职业健康安全波动发生的内在性条件[14]。因此,对于职业健康安全波动的治理需要综合运用针对劳动力产权的社会性规制和针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性规制来加以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平等看待劳动力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出现前强后弱的等级产权结构,以大体实现经济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对比中我们发现,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权变性和可塑性等特征。从多样性的角度而言,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国与国之间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问题上倾向于以合作为本,强调政府、工会、雇主、劳动者之间对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共同责任;而美国则倾向于以法令为本,崇尚构建以私人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机制,由市场的力量自发调节对健康安全产权的保护,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参与,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放任政策的特点[15]。从权变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对待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政策主张经历了由经济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干预的规模;而社会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机会的均衡,希望扩大政府干预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造成的后果,对经济、社会进行适当调节,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从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可通过对权益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目标解析来寻求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与辅助性管制等手段的协调运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其规制效率因手段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瑞典鼓励劳动者与利益集团进行广泛的集体谈判和跨阶层合作,并配有辅助性的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要素累积的外生型经济增长模式到劳动力要素累积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之中,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增强。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它还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但是,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经济增长既会造成对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同时也会带来劳动者的经济性收益。因此,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目标取决于我们实现劳动力产权经济性收益与社会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众多目标间的总体均衡,最小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又有赖于社会“产权制度”或“权利秩序”的动态优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制度、环境、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对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它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权利冲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的协同规制需要以劳动力产权制度的改革为前提,解决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失衡等问题,这是实现从低效的政府干预到高效的多元互动转变的关键所在。
中国劳动力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实现应寻求劳动力市场中利益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并进而构建一种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维一体”的协同规制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应是体现政府、社会、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多方参与、协商共管的社会共责机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导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时,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威权来界定职业健康安全产权(或秩序)的方式,着眼于劳动力产权主体间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确立劳动力产权主体与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调适,实现多元互动,将职业伤害的系统风险和成本予以内化。
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对规制手段的分类[16],我们可以对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综合利用,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问题中所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首先,从经济性规制而言,应对第二产业中产业规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术水平不足的生产厂商加以限制形成进入壁垒,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生产厂商实行价格处罚措施,对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投入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投入的实行价格补贴,使单个生产厂商对职业健康安全的边际成本投入符合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的原则,降低职业健康安全的劳作风险。其次,从社会性规制而言,应对劳动力产权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并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保护机制进行调整,促进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就产权契约的订立进行自由博弈,以实现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平与正义。再次,从辅助性规制而言,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们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表现出弱化规制的行为。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还需要借助并加强对政府规制的执法监督,通过健全职业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职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以及职业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辅助性组织,从而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和程序正义,并努力使这些辅助性的力量摆脱国家规制部门意志的左右,以体现多元社会的共责之义。
[1] 王 珏.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6):39-44.
[2] 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M].上海财经大学,2006.
[3] 程启智.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与产权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 范省伟,白永秀.劳动力产权的界定、特点及层次性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3(8):42-46.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姚先国,方 浩.劳动力产权:分析角度、现状与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10(4):66-71.
[7] 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 钟武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中国化:联合产权理论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76-80.
[9] 洛克.政府论[M].冯克利,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10] 斯蒂文G米德玛.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M].罗君丽,李中奎,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11] 毛 健.经济增长理论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3] 张 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4] 程启智,王 忠.基于风险控制的职业健康和安全管制权力配置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12):38-42.
[15] 陈根锦,邓广良.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香港新自由政策体系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conomic Growth,Labor Force Property Right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WANG Zhong,CHENG Qi-zhi
(School of Economics,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Hubei,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inner link of economic,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from the angle of labor force property right and capital property right,and also to construct one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perty right.Based on the former research,it further studies the inner reasons why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would fluctuate tag alo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hina should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labor force property right,and realize the multimember mutual gamble among poly-profit individual,aiming to set up one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 which comprises the government,society,laborer and employe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economic growth;labor force property right;cooperative regulation
F406.8;F241.2;D08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1
2012-02-15
王 忠(1979-),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府管制与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程启智(1952-),男,湖北省宜昌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管制与政治经济理论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73113)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