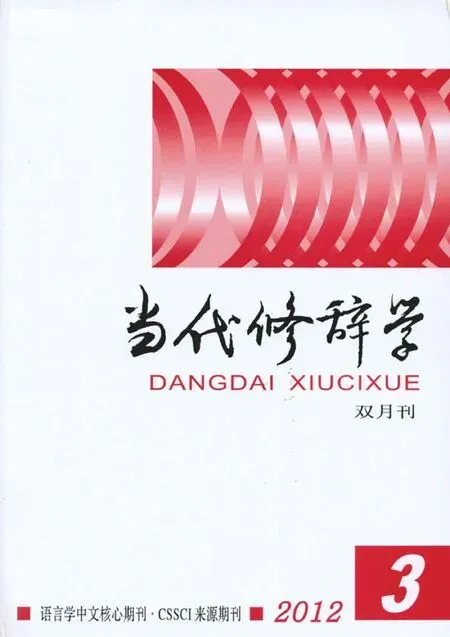对话性: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
王永祥 潘新宁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97/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南京210035)
提 要 超语言学是巴赫金建立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学理论。超语言学突出地表现出交往性、对话性思想。对话性是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支柱、理论核心。本文从对话和对话性的内涵、对话性的表现形式——双声与复调等诸方面阐释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的对话性思想。
一、引 言
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是针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而提出的语言研究理论。索绪尔是在自身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内部研究语言,而巴赫金则是在语言之上,或者说是在语言之外研究语言。他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明确提出他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巴赫金1998(5):239)。“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1998(5):269)。
在一个语言被设想为抽象符号系统的时代,巴赫金高度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关系中、对话中的语言——话语。在那个普遍将语言视为体系的时代,巴赫金在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有保留的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新颖的注重关系性、注重对话性的超语言学,使他的语言学理论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巴赫金在他的超语言学理论中围绕话语等概念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他的对话性思想。他指出,“话语是针对对话者的”(1998(2):435);“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决定,即无论它是谁的,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1998(2):436)。作为话语的基本单位,表述也只能构建于两个由社会组织起来的人之间,“任何表述和完成型的书面语,都在回答着什么,针对着某个回答。它只是整个言语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任何一种文献都在继续着前人的劳动,与他们争辩,等待着积极的回答,预料着回答等等”(1998(2):419)。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是一种交往性、对话性语言学。对话理论是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支柱,对话性是他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
二、对话与对话性
何为对话?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对此如何阐释?
在巴赫金那里,对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Bakhtin/Voloshinov1986:95;巴赫金1998(2):447):狭义的对话即人们面对面的、直接的、发出声音的言语交际,也叫对语。它要求进行言语交际的两个个体(在时空上)同时在场。它是最普遍的口头言语交际形式,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言语交际形式,巴赫金把“对话中对语之间的关系”视为“对话关系最外显醒目而又简单的一类”(1998(4):333)。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话有了更广泛的言语交际形式,如电话、电报、通信、电邮、网上聊天等。不仅如此,“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1998(4):333)。因此,广义的对话不同于实际对话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要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它包括任何类型的言语交际(Bakhtin/Voloshinov1986:95;巴赫金1998(2):447)。书籍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它预测、期待、联系着读者和评论家的积极理解和应答性反应,影响着有关同一言语交际领域的未来的著作;另一方面,它针对、回应着该领域过去的言语行为(包括作者本人和其他人的言语行为)。于是,“书面的言语行为仿佛进入了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对话:回答着什么,反驳着什么,肯定着什么,预料着可能的回答和驳斥,寻求着支持等等”(巴赫金1998(2):447-448)。巴赫金广义的对话打破了参与言语交际的个体必须同时在场的限制,打破了言语交际方式只能为口头形式的限制,他抽取了对话的本质:两个个体只要涉及同一个主题,即便生活在相隔数百年的不同时代,即便生活在相距上千里的不同地区,也能成为说者(作者)与听者(读者),也能产生言语交际,也能进行对话——问题的共性产生了对话关系。总之,巴赫金超语言学认为作品、理论、话语等等是一种关系主义、对话主义的表述方式:“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1998(2):380)
应该说,巴赫金在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内从对话中抽取出了对话性的本质,并使其成为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这是巴赫金在语言学领域里的重大贡献。如前所述,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即话语),超语言学是在“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巴赫金1998(5):269)。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总是作为一方的现实的对语而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产生对话性相互作用之中”(巴赫金1998(3):59),“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巴赫金 1998(5):242)。
巴赫金通过观察表述之间的对话关系来探究话语与表述的对话性,认为“对话关系(其中包括说话人对自己语言所采取的对话态度),是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1998(5):242)。对话关系既存在于不同言语主体的表述之间,也能产生于某一言语主体的表述的内部。李曙光(2007:64-65)将它们分别称作表述际对话关系和表述内对话关系。表述际对话关系不难理解:表述的主体更替性、完成性、诉诸性和情态性无一不决定了表述与表述之间具有对话性。如果将“生活是美好的”和“生活不美好”这两个论断摆在一起,它们之间具有这样的逻辑关系:一个论断否定另一个论断,但它们没有对话关系。如果这两个论断作为两个不同的言语主体的表述而出现,它们之间便产生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任何两个表述如果被放在涵义层面上加以对比,就会处于对话的关系之中,“拿两个彼此一无所知的他人表述来对比,只要它们稍微涉及同一个主题(思想),彼此便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对话关系。它们在共同主题、同一思想的疆域内互相接触”(巴赫金1998(4):318)。例如,当我们就同一个问题选辑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和哲人的不同表述时,这些学者和哲人(的表述)便展开了对话。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并非有意为之的对话性形式(1998(4):322)。
巴赫金还阐释了表述内对话关系。他说:“对话关系不仅存在于完整的(相对完整的)表述之间;对话的态度可以针对表述内部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部分,甚至是任何一个单词,只要那个单词不是被当作语言中无主体的单词,而是被当作表示别的某人的思想立场的符号,被当作另一个人的表述的标志;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中听出别的某人的声音。于是,对话关系可以渗透到表述内部,甚至渗透到单个的词语之中,条件是,其中有两个声音发生对话性的碰撞。”(Bakhtin1984:184)表述内部的这种“对话性的碰撞”即巴赫金所说的微型对话,他又称之为双声现象(见下节)。
除了在表述之间和表述内部,巴赫金(1998(5):244)认为对话关系还存在于:(a)不同的语体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b)人们与自己说出的话语(不论是整篇话语还是它的某些部分)之间,(c)所有能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之间(条件是:这些事物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巴赫金还研究了独白之中的对话性,他认为,“即使在深刻独白性的言语作品之间,也总是存在着对话关系”(巴赫金1998(4):334);同时,独白语中可能包含着不同声音①的争辩,对话渗透进每一词句之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之中、渗进面部表情的每一变化之中,激起不同声音的交替与斗争。这便是决定陀斯妥耶夫斯基语言风格特色的微型对话,这便是巴赫金要着力研究的双声语。
概言之,对话关系普遍存在于言语交际之中,对话性是话语的本质属性。
三、双声与复调:对话性的两种表现形式
作为文学批评家,巴赫金的文学批评实践非常独特:他以自己的超语言学思想为指导,以言语交际中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即话语)为研究对象,以分析小说话语为切入点,独具慧眼地阐释了自己对小说语言特征的理解:“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1998(3):39)他认为小说整体可以分解为几个从属的相对独立的统一体,长篇小说的修辞特点正在于将这些统一体组合为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小说的语言,是不同的‘语言’组合的体系”(1998(3):40);“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进入长篇小说,在其中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体系”(1998(3):81)。巴赫金以社会学性质的修辞学分析小说话语,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研究,从而提出他的对话性思想。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他揭示了小说语言对话性的两种表现形式:双声与复调。它们分别对应于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
1. 双声
双声原本是一个音乐术语(巴赫金的著作中使用了许多音乐术语,如双声、复调、对位法、泛音等),原指在演奏小提琴等乐器时可以一弓拉奏两条弦,此时两条弦发出的便是双声(缪天瑞1998:563)。双声还可能出现于多声部民歌之中。
在小说话语中,双声又是什么呢?巴赫金认为,杂语一旦引进小说(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引进的),都是“用他人语言讲出的他人话语”,这种语言便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双声语,“它立刻为两个说话人服务,同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意向,一是说话的主人公的直接意向,二是折射出来的作者意向。在这类话语中有两个声音、两个意思、两个情态。而且这两个声音形成对话式的呼应关系”。双声语就是内在对话化了的语言,其中包括幽默的语言、讥讽的语言、叙述人的折射语言、人物话语中的折射语言等等,“它们内部包含着潜在的对话,是两个声音、两种世界观、两种语言间凝聚而非扩展的对话”(1998(3):110)。
通过分析小说中作者话语与主人公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巴赫金对话语作了一些重要区分(凌建侯1999):主体性话语与客体性话语、单声语与双声语、单一指向的话语与双重指向的话语等。主体性话语与客体性话语的区分直接反映着小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当主体性话语与客体性话语(作者话语与主人公话语)“在一部作品中各守自己的领地,独立出现时”,它们都是单声语,都仅仅反映各自单一向度的意识、立场、意向。
通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话语的分析,通过对言语进行详细的分类(即第一、第二、第三类语言,详见巴赫金1998(5):246-256),通过与单声语的比较,巴赫金进一步阐释了双声语现象。他发现,一般的话语要么直接指述事物,要么就是被描绘的客体性的言语,其中只存在一种声音;前者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第一类语言,其目的只在于表现自己的对象,使人们直接了解事物;后者是第二类语言,它虽然也表现自己的对象,但同时又构成别人(即作者)所要表现的对象,它本身已经成为被描写的客体性的语言,作者对它的处理方法是:整体拿来,不改变其语义和语调,不赋予它别的指物述事的含义。巴赫金将第一、第二类语言都称作单声语。
但是,如果作者所利用的别人话语既保留其原来的指向,又添入作者新的意义,就会“一种语言竟含有两种不同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声音”(1998(5):250),这便是第三种语言——包容他人话语的语言(双声语)。第三类语言又分成三个细类,分别以仿格体、讽拟体和暗辩体为代表。巴赫金认为仿格体是单一指向的双声语,作者为了表现立意而利用他人语言,但保留他人语言自身的意向(1998(5):256),其间两个声音的互相赞同、互相肯定,这已经构成对话关系;讽拟体也借用他人语言,但作者赋予他人话语以一种新的意向,所以讽拟体是一种不同指向的双声语,这种语言成了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这两种声音之间互相敌视、互相对立;暗辩体不同于公开明显的辩论,不是直截了当地反驳他人的语言,而是间接地抨击他人的语言。暗辩体中的作者语言是在它所论说的对象物身上与他人语言相交锋。巴赫金将这第三个细类称作积极型的双声语,因为他人语言没有被作者掌握在手里而处于被动地位,相反,它积极影响到作者语言,迫使其作出相应的变化。
我们以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智斗》一场的几段对话为例,大致可以看出上述三种双声语的特征。《智斗》中胡传魁见到阿庆嫂时问阿庆到哪去了,阿庆嫂说阿庆“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然后又说“(他)在上海跑单帮哪。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胡传魁接着搭茬:“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这里的“男子汉大丈夫”,是民间俗语,胡传魁借这句俗语,表达了他对阿庆行为的首肯。说话者的话语意向和借用的他人话语的意向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仿格体。接下来胡传魁把刁德一介绍给阿庆嫂后,阿庆嫂发现刁德一是阴险狡猾的敌人,赶忙虚与周旋地说“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这里的“贵方宝地”、“树大根深”,或俗语或成语,阿庆嫂借来奉承刁德一,实际上却暗藏了对刁德一这种“地头蛇”角色的讽刺和挖苦。这便是讽拟体。接下来刁德一唱了一段夸赞阿庆嫂的话:“阿庆嫂!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阿庆嫂赶忙也以唱作答:“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开茶馆,盼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也是司令洪福广,方能遇难又呈祥。”这里,阿庆嫂运用“江湖义气第一桩”,“背靠大树好乘凉”之类的俗语,即是一种暗辩体。它不是直接地为自己抗日救国的行为辩护,而是假借“江湖义气”,“背靠大树”的民间生存理念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信念,并旁敲侧击地辩驳对方。我们看到,这种双声语确实使戏剧的对话充满张力而且妙趣横生。
概言之,双声语具有双主体性,即作者话语和他人话语各自的主体(作者与他人);双声语无论是单一指向,还是双重指向,都包含了两种判断,即作者与他人的判断;双声语就是两个声音、两种意识、两种观念、两种评价在同一对象物身上遭遇,在一个意识中相逢,在作者语言的每一成分中交锋;这两个声音之间形成了或赞同、或反驳、或补充的对话性关系。这就是微型对话关系。
根据巴赫金的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切方面(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话化的。这种对话化首先表现于小说主人公思想意识内部的微型对话,表现于主人公思想的矛盾和意识的分裂,从而形成了独白中的对话和对话中的对话这两种微型对话形式。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话语中暗含对他人话语的态度,包括预测的、评价的、赞同的、反驳的、补充的态度;戈利亚德金自怨自艾的申明和解释,伊万·卡拉马佐夫在伦理上和玄学上的托辞,马卡尔·杰符什金察言观色的语言,都能折射出他人语言。“‘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巴赫金 1998(5):276)。
对他人话语的预测和内心思想意识的分裂都构成双声的基础,促成独白中的对话,形成微型对话关系。
微型对话的另一种形式——对话中的对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及其语言之间关系的安排就是这种典型;阿廖沙的话和魔鬼的话都重复着伊万的话,却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语气:作为“他人”的阿廖沙在其话语里加入了钟爱与和解的色调,而魔鬼给伊万的内心的对话所带来的是讥讽和绝对谴责的语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中相互冲突和争论的,不是两个完整的独白声音,而是两个分裂的声音(至少有一个是分裂的)。一个声音的公开对语回答另一个声音的隐蔽对语”(巴赫金1998(5):346);巴赫金看到,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们内在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呼应或交锋”(1998(5):359)。形诸布局结构的表面对话之中蕴涵着暗中彼此呼应的内心对话,这便是对话中的对话。
2. 复调
与微型对话相对的是大型对话。大型对话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构筑其小说话语艺术的根本方法。巴赫金以另一音乐术语“复调”表述大型对话。“复调音乐”(polyphonic music)和“主调音乐”(homophonic music)都属于“多声部音乐”(many-voice music);主调音乐“只有一个主要的旋律,它可以在任何声部出现,其他的声部缺乏独立性,只对主旋律起烘托和陪衬作用”(高天康2003:2);而复调音乐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在艺术上有同等意义的各自独立的曲调前后叠置起来,同时协调地进行为基础的音乐”(高天康2003:1-2)。复调音乐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各声部都具有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它们彼此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
巴赫金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如同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他颠覆了独白小说的传统,突破了独白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创造了一个文学艺术的复调世界。
在巴赫金看来,独白小说类似于主调音乐。在独白型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式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只是作者意识的一部分,主人公的声音缺乏独立性,只能对作为主旋律的作者声音起烘托和陪衬作用。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则类似于复调音乐。在这种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分别唱着自己的互不融合的声部,主人公不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它们互相独立。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巴赫金1998(5):70),是能够直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议论具有特殊的独立性;它似乎与作者议论平起平坐,并以特别的方式同作者议论结合起来,同其他主人公同样具有十足价值的声音结合起来”(1998(5):5),彼此之间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1998(5):5),这些不同声音组成了真正的复调,这些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于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
“哪里一有人的意识出现,哪里在他(指陀斯妥耶夫斯基——引注)听来就开始了对话”(1998(5):56)。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具有对话性,整个小说的结构就是一个“大型对话”结构。所谓大型对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品中反映出的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本质。’换句话说,是生活中人类思想的对话关系”,二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董小英1994:32-33)。
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不是高踞对话之上的、决定一切的立场,而是一种认真实现了的彻底的对话立场,作者“是和主人公谈话,而不是讲述主人公”(巴赫金1998(5):84)。这样,主人公便具有其内在自由、内在逻辑、独立性和未完成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另一个货真价实的‘我’(‘自在之你’)”(1998(5):83);因此,在陀氏的复调小说中,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均具有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不是文学中假定性的对话,而是严肃的、真正的对话。这种大型对话是作为一个非封闭的整体构筑起来的。是一种未完成的对话。复调小说的作者把主人公“当作在场的、能听到他(作者)的话,并能作答的人”(1998(5):84)。
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是巴赫金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时所提出的一对范畴,它们最终构成了巴赫金的对话性原则;在巴赫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构建对话的原则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是主人公们公开对话与内在对话的交叉、呼应或断续。到处都有一些观念、思想和话语分属于几个互不融合的声音,在每种声音中又都独有意蕴”(巴赫金1998(5):369);“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1998(5):340)。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形诸布局结构的对话,与内在对话(亦即微型对话)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内在对话为基础。而它们两者同样密不可分地与囊括它们的整部小说的大型对话联系在一起”(1998(5):359)。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又可以相互转化。一方面,当构成微型对话的、处于一个话语主体内部的两个声音进一步发展分裂为两个话语主体的思想意识的时候,“原来的内部对话,就被公开化,原来看不见只能听得到的两种思想,两种声音的争辩,变成了两个人——自我和他者的人际矛盾”(董小英1994:31),“当内心矛盾已经发展到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思想矛盾就变成了作品结构的形式,而且,这种悬而未决的思想矛盾贯穿整个作品,这时,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对话,而成为大型对话了”(1998(5):32)。当然,巴赫金所提出的“大型对话”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小说文本内部,相对于微型对话而言,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主人公相互之间的形诸布局结构的对话关系是大型对话;而相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整个文学创作来说,这种大型对话又成了“小对话”或“微型对话”。与此同时,巴赫金也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作家展开了大型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巴赫金找到了他的隔世知音——陀斯妥耶夫斯基。
四、结 语
总之,巴赫金在语言表述的内部、外部、独白、对白以及作品的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等等多重关系中发现了对话及对话性,并以对话性为核心,构建了他的超语言学理论。这不仅为20世纪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而且也将对21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声音”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白春仁、顾亚铃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译本的译者注中对“声音”一词作了说明:“声音”在该书中获得了术语意义,指的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某人思想、观点、态度的综合体”(巴赫金 19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