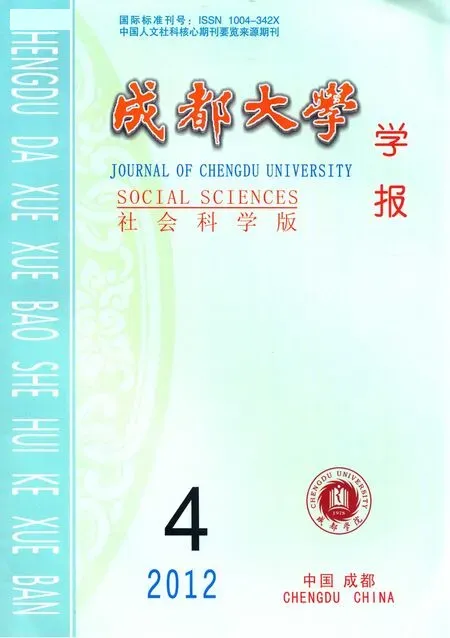羌族地区的石器时代历史文化遗存
黄辛建 张 弘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汶川623002;成都大学,四川成都610106)
羌族地区的石器时代历史文化遗存
黄辛建 张 弘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汶川623002;成都大学,四川成都610106)
从目前已发掘的文化遗存来看,羌族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轨迹。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痕迹则遍及了整个羌族地区,随后出现的石棺葬则是羌族地区人类活动连续性发展的明证。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据点的形成,基本奠定了羌族地区今后人类聚居群落的基本状况及城镇发展的基本区位。
羌族地区;新石器时代;石棺葬;羌族聚居群落
羌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带,即地理上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1]P42。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在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交流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孝通先生将其形象地称为“藏彝走廊”。羌族地区北接甘青、南连四川,居于藏彝走廊地区的岷江上游及湔江流域一带,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及黑水等县,以及与之毗邻的绵阳市西部北川羌族自治县一带。
一 旧石器时代的羌族地区
早在旧石器时代,羌族地区就已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位于今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烟云洞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是羌族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是目前羌族地区已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据推测,该遗址年代距今约2-3万年[2]P9。烟云洞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猿王洞风景区内,悬在距九黄环线公路约200米的半山腰,1989年,当地人在挖掘传说中的龙骨时,意外地发现一块属于晚期智人左下门齿的化石,而在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面,考古人员在挖掘过程中则发现了更多的动物牙齿化石,它们可能与2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有关系。198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北川县文化馆收藏到文物资料中发现的一枚北川人牙化石地点,则属于在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晚期。[3]
在同属于藏彝走廊的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发掘还发现了汉源富林、汉源狮子山、攀枝花廻龙湾、甘孜州炉霍县等多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汉源富林遗址是1960年地质调查发现的,位于流沙河与大渡河交汇处的大渡河左岸二级阶地上,高于河面20-25米。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四川省博物馆一道对遗址进行了挖掘,在约3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50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植物遗迹、用火遗迹等。研究确定,富林遗址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底层属晚更新世的晚期阶段。汉源狮子山遗址与汉源富林遗址仅一河之隔,发掘后显示的“主要特征与隔河相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林文化特征基本相同”[4]。攀枝花廻龙湾旧石器洞穴遗址于1987年被发现,地处四川西南金沙江北岸支流把关河的一条小溪畔。遗址分上、下两个文化堆积层,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5]P961983年,在甘孜炉霍县鲜水河东岸发现含有古人类和旧石器材料及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层位,可以断定属于晚更新世晚期,距今11000年左右,当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存。[6]
二 新石器时代的羌族地区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考古发现表明,人类活动已遍及整个羌族地区。目前,在该地区正式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石器出土地点十分丰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遗物采集点达到80多处。分布地点从松潘到汶川,从理县至北川,几乎遍及整个羌族地区。[7]其中最著名的主要有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箭山遗址等。
营盘山新石器遗址是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5]P119,位于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岷江东岸的三级缓坡台地上,距今约5500—5000年之间。该遗址发掘始于2000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容丰富,有古人类房屋基址9座、墓葬坑和殉葬坑5座、火灰坑80余个等。遗址中还发现一处大型广场遗迹,下存多座殉葬坑。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各类器物总数近万件,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主要以手工制作为主,形制主要有平底器和小平底器两种。出土石器则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种,有切器、砍器等,并有少量体积较小的菱形磨制石片,如斧、镜、刀等。出土玉器主要包括环钢形器等装饰品。
姜维城遗址是羌族地区发现最早、保存较为完好、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8]P13遗址地位于汶川县威州镇后山上,为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处、岷江南岸河流转弯处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遗址的特点主要有:遗址地点位于两条河流交汇的台地上,与同期的羌族地区文化遗存所处地点基本相似;出土陶器主要是夹砂陶,陶胎厚实,陶色有橙红,黑彩等,纹路为条带纹。石器类型主要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姜维城遗址是以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农业经济类型。
箭山寨遗址位于理县薛城乡杂谷脑河岸梭罗河与杂谷河交汇所形成的舌状台地上。发掘出文物主要以陶器为主,且主要为夹砂陶,陶器陶胎较厚,胎内有经人工粉碎后附着其上的石英粒、片岩和页岩粒等,陶器的工艺制作手法为手工制作,表面纹饰主要是绳纹有弦纹、平行线等,器物为平底罐、瓶等,陶色以橙红、黑彩为主。箭山寨遗址体现出当时是以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社会经济形态。[9]P16-18
三 羌族地区的石棺葬文化
所谓石棺葬,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度考古文化遗存[10]P110,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11]。石棺葬主要分为石棺墓、石板葬或者石板墓等类型,[12]是继新石器时代之后羌族地区最重要、最具有典型性的独特的考古文化遗存。这里的石棺葬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内涵之丰富、复杂,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羌族地区的石棺葬文化遗存主要为墓葬,遗址较少,另有少量窖藏及零星的采集点。羌族地区石棺葬以茂县城北撮箕山石棺葬、茂县凤仪镇石棺葬、理县佳山石棺葬、汶川黄岩村墓地为代表。其分布范围北起松潘,南至汶川,西起黑水,东至茂县和北川,中心区域在茂县中部岷江沿线沟口乡以南,茂县光明乡以西岷江沿线,汶川县北部等地,与今羌族地区高度重叠。[13]P89
1938年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在汶川县雁门乡发掘了第一个石棺葬,写成《汶川县小寨子残墓发掘记》于1951年发表于成都《工商导报》。1944年,美国学者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也曾报道过石棺葬在羌族地区的分布、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1964年,四川大学童恩正先生赴羌族地区的茂县、汶川和理县等地作考古调查,在当地清理和发掘了28座石棺葬,并以此次清理情况为核心,将1938年冯汉骥先生的资料加入其中,写成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首次对羌族地区的石棺葬文化遗存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1978年,四川省文管会的考古专家在茂县的城关进行挖掘时,发现并清理了46座石棺墓,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地发掘石棺葬墓地,对深入认识石棺葬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等部门的专家又在茂县撮箕山发掘清理了64座石棺墓葬。1986年,茂县博物馆人员又在基建清理过程中发掘石棺墓360余座,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至今发掘数量最多、布局最为集中的一处石棺墓葬群。1992年,茂县博物馆考古人员等在牟托村发现并清理了一座疑似古代官员的大型石棺墓和三座陪葬墓坑,这也是我国至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的石棺墓葬群,[14]P60这表明羌族地区的石棺葬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末年,与该地区的新时器时代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与新石器时代相衔接。同时,羌族地区的石棺葬文化还受到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但主要是土著民族所创造,应视为本地区主要的一种土著民族的文化遗留[15],“它主要是土著民族的葬俗”[16]。
结语
目前,追溯现代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所建立起来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模式,即根据发掘的古人类遗存,进行分析和比对,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古人类的祖先是从何时、何地而来。在我国云南元谋县境内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化石即为其中的典型。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另一种方法成为研究的主要趋势,即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现代人群的DNA样本进行比对研究,然后找出人类的祖源。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坎恩得出这样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人类共同起源于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17]P50按照生物遗传学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藏羌民族地区的人类活动的历史仅仅是在距今35000年至30000年之间以内的事情。[5]P91与此相对应,从目前已发掘的文化遗存来看,羌族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轨迹。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痕迹则遍及了整个羌族地区,随后出现的石棺葬则是羌族地区人类活动连续性发展的明证。
2008年,“5·12”汶川8级特大地震对羌族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在地震中严重损毁。如今,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时间,在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同时,对羌族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灾后保护、挖掘、收集整理和修缮工作也有所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挖掘羌族文化,推动羌族地区经济、旅游与文化发展,成为羌族地区地震灾后发展的主线。如汶川县绵虒县城已经打造出以大禹祭坛为核心的系列文化带,北川新县城、汶川县城均打造成了以大禹文化为核心的羌族新城镇。可以说,羌族地区在地震灾后显现出了异常踊跃的以历史文化尤其是羌族文化为核心和以大禹文化为亮点的灾后文化重建模式,并借此推动羌族地区的经济、旅游的新发展。
综上所述,羌族地区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挖掘仍有所不足,对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化本身,并未融入到今天的羌族地区的发展体系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箭山遗址及系列石棺葬文化遗存在羌族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点的分布基本奠定了该区域今后人类聚居群落的基本状况及该区域城镇发展的基本位置。今天羌族地区的重要城市,如汶川绵虒、茂县凤仪、北川县禹里乡等均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点发展形成的。因此,以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基点,追溯羌族文化的土著元素,使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存与羌族文化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广泛分布于羌族地区的丰富的石器时代历史文化遗存的社会功能和现实价值,成为当前羌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1]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北川县烟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
[3]叶茂林,邓天富.记北川县采集的化石材料》[J],《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4]陈全家.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
[5]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6]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J].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7]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1995年第5期.
[8]辛中华,郭富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05年第4期.
[9]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J].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10]石硕.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8年第5期.
[12]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M].四川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3]耿少将.羌族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4]罗二虎.20世纪西南地区石棺葬发现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15]童恩正.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J].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
[16]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葬研究[J].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7][美]斯宾塞·韦尔斯著,杜红译.人类史前[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
K871.1
B
1004-342(2012)04-55-03
2012-04-19
项目简介:本文系阿坝师专重点课题(11SB114)“藏彝走廊:民族变迁与融合”、四川省教育厅面上课题(ASA11-20)“藏彝走廊:民族变迁与融合”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黄辛建(1979-),男,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在读博士;张弘(1974-),男,成都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