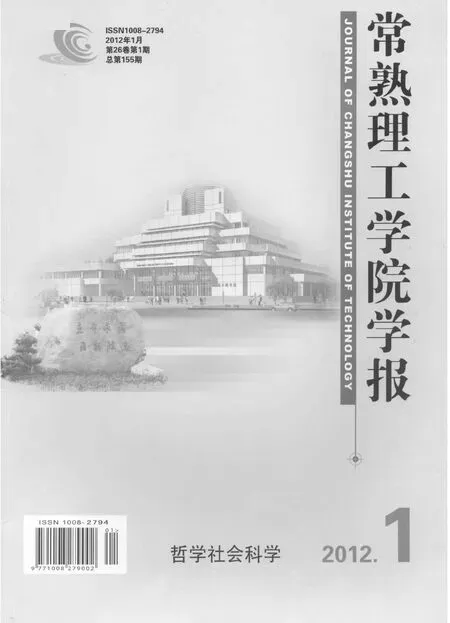马克思分工范畴的内涵演进及其哲学意义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雇佣劳动与资本》
李丹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93)
马克思分工范畴的内涵演进及其哲学意义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雇佣劳动与资本》
李丹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93)
《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三部文献是体现马克思中期思想的主要文本。在这个阶段,分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证范畴,被马克思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其地位与作用。分工范畴内涵的深化与发展就是其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批判性及其所蕴含的生产关系维度被逐步发现、揭示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马克思最终确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和逻辑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推动和影响。
分工;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之后,马克思逐步摆脱人本主义立场,更系统地研究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发现,要想彻底驳倒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不能从哲学论证出发,而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方法,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基点,展开基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开始尝试这一点,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始的。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成熟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维度的发现。而这趟“发现之旅”,分工范畴不仅是见证者,更是推动者。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范畴
在《形态》中,马克思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分工为逻辑起点,对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史进行了一番追溯。“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25当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的自然分工时,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随着分工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作用,才慢慢出现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可见,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一定的现实中的个人,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交往,并由于交往的需要而生产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马克思因此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30这一历史回溯反映了马克思此时具有的动态的历史视域——一个发展着的由分工推动的所有制演变史,以及颇具政治经济学色彩的理论前提——“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30。然而,由于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只能通过对欧洲经济发展史的现象式描述来阐发其哲学观点,既无法深入到具体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本质,也无法解释相继的所有制形式之间是如何实现过渡的。
马克思接下来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伴随着对“生活决定意识”的论述,而分工仍作为其论述的起点并贯穿始终。马克思的历史是动态的、过程的、具体的历史,意识就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出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当然是社会的产物。意识也有其发展的历史:从纯粹的畜群意识发展到本能意识,到足以代替本能的意识,再发展为能够现实地想象的意识;而要能够现实地想象,就必须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分工的发展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分担。这样,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就一定会发生矛盾,并导致:第一,某一民族内部出现矛盾,或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矛盾——从根源上来看,要想这种矛盾不发生,只有再消灭分工!第二,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产生矛盾——由于共同利益“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37,而这种共同利益对个人来说却是异己的,因此要想消除这种矛盾,同样只有消灭分工!如此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后,马克思总结说,要说明意识的所有产物和形式,就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43。
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一般社会存在和本质的哲学层面上来批判的。但值得肯定的是,马克思用分工取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规定,使之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证范畴。他的政治经济学尝试就体现在他从分工的角度来寻找异化产生和消亡的根源,并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这对他克服人本主义、在社会历史视野内考察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也意味着他开始从哲学层面的理论论战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换。
《形态》中的第二个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这是通过回顾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私有制的发展而得来的,这部分也是本文献对分工的第二次集中表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是城市和乡村分离。到中世纪,城市里形成了各种行会,行会内部基本没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由此产生商人以及城市间的贸易联系。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又引起新的生产上的分工,其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由此开始了活动资本积累及各国间的商业斗争。17世纪中叶以后,商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需求推动了大工业的产生。大工业的发展造成大量生产力,而这大量的生产力对不能适应其发展程度的私有制来说就成了破坏的力量。可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不断攀升并冲破固有交往形式的束缚、催生出新的交往形式,一段时间后又要再冲破交往形式的桎梏。马克思总结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83笔者认为,分工在其中的地位就在于:一方面,分工的扩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交往形式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要求分工不断扩大和细化,交往形式的发展、成形及其内部结构也决定了分工如何发展。
马克思说,分工造成社会关系独立化,即阶级、等级差别明显。各阶级的共同体中,个人只是作为阶级成员联系在一起,“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1]85实质上,在分工的范围内,一个阶级的解放只是变成另一个阶级,一个等级的破产也只是变成另一个等级。只有无产阶级除外,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动产,全部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本阶级范围内不可能获得变为另一个阶级的条件。这样,马克思得出结论:要建立一个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和自由的真正共同体,就应该消灭劳动分工。
虽然《形态》中分工已经是一个经济学实证范畴,但由于马克思此时刚涉猎政治经济学不久,他对一些经济学范畴的界定还不够准确,甚至存在错误。他多次提出要消灭劳动分工,但事实上他针对的是束缚人的奴役性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即劳动者分工,这两者绝不能等同。此外,虽然马克思已有意识地将分工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待其作用,但他还未关注生产过程本身,无法挖掘出分工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现不了分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本质差异。
二、《哲学的贫困》中的分工范畴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主要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有个典型的叙述逻辑:先假设某人对某物有某种需要,然后他向另一个拥有该物的人建议交换,由此产生交换价值。于是,交换价值的产生就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这种通过假设前提而得出假设的结论、由此建构出来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架空的、抽象的。生产者、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需要等等都被架空为纯粹的概念、词句,完全脱离了实际的生产和历史过程。马克思说,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不是这样。蒲鲁东不知道他所假设的需要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他提出需要本身就假定了分工和交换的存在,因而就假定了交换价值的存在。“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阶段。”[2]79“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2]87“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2]104这才是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表现。
可以看出,受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影响,以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为工具,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批判话语已经是经济学的了。他突破性地跃出了《形态》中所有制演变史的层面,而开始关注社会生产过程,如分工、生产、交换、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交换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他不仅摆脱了人本主义,更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带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就此走向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马克思也难免沿袭了李嘉图的一些错误,例如,他对劳动和劳动力还是没有区分清楚,也还没有论及交换价值与价格、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严格区别。
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针对蒲鲁东的《经济表的分析》,马克思展开了七个说明,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和前提,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并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尤其是突出了生产关系维度。在第一个说明中马克思正式提出,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生产如何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究竟如何产生。这一研究方向的提出直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使马克思远远高出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产关系维度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幕前。第二、第三个说明分别指出:作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143蒲鲁东却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通过辩证运动而互相产生的社会阶段,“当他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不得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但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2]144马克思就此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四到第六个说明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社会天才”的矛盾。第七个说明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将资产阶级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看作天然、永恒的,只是为了使人相信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应当永远支配社会。马克思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2]155到这里,《形态》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宣告发展成熟。
历史要发展,生产要维系,分工就不可阻挡。束缚人、奴役人的分工会被改变,但分工本身不可能被消灭。这一重大发现,就是以生产关系维度的发现、历史视域的确立以及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的确立为基础的。当马克思发现社会形态及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根本区别时,他也会发现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分工结构和性质。这也是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区分开来的一个产物。
这个阶段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入手来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同时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立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开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这使得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论著都很自然地存在一种过渡性质,即科学的方法和研究前提与尚没有解决的经济学具体理论问题的矛盾性。”[3]518所以在该著作中,经济学与哲学的讨论和逻辑是分离的,“他尚未将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有机地深化到经济学的科学分析中去。”[3]537
三、《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分工范畴
《雇佣劳动与资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此时已开始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是劳动力的表现,工人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其劳动力,工资就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格。在阐述工资是如何决定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有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与逻辑,研究对象正是生产过程和相关的生产关系领域。他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4]487
之后,马克思自然转向对代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讨论。资本的实质是活劳动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资本和雇佣劳动相互产生、互为条件:资本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保存并增大自身;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而,表面看来资本的增加使工人收入增加了,但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也增大了,工人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奴隶。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面目。马克思痛快淋漓地揭示出,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4]498
继《哲学的贫困》中区分出现代分工之后,承接《形态》中以分工为着眼点的批判视角,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分析了现代分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作用,由此展开他独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说,生产资本增长之后,竞争激烈的资本家为获得市场必须更便宜地进行生产、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于是要求细化分工、改进机器。新机器很快就会普及,导致生产力普遍提高,资本家们又站上竞争激烈的战场。于是又要求生产力再提高、分工再细化、机器再改进……但对工人来说,分工的细化作为这个循环的关键环节造成什么后果呢?第一,“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4]503;第二,导致劳动简单化,工人无需投入紧张的体力、智力或特殊技巧,导致竞争者增加、工资不断降低;第三,工人要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要加大工作量,但越是如此,所得的工资反而越少。在资产阶级社会,工人要想维持生存,只能不断把自己出卖给奴役自己的敌对权力。马克思通过现代分工清楚地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丑陋本质。至此,分工的生产关系属性的面纱完全揭开了。这里相对于《哲学的贫困》的进步就在于,马克思不仅区分了不同历史阶段分工的性质的不同,更展现了分工自身的矛盾本质,即批判性。它不断地否定自己,但这种自我否定越是彻底,就越讽刺了决定它的生产关系的荒唐本质!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终于以独立完整的形象来直面资产阶级社会,哲学话语的批判终于不再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立,而是“对象化在现实的经济分析之中”[3]537。这是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学直接接合,”“在古典经济学之上独立地解决经济学问题、真正从经济学上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尝试。”[3]537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再到《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两年,正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克服人本主义、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最终使之发展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剑。通过上述解读可以看到,这个质的飞跃的思想历程,也是分工范畴的内涵一步步丰富、深化的过程,这两方面是相互见证、相得益彰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Marx’s 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from German Ideology to Wage Labor and Capital
LI D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s:German Ideology,Poverty of Philosophy and Wage Labor and Capital are three important books that represent Marx’s mid-term theories and thoughts.During this phase,division of labor,whose status and function were observed by Marx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has become an empirical category.In es⁃sence,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category’s connotation is also the process how its historicity and criticality as well as its production relation are gradually discovered and revealed,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helping Marx employ the discourse and logic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the method⁃ological premi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vision of labor;production relations;historical materialism;political economics
A811.1
A
1008-2794(2012)01-0013-04
(责任编辑:徐震)
2011-11-11
李丹(1988—),女,江苏溧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