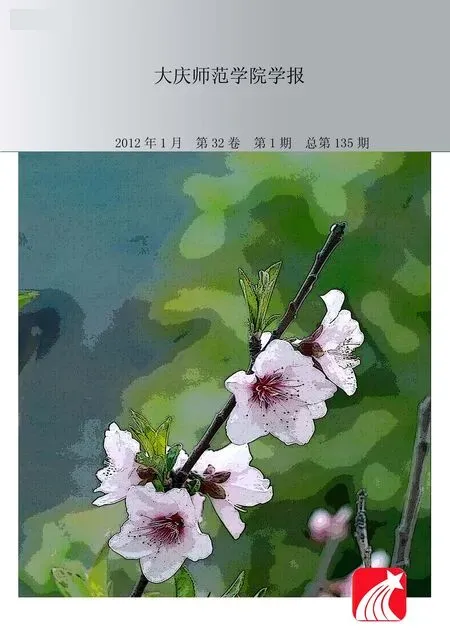晚明官员的收入构成
庄 赢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编者“首先将明朝历史两分,划定为前后期,以成、弘划线,其前为明前期,其后为明后期;然后将研究范围确定在成、弘以后,重点在嘉、隆、万以至明末,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1450—1644),期间大约二百年的时间跨度”[1]2。在参考并比对了当前明史学界关于晚明起止时间的种种分法后,笔者最终选取了万明先生对晚明起止时间的分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级官吏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者,政治上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经济收入上反映出来,晚明官员的收入主要由官俸收入、地产收入、经商收入及灰色收入构成。
一、晚明官员的收入形式
(一) 俸禄收入
官俸是国家支付给官吏的报酬,以保证其自身及家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怎样规定官吏的薪俸,不仅关系到官吏的自身利益及其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关系到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明代官分九品,各有正从,共十八级,是官吏队伍的基本组成部分,除九品外,还有未入品级的杂职吏员,以此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官吏系统。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个机构中,是明王朝治国理民的工具。明朝建国后,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了元初“百官未给俸,多贪暴”[2]卷30的历史教训,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充分调动文武官员在治国理民中的积极性,十分*重官吏薪俸的制定。
明代俸禄发放以官员品级为基础,所有的官员品级共分为十八等,实行年俸、月俸双轨制。明代官员俸禄制度的最初确定始于洪武四年(1371年)。是年,明太祖命中书省、户部制定文武官员的俸禄标准,规定: “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二品六百石,从二品五百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石;正四品二百七十石,从四品二百四十石;正五品一百八十石,从五品一百五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五石;正八品七十石,从八品六十五石;正九品六十一石,从九品五十石。省、部、府、州、县、卫、所、台宪有司,官验数月支。”[3]卷60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米、禄钞之制,“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四千六百八十八顷九十三亩,岁入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3]卷60明太祖在给户部的敕书中提到:“稽古建官,略知等第,其依品级次第……朕观古今之无品也,则以禄为式,是尚质量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与文质之道,虽华朴之有殊亦模范之可径,守之不紊,履之不烦。今之任官烦资,食禄法品,勒石昭示,命户曹司之,毋紊轻重之条,依期而给与之,斯之公良哉,故兹制谕。”[4]卷12明代官员俸禄制度的最终确定乃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首先是对公、侯、伯的俸禄发放制度进行改革,“令公、侯、伯皆给禄米,论功定数,责成他们各归旧赐田于官”[5]卷82,废除了明初“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5]卷82之制;其次,将核定官俸与文武官员的品、阶、勋相结合,根据官制统一按月发放官俸,规定:“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5]卷82这次俸禄改制与洪武十三年相比,正一品增加四十四石,正从八品和正九品分别增加一到三石,其余则大多减少了俸禄,多的减至一百八十八石,少则二石不等。很明显,这次改制大大降低了官俸的基本标准,进一步缩小了各品级间岁俸的差距。此后历代相沿,“自后为永制”[5]卷82。
从上述可见,明代官俸极其微薄。《明史》的纂修者曾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5]卷82清代历史学家赵翼亦说:“明官俸最薄。”[2]卷32另外,从俸禄的支领方面来看,官员应得到的俸禄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保证按月足额支领的。明朝初年, 为保证官员廉政, 实行考绩合格后发放俸禄的政策。“稽其在职一年内无过者, 照品给半禄终制; 三年历考无过者, 给全禄终制。”[6]卷43此种政策也一直延续至晚明,对于本以俸禄极其微薄的官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明代后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1]242“另一方面,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一系列制度改革并行,与社会变迁同步。”[1]243时至明万历年间,官方典章中已不再称薪俸或俸粮、俸米之名,而称其为俸银。如《明会典》所记:“万历九年题准,行在京各府卫掌印官查将各官关支俸银,如有事故等项,即行截日扣送太仓库。”[7]卷39明官员的薪俸在经历了米折钞、折支胡椒与苏木、折支绢布与衣服、折支盐茶与其他等多种形式之后终于找到了其最后的归宿,并一直为清朝所沿袭。
时至晚明,依然有些官员除本薪外还领取兼职的俸禄,或二俸,或三俸。兼支二俸例有,如嘉靖年间严嵩兼支正一品、尚书禄。后嘉靖三十八年“甲午以大学士严嵩年八十,诏苑直出入乘肩舆、岁支伯爵禄,赐银百两、彩币八表里及宝钞羊酒,仍宴于礼部”[8]卷468。从此严嵩兼支正一品、尚书及伯爵三禄。
(二)地产收入
无论是出于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还是担心随时会飞来横祸便丢官罢禄,封建官员多把土地作为常产,视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财富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不仅如此,在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的多寡往往反映出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因此,明代各级官员对占有土地倍加垂青。基于此,晚明各级文武官员利用皇帝的拨赐和他们无厌无休的占夺、侵吞民田形成了一个个规模庞大的田庄。有“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5]卷210的严嵩,有“将官假养廉而侵夺其膏腴之地”[9]卷220,有“良田八万余顷”[10]的张居正”,有“因官至富,金穴铜山,田连州郡”[11]卷6的士大夫。由此可见,地产收入已经成为明代官员的收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造成官员利用职权强取豪夺田地现象的出现与明代取消职田不无联系。在明代之前,职田即是我国官俸的一个组成部分。《宋史·职官志》云:“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税,晋有色章田,后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齐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内外官各给职田。”[12]卷172宋、元品官均有职田。明朝洪武初年,有“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又赐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禄”[6]卷43,也有赐百官公田以充律禄的,但未久即废。明内阁阁臣于慎行在《谷山笔麈》里曾说:“唐时百官皆有职田。……宋时犹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别无给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13]卷63然而,官员运用种种手段所占有的田产却在事实上代替了职田的授予,以至于土地兼并“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形成“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14]卷84。许多官员扩大庄田以提高收入。徐阶之富,范守己的《曲洧新闻》言之甚详:“其田赋在华亭(徐阶)者,岁运米万有三千石,岁租银九千八百余两,上海、青浦、平湖、长兴者不计也,佃户不下万人。”[15]卷34次者,隆庆年间的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5]卷307,再则湖州的董份,松江的董其昌,亦皆田过万顷。福建的仕宦富室,亦“相竞蓄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临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累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16]卷4。
拥有土地的官员对田庄的经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通过政府招佃收租,庄田主从政府领取子粒银两:一为庄田主直接交佃户耕种。”[17] 573除了上述经营方式外,明代官员在田庄内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充分利用田庄空地种植林木,广育经济作物以扩大收入。而且有的官员还亲自决策经营方针,组织劳动分工,指导生产。《霍氏家训》云:“凡耕田三十亩,岁别储谷十五石为种。凡耕田三十亩,岁给公粪五十石,给粪资钱千文,莳秧钱四百。凡耕牛,皆圜之一栏,凡畜猪,即皆圜之一圈。积粪均资田圃,年轮纲领者一人均之。池塘养鱼需要供粪草,筑塘墙,桃李荔枝,培泥种草,人无遗利,则地无遗利,各派定某管某处,开列日期,不时查验,毋令失业。”由此可见,经营官僚地主已于晚明出现,田庄的多种经营方式已蔚然成风。
(三)经商收入
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三妻四妾、子女成群,仅仅依靠俸禄难以维持家庭开销。不仅如此,时至晚明,“农商皆本”思想已为许多士大夫所接受,东林党人赵南星就说过,“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士进而后称贤乎”[18]卷7。此话就暗含着“农商皆本”的理念,加之商业利润的刺激,促使晚明大批官僚士大夫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势,委派亲属仆人,甚至亲自参与商业经营,以期获得巨额利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纷纷加入经商的人流中,官商合流日益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他们争相购置邸店客舍,经营质库车坊,贸迁营利,商业收入在官员家庭收入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城市商业繁荣,流动人口极多,于是许多官吏便在城市中开设邸店、饭庄,出租店铺,以获厚利。首辅徐阶“大置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19]卷26。广东南海霍氏,在经营农业之外,亦不得不兼营工商业,《霍渭崖家训·货殖》记载,“凡石湾窑治、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司窑治者,犹兼治田,非谓只司窑治而已。益本可以兼末,事末不可废本故也”[20]卷1。上海的大理寺评事顾氏,“家故勤织纴,织布美,有兰花、菱花、紫花、天水碧诸名,赖是以佐客”[21]卷76。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谈及明代官僚地主经济时曾说,“自万历以后,水利、碾硙、渡场、市集,无不属于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22]卷13。范守己的《御龙子集·曲洧新闻》卷二,描述了嘉靖、万历之际江南一些身份性的官僚地主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甚是生动有趣,“王元美(世贞)席有先业,其家亦巨万,……时岁将终矣,诸质舍算子钱者类造帐目呈览,主子钱者舁簿白元美曰:已算明。元美问曰:几何?曰:今岁不往年若也,三十万耳。元美颔而收之”。又记载,“董尚书(份)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家畜童仆不下千人,大航(即游船)三百余艘,各以号次听差遣”[15]卷34。其他官员也是如此,可见,依靠商业投资取得收入已成为晚明官员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
(四)灰色收入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血雨腥风中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太祖朱元璋是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成的封建帝王, 贫寒的出身及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促使他痛恨奢侈浪费,崇尚节俭,在古代中国封建帝王之中是一个以勤勉朴素而著称的杰出政治家。因此,明代官员的俸禄也就相应地变得微薄。然而,明朝又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处处充斥着封建特权,宗室、贵勋与文武百官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一系列特权,并且明代官员薪俸之低,已如前所述。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要求官员们在极度朴素的条件下生存十分困难。事实上,晚明中的大多数官员过着非常豪华和奢侈的生活。例如明世宗时的内阁首辅夏言、严嵩,明神宗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都是如此。他们豪华奢侈的生活绝非微薄的俸禄所能维持的。这些人的主要收入在于接受各级官员的“馈赠”。贪污受贿在晚明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上自被誉为“真宰相”的内阁首辅大学士,下至七品芝麻官、不入流的小吏,都以贪污受贿为正事,因此官员横征暴赋,不奉典章,擅破人家,自丰私室。以致自家“管内产业吁陌相连,童仆资财动以万计”。官吏这种依仗权势,劫人肥己、卖官受贿的行为在明朝较为普遍。史载大学士严嵩积资在四百万两以上,其他金银器物、珍宝古玩,不可胜计;大学士高拱的资产也在百万以上;内阁首辅申时行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5]卷231到晚明,社会每一角落都充斥着贪污的现象。“督抚莅任,例贿权要,名‘谢礼’;有司奏请,佐以苞苴,名‘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弥缝,失事希庇护,输贿载道,为数不赀”,正是当时无官不贪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史称,嘉靖时期“贪官暴吏,布满中外”[23]卷1,嘉隆以后“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分析明代官员贪污原因时,也认为是俸禄菲薄所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自赡其家也”,“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22]卷12。
“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令“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触目警心”。[2]卷32法律不可谓之不严,然而贪污之风却有增无减。晚明官员们之所以置名节、清誉乃至头颅于不顾,实与俸禄微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言:“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乎!”[24]卷75可谓一语中的。
部分官员还因战功显赫、理政有嘉,在宴会、典礼、巡幸、节日中均可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有时数目极大,尤以辅臣及讲官集团更具代表性。明神宗时,因战功显赫而赏,如:“丙寅,兵部奏御土蛮犯铁岭镇西等堡功次,言‘李成梁督各路兵马奋勇出边与贼立战,获虏首五十七颗、马二百七匹,被伤家丁一十七名,射死官马七十七匹,成梁又差家丁出境,哨探获虏首一颗、马一百匹。’赐总督刘应节银币,巡抚张学颜升俸一级,李成梁升实职二级,兵备王之弼、贺秦等各赏有差。”[9]卷12因理政有嘉而赏,如“赐总督宣大山西尚书郑雒、巡抚许守谦、邓林乔、沈子木,总兵麻贵、李迎恩、董一元、李如松等以下各银币有差,以三镇岁市报竣也”。余者在宴会、典礼、巡幸、节日中而赏如“甲午,上御皇极门引见朝觐廉能官浙江左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员,面加奖励,仍各赏银两表里钞锭,赐酒馔内。云南大理府知府史诩不到逮问”[9]卷21。“己卯,以册封沅怀王,命大学士申时行充副使捧册,赐银币。”[9]卷201“丙辰扈 驾阅视 寿宫,赐辅臣申时行等金币、银花有差,寻又赐大红彩织金蟒衣,罗一表里,绿罗一表里。”[9]卷203“甲寅,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纱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纱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美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各银十两,本品罗衣一袭,居正等疏谢 上报闻。”[9]卷16凡此种赏赐,不胜枚举。
二、晚明官员收入的历史影响
(一)晚明官员收入对自身家庭的影响
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晚明官员收入的多寡会给其家庭本身、家庭成员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晚明官员收入的状况对个人在家庭、在社会的地位,乃至生命安危均有直接影响。
1.吾富有财时,众人谓我好
“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街头无人问”,这句诗真实反映了家庭收入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重大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家庭男子往往成为本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担者,男子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大小不仅决定家庭的荣耀与尊严,而且也对本人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身为官员这种影响更为清晰明显。
2.“财”多百般好,亦是招祸源
诚然,官员收入的增加会提高该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使其家庭成员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身为官员,他们的收入亦需要政治权势来庇护,否则该官员的家族产业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既有来自黑道的杀人抢劫,也有来自朝廷的抄家没财之灾。晚明许多官员因其经济收入过于显眼,或者是由于贪赃枉法而引起了其他权贵和皇帝的妒怒,没财抄家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官员收入对社会的影响
拜金思潮风起云涌,人伦纲常弃之不顾。
晚明社会各级官员竞相逐利,到处为金钱奔走呼号,钱成为各级官员崇拜的对象。晚明人朱载堉《山坡羊·钱是好汉》写道:
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社会上的伦理纲常,也逐渐异化,本是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至晚明时却是“比族忌嫉,富贵贫贱,上下欺虐”。过去“卑幼遇尊长,道傍拱让先履,今冠人财主,驾车乘马,扬扬过闾里:刍牧小奚,见仕官辙指呼姓名无忌惮,贵贱皆越矣”。连父子兄弟之间也缺乏情谊,“今或弟强兄弱,横臂驺途,眇目布老,车马簇之,赫奕临之”[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可谓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微观缩影,对晚明官员家庭的稳定、朝代的兴衰皆具有不可小觑之影响。研究晚明官员家庭收入的状况,对认清晚明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具有更加直观的效果,从量变到质变,从微观到宏观为我们道出明朝的腐朽,亦可知明朝的灭亡乃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明太祖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
[4] 陈仁锡.皇明法世录[M].明刻本,卷12.
[5] 张廷玉.明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
[6] 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7] 万历.明会典[M].明刻本.
[8] 明世宗实录:一[M].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
[9] 明神宗实录:二[M].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
[10] 佚名.天山冰水录[M].附录.
[11]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六册[M].户部:卷六.
[1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 范守己.曲洧新闻[M].
[16] 谢肇淛.五杂俎[M].
[17] 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其实序[M].
[19]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二六[M].
[20] 霍韬(渭厓).霍渭厓家训:卷一,货殖第三[M].
[21] 陈所蕴.明文林郎大理寺左事左评事研山顾先生墓志铭[M].
[22] 顾炎武.日知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3] 伍袁萃.林居温录[M].明刻本.
[24] 古今图书集成 [C].民国23年影印.
[25] 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M].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