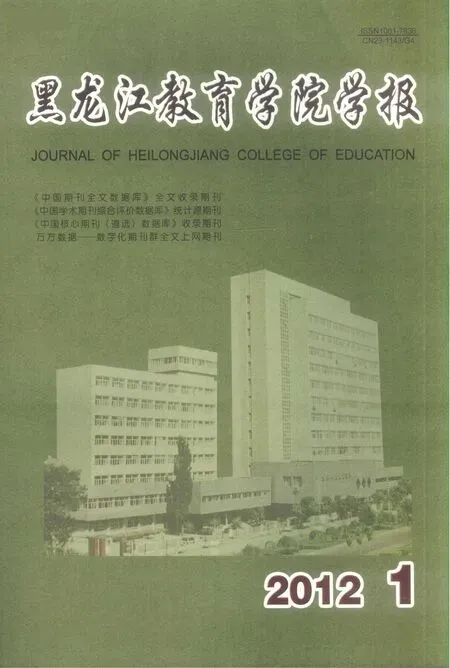从心灵之痛到亲情之暖——比较小说《余震》与电影《唐山大地震》内容表现之异同
胡 玥
(宁夏大学,银川750021)
1976年7月28日是一个比往常更加闷热的夏日,凌晨3时42分在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突然发生里氏8.2级(国内测量为7.8级)强烈地震。在距地面16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约400倍的猛烈爆炸发生了。在短短23秒的时间里唐山被夷为废墟,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这场大地震共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
34年之后,著名导演冯小刚将这23秒地震给人心灵所带来的“余震”搬上了荧幕,有了电影《唐山大地震》。电影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面对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绝境下无奈选择了牺牲姐姐而救弟弟,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让幸存者陷入一个震后32年的情感困境。导演冯小刚说,这部《唐山大地震》电影的情感力量可以真正传到观众的心灵深处,让人反思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和生死考验,是对人“心灵的拷问”。电影上映仅25天,票房便破6亿。
看过影片的人,在描述感受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感人”,这也将电影的原著《余震》[1]的作者张翎推到了台前。张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1986年到加拿大求学,先在卡加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后又去美国攻读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她在加拿大卖过热狗,做过翻译、教师、行政秘书等多种职业,但取得听力学位后就一直做听力康复师至今。张翎与严歌苓、虹影一起,被称为海外女作家的“三驾马车”。其中张翎成名最晚,但近两年却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仅2009年一年,她就连夺中国首届华侨文学奖的评委会特别大奖,《当代》年度五佳长篇小说奖,《中华读书报》年度小说家奖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奖”等多个奖项。随着《唐山大地震》的上映,张翎的知名度更是迅速蹿升。
早在2007年初,冯小刚就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阅读了小说《余震》,这部小说触发了冯小刚的创作欲望,他致电小说作者张翎,希望能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但最终未果。2008年,当唐山市委和电影局把《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任务交给冯小刚时,他立刻想到了也许《余震》能帮他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于是就有了今天这部根据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
比较电影《唐山大地震》和小说《余震》。就内容而言,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动”不同,原著《余震》里更多的是残酷的现实以及苦难背后的反思。对张翎本人的写作来说,“小说不是为悦人耳目而写”,她说,“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则是一个‘暖’字。我觉得电影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在电影里,疼痛被温暖取代。
小说《余震》以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一对龙凤胎因为唐山大地震而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小说女主人公王小灯在唐山大地震当天,7岁的她和弟弟同时被埋在地下却只能救出一个,生死关头,母亲放弃了她。后来,她凭借顽强的生存意志活了下来,但生活中她又遭遇了继母病逝、继父的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等诸多不顺的事,为此她多次试图自杀,最后躺在了心理医生的病床上……累累伤痕造成她的悲剧人生。小说的最后,她千里回乡,找到母亲,隔着30年的时空距离,母亲从阳台上俯下身来,问“闺女,你找谁?”一切戛然而止。
而电影《唐山大地震》主要讲述的是1976年在唐山卡车司机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为救孩子,方大强死了,方登和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元妮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姐姐方登听到了母亲作出的抉择。震后,元妮独自抚养儿子,坚强地活了下来。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夫妇领养,进入了全新的世界。母女、姐弟从此天各一方。32年后方登回家看到了供奉在她年幼画像前的“桃儿”,母亲李元妮一下子跪倒在她面前向她忏悔,32年来母女之间的怨恨、遗憾、惦念、愧疚……也在顷刻间被亲情这个斩不断的情丝所化解。
《余震》里的王小灯,内心有一扇生了锈的窗,怎么推也推不开。她不是电影里那个和养父有融洽父女感情的方登,她是遭受养父性侵犯后“逃离”家庭的王小灯;她不是电影里那个与女儿如朋友般互相照顾的妈妈方登,她是偷看青春期女儿的聊天记录、不断与之发生冲突的王小灯;她更不是未婚先孕遭受男友大杨抛弃的单身母亲方登。她是与大杨有一段13年的婚姻,却对丈夫“疑神疑鬼”而提出离婚的王小灯——她不是浴火的凤凰。地震中母亲的选择教会了她一种拥有方式——紧紧地拽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而她拽得越紧,失去得越多。
写出如此动人故事的张翎的主业是加拿大一家医院的听力康复师,更离奇的是,她根本不是唐山人,也从未去过唐山。促使她产生创作欲望的那个下午,是在2006年7月28日,而这一天正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纪念日。
那天,张翎在机场看到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被书中那些普普通通的唐山人的命运震撼了,“那些关于劫难的记忆当时击中了我,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幸存孤儿,在文章的结尾被简单概括为‘后来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或者‘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和‘后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这样的表述。”
“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于是便有了《余震》——它是一个关于“苦难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的故事。
回到加拿大,张翎到图书馆里搜集了关于唐山地震的图书,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张翎就创作出了2万字的《余震》[2]。
张翎在小说封底写道:“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
同为表现唐山大地震在震后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与电影选择了以“亲情”、“家庭”作为大主题,并以母亲、女儿、儿子三条线索展开不同的是,在小说中张翎把故事的后续关注点全部放在了劫后余生的王小灯身上。对于个人来说,在灾难中生存下来是一种幸运,但不可否认的是,地震所带来的后遗症,不仅仅是震后的生存问题,更可能是伴随终身的心理问题。电影《唐山大地震》表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同时也关注了灾后人们如何释怀并摆脱心灵的枷锁。而《余震》写一个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女孩的成长经历。不仅仅表现出大地震给唐山造成的破坏,更着力表现那场浩劫在经历者内心深处造成的强烈余震。张翎曾说:“余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余震。”小说主要想表现的是这场大地震之后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意义更为深刻。
[1]张翎.余震[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北京候机厅萌发创作灵感 飞机误点成就张翎《余震》[EB/OL].中新网,201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