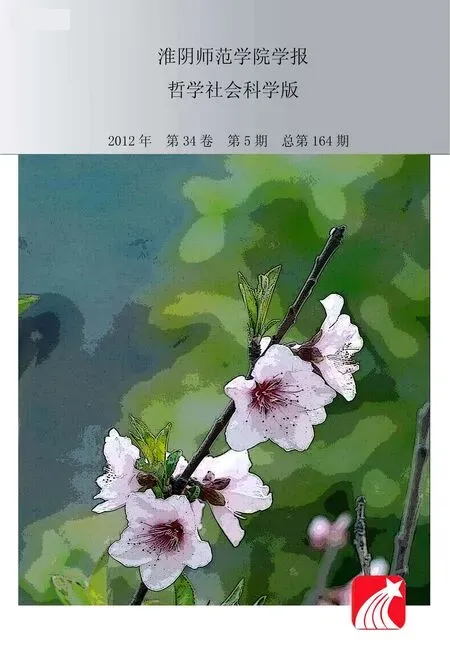读北魏吕达、吕仁墓志
张 蕾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1987年8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黄河北岸的吉利区配合洛阳炼油厂三联合装置车间的基础工程开展考古工作,其中两座规模较大的北魏墓葬出土有三方墓志,墓志记载墓主人分别为吕达、吕仁父子。《考古》2011年第9期刊载的《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一文对这两座墓作了简要介绍。吕达墓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平面近方形,四角抹圆,墓壁向外弧凸,两方墓志分别出土于后甬道近墓门处和墓室东南角。吕仁墓为平面呈铲形的土洞墓,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呈横长方形,弧顶,墓志出土于墓室东南角。
此外,发掘简报还登出墓志的拓片照片。出土于吕达墓室东南部的墓志(下文简称“墓志一”)盖作盝顶,无字,四角各铆有一铁环,志石长宽均74厘米,表面磨光,有阴线界格,志文阴刻,共28行,满行28字。出土于后甬道近墓门处的墓志(下文简称“墓志二”)无盖,长宽均56厘米,志文共28行,满行28字。出土于吕仁墓室东南角的墓志(下文简称“墓志三”)为青灰石质,方形盖作盝顶,长宽均50厘米。三方墓志均保存完整,文字基本清晰。朱亮先生在《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录有以上三方墓志志文,然错讹尚多,且视墓志一与墓志三为伪刻[1]。今仔细核对考古简报所附墓志拓影,再次对志文进行校释,并对吕氏家族的族属与籍贯、官职、墓志撰写与所谓“伪刻”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志文校释
墓志一:
魏故威远将军积射将军宫舆令吕君之墓志铭
君讳达,字慈达,东平寿张清乡吉里人也。盖神农之苗裔。太公既以鹰扬」树绩,大风蔚于东海;吕叔亦以音徽踵烈,高声迈于南夏。衣冠之盛,历秦」汉而为极;蝉冕之隆,迳晋魏以为甚。等七叶而传辉,齐五宗以继曜,葳蕤」以之遐畅,听逖于是自远。曾祖父牛,凉侍中、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英情秀逸,机悟如神,在世许其高大,月旦科以千里,故能制锦青蕃,栖蝉」绛阙,擅当官之誉,跨不世之名。祖父台,少以栖迟纳赏,高尚自居,盘桓川」泽,潜晦为心。虽鸣雁亟委,逸想弥隆,玉帛屡征,不以屑怀。乡部称以遐蹈,」州里言其远逝,虽子渊不群,君山独往,方之于此,尝何足喻。然君志绝笼」罩,声逸烟霞,器为时求,才勘世举。凉宁府君亦一时之英,自以才望既隆,」民物攸归,幸君屈辱,用裨共治,以为郡功曹。君秉节不移,执操弥固,非其」情也,遂不应命。父安,镇远将军、天水太守。器识渊华,才韵清远,妙解物情,」善于治政。抚莅未几,风化大行;接壤怀仁,邻乡愿附。虽浮虎清江,未足云」异,止蝗绿野,方之何奇?信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君禀气天地,承灵川」岳,踵奕世之风,继累叶之轨,贞情峻邈,逸想冲云①《选编》作“深”,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云”。,黄中显于岐日,通理彰」于丱岁。故能出龙闱以衣朱,入虎门而委珮,去来九重之中,往还二宫之」里。淑慎虔恭之节,每郁沃于帝心;清贞肃穆之操,亦留涟于圣旨。方」当藉兹宠会,用阶尺木,击水上腾,抟飃九万,而川流一往,逝景不追。以正」光五年四月辛巳朔一日辛巳春秋六十有四,遘疾卒于洛阳之承华里」舍。粤以十一月丁未朔三日己酉迁殡于河阳城北岭山之下。小子仁惧」世代之迁贸,恐崚②《选编》作“峻”,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崚”。谷之易处,询硕彦以镌志,庶流芳于泉户,乃作铭志,其词曰:」惟天降祉③《选编》作“礼”,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祉”。,惟地纳灵,笃生若人,命世为英。虔恭结誉,淑慎流声,栖迟百氏,」优游六经。方抟九万,击水上征,如何不淑,早世沦倾。哀云晓坠,悲风夜惊,」一归万里,长秘④《选编》作“秋”,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秘”。泉庭。圆长方久,路迥川平,萧萧垄树,蔚蔚松青。敬敷徽猷,」式照⑤本字不清,据墓志二、墓志三,推测作“照”。玄铭。」正光五年岁次甲辰十一月丁未朔三日己酉志」夫人天水尹氏,父育,沙州刺史。
墓志二:
魏故辅国将军博陵太守吕公之墓志铭
君讳通,字慈达,东平寿张清乡吉里人也。盖神农之苗裔。太公既以鹰扬」树绩,大风蔚于东海;吕叔亦以徽音踵烈,高声迈于南夏。衣冠之盛,历秦」汉而为极;蝉冕之隆,迳晋魏以为甚。等七叶而传辉,齐五宗以继曜,葳蕤」以之遐畅,听游于是自远。曾祖父牛,凉侍中、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英情秀逸,机悟如神,在世许其高大,月旦科以千里,故能制锦青蕃,栖蝉」绛阙,擅当官之誉⑥志本作“舆”,参照墓志一,当是“誉”之误。,跨不世之名。祖父台,少以栖迟纳赏,高尚自居,槃桓川泽⑦“泽”,志脱,据墓志一补。,」潜晦为心,虽鸣雁亟委,逸想弥隆,玉帛屡征,不以屑怀。乡部称以遐蹈,州」里言其远逝。虽子渊不群,君山独往;方之于此,尝何足喻?然君志绝笼罩,」声逸烟霞,器为时求,才勘世举。凉宁府君亦一时之英,自以才望既隆,民」物攸归,幸君屈辱,用裨共治,召为郡功曹。君⑧本字不清,据墓志一、墓志三,推测作“君”。秉节不移,执操弥固,非其情」也,遂不应命。父安,镇远将军、天水太守。器识渊华,才韵清远,妙解物情,善⑨《选编》作“菩”,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善”。」于治政。抚莅未几,风化大行;接壤怀仁,邻乡愿附。虽浮虎清江,未足云异,」止蝗绿野,方之何奇?信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君禀气天地,承灵川岳,」踵奕世之风,继累叶之轨,贞情峻邈,逸想冲云⑩志本作“深”,参照墓志一,当是“云”之误。,黄中显于岐日,通理彰于」丱岁。故能出龙闱以衣朱,入虎门而委珮,去来九重之中,往还二宫之里。」淑慎虔恭之节,每郁沃于帝心;清贞肃穆之操,亦留涟于圣旨。方」藉兹宠会,用阶尺木,击水中流,凭风九万,而川流一往,逝景不追。以正光」五年四月辛巳朔一日辛巳春秋六十有四,遘疾卒于洛阳之承华里舍。」天子哀悼,缙绅悲惜,賵吊之礼,有国常准。乃下诏追赠辅国将军、博陵」太守,考德立行,谥曰静,礼也。粤以十一月丁未朔三日己酉迁殡于河阳」城北岭山⑪⑪《选编》脱“山”。之下。小子仁惧世代之迁贸,恐峻谷之易处,询硕彦以镌志,庶」流芳于泉户。乃作铭志,其词曰:」惟天降祉,惟地纳灵,笃生若人,命世为英。虔恭结誉,淑慎流声,栖迟百氏,」优游六经。方抟九万,击水上征,如何不淑,早世沦倾。哀云听坠,悲风夜惊,」一归万里,长秘泉庭。圆长方久,路迥川平,萧萧垄树,蔚蔚松青。敬敷徽猷,」式照玄铭。」正光五年岁次甲辰十一月丁未朔三日己酉志。夫人天水尹氏,父育,沙」州刺史。
墓志三:
魏故宁远将军吕君之有墓志铭
君讳仁,字屯仁,东平寿张清乡吉里人也。盖神农之苗裔。太公既以鹰」扬树绩,大风蔚于东海;吕叔亦以音徽踵烈,高声迈于南夏。衣冠之盛,」历秦汉而为极;蝉冕之隆,迳晋魏以为甚。等七叶而传辉,齐五宗以继」曜,葳蕤以之遐畅,听沃于是自远。曾祖父牛,凉侍中、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英情秀逸,机悟如神,在世许其高大,月旦科以千里,故能制」锦青蕃,栖蝉绛阙,擅当官之誉,跨不世之名。祖父安,少以栖迟纳赏,高」尚自居,槃桓川泽,潜晦为心①本字不清,据墓志一、墓志二,推测作“心”。,虽②本字不清,据墓志一、墓志二,推测作“虽”。鸣雁亟委,逸想弥隆,玉帛屡征,不以屑」怀,乡部称以遐蹈,州里言其③“其”,志脱,据墓志一、墓志二补。远逝。虽子渊不群,君山独往,方之此于④据墓志一、墓志二,当作“于此”。,尝何」足喻?然君志绝笼罩,声⑤“声”,志脱,据墓志一、墓志二补。逸烟霞,器为时求,才勘世举。凉宁府君亦一时之」英,自以才望既隆,民物攸归,幸君屈辱,用裨共治,以为郡功曹。君秉节」不移,执操弥固,非其情也,遂不应命。父达,辅国将军、博陵太守。器识渊」华,才韻清远,妙解物情,善于治政,抚⑥本字不清,据墓志一、墓志二,推测作“抚”。莅未几,风化大行;接壤怀仁,邻乡」愿附。虽浮虎清江,未足云异,止蝗绿野,方之何奇?信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君禀气天地,承灵川岳,踵奕世之风,继累叶之轨,贞情峻邈,逸」想冲云,黄中显于岐日,通理⑦本字不清,据墓志一、墓志二,推测作“理”。彰于丱岁。淑慎虔恭之节,每蔚沃于」帝心;清贞肃穆之操,亦留涟于」圣旨。方当藉兹宠会,用阶尺木,击水中流,凭⑧《选编》作“并”,经核对墓志拓片当作“凭”。风九万,而川流一往,逝影」不追。以永安二年五月乙丑朔八日⑨“日”,志脱,据墓志一、墓志二补。壬申春秋卅二,遘疾⑩“疾”,志脱,据墓志一、墓志二补。卒于洛阳承华之」里舍。粤以正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迁殡于河阳城北岭山之下。小子」叶惧世代之迁贸,恐崚谷之易处,询硕彦以镌志,庶流芳于泉户。乃作⑪」铭志,其词曰:」惟天降祉,惟地纳灵,笃生若人,命世为英。虔恭结誉,淑慎流声,栖迟百」氏,优游六经。方抟九万,击水上征,如何不淑,早世沦倾。哀云晓坠,悲风」夜惊,一归蒿里,长秘⑫泉庭。圆长方久,路迥川平,萧萧垄树,蔚蔚松青。敬」敷徽猷,式⑬照玄名⑭。」普泰二年岁次壬子正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志。
二、吕牛官职所见吕氏族属与籍贯
吕达、吕仁父子文献不见记载。墓志中称吕达为“东平寿张清乡吉里人”,其曾祖父吕牛为“凉侍中、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有关沙州的建置,查《晋书·地理志》可知前凉张骏时始有沙州建置,张骏分前凉所统之地为凉州、河州和沙州三州,自领“凉州都督,摄三州”,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祚又以敦煌郡为商州”[2]434。商州疑为沙州之误。《魏书·张寔传》载张骏以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3]2195。五凉时期先后有前凉、后凉、北凉(段业期)、西凉、北凉四个政权管辖过沙州,后凉、西凉、北凉诸政权在沙州的建置上,均是以前凉设置为基础而稍有增设或析分。因此,吕牛可能效命于以上四凉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政权。
《晋书》、《魏书》记载的四凉中曾任职为沙州刺史的有前凉张骏时期的杨宣(324年前后)、北凉段业时期的孟敏(397年),以及后秦姚兴给北凉的沮渠蒙逊的封官(404年)。杨宣为征西域的能将,史载其“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2]2237。孟敏降段业前原为后凉敦煌太守,敦煌郡乃沙州治所,孟敏必也熟知沙州诸事,段业任其为沙州刺史,这是段业在政权初建时迅速稳定沙州的举措之一。而后秦姚兴给予沮渠蒙逊封官,则是北凉攀附后秦、与之结好的结果。沮渠蒙逊并无实领之权,因为沮渠蒙逊被姚兴封为沙州刺史是在404年,沙州实际上归西凉所辖。东晋十六国时期个别政权与各方势力之间,既相互征伐,又合纵连横,一些政权遥领虚封的地域不在本国的实际疆域范围内,遥领虚封的对象也非本国真正的臣子,胡阿祥先生将这种情况称为“虚授”、“遥封”[4]。后秦政权虚授北凉沮渠蒙逊以沙州刺史,这样的例子在后秦也很常见,例如南凉秃发傉檀向后秦姚兴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姚兴便虚授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2]3149,等等。可见,沙州乃整个河西地区的西部,西接西域各国,沙州刺史须统管全州事务,以保护西陲安全和控制西域诸国。
在曾管辖沙州的四凉政权中,汉人出身的前凉和西凉政权都非常重视与陇西和敦煌两大右姓集团的政治联合。史载前凉张轨“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2]2221-2222;西凉李暠选用清一色的河陇著姓担任要职,例如在公元400年李暠对诸臣的封官当中,便多以宋、索、阴、汜、令狐、张氏等大族的人居多[2]2259。北凉的沮渠蒙逊也将谠言与广开贤路作为稳固其统治的手段,且对西凉“旧臣皆随才擢叙”[2]3199。而出身氐族的吕光是依靠氐人的军事力量,以关陇酋豪的身份统治河西地区的。吕光自建立后凉政权后,便仿效前秦的“氐族本位”政策,任命氐族官员来统治河西地区[5]。吕姓子弟因氐族吕光建立后凉政权而得以发迹,查缪荃孙《后凉百官表》得知,吕光任命吕氏家族以军国重任,诸吕子弟中的吕覆、吕纂、吕他、吕绍、吕方、吕宝、吕邈、吕延、吕弘、吕超、吕纬、吕隆等均居将军、郡守之位[6]。后凉虽也任用非氐人士为官,但多是随从其征西域的将领,且一般不居要职,即使有居要职者,也极易因谗获罪,杜进便是一例[2]3058。
因此,综合文献中四凉时期任沙州刺史一职的人物记载、四凉政权的用人记载以及吕姓被委任的记载来看,吕牛很可能任职于后凉政权。
前凉自376年灭亡后,沙州便处于前秦统治之下。383年吕光奉苻坚之命率兵西征,于次年八月“抚宁西域”,389年吕光“僭即三河王,置百官自丞郎以下”[2]3055,且“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为始祖”[2]3059,396 年“僭即天王位……立世子绍为太子,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2]3060。397 年,“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2]2257。至此,在吕光末年的397年,后凉失沙州,沙州进入段业统治时期。因此,吕牛任沙州刺史一职的时期可能在后凉吕光统治的389年至397年期间,396年吕光封“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2]3060,吕牛或许在这一年被封为“西海侯”一爵。
综上,任职“凉侍中、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的吕牛可能是后凉氐族贵族,那么墓志中称吕达为“东平寿张清乡吉里人”则有冒望之嫌。
魏晋南北朝社会以郡望别姓氏、以郡望别贵族,这是当时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外部特征。为适应这一特征,北族入主中原后,为显示自己的家族出身与地位,往往假托汉人著名郡望为自家地望,这种现象屡有出现。北魏太和改制后,北族攀附华夏旧族改著籍贯者蔚然成风[7]。墓志中冒望的例子也很多,例如《罗达墓志》自称为“代郡桑乾人,益州刺史尚之后”。“益州刺史尚”即罗尚,罗尚在西晋惠帝时曾任益州刺史,但《晋书·罗尚传》中载罗尚是襄阳人,这说明罗达是妄托先祖,根据他的籍贯代郡桑乾,罗达应当是六镇武人,而其先祖也不会是罗尚[8]。又如《魏书》和《北史》中都称皮豹子为“渔阳人”,但其孙皮演墓志却称“下邳郡下邳县都乡永吉里人也”[9]。再如《魏书》卷九三《侯刚传》明确记载了侯刚富贵以后,想要努力改变自己代人的身份,攀附上谷侯氏以改变其郡望和籍贯,“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3]2006。《侯刚墓志》则称侯刚“上谷居庸人也。其先大司徒霸,出屏桐川,入厘百揆,开谋世祖,道被东汉”。以及侯刚之孙侯义在其墓志中自称“燕州上谷郡居庸县人”,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果[10]。
另外,入魏河西士人中有一部分祖籍中原而在永嘉之乱前后流寓河西者,其中不乏原为河西本地人后冒籍中原者,可考者有广平程氏、清河崔氏、河内常氏、济阳江氏等家族。[11]
正如十六国非汉人政权的统治者以华夏始祖为族源一样,后凉氐族贵族吕牛的后人在入魏时为了保持其家族的地位而冒引东平吕氏这一望族,且追溯至“神农之苗裔”,这正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后心理上的趋同。
三、吕台、吕安、吕达的身份及官职
墓志中称吕台曾被凉宁郡太守征召为凉宁郡功曹,台“秉节不移,执操弥固,非其情也,遂不应命”。有关凉宁郡的建置,文献中未详细记载其设郡时间。《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命废耀灵为凉宁侯而立祚”[2]2245-2246。疑前凉置凉宁郡。郑炳林先生在《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凉州)》一文中考证凉宁郡为凉州所辖[12]。《魏书·地形志》有梁宁郡,属凉州,领园池、贡泽二县[3]2156,似与五凉时期的凉宁郡同。
东晋隆安二年(398),“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执太守吕纯以归……于是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赵郡孟敏皆以郡降业。业封蒙逊为临池侯,以德为酒泉太守,敏为沙州刺史……凉常山公弘镇张掖,段业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弘引兵弃张掖东走,段业徙治张掖”[13]3470-3471,隆安五年(401),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其年,“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13]3528。据此,398年段业自后凉吕光处据有凉宁郡,401年凉宁郡为西凉李暠所据,直至420年西凉灭亡时北凉才重新据有凉宁郡。
因墓志未记吕台的生卒年,所以联系凉宁郡的建置及其先后所属政权来看,吕台被征召的时间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一为398年吕光失凉宁郡之前,吕台作为后凉氐族贵族被征召而不应命;一为398年吕光失凉宁郡之后,凉宁郡先后处于北凉和西凉的管辖下,吕台作为前朝贵族子弟而被征召,但考虑到北凉与西凉的用人政策,吕台被征召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不排除吕仁为抬高其家族地位与名声而谬写吕台被征召却不应命的可能。
综上,若吕台被征召之事为真,则其在398年吕光失凉宁郡之前被召为郡功曹但不应命的可能性较大。
依前文推测,吕牛、吕台可能生活在河西五凉政权之下,而吕安则可能为这一家族中仕魏的第一代人。墓志中称吕安为“镇远将军、天水太守”。镇远将军一职在太和改制前为从三品下,改制后为正四品下①文中吕安、吕达、吕仁的官品等级参见(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十二《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及余鹿年《北魏职官制度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天水郡为北魏秦州所辖,天水太守为正四品下。因吕安事迹文献无载,加之北魏赠官制度文献记载不甚明确,所以吕安的职位尚且不能断定是生前最终官还是死后赠官。若为死后赠官,据窪添庆文先生考订,吕安的“镇远将军+天水太守”这一组合形式也符合北魏赠官的一般形式。北魏河阴之难前,合并将军号与官职,五品以上的官员死后的赠官较生前最终官的上升幅度一般为0—2级,4级以上便为超赠。[14]据此可推测,若吕安这一官职为死后赠官,那他生前的官级至少是在五品左右,属于北魏中等官员。若此官职为吕安生前最终官,那么吕安生前则主要活动在秦州天水郡一带,天水郡不仅靠近河西地区,而且那一带也多有氐人活动,吕安凭借此优势“妙解物语”且“善于治政”,最终跻身于北魏中等官员之列。
吕达卒后,“天子哀悼,缙绅悲惜,賵吊之礼,有国常准。乃下诏追赠辅国将军、博陵太守,考德立行,谥曰静,礼也。”“礼也”即“符合礼制”之意,表明皇帝对吕达的赠官以及赐谥都符合礼制的规定。
吕达卒年为正光五年(524)四月,年六十四,则其生年当为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吕达生前为威远将军、积射将军、宫舆令。威远将军为武散官,在太和改制前为正五品中,改制后为从五品下;积射将军为中央职官中的武官,官品为正七品上;宫舆令品级不详。吕达死后皇帝追赠其为辅国将军、博陵太守,辅国将军为从三品;博陵郡为定州所辖,博陵太守为正四品下。吕达死后赠官品级较其生前最终官的品级而言,散官品级由从五品下上升到从三品,上升了2级;职事官品级由正七品上上升到正四品下,上升了3级,合并将军号与官职,吕达的赠官品级比其生前最终官品级上升了2—3级,这符合北魏赠官的一般情况。
从东晋南北朝给谥情况看,侍中以上方可赐谥[15]。也就是说,当时给谥资格限定于三品以上。吕达的品级为从五品下,不符合给谥资格。汪受宽先生认为中低级官员因“特恩”而给谥者有如下几种:曾为天子近臣者,因直谏而死者,行为节义者,学问声名者[16]。吕达为中央武职官员,虽品级为中下等,但“能出龙闱以衣朱,入虎门而委珮,去来九重之中,往还二宫之里。淑慎虔恭之节,每郁沃于帝心;清贞肃穆之操,亦留涟于圣旨”。墓志的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与溢美之嫌,但也以此可见吕达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考虑到孝明帝年纪尚小,无力揽朝政大权[17],故吕达当效力于自515年便“临朝称制”[13]4618的胡太后。吕达卒于 524 年,在此前的520年侍中元叉与中侍中刘腾发动政变,史载“侍中元叉、中侍中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乃幽皇太后于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总勒禁旅,决事殿中”[3]230。元叉专政后,隔绝二宫,阻止胡太后干政,效忠于胡太后的吕达也因此失脚并于四年后病卒。胡太后在孝昌元年(正光六年,525)四月“复临朝摄政,引群臣面陈得失”[3]240,念及旧情,故下令给予吕达赠官、谥号,这也是吕达墓中出现两方墓志的原因。
吕仁卒年为永安二年(529),年三十二,则其生年为太和十八年(496),吕仁生前官职仅有正五品上的武散官号宁远将军,无职事官,这或许与其早亡有关。另外,尔朱荣在528年发动河阴之变后,采纳费穆的意见,“沉太后及幼主于河”[13]4741,且下令诛杀王公卿士百官大夫死者两千余人①《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作一千三百余人,《魏书》卷九《肃宗纪》作二千余人,《洛阳伽蓝记》作三千人,但本文此处不细究确切人数。。效忠于胡太后的吕达一家也因此而家道中落,致使吕仁卒后嗣子吕叶在请人为父撰写墓志时也以吕达墓志为底本,且错讹很多。
四、墓志的撰述与“伪刻”问题
前文已提到,墓志一与墓志三均被放置在墓室的东南角,墓志二被放置在后甬道近墓门处,墓志二虽为重刻墓志,但其并未代替墓志一而被放置在墓室东南角,这或许存在如下可能:墓志二乃因胡太后复辟后给予吕达赠官和谥号一事而刻,联系上文第三部分所述,墓志二的刻写时间必定在吕达下葬之后,墓志二以墓志一旧志稿为底本,但刻好后并未改题新的刻写日期。嗣子吕仁于墓志刻好后进入吕达墓将其放置在后甬道近墓门处。
墓志中分别有小子仁、小子叶“惧世代之迁贸,恐崚谷之易处,询硕彦以镌志”,亲友虽对墓主生平熟悉,但能否承担写作任务则恐未必。从吕氏祖孙六代的任职看,吕氏成员多任武职,在文学修养上则相对较差,因此吕仁、吕叶才请托“硕彦”为父撰志。考古简报结语处称“吕达墓志是由其子吕仁撰写,吕仁墓志由其子吕叶撰写”[18],此说欠妥。
吕达、吕仁父子的三方墓志甚至在先辈姓名及祖辈行迹上出现了谬误,例如吕仁在请人撰写其父吕达墓志时,父亲在前后两方墓志的名字竟不相同;又如吕叶以吕达墓志为底本,在为其父吕仁撰写的墓志中,竟将高祖吕牛写成曾祖吕牛,曾祖吕台的事迹被安在祖父吕安这里,祖父吕安的事迹却无载。考虑到普泰二年(532)距正光五年(524)仅八年,且吕仁卒年三十二岁,其嗣子吕叶年纪尚小,家中以所藏旧志稿为底本为吕仁作志的可能性极大,因事出多端,故误刻极多。
朱亮先生在《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中将墓志一与墓志三列入伪刻[1]201、208,且并未阐明理由。从考古简报的墓葬平面分布图可知,吕达墓虽有盗洞,但墓室内随葬品位置似未遭严重扰乱;吕仁墓并未遭盗[18],三方墓志均出土于这两墓中,故墓志一与墓志三不应作伪刻。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与墓葬中的陶器、瓷器等陪葬品一样,墓葬中的墓志也应视作陪葬品,因此,不能撇开墓志陪葬品这一性质,而仅对墓志铭文进行研究,以至于当墓志在撰述等方面出现谬误时而被误作伪刻。
综上所论,从吕牛任职地域及时间来看,吕达一族当为后凉氐族贵族,在以郡望别姓氏、以郡望别贵族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在入魏后假托东平吕氏为己望,以保持自己家族的仕宦地位。吕达因生前效忠胡太后,故胡太后复辟后给予其赠官和谥号,这也是吕达墓中有两方墓志的原因;加之吕达、吕仁父子的三方墓志都出土于墓葬中,虽墓志撰写具有格式化且误刻极多,但不应为伪刻。
另外,绝大多数已经汉化的氐人即使姓氏上有氐人之嫌,但从史籍上已不能详考,例如隋襄如县令吕瑞,秦州天水人;兵部郎中强宝质,略阳人,从他们的姓氏和籍贯来看,似属氐人后裔,但已不能追溯其源[19]。这期待更多的相关墓志出现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 吕通墓志(正光四二),吕达墓志(伪刻三一),吕仁墓志(伪刻四四)[M]//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79,201,208.
[2]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5):47-53.
[5] 赵向群.五凉史探[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05-108.
[6] 缪荃孙.后凉百官表[M]//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第二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5-8.
[7] 赵海丽.北朝墓志文献研究[R].济南: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
[8] 罗达墓志[M]//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45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52.
[9]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29;[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1;皮演墓志[M]//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83.
[10] 侯刚墓志[M]//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01;侯义墓志[M]//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231.
[11] 张金龙.河西人士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1995,23(2):139-145.
[12] 郑炳林.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凉州)[J].敦煌学辑刊,1993,23(1):32-42.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10卷·晋安帝隆安二年(398)[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 窪添庆文.关于北魏的赠官[J].文史哲,1993(3):81-83.
[15]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867.
[16] 汪受宽.谥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5-126.
[17] 张金龙.灵太后与元叉政变[J].兰州大学学报,1993,21(3):95-101.
[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J].考古,2011(9).
[19] 杨铭.氐族的姓氏及婚姻[J].西北民族研究,1992(1):24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