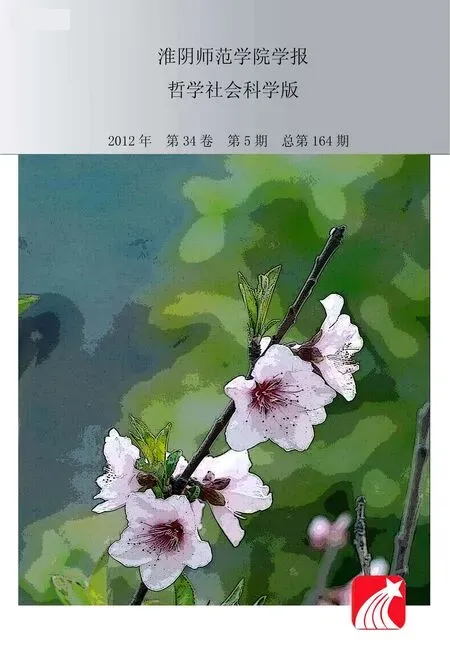电视剧不属于视觉文化
——从电视剧与文学性的关系谈起
盖 生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电视剧不属于视觉文化
——从电视剧与文学性的关系谈起
盖 生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电视剧作为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对象,其影响的范围、程度,都已远远超过文学。但是电视剧不属于视觉文化,其存在及消费方式等方面与作为视觉文化表征的电影有较大的差异。电视剧的文学性是其存在的本根和发展的主导因素,在叙事、描写、抒情等方面,与文学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这使其成为文学边缘化之后,唯一能够较全面发挥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同时,把电视剧作为文学研究的延伸和理论转场,既盘活了文学理论的剩余资源,又能拓展文学理论的创新空间。
电视剧;日常生活;视觉文化;文学性
电视剧理应与文学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电视剧是以剧本或谓电视文学为基础的视听综合艺术。但是,近年来,由于所谓的“图像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电视剧有以“吸引眼球”为价值取向,使传统的以剧本为中心,向以导演为中心位移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学剧本的个人化写作也被集体性策划所替代。所谓在宾馆侃出来的剧本,和一边拍一边写的剧本,已不再是电视剧制作的“商业秘密”。就是说,在某些电视剧创制中,文学性遭到了忽视。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与电视剧创制者及文艺理论家们对电视剧属性的误解有直接的关系。
一、电视剧作为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对象
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看电视成为几乎所有人必要的生活方式之一,电视剧作为强势消费文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虽然在我国仅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达1 000部以上,但据“中国网”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从国民对各类出版物接触时长看,2009年,我国18—70周岁识字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4.70分钟,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1.02分钟,人均每天读杂志时长为15.40分钟,人均上网时长为每天34.09分钟,人均通过手机阅读的时长为6.06分钟。而每天看电视时间,“人民网”2005年4月28日报道,根据正在法国戛纳举行的戛纳电视节春季展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2004年日本人平均每天有5小时零1分钟都用在了看电视上。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4小时46分钟。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是4小时41分钟。这份年度统计报告是在调查了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27亿观众和120个电视频道后,得出以上的结论。另据曾庆瑞引用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12月8日,总计已生产出20余万集电视剧,仅2009年全国生产电视剧359部11 469集。2009年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8 000集,全国人均每天看电视剧的时间约为58分钟[1]。
由于电视机及收视费基本是一次性的经济投入,看与不看钱都已经付过,所以一有闲暇,打开电视机随便看几眼是最方便也是最好的打发时光的方式,这应该是国民看电视剧时间所以普遍高于读文学作品时间的主要原因。另外,电视剧是一种可直接诉诸视听的最大众化的综合艺术形式,识字不识字大致都能够看得懂,所以,电视剧受众必然是最大的文化消费群体。“电视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它对公众的巨大影响远远不同于印刷媒体”[2],或者说,电视剧已经成为一种半强制性的社会宰制,其受众之多,传播范围之广,以及其日常生活化和生活方式化,是任何一种消费文化都无法比拟的。
但是,由于电视剧的播放速度一般不能随意调控,这使看电视剧没有了“掩卷而思”的从容。而且,电视剧只能被动地看和听,不能充分调动接受主体的想象力,这又牺牲了文学阅读那种通过想象而产生的丰富的内感觉。所以,在此意义上,看和听虽然具有感官接受的直接性,却由于缺乏整个内心世界多维的交织和共感,其视听感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平面的、单维的。这应该是一些坚守“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立场的文艺理论家不屑于研究电视剧,或者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传媒文化、视觉文化的重要原因。
二、电视剧与视觉文化
在人们的习惯中,电影和电视剧往往并称为影视艺术,也叫视觉艺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剧属于视觉文化。其实,这里存在着学理上的粗疏和认知方面的误解。
近年来,由于受欧美当代理论家的影响,一些文艺理论学者转向研究视觉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视觉文化或谓图像文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印刷的文字文化。而且,视觉文化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表征,虽然“印刷文化当然不会消亡,但是对于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它已经成为现代主义的标记)却孕生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越是视觉性的文化就越是后现代的”[3]。所以,文艺理论学者如何应对视觉文化的挑战,似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题中之义就是,应该把包括电视剧在内的视觉文化,作为文艺理论研究转向的对象。大致说来,这种策略是明智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电视剧属不属于视觉文化?它与包括电影在内的所谓图像艺术在本质上是否有所区别?
何谓“视觉文化”?按照周宪所梳理、厘定的说法,一是指“高度视觉化的文化”;二是指“大凡运用视觉媒介或形式的任何人类活动均属于视觉文化范畴”;三是“将视觉文化理解成为一种话语的谱系学”[4]15-16。可见,视觉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其所指主要是图像或以图像为主语言为辅的文化形式。但是在周宪研究的语境中,并没有明确地把电视剧作为视觉文化,却把电影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表征,我以为这是他的谨慎高明之处。而在其他学者的语境中,却有意无意地将电影和电视剧统称为影视艺术,就是说,把电视剧作为视觉文化的一类。譬如张晶在其《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视觉文化的提升》中,把电视剧《西游记》、《三国演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我是太阳》等,统称为“传媒艺术在以文学作品为其蓝本”基础上创作的影视艺术[5]。言下之意,影视艺术是传媒艺术的一种,而传媒艺术则是视觉文化的基本构成。再如张永清在其《文学研究如何应对社会文化的挑战》中,直接把“摄影、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等”统统归结为视觉文化[6]。
其实,电视剧和电影尤其是和摄影、网络媒体等真正的视觉文化是有较大区别的。摄影和网络媒体姑且不论,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就是电影和电视剧,随着社会需求的分化,无论是受众的消费方式,还是它们各自的文化存在,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譬如今天的电影,尤其是一些大片,已经“从叙事电影”转向为“奇观电影”,即由“以话语为中心,讲究电影的故事叙事性,注重人物的对白和剧情的戏剧性”,转而为“以图像性为主因,突出了电影自身的影像视觉性质,有意淡化甚至弱化话语因素,强化视觉效果的冲击力”[4]255,所以把电影归属为视觉文化还是恰当的。而且,对电影的消费,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毕竟还是偶尔为之甚至有些奢侈的行为。一是由于票价不菲,动辄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消费,不可能是所有国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二是看电影还要大家都集中到电影院去,和众多的陌生人坐在一起,呼吸着不洁的空气,很不方便;其三,看电影的时间毕竟有限,即便是上、下集的影片,也不过是三个小时左右。这样,为了寻求感官刺激而看电影,所谓不求叙述故事的意义和画面之外的“韵味”,只想在高科技的声、光、电的视听感官的“震惊”中获得某种快感,调节一下都市生活的紧张,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看电视剧就不同了,看电视剧已经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几乎是每天必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且一般是在闲暇之时,或者餐前饭后,一家人舒服地倚在沙发上,一边说笑一边观看,借以修养身心打发时光。所以,品味电视剧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想想画面背后的意义,一般也是看电视剧所必要的程序。如果电视剧也是如电影一样充满着高强度、密集型的感官刺激,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深层次的意义,像电影《十面埋伏》一样,在五彩缤纷、高速飞旋的画面,和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背后,却如剥洋葱似地什么都没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就是一切,长此以往,受众就会感到身心疲惫,甚至连休息都没有得到。其实一般人看电视剧,除了消遣娱乐和休息外,或多或少还有些了解人生、观照自我的目的。所以笼而统之地说电视剧与电影一样,都是视觉文化或谓图像文化是不准确的。而且事实上,在当下的电视剧中,图像没有取代故事,它只是故事呈现的载体;图像也没有压迫或遮蔽话语,它只是电视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话语一起完成了直观的呈现性叙述。就是说,文学性仍然是电视剧的基础和主导性因素。而笼统地把电视剧归结为视觉文化,或者混淆电视剧与电影的区别,弊端之一是容易给电视剧制作以偏离其特长及本体的暗示和鼓励,使文学性这一电视剧的本根失去或被淡化;之二是在文艺理论家的研究中,电视剧可能被作为一般的浅薄的视觉文化而遭到贬抑,使其与文学性渐行渐远,从而得不到文艺理论应有的扶持及锤炼,不能够健康地发展。
三、电视剧与文学性
那么,电视剧与文学性是什么关系?在学理上,应该说,电视剧与文学性永远不可能脱离干系,因为电视剧剧本就是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本来,电视剧剧本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早就是理论界的基本共识,譬如出版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四院校的《文学理论基础》,曹廷华的《文学概论》,以及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就已经把电视剧剧本列入文学形式之中了。而在曹廷华的《文学概论》中,直接把“影视文学”作为与诸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并列的第五文体。但是,近些年来理论界由于受欧美文化研究的影响,一般习惯于把电视媒体等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严厉批判,使电视剧文学也受到理论株连。因此,在一些文学原理文本中已经没有了电视剧剧本的位置。就连影响较大的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文学理论》,以及南帆等著的《文学理论》中,都在文学体裁一节里删除了电视剧剧本。我猜想,在一些理论家看来,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电视剧剧本虽然是语言文本,但它并不是案头阅读之物,而是电视剧的组成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文学领域谈它。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文艺报》展开关于“剧本是文学”的讨论,说明视觉文化已成强势,它们已不屑与边缘化的文学结缘,如前所述,电影剧本已由叙述故事,转而为“奇观”画面的摄制提示,进而影响到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各种剧本的价值取向,所以,剧本作为文学形式已经成为问题,讨论的目的就是要回归剧本渐行渐远的文学性。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电影与电视剧的较大差异,电影剧本和电视剧剧本虽然有诸多相近之处,但是区别还是明显的,所以有的文艺理论学者把它们统称为影视文学并不准确。但由于文体一般只是类的划分,而且电影文学和电视剧文学同样作为表演的依据和提示,一般也都采用的是蒙太奇语言,除人物语言外,都需要转化为视觉画面,因此无论是将之并称还是统称,并不妨碍人们对这两种体裁的基本认知。况且在具体的论述上,电影文学和电视剧文学还是作区分的,正如人们虽然习惯于把文艺通讯、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统统归结为散文,而在进一步分类中却各说各的一样。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人以影视文学统称,也不支持混淆电影和电视剧的性质,因为随着电影与电视剧的分化的逐渐扩大,两种文学体裁之间的差别也会进一步拉大。
什么是文学性?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7]雅各布森把文学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即由文学作品的“材料”及其“程序”所构成的特殊的“陌生化”“奇异化”的语言结构。近年来,吴炫从其否定主义文艺学理论出发,认为文学性是文学创作“穿越现实的程度”[8]。虽然说,这两种界定都极具本体论的概括性,但是正因为如此,才似乎更为抽象,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在我看来,与其把文学性终极化为形而上的定义,不如形而下化为具体的艺术表现方式。譬如说,所谓的文学性,不妨视为以诸如叙述、描写、抒情等为表现形式的艺术虚构。这样,既能够有效地区别非文学的语言文本,又便于将其延伸、覆盖到电视剧领域。因为,虽然如新闻、历史乃至法律等语言文本,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叙述或描写的手法,但一般却排斥抒情,更不会把诸如叙事、描写等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法密集使用。正如文学作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论辩,但一般却不会将其作为文学的基本表现手段一样。没有必要把偶然的例外作为否定一般的根据。
当然,不可否认,与文学不同的是,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确是以收视率为基本目标的文化工业的主要产品,无论它的创作过程,还是制作过程,都与文学有许多不同之处。譬如电视剧剧本的创作,需要剧作家和导演两次创作的合成,即电视剧故事剧本和分镜头导演脚本。在这种合成中,一般要以弱化文学的语言表现功能,强化视听效果为指向。其结果,必然是增强了感官感受的直接性和确定性,减少了想象的从容并缩小了内感觉的空间。文学描写惯常使用的修辞手法,诸如比喻、象征、拟人等,都要以是否能够转化为视听的画面及音响为前提。不仅如此,就电视剧的制作、生产而言,剧本的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般的电视剧生产流程,大体需要有策划、创意、写作、表演、拍摄、制作、合成、包装、营运、传播等诸多环节。在此意义上,电视剧的制作较之文学创作要复杂得多。就电视剧创制目的而言,纯艺术目的一般也要服从于至少要较多地兼顾到商业目的。因为电视剧是一种成本较大的文化产业,它不同于文学创作,一部小说如果不能出版或发表,至多是浪费了创作者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而电视剧一旦因预测收视率过低而不能保证在电视台播出,整个电视剧的制作成本就会化为乌有。因此,电视剧创制较之文学创作一般要更多地考虑到一些非文学乃至非艺术的因素。不仅题材要揣摩、迎合当下社会心理需求:诸如时尚的还是怀旧的,黑幕的还是纯情的,等等,而且,在策划时,就考虑到诸如美女的亮眼因素,硬汉的人气因素,等等。这说明,在电视剧创作及制作中,文学性虽然一般仍然是一种基础和主导性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甚至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追求,在电视剧创作和制作中就可能成为量力而行的兼顾因素。譬如文学创作的生命往往就是创新,但电视剧的创作和制作如果过于追求表现形式上的求新就是危险的。因为创新往往意味着要舍弃已有的受众而重新培养、开辟消费市场。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戴安娜·克兰曾言:“创新被认为有风险,所以电视台更倾向于生产与过去的成功之作相似的产品。”[2]64因为电视剧在播放中一般是不可逆的,在即时性的视听中,即便是意味深长、韵味无穷的镜头,对于只喜欢看故事的普通受众来讲,一般也不会细细反刍其中的妙味,更何况还要适应诸如新的题材、新的形象类型、新的表现手法了。所以,在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文学性可谓处处受制,时时有被消解的可能。
但是,电视剧在表现社会生活上的优势也不可漠视,早在1908年,列夫·托尔斯泰就已经意识到电影将在“作家的生活中引发一场革命……我们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阴暗的银幕和冰冷的机器。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将成为必须……场景的迅速转变、情感和经验的结合——它对此的表现比我们所习惯的拙笨而又耗时的写作要好得多。它更接近生活”[9]。虽然,托尔斯泰说的是最初的古典电影,但在道理上是一样的。至于说电视剧较之文学,堵塞了受众的想象空间,其实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因为,电视剧并不是一般地堵塞了受众的想象空间,它堵塞的主要是具象想象和内感觉的空间,而在展开联想和想象上,与文学阅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说,那种裹挟着情感和充满了暗示性的,意在激发内感觉的文学叙述和描写,虽然在电视剧中已经转化为蒙太奇镜头的物象的直接呈现,但这些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叙述和描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叙述技巧的要求,电视剧要远远超过一般的文学叙事。因为电视剧是即时的表演的艺术,情节如果没有波澜,就不会吸引受众,没有受众收视率就会降低,就意味着失败。在这一点上,与文学叙事如小说就大不相同。小说除侦探题材之外,情节可紧张亦可舒缓,节奏可快可慢,叙述的密度可大可小,甚至淡化情节的散文化小说和没有情节的意识流小说,读者也可能接受。但是,电视剧就不同了,如果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小说情节来讲可能是根据表现内容的需要,属于“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对于电视剧而言,几乎就是“雪中送炭”。电视剧一般是分集播出的,这就要求每一集几乎都要有看点,即意外和波澜,这就较之文学情节更精致,更合理。而且,好的电视剧剧情,一般都要逆着普通受众期待的方向发展,都应该是“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譬如电视剧《闯关东》的情节,几乎都是由一系列的在情理之中的意外推动发展的:故事一开始,是传文热热闹闹地去娶亲,结果娶亲的粮食被土匪抢走;多年没有音讯并传因参加义和团被杀的朱开山一下子有了消息,而且在富饶的关东站住了脚,要他们全家都去;鲜儿的父亲不同意她同行,朱家好不容易上了船,鲜儿却在岸上出现了;旱路上的传文和鲜儿历尽千辛万苦结果还是失散;全家刚刚团圆朱开山又去淘金;淘金成功买了地本来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又因传武拒亲而得罪当地一霸再起事端;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又遭到土匪的烧抢;搬家到哈尔滨又与其他帮派结怨,等等。剧情可谓波澜曲折,而每一个意外又都合乎剧中所给出的情理,这就是电视剧叙事的特点。在此意义上,电视剧叙事的文学性甚至强于一般的文学叙事。正因为此,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般都要在情节设计上,较之原作更曲折、更复杂、也更有意味。
文学的描写固然有所长,但也有所短,譬如文学描写确可以“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般却不容易真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10],更不可能同时描写一个以上的对象。而电视剧则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任何可见之景之物完全呈示于受众的眼前,并且能够同时在同一画面中展示多个不同空间的对象,一个角色也可以在瞬间就表现出多种变化、微妙的表情。对于前者,文学语言一般无法做到,至于后者,文学语言也只能用诸如“既惊又喜”,“有些悲伤,又有些欣慰”等抽象的词汇来暗示,读者只能在这几个抽象的词汇的框范内体会。可见,文学和电视剧在描写上各有短长,难说哪一个就具有绝对优势。再如抒情,虽然电视剧一般不能像文学那样直接以语言抒情,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画面色彩的变化和富有寓意的蒙太奇镜头来暗示,更重要的,还有音乐烘托氛围,这与文学借景抒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电视剧还保留文学性的最重要的维度:人物对话。对于人物对话,电视剧甚至较之文学更为重视。因为电视剧作为表演的艺术,一般不方便直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戏剧艺术一样,对话成为它们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成功的电视剧,往往都得益于精彩的、富有韵味的对话。由于对话是在鲜活生动的画面中进行的,并不会像在文学作品中对话如果多于描写,就会叫人感到抽象甚至概念化。其实,电视剧如果没有了音乐和人物对话这听的维度是不可想象的,再眼花缭乱的画面,没有声音,受众只能是茫视。这也是我不同意叫电视剧为视觉文化而称之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原因。
有的人以为,看电视剧不需要心的参与,它只给眼睛和耳朵等感官以刺激,因为电视剧一般只能靠演员的对话、表情、动作等表演呈现外在的故事,受众无法像读小说一样,通过阅读作者带有情感倾向的描写和叙述,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因为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演员的对话、表情、动作和富有意味的蒙太奇画面去体会和想象的,如果处置得当,甚至会引发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譬如早期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就有这样的情景:霍元甲被害后,陈真先是情绪失控,后来就坐在灵前默默不语,赵倩男说:“陈真,你已经在这儿整整坐了三天三夜了。”接着,剧情表现了陈真一系列的复仇行动。表面看,赵倩男这不经意的一句话,似乎与陈真的复仇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恰恰是解析陈真后来所以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复仇行动的关键。因为,赵倩男这句话,很自然地让受众联想和想象到,陈真能够在师父的灵前一直坐了三天三夜,其功力之深、性格之犟可见一斑。而且,在这三天三夜里,陈真一定会想了些什么。也许,他想起了和霍元甲的恩恩怨怨,思考了师父被害的种种可能,以及如何查找师父被害的原因,如何去报仇,等等。由于有了陈真在霍元甲的灵前“坐了三天三夜”的铺垫,他后面的一系列复仇行动就都顺理成章了。
可见,好的电视剧所能引发人的联想和想象,与文学阅读是别有意趣的。同时,正如文学也有消遣性阅读和审美性阅读的差别一样,电视剧的创作也存在着普通消遣和审美欣赏的不同的需求,所以不能说文学阅读就是高级的文化消费,看电视剧就一定是底层次的消遣。同理,也不能说文学作品就是富含文学性的艺术精品,电视剧就是文学性缺失的文化工业产品。而且事实上,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血色浪漫》、《亮剑》、《命运》、《雪豹》等电视剧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反响,甚至超过了当年某一畅销小说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蕴涵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性。这些文学性构成了电视剧艺术性的基础和价值导向,成就了一个个的电视剧精品。
至此,可以说,由于电视剧具有无可置疑的文学性,或者说,文学性是电视剧艺术成就的价值保障,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继文学边缘化之后,唯一能够较全面发挥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因为看电视剧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电视剧中所包蕴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社会责任等,人们在耳濡目染中不受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一部电视剧能够引起较大的轰动效应,就说明它已经发挥了某种社会功能。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电视剧,并没有引起广大文艺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没有充分认识到电视剧在发挥社会功能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我看来,文艺理论家与其坚守“文学是语言艺术”这多少有些贵族化的学术立场,不如关注、扶持一下电视剧这几乎是每人每天必看之物,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当然,这种研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将其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的一般性关注,也不是从社会学视角作为闲暇时间的消费文化现象来分析,更不是如以往的某些电视剧评论,满足于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角度,对诸如人物形象的社会内涵、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等方面,作一点讨论,而是以电视剧为文学研究的延伸和转场领域,从基本范畴、一般原理,到前沿的个案问题,都给予系统的理论覆盖和阐释。这样,既能盘活文学理论的剩余资源,又能拓展文学理论的创新空间。
[1] 曾庆瑞.电视剧文学剧本——文学的新样式[N].文艺报,2010-05-17(3).
[2]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4]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张晶.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视觉文化的提升[J].江海学刊,2010(1).
[6] 张永清.文学研究如何应对社会文化的挑战[J].江海学刊,2010(1).
[7] [法]茨维坦·托多洛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4.
[8] 吴炫.论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J].文学评论,2010(1).
[9]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4.
[10] 欧阳修.六一诗话[M]//[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267.
I207.352;J905
A
1007-8444(2012)05-0664-05
2012-05-25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20世纪文学原理关键词论要”(10FZW009)。
盖生(1956-),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