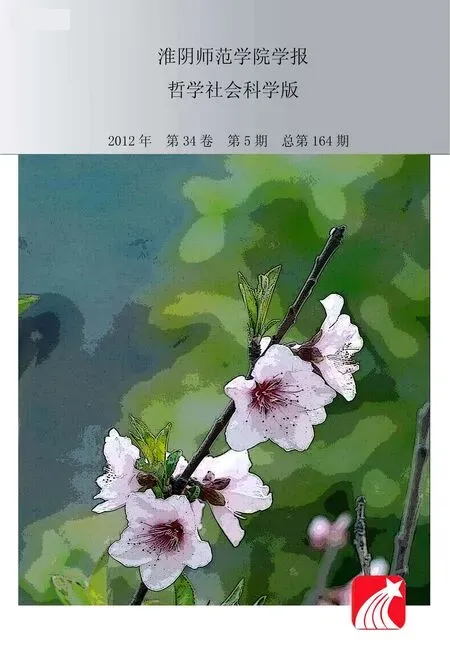依调填词二论
田玉琪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唐宋词调的根本特征是依调填词,虽然唐宋时期亦不乏先词后乐如姜夔先制词后作谱的例子,但在音乐与文词的关系上,音乐处于支配和主导的地位,文词处于从属、服从的地位,则是唐宋词声词关系的基本情况。依调填词的具体情况前人和时贤在论词中已多有论述,这里试从雅乐的依调填词、词体的一字一音两个方面作一论述。
一、雅乐的依调填词
我国古代乐歌大体经历了感发为歌声律从之、造诗以配乐以及因乐制词三个阶段。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论歌曲之变云: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1]74
王灼在这里指出先秦乐歌以感发为歌、声律从之为主,汉魏六朝乐府以造诗以配乐为主,隋唐以来词曲则以依乐制词为主。王灼所言隋以来“曲子”,其词乐配合基本关系乃先乐后词,即“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各个时期都有复杂的情况。依调填词,或者说先乐后词,自然起源也不在隋代,而是由来已久。
依调填词的前提自然是要先有乐调,并且这个乐调要重复使用。乐调的重复使用在先秦、汉魏民间的情况如何,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难以考察。而在文献记载的宫廷乐曲中,汉魏六朝时期同一乐调重复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即如汉代宫廷乐曲,《宋书·乐志》云:
(汉高祖)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2]第5册142
乐调的重复使用在一朝一代尤为明显,变化往往不大。而在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乐调的相沿使用也是常见之事,如:
梁初,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并用宋、齐元徽、永明仪注,唯改《嘉祚》为《永祚》,又去《永至之乐》。[3]30
是时(陈初)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2]第7册83
乐调的重复使用为依调填词提供了充分条件,虽然在汉魏六朝时期乐调重复使用往往伴随的是歌辞的重复使用,但也有大量的新作歌辞。这些新作歌辞,有的便是依调填词。我们看谢庄作《宋明堂歌》,中有《歌青帝》、《歌赤帝》、《歌黄帝》、《歌白帝》、《歌黑帝》五乐歌,歌词分别如下[3]16-18:
《歌青帝》:参映夕,驷照晨。灵乘震,司青春。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萌动达,万品新。润无际,泽无垠。
《歌赤帝》:龙精初见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离实司衡,水雨方降木槿荣。庶物盛长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黄帝》:履建宅中宇,司绳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凉。景丽条可结,霜明冰可折。凯风扇朱辰,白云流素节。分至乘结晷,启闭集恒度。帝运缉万有,皇灵澄国步。
《歌白帝》: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
《歌黑帝》:岁既晏,日方驰。灵乘坎,德司规。玄云合,晦鸟归。白云繁,亘天涯。雷在地,时未光。饬国典,闭关梁。四节遍,万物殿。福九域,祚八乡。晨晷促,夕漏延。太阴极,微阳宣。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
其中《歌青帝》三言十二句,依韵分三段,《歌赤帝》七言六句,句句用韵,依韵分两段,《歌黄帝》五言十二句,依韵分三段,《歌白帝》每韵作四五句式,分三段,《歌黑帝》三言二十四句,依韵作三段。后谢朓于建武二年(498)亦作五帝之歌,字句韵及分段情况全同谢庄。[3]28-29《南齐书·乐志》即云:“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唯世祖四言也。”[2]第5册174如果说,谢庄所作歌曲可能是先辞后乐的话,谢朓所作则明显是先乐后辞,或云依调填词。而且谢庄这一套歌曲当传至北齐,《乐府诗集》卷三载北齐《五郊乐歌》,其体式正与谢庄体式基本相同,具体情况是:《青帝高明乐》三言十二句,依韵分三段,《赤帝高明乐》,《乐府诗集》每韵作四三句式,实为七言六句,句句用韵,与谢庄词体式同,《黄帝高明乐》、《白帝高明乐》、《黑帝高明乐》与谢庄词体比较除少一段外,其他相同。《黑帝高明乐》每韵虽用四二句式,亦可看做谢庄两个三字句一韵的变格形式,其词如下:
虹藏雉化,告寒。水壮地坼,年殚。日次月纪,方极。九州万邦,献力。是光是纪,岁穷。微阳潜兆,方融。天子赫赫,明圣。享神降福,惟敬。
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变为六字句形式,即:
虹藏雉化告寒。水壮地坼年殚。日次月纪方极。九州万邦献力。是光是纪岁穷。微阳潜兆方融。天子赫赫明圣。享神降福惟敬。
这种情况在六朝传统的雅乐歌辞中并不少见,前面谈到陈初“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七室舞辞”的改制实际上也是这种典型的依调填词。
以往考察依乐制词或依调填词往往不顾雅乐歌词的情况,雅乐与俗乐本有密切的关系,雅乐之源本为俗乐,并无天然鸿沟。由于雅乐使用更多的程式化音乐,其歌词制作自然也体现了程式化的特点,具有依调填词的特征。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肯定地说依调填词的源头在宫廷雅乐,但完全可以说宫廷雅乐的程式化音乐特征促进并逐步强化了依调填词的发展。
二、词乐配合之一字一音
作为音乐文学的唐宋词,文词与音乐配合的基本方式是一字一音的。所谓一字一音,就是作为歌词的汉字与歌唱的音符总体上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个汉字配一个音符,这是基本的情况,不排除个别字会小有变化,如字音的延长,字音在主音的基础上升高四度和降低四度,等等。不少学者虽然总体上承认唐宋词乐的配合关系,但又多不认为词乐配合是“一字一音”,或以为可加衬字,或以为可以灵活安排,更有学者否认同一词调词与乐的固定搭配关系,以今乐对照古乐,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为音乐所配的歌词完全可以是多样的,字句多少等都可以变化,等等。
我们认为同调异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填词时作者对音乐节奏的不同处理或者所填音乐本身小有不同,同调异体不能否定一字一音的总体情况。试以温庭筠的《河传》与韦庄的《河传》比较:
江畔。相唤。晓妆鲜。仙景个女采莲。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舡。红袖摇曳逐风暖。垂玉腕。肠向柳丝断。浦南归。浦北归。莫知。晚来人已稀。[4]123(温庭筠词,55 字 14 句 14 韵)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茏。画挠金缕。翠旗高飐香风。水光融。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4]163(韦庄词,53字13句12韵)
虽然两词在句法用韵上面很有一些不同,颇可以证明词乐配合的灵活性。但是温庭筠《河传》同调有三首词,韦庄《河传》同调也有三首词,分别又是完全相同的,是固定的模式,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用灵活性来解释温庭筠与韦庄的不同词作,却只能用稳定性来解释他们各自的创作。他们自己在创作时正是从一字一音的角度填词的。我们再从另一角度看,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一为55字,一为53字,在总的字数上还是相当接近的。
论者常常用柳永的《倾杯乐》词调来论证词与乐配合的灵活性,并且证明像柳永这样的词人才是真正的音乐家词人,等等。以柳永《倾杯乐》论证词与乐的配合灵活的观点,前提是众多《倾杯乐》词作,只是用一个词调。谢桃坊对此已有过驳证,指出仅自唐代《倾杯乐》在不同时期就有多个不同曲调。陈旸《乐书》中曾谈到北宋时据古曲新翻曲调,《倾杯乐》曲便新翻出二十八个曲子[5]卷一五七,虽然同名为《倾杯乐》,却不能混为一谈。不过,柳永的《倾杯乐》既有同名异调,也有同调异体的情况。同调异体的确能说明词与乐的配合有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相当有限。从柳永的《倾杯乐》同调异体中同样可说明“一字一音”的问题,不妨看其同为林钟商的两首《古倾杯》:
冻水消痕,晓风生暖,春满东郊道。迟迟淑景,烟和露润,偏绕长堤芳草。断鸿隐隐归飞,江天杳杳。遥山变色,妆眉淡扫。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 动几许、伤春怀抱。念何处、韶阳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别后暗负,光阴多少。[1]27(108 字 22 句 11 韵)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 惨黛蛾、盈盈无绪。共黯然消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鳞羽。[1]27-28(110 字 20 句9 韵)
前面我们讲到在现代新生活方式下,茶具也变得多样化,个性化,所谓茶具是生活方式的缩影,未来的茶具继续围绕着新式生活方式来设计研发。新式生活不单单是单方面的生活新,而是叠带使的新。比如旅行便携茶具,一改匆忙急切的出行,快乐、精致,出行中也具有仪式感。自己的随身物品,家里的陈设物,居家用具等等,这些东西的优劣,会直接关联到自己的心情、心静、情绪,这些因素影响的就太多了。
这两首词初看部分句法相差很大,但仔细对比,两者应为同调。只是在断句方面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如果把差别大的几句中的标点去掉,在字数上它们基本相同,一一对应。如在两词中相对应的部分,断句不同的主要句子分别是:
第一首:断鸿隐隐,归飞江天杳杳。遥山变色,妆眉淡扫。
第二首: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
第一首:念何处、韶阳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
第二首:共黯然消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
如果我们把中间标点去掉,则变为:
第一首:断鸿隐隐归飞江天杳杳遥山变色妆眉淡扫。
第二首: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
第一首:念何处韶阳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
第二首:共黯然消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
虽然第二首词总的字数比第一首多两字,但并不能说改变了总体上的一字一音律。
相似的情况,不妨再看一看柳永与周邦彦之《浪淘沙慢》: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 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1]26-27(柳永)
昼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缆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1]598-599(周邦彦)
两词在《康熙词谱》卷三七中均为例词,《康熙词谱》以柳词“无别首可校”[6]1149,说明《词谱》编撰者以柳词和周邦彦词是作同名异调看待的,其他词谱也均将两词看做是异调,这并不正确,两者实际上属同调异体,只是句读小异罢了,总体看大的句韵还是很接近的。试以两词的上片为例,柳词第一韵11字,周邦彦词同,柳词第二韵12字,周词二三韵相加也是12字,只是周词多用一韵,柳词第三韵8字,与周词第四韵8字同,柳词第四韵20字,而周词第五、六韵相加20字。下片的情景也大致相同。在词调的同调异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说,这种情况固然说明词调音乐与歌词配合的灵活性,然而这种灵活性正是在一字一音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万树在《词律》中认为词与曲不同,不可以加衬字,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上面字句的比对,表面看可能有些机械,但在这种机械的对应中,体现的正是词乐配合的基本规律。作为歌词,在断句方面,可以有相当的灵活性,歌者完全可以自行调节。这种断句的灵活在姜夔十七首旁谱的词乐配合中也多能证明,刘崇德先生在《燕乐新说》中就指出:“由于乐拍所限,十七首带有旁谱之词,其歌辞之断句有些与按诗文句读全然不同者。”[7]275
从词与乐配合的一字一音角度看,字数是确定词调的最关键要素,基本可以说,音符的多少就根本决定了字数的多少,其次才是句法和韵位。词调相同,字数相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可以略为改变的话,也一般不会超过三五字。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首定字格,以字数作为分辨词调的基本依据,为制谱者提供基本规范,也正从文词的角度体现了词乐配合之一字一音关系。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抒写一时之意,意尽则止,故歌无定句。因其喜怒哀乐,声则不同,故句无定声。今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何与古相戾与?[1]80
王灼借他人之言谈古今歌辞异同,然后加以评说。其中“一字一拍”中的“字”和“拍”,既指乐谱的谱字和拍句,又指与之配合的文字与句法,“不敢辄增损”正是其字与音的特点。沈义父《乐府指迷》说: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1]283
文中“曲谱”是指乐谱,下文中“腔”是指韵,“一腔”即“一韵”,“字”则指谱字,“句法长短不等”,也指谱字多少不一。这里沈义父间接解释了唐宋词中同一个词调何以会出现字句小有不同的情况,原因或是乐谱小有变化,“盖被教师改换”。姜夔带有十七首旁谱的词作更是一字一音的音乐证明。姜夔每首词的文字主音符号非常清晰,一字只有一个主音。今人有不少学者对姜夔乐谱作了翻译,其中在对折拽(掣)符号的处理上,杨荫浏将之处理为附点符号,刘崇德先生作为倚音看待[7]266-267,虽原理相通,但从词乐配合一字一音角度考察,似以后者为善。
最后再举一词乐配合的具体例子,我们先看周密《采绿吟》:
采绿鸳鸯浦。画舸水、北云西。槐薰入扇,柳阴浮桨,花露侵诗。点尘飞不到,冰壶里、绀霞浅压玻璃。想明珰、凌波远,依依心事寄谁。 移棹舣空明,苹风度、琼丝霜管清脆。咫尺挹幽香,怅岸隔红衣。对沧洲、心与鸥闲,吟情渺、莲叶共分题。停杯久,凉月渐生,烟合翠微。[8]3270
作者自序云:“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练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翁为翻谱数字,短箫按之,音极谐婉,因易今名云。”可知此调非周密自度曲,乃是杨缵据《塞垣春》谱新翻曲,周密所言杨缵仅翻谱数字,此数字自为乐谱谱字,那么周密的《采绿吟》与《塞垣春》在字句上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张先的《塞垣春》:
野树秋声满。对雨壁、风灯乱。云低翠帐,烟销素被,签动重幔。甚客怀、先自无消遣。更篱落、秋虫叹。叹樊川、风流减。旧欢难得重见。 停酒说扬州,平山月、应照棋观。绿绮为谁弹,空传广陵散。但光纱短帽,窄袖轻衫,犹记竹西庭院。老鹤何时去,认琼花一面。[8]84
二词比较,《采绿吟》双片99字,《塞垣春》双片96字,从一字一音的角度看,不同仅二处:
周词:苹风度、琼丝霜管清脆。
张词:平山月、应照棋观。
周词:停杯久,凉月渐生,烟合翠微。
张词:老鹤何时去,认琼花一面。
这两处不同杨缵实际上一处增加二谱字,一处减少一谱字,也就是总共动了三处,也符合周密所说“翻谱数字”。周密词与张先词比较,在韵位和句法上还有若干处小的不同,这是词乐配合所允许的,不必过于计较。由此看来,《采绿吟》与《塞垣春》历来被视为两调,也是没有必要的。
词体音乐与歌词一字一音的配合关系,与雅乐歌词的词乐配合比较接近。雅乐歌词虽然有时会有一字多音的情况,如北宋元丰年间杨杰便要求大乐“一声歌一言”,“请节其繁音”[2]788,但总体配合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从现存南宋《诗经》乐谱①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一四《诗乐》载十二首《诗经》乐谱,此乐谱为赵彦肃所传,据云为开元遗声。和姜夔《越九歌》[9]等雅乐乐谱中可以得到清晰的表现。到了明代,从宫廷《魏氏乐谱》来看,大部分“雅乐”声诗依然严格遵循着一字一音之配合关系,只是有的曲调用了散曲音乐,如《立我丞民》(调寄《豆叶黄》)、《思文后稷》(调寄《金字经》)[10]258-259,便成为一字多音的情况。清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雅乐歌词乐谱,既有一字一音者,亦有一字多音者,其一字多音的情况,正是沿用明代雅乐用散曲的旧俗,对此,乾隆曾提出批评:
又书中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徵、羽字样,未免援古入俗,自应仿照《律吕正义》逐细添注,方为赅备。盖古乐皆主一字一音,如“关关雎鸠”、“文王在上”等诗咏歌时自应以一字一音,庶几合“声依永、律和声”之义,若朱载堉所注歌诗音章谱,每一字下辄用五、六、工等字,试以五音分注,未免一字下而有数音,又援雅而入繁靡也……且如殿陛所奏中和韶乐,从前未免沿明季陋习,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数音者,听之殊与俗乐相近,经朕特加釐正,俾一字各还一音……[10]应该说,这不仅是乾隆个人观点,更是宫廷雅乐乐官的基本主张。
从渊源关系的角度看,唐宋词体的一字一音显然源自雅乐歌词,当然,此雅乐歌词并非就是唐宋雅乐歌词,而是我国古老的“声依咏、律和声”的歌诗传统。应该说,时间越古,其音乐或歌词越简明纯朴,从一字一音的基本规律来看,唐宋词体在歌唱方面还保留着我国古老的歌诗传统。
[1]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二十四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陈旸.乐书[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陈廷敬.康熙词谱[M].长沙:岳麓书社,2000.
[7] 刘崇德.燕乐新说[M].合肥:黄山书社,2003.
[8]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0] 刘崇德.魏氏乐谱今译[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
[11] 朱载堉.乐律全书[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