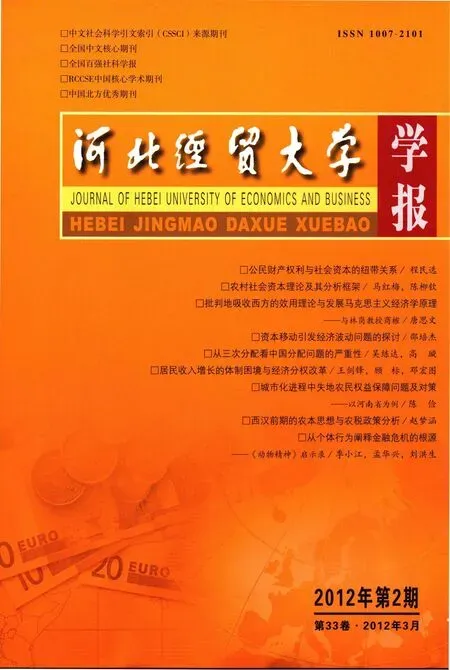公民财产权利与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程民选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4)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 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 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 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