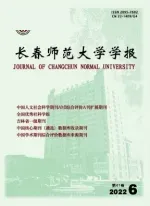吴质与“建安七子说”
孙浩宇1,2
(1.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吴质与“建安七子说”
孙浩宇1,2
(1.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之中最著名的实有六人,但曹丕《典论·论文》却提出了“建安七子说”,原因有二:一是吴质曾提过“郑国七子”对其有启发,二是为合礼制之需要。
吴质;郑国七子;“建安七子说”
一般认为,“建安七子说”源于曹丕,证据是他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7年)的名作《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这段话接下去讲的是曹丕对“七子”作的一番评论,言其各有擅场而非文体兼备,由此中国文学史上便有了著名的“建安七子”。
而吴质与“建安七子说”有何关系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应先说一下吴质。
一
与今天吴质的湮没无闻正相反,当年吴的地位、权势都要高于“建安七子”(指除孔融以外的六人,其与吴质同时,下同)。《三国志·魏书》记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与“建安七子”差不多,吴也做过一段文学侍从,《三国志》注引《魏略》:“(质)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但他显然意不在此,甚至还很看不起这种角色,在后来的《答魏太子笺》中他写道: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
在吴质看来,陈琳、徐干、刘祯、应瑒之辈只会舞文弄墨,非军政实干之才,死则死矣,可期后贤。在这种想法下,吴很快就不做侍从了,“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祯等并在坐席。祯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在别人仍悠游诗赋时,吴已走上了实干岗位。所以,吴质最终能位封列侯主要不因文才。他是天生的投机家,善于处理人事关系,自然他能成为曹丕的心腹。关键时刻吴的“四两拨千斤”“扭亏为盈”①让曹丕大为感激,也积累了他仕途光大的资本。吴质后来受到曹丕、曹睿两代皇帝的倚重②,《三国志》引《吴质别传》载:
“(曹睿)太和四年,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
这段话颇有意思。陈群与司马懿同为顾命之臣③,吴质说陈从容闲雅,对政事投入不够,且缺少司马的智谋和实干,这或与事实相去不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质居然认为司马懿很忠诚。这真有点“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吴帮曹丕赢下兄弟之争,获取了皇位,但也成全了魏的掘墓人。当然,吴本身还是颇能威重,或者说善于作威作福④,所以其政治才能还是可以肯定的。
由上,我们能看出吴质与曹丕的关系非同一般。吴曹之间亦君臣亦师友,其遇合甚至不下孔明之与刘备。《三国志》注引《吴质别传》载:“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曹丕对吴质感激、尊重,其待遇超越礼数,而吴同样报答以情真意切。黄初七年曹丕晏驾,吴质写到:“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知己、恩遇、悲伤、感激打并一起,极尽思慕之情,让人不忍卒读。今存较完整的吴质与曹丕的书信各三封,双方问答,可作为吴曹关系的又一证明。
以上我们对吴行迹及其与曹丕的关系作了梳理:吴曹关系很亲密,在政治上,曹倚重吴。那么,这与“建安七子说”有何关系呢?首先可以肯定,吴对曹的影响不仅在于政治,当然还包括文学。
二
当时吴质、曹丕、曹植、杨修等彼此间常以文学为话题。《文选》里保留有三组书信,分别是吴质与曹丕、吴质与曹植、曹植与杨修之间的问答。按“笺”与“书”两类序列为:杨修《答临淄侯笺》、吴质《答魏太子笺》、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与吴季重书》、吴质《答东阿王书》。考证其中的几篇,对我们认识“建安七子说”的形成及吴质的作用很有帮助。
首先,考证诸作的写作时间。
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有“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因阮瑀逝于建安十七年。知此书当写于此后不久;而吴质始为朝歌令应在此前。又《三国志》注引《魏略》有:(建安) 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知吴质过邺并迁元城令(有《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当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与吴季重书》中,《文选》注引《典略》曰:质出为朝歌长,临淄侯与质书。吴质《答魏太子笺》有:“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故:曹吴的书信往还当不早于建安十七年而不晚于建安十九年。
按:曹植《与杨德祖书》有“仆少小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知曹植《与杨德祖书》、杨修《答临淄侯笺》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时曹植仍为临淄侯。
按:李善注引《典略》有:“初,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曹丕《与吴质书》有“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知此书与吴质《答魏太子笺》不早于建安二十三年。而《典论·论文》又作于其后。
下面,我们依次探讨这三组文章。
曹植《与吴季重书》讲:“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讽而诵之。”吴质《答东阿王书》回复:“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玮,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彼此都谈到曹植所赠的诸贤文章,此诸贤之名未言明,但极有可能要包括曹丕、曹植身边的六人(指徐干、应瑒、陈琳、刘祯、阮瑀、王粲等)。
吴所提“赵武过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实为比况。参《文选》注,左氏传曰:“赵武与诸侯大夫会,过郑,郑伯享赵孟於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诗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蟲,伯有赋鹑之奔奔,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叔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显然,吴质是以此“郑国七子”比拟曹植信中所推介之诸贤。
这七子何许人?这七位都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的郑国贤人。《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世叔是子太叔,子羽是掌使之官,子产就是《孟子》里那位被下属烹吃了鱼还说“得其所哉”的贤大夫,当时郑国的辞命,每由这四人写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七位的德能可见一斑。
此处,吴质不经意间谈到了春秋时颇有名气的“郑国七子”,可以代表吴对修饰润色之臣的一种定位和期待。不过世易时移,建安早已不是士大夫居国则重、去国则轻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以曹植、曹丕身边的侍从已很难再有子产等的世功。因此在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无人再明言“郑国七子”。我们无法判断其时对二曹身边的六人等是否已有了“七子”、“六子”或“十子”的说法,但吴质这一比拟对“建安七子”说的形成却不妨注意。
接下来曹植与杨修的问答就能看出这种影响。曹植《与杨德祖书》可谓一篇专门的文学论文,其中谈到王粲、陈琳、徐干、刘祯、应瑒、杨修等六人,一句“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是一段自觉的作家论,颇有含英咀华、就此勘定的味道。最后曹植写道: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这段文字真实地表达了曹植对创作的心态,作为藩侯,曹有立功之想,但对自身的辞赋才华也颇自珍和玩味,考虑到现实处境,曹植也一直心存“成一家之言”的“立言”之念。
杨修《答临淄侯笺》更像一篇文学态度论,很有针对性。
“《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锺,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第一段,因曹植声言“辞赋小道”,故此处杨修着力强调前贤之作“莫能损益”的文学价值和“字直千金”的社会价值,力图安慰曹植的心情。
第二段,强调“立言”与“立功”“立德”并不相害的道理,参之曹丕《典论·论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唯幹著论,成一家言”的说法,不难感到杨修的文学观较之二曹的各执一端要更公允恰当,而且也能看出他们彼此间文学观念的影响。
在《典论·论文》前,曹丕写了《与吴质书》,这篇情理并至的书信主体是一段作家论: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後,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於锺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其中提出的六人依次是:徐干、应瑒、陈琳、刘祯、阮瑀、王粲,由此可看出曹丕对“成一家之言”的徐干和“有述作之意”的应瑒的推许。对比《典论·论文》中六人: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祯,大致以年岁为序,可看出私函与公论之用心有别。
吴质与曹丕在对六人的评价上基本一致。他在《答魏太子笺》中写道:“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於雍容侍从,实其人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至於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六人之才只堪侍从,阮瑀、陈琳可比东方朔、枚皋,徐干可比司马相如,而吴未提及王粲,与曹丕将王排在末席也是声气相应,当然这与文学之外的原因或也有关,此不究。
不管怎样,曹丕、吴质常探讨包括文学在内的话题,二人惜为知己,每相得。曹丕《与吴质书》提出六人已是“建安七子说”雏形,而此中他与吴质也先期达成了共识。
三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到不久之后的《典论·论文》,曹丕在政治味道很浓的论文中,忽然将六人变成了“七子”?
《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虽然陈寿继承了曹丕的“建安七子说”⑤,但也只讲了七分之六,未及孔融。
曹丕力主“七子”,推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在礼制上于古有据。按:《周礼》讲诸侯礼应取七之数,如《夏官司马》:“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周礼·秋官司寇》:“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缨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其时曹丕的地位与诸侯的身份正相宜,故其作《典论》在论文时要按《周礼》取七之数。
其二,上文论及,以吴质与曹丕的关系,他在《答东阿王书》中提到春秋“郑国七子”难免会影响到曹丕,让曹丕论文时想到要以此七子比彼七子。《韩诗外传》讲:“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反观从东汉末的初平年间经建安直到曹魏的正始中,天下纷扰,人心不古,纲纪衰弛,儒道尽废,学风尽丧。《三国志》注引《魏略》谈到儒宗七子,曹丕于此又提文学七子,可见他在礼制和文德上的匡扶之心。
总之,曹丕提出的“建安七子说”是一个礼制和文学兼顾的评价,其形成与吴质、曹植、杨修等之间的文学讨论很有关系,其中吴质的“郑国七子”说尤值得注意。
[注 释]
①《三国志》所引《世语》记载了两件事。一次是: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一次是:(杨)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脩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脩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②《魏略》: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
③《三国志》魏文帝本纪:(黄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吴质不为顾命,大概因为年龄。)
④《三国志》:(崔林为幽州刺史,而此时)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吴中郎将,上所亲重,国之贵臣也。仗节统事,州郡莫不奉笺致敬,而崔使君初不与相闻。若以边塞不脩斩卿,使君宁能护卿邪?《吴质别传》: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此前有吴质席间讽刺曹真之事,得意忘形,文长不录。)
⑤《三国志》王粲传载:“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此七人即“建安七子”。
[参 考 文 献]
[1]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3]俞绍初,辑.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曹丕著,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I206.2
A
1008-178X(2012)11-0042-04
2012-09-23
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9B167);吉林省教育厅项目([2011]第175号);长春师范学院校级项目。
孙浩宇(1978-),男,河南卫辉人,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