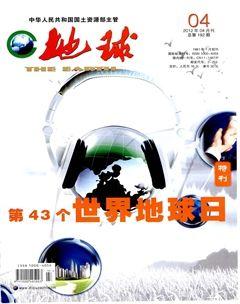可可西里的枪声
臧敬
(一)
“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一束机车的强光打过来,母藏羚羊倒在地上抽搐着,鲜血顿时蔓延开来,染红了一地冰碴。一个老人默默无声蹲下身子,熟练地剥开羊皮。白雪皑皑的远山冷峻无息,三个枪手抄着手走了过来,笨重的靴子踩在冰碴上沙沙作响,透骨的冷将哈气都快凝成了冰。
“日的,还有羊崽子!”一个枪手看着老人剥开的羊肚子,带血的小生命在蠕动着。
“嗯,叫他也过来。”领头的人平静地招呼了一声。
年轻的枪手押过一个双手被反绑,嘴角淌着血的汉子,跪在地上,母羚羊的眼睛始终是睁着的,看着他,眼神却已经涣散了。
“你是巡山队的吗?”领头人的声音亲切又柔和。
“是!”被绑的汉子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嗯好!巡山队的。”领头人将割下的皮子扔在他身边,冒着血腥的热气。
“是格桑的人吗?”领头人边问着边指挥人们把羊抬上车。
“是!”汉子回答得很坚定。
领头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嗯,好!格桑的人就好!来,你把他放了吧!”
年轻的枪手听话地蹲下身去,准备割开绳子,“砰”的一声,血沫子溅了满脸,汉子倒在地上,脑浆涂了一地。
领头人吹了吹余热的枪口,那张典型的饱经风霜牧民的脸,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转身,拎着枪上了车。
年轻的枪手蹲在地上,看着死去的巡山队员,默默无语。
这个被盗猎者打死的队员,名叫强巴。
这一夜,可可西里又下了一场大雪,铺天盖地的雪花精灵一般,抚平了盗猎者留下的脚印,也埋葬了刚刚牺牲的巡山队员强巴。强巴仰躺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瞪着眼睛望着天,白茫茫一片。
西部工委巡山队员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完全冻僵,像是个雕塑一般。
(二)
公共汽车在大莽林川之间一路盘山,视野渐渐开阔。窗外湛蓝的天空中,有秃鹰在不住盘旋,越来越多。颜璞望着窗外的路牌,欣慰地笑了,几天的奔波,终于到了,青海玉树治多,可可西里西部工委巡山队就在这里。
可可西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可是自从1985年之后,随着欧美市场对藏羚羊绒的需求,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短短几年,藏羚羊从一百万只锐减到不足一万只。1993年,当地武装部门组织了一支武装巡山队,领导人是藏族转业军官格桑,巡山队和盗猎分子发生激战,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1996年冬,巡山队员强巴在执行任务时候被杀害,报社紧急派懂藏语的颜璞来采访。
在一个破旧的小站,颜璞下了车,小贩们在沿街叫卖,有穿着藏红色喇嘛袍的僧侣,也有摇着转经轮的老人,满目灰尘。颜璞顺着山路一直朝里走,雪山脚下的寺庙里传来钟声。一群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跑过来,看到颜璞胸前的相机,于是争先恐后地喊着要照相。望着这群笑得天真烂漫的孩子,颜璞不好拒绝,“咔咔咔”一通连拍。
“叔叔问你们,知道格桑在哪吗?”颜璞放下相机,笑眯眯地问道。
霎时间,孩子们收敛了笑容,一个个全都跑开了。颜璞迷茫地看着远去的小孩们,突然一个孩子转过身,用手指指向对面的山头。
颜璞来到山前,看着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离寺庙不远的山腰间,这里正举行着原始而古老的天葬。以格桑为首的巡山队员们围在放着强巴的天葬台四周。经幡迎风猎猎作响,天葬师举起海螺,朝天空吹响号角,柏葉烟雀跃着,摇动的鼓铃与天葬师的诵经声交织在一起。远处盘旋的秃鹰越来越多,停在了天葬台不远的地方。
随着一梭子枪声响起,天葬师开始肢解逝者。一个四十来岁挺拔瘦削的人闭上了眼睛,眼角模糊着泪,这个人,就是西部工委巡山队队长格桑。
(三)
在一户普通的藏民小院里,杂七杂八的堆放着油桶、破旧的车胎、盘绳,还有一辆满是泥泞的北京吉普和一辆看不出模样的卡车。几个人钻在车下检修,地上堆满了零件。
颜璞尾随着天葬归来的格桑一行跟进了小院。格桑转身,上下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小伙。
“您好!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呃,我想采访你们!”颜璞上前一步,谦逊地笑着。
格桑面容冷峻,没动声色,好半天,才开口:“咋说?”
颜璞愣在那,憨笑着,听不懂。
格桑身边的阿旺热情地招呼说:“就是介绍信。”
颜璞恍然大悟,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来,双手递上前。
格桑扫了一眼,撇了一下嘴角,又递了回去,甩下一句“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就准备抽身走。
“听说你们正筹建自然保护区,我是为这事儿过来的。”颜璞提高了嗓音,他知道这是格桑的一块心病,格桑一直向上反映这个问题,可是每一次都石沉大海。
果然,格桑停住了脚步,吩咐身边的阿旺给颜璞安排住处。
阿旺是个很帅气开朗的小伙,留着卷曲的长发,反倒更显英气。他接过颜璞的背包,带他穿过院落,一群修车的队员异样地盯着这个外来客,貌似并不友善。这里曾经有记者来过,但是他们跟上头一个鼻子出气,巡山队改革的一切计划,没有一次落实到实处。
颜璞低头走上阁楼,不由惊了一下,楼顶的土坯上满是一张张藏羚羊皮,阳光下竞有些晃眼。
阁楼的空间不大,但摆设得整整齐齐。颜璞低头翻看着有关可可西里的照片,被残杀的藏羚羊、西部工委巡山队员、队长格桑、牺牲的战士……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有些不忍心再看下去,抬头,忽然发现一个漂亮的藏族姑娘端着一壶水站在门口,看着自己。姑娘穿着华美的氆氇,水亮透彻的大眼睛,冲着自己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颜璞笑着问道。
“央金!”姑娘轻轻走了进来,将一杯水递给颜璞。
“啊!你是格桑的女儿吧。”
姑娘点点头,拿起一本剪报翻看了一下,冲着颜璞友好地笑了笑:“你看吧!我不打扰你。”
姑娘转身出去后,颜璞看到剪报下放了一串佛珠,友好的象征,藏族人最直接的表达。
晚上,大家围坐在桌前,分着一盆烤全羊。颜璞跟他们坐在一起,拿起一块肉学着样子割起来。
“拿刀的方向反了。”席间有人用藏语说了一句。
颜璞冲他笑了笑。
“你听得懂藏语?”格桑有了些兴趣。
“嗯,我爸爸是藏人。”颜璞很坦诚的眼神,让格桑觉得这个外来人变得亲切起来。“我们藏人吃肉,刀口是对着自己的。”
颜璞自觉地调转了刀口方向,尴尬地笑了笑。顿时,爽朗的笑声四起,让远来的他觉得充满了乡土的温馨。
格桑问为什么刘滨没来,席问几个兄弟冲他挤挤眼,他也会意了,这个家伙,有一点儿空就往夜店里钻,狗改不了吃屎。话是这么说,可是他还是很看重这小子,敢拼敢闯敢干。刘滨也是巡山队的,退伍之后开出租车,后来自愿跟了巡山队,每次巡山,他都打起来不要命,天生有股血腥,但就是太好斗了。
而这个时候的刘滨,确实是在夜店里买醉,这里有他的女人冷雪。夜店里放着流行的嘈杂音乐,刘滨和一帮人划拳喝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杯,洒得满身满地都是,喝着喝着,竟然泪流满面。强巴是他的好兄弟,多少次出生入死,竟然就这样说没就没了。而盗猎者却依然肆无忌惮地逍遥法外。没办法,他们巡山队,很长时间没有经费没有枪没有工资,只能豁着命硬拼。冷雪收敛了方才的风情泼辣,将刘滨揽在怀里,给他擦去了眼泪。
席后,大家就各自散去了。
(四)
这天夜里,熟睡的颜璞被外边急促的脚步声吵醒,当他准备起身时,一个人推门而入,一束手电筒光打在他脸上:“赶快起来!今晚有任务。”
颜璞慌慌张地起身收拾上包裹跑到院子里,看到格桑正在指挥大家往车上整理装备,进进出出,忙上忙下。队员的家属也都过来送行,一个劲的嘱托着:一定要活着回来!有的在小声地抽泣。随着马达的发动,两辆吉普、一辆卡车钻进了黑暗当中,向着可可西里出发了。
第二天早上,在进入可可西里的关隘口,车队停了下来。远处传来汽笛的声音,干燥的大地上扬起一层黄沙。
“来车了!”大伙都警惕起来。
“我们每次进山,都会在这里设卡。”格桑跟颜璞边说边顺手抄起枪。
“能抓到盗猎分子吗?”
“不一定,这里是离藏羚羊产羊区最近的地方,他们经常路过的。”
车子被迫停在了路边,卡车上站着男男女女十来个人。
“你们从哪来的?”阿旺上前询问。
“五道梁工地。”司机摇下车窗,老老实实回答。
“要到哪去?”
“格尔木!”
“我们是西部工委巡山队的,要对你们进行检查。下车!”阿旺把门拉开,司机乖乖地走下车,站在一边。
“有没有带皮子?”队员扎西上前询问。
“没有!”司机回答得唯唯诺诺。
几个巡山队员上前把他按在车边,从头扒拉到腿,然后又拿出刀子在他空荡荡的绿大衣上划开一道口子,从里面取出一撮藏羚羊绒,捏到他眼前。
“这是什么?”阿旺又气又恨。
“棉花呗!”司机低着头,没有底气,只要长着眼睛就能看出那怎么会是棉花呢?
“放屁!带下去!”
两个队员押着司机走到远处,扒掉大衣,一阵拳打脚踢,询问盗猎者的下落。
其他人也被从车上赶下来,队员们在上面搜查私藏的羊绒。
颜璞看着远处被拳打脚踢的司机,便问格桑怎么处置。
“放了呗!这个路上,帮盗猎分子带羊绒的太多了。我们只能没收,没有权利抓人。”说这话的时候,格桑的话音异常低沉,无奈又无力。
不久,一伙人又上了卡车,不動声色地开走了。
队员们看着卡车远去,一个个心情复杂地上车,盗猎者,应该现在还没出可可西里。
(五)
第二天,巡山队来到了不冻泉保护站。一座孤零零的破旧帐篷支在山脚下。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帐篷前面有一个旧竹篙直立着,算是旗杆,上面挂着一面被风撕碎的皱巴巴的国旗。一个黑瘦的藏族汉子远远地向着车队边招手边跑过来,人们纷纷下车,拥抱着,欢呼着。
“这位是北京来的记者,专门做调研的。这个是我们在这边驻守的队员多吉。”格桑互相介绍着两个人。
“多吉,记者回去一报道,你不就成大明星了嘛!”队员们起着哄,开着玩笑,向帐篷走去。
来到帐篷,里面的一个小凳子上,摆着几片咸菜,一碗没化完的冰坨。
“就吃这个啊!”颜璞看了一眼多吉,顿时心里不是滋味。
“已经不错了!还没冻得厉害,要不然,胡萝卜都能碎成渣滓。”多吉倒是很满足地笑着给大伙倒水。
“最近有什么新闻没有?我的收音机坏了。”多吉问格桑。
“强巴走了!”格桑说得很平淡。
“哈!又去找他那旧相好了吧?唉!他这人呐……”多吉半开玩笑地边说边切菜,他太了解这个伙计了。
“他死了!”
正在切菜的多吉呆住了,良久,转过身去,抹了一把眼角的泪。
帐篷外面,一伙人敲着饭盆跳起了藏舞,一霎间寂寞的高原小站上,有了活力。大伙忘情地围在一起又跳又唱。最后的时候,队员们排在一起,颜璞给集体照了张合影,把满脸的笑容和着荒漠高原的孤独一起留在了记忆里。
吃完饭后,大伙纷纷上车,又要向着可可西里深处走去,多吉站在帐篷前面,远远地挥手告别,一直目送到车队消失在地平线上。又开始自己一个人的坚守,苍茫大地下,连同帐篷、旗杆和那袅袅升腾的烟雾,都显得如此凋零和孱弱,生命放任在广漠之中,渺茫得如同一粒沙。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了,有他在,盗猎者不敢过来。一个人住了三年,确实没办法,我们人手不够。”颜璞向外探着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小站,听到格桑这样的一番话。
(六)
可可西里这块地方,人类只是一个过客,野生动物才是这里的主人,在这冰天雪地之中,它们像精灵一样奔跑在这片最原始的土地上,却随着枪声的四起,这种和谐也就彻底地被撇了。
第三天,颜璞和队员们窝在车厢里睡觉的时候,被突然的急刹车惊醒,车队到了卓乃湖。可是令他们震惊得是:目力所及,遍地都是被剥过皮的藏羚羊的尸体,一只只嗜血的秃鹰正忙活着收拾残局,吃得津津有味,扑棱着翅膀穿梭在尸体周围,忙得不亦乐乎。
队员们清点着,四百五十六只。
远处冻冰的湖面上,一对父子蹲在凌筏子上,在一个冰窟窿里捞着鱼。
“过来!”队员们愤怒地招呼两个人。
两人回头看了看,没动声色。“砰砰”几声枪响,二人吓得举起手哆哆嗦嗦地走过来。
“见没见打羊子的?”格桑阴郁着一张脸问老人。
“见了!”
“多少人?”
“不知道!”老人哆哆嗦嗦地回答。
“你见了没有?”格桑压住火气,转身问另一个人。
“见了!”
“多少人?”
“不知道!”
“让你不知道?说不说!”刘滨气势冲冲地捉住男孩的脖领,抡拳头就打上去,“骗我们是不是?再不说没收了你们的船。”
“不知道!他们打得时候,天太黑,我们趴在船里,什么也没看见!”男孩捂着一张被打得鼻青眼肿的脸,带着哭腔说着。
刘滨收住了手,老人颤微微地给儿子擦去嘴角的血,一句话也不敢再多说。
“你们有捕捞证吗?”格桑叹了口气,问道。
“没有!”良久,老人才说出口。
“罚款!”格桑带着几个人离开。
扎西从布包里掏出印章,哈了口气,双手冻得颤微微地在罚款单上勉强盖上一个印章。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递了过来。扎西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放在包里。
其他人开始捡拾地上的藏羚羊尸体,堆放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坑里,洒上汽油,瞬间,燃起了烈焰。火苗攒动,浓烟滚滚,骨头的燃烧声哔哔啵啵地响着,秃鹰在上空盘旋。“我们每年进山,都会埋葬一万多只藏羚羊。”格桑告诉颜璞。
(七)
到第六天,车队行到了野牦牛谷,这里群山环绕,灌木丛生,地下封冻的岩石异常坚硬。车队开得飞快,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危险。突然一声枪响,排头的破北京吉普乱了方向,扭撞到一旁的灌木丛中,里面的队员被甩了出去。
大伙赶紧下车,端起枪防备着,队长跑到那辆车前,拉开车门,司机达瓦肩膀中弹倒在地上。于是,格桑赶紧叫过曾经当过医生的贡西过来包扎。
大伙顺着灌木丛搜寻目标,却没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有一辆被遗弃的卡车。刘滨趴在地上敲了敲油箱,已经没有油了。
格桑看着地上的轮胎印,招呼大家,赶紧上车,盗猎者刚刚过去半天。
第七天的时候,车队来到楚玛尔河。河对面有一伙人围着一辆卡车。
“就是他们!”格桑让自己的车队拉响警笛,呼啸着开过去。
河对面的人们听到警笛声开始四散逃窜。
车子开到河岸边,格桑带头脱了裤子挂在肩上,趟进了刺骨的河水中。枪声四起。
当下队员们就把对面的十几个人全都按在地上,铐上手铐。车上只搜出几杆猎枪。一个男孩中弹了,染红了整条裤腿。几个队员把他抬到格桑面前,男孩气息奄奄地说着“大叔,救救我!”,贡西翻看伤口,子弹打在动脉上,没有救了。
巡山队把这帮俘虏带过河,哆哆嗦嗦穿上裤子,冷得上下牙直打架。
“马老四,你这次怎么说?”格桑来到一个干瘦的老人面前,那老人蒙了灰的眼睛,像个洞一样,让人摸不清深浅,老老实实站在格桑面前。
“你给我件大衣吧!我冻得不行了。”他的话语近乎哀求。
“你们老板呢?”格桑并不吃他这一套。
“是他们让我扒皮子的嘛!没有办法!”马老四一个劲儿狡辩。
“你老实点!”
“我现在也是这个……我不知道啊!”
人群中,队员们挨个逼问着掰着手找枪手,都惊慌地推说不是。刘滨按着一个男孩的头,大声责问是不是枪手。
马老四赶紧说不是不是,那是他的小儿子,跟他一起扒皮子的,随手又指了指旁边蹲着的一个汉子。
“马四儿,你别冤枉人!”那人慌慌张张地埋怨着,却早被刘滨几个人反擒住手,“老实点,你是不是?”
“不是!我是正经八百的司机。”
“是司机为什么不走?”
“车子坏了,没办法修嘛!”
“胡说八道!”刘滨几人拽起那人就朝着远处的斜坡走去,边打边质问是不是枪手。那人一口咬定就是被诬陷的。于是几个人又是一顿野蛮原始的拳打脚踢。
颜璞看不过去了,他觉得即便是有过错的,也不能这么乱打,几次跃跃欲试,都被格桑一把拽回来,扔在地上,有些不屑,他们这些在北京习惯了太平盛世的记者们,哪里见过真正的残忍和暴戾?他们滥施的同情心在这块土地上是一点都不会奏效的。
那个被打的人终于妥协了,带着刘滨几个人来到他们藏皮子的地方。队员们挖出来,一张张铺散在地上,满满一地,明晃晃一片,四百五十六张。
格桑看着羊皮上的枪口,叹了口气:“现在是产羔期,真可惜!枪手跑了,这些都是小口径,羊子是用冲锋枪打的。我追了他们好多年了。”
收整队伍后,队员们把羊皮装上车,让马老四一列人跟着上了卡车。
摇摇晃晃的卡车斗篷里,挂着一盏摇曳的油灯。马老四看到颜璞手里夹的烟,就冲着他要一根抽:“给我一根呗!都好多天没抽过了。”
颜璞递给他一根,两个人就在一起搭讪起来。
“你是做什么的?”记者笑着问,很和蔼,没有格桑他们那样凶。
“扒皮子的。我在格尔木是扒皮子扒得最快的一个。”马老四回答得很坦然。
“一张皮子多少钱呢?”
“五块!我的孩子们都在。老大、老二、小三!”马老四指着身边三个年轻人说道。
“那你们之前做什么?”
“以前放牧呗!放羊、放牛、放骆驼。后来变沙漠,全都死了,放不了了。卖的卖了,杀的杀了。人也没吃的了,人也快活不下去了,不包皮子怎么着。”
听完這翻话,颜璞陷入了沉思。突然车晃了一下,车斗里的人们撞做一团。
“下车下车!”
卡车后轱辘陷在泥坑里了。
大伙纷纷下车,马四一伙蹲在地上,看着巡山队员门往外拖车。可是越是打轮,越是陷得深。只能改成推。马四一帮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帮忙往外挪。推的推,拉的拉,马老四在旁边挥着一双带着手铐的手喊着号子,终于出来了,人们都欢呼起来。
车队又开始在荒漠上疾驰。
(八)
第九天的晚上,巡山队又开始安营扎寨。
分发干粮的时候,队员们发现粮食已经快不足了。阿旺提着口袋走进去,发给俘虏们每人半个。马老四又开始带头嚷嚷:“多给点呗!好几天没吃了!”
“告诉你马占林,没你吃的。我们省下来的你知道不知道?!”阿旺气冲冲地瞪了马四一眼,这家伙到哪都搀和一下。
颜璞偷偷掰给马老四半个,马四笑眯眯地小声点头致谢,狼吞虎咽吃起来。
不知道谁哼起了一首思乡的民歌,呼应声四起,大伙都唱起来,越唱越显得惆怅,人群里岁数小的竟然哭了起来。
颜璞走出帐篷外,扎西和阿旺站在卡车边上,抬头看着湛蓝的星空,星星一颗颗清亮得如同猫眼,闪闪发光,纯净与自然,没有丝毫的污垢。
“嘿!这里缺氧,难受了就到外边站站,挺好的!”阿旺笑着对颜璞说。
“漂亮吧!最开始进入可可西里的时候,我是发了疯地想回家去,可是过不了两三天,就又想这里了。‘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里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你在可可西里踩下的每一个脚印,就是有史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扎西一本正经地深情地说着。
颜璞诧异地看着他,阿旺在旁边笑翻了天,拍着扎西的头。
“呃!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地质学家说的。他来自北京,当年我送他进的可可西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里到处是吃人的流沙。”
一宿无事。
第二天早上,格桑铁青着张脸直奔刘滨,他昨晚值班,可是马四父子已经跑了。格桑一脚将刘滨踢到在地,用硬梆梆的靴子踩在他脸上,咆哮着:“什么时候睡着的?叫你连个人都看不住!”接着又是几脚。刘滨从地上爬起来,跟着格桑他们去追馬四父子。
雾气迷蒙的高原上,冷风刮得透骨。马四父子在迎着风朝着雪山方向走着。
当听到喊声的时候,马四乖乖地举起手。刘滨与阿旺和达瓦奔跑着去追另外三个。
高原上再加上剧烈的跑动,整个人的肺要涨得爆炸。刘滨紧追着马家的大儿子不放,最后都瘫软在雪地上,还在一下一下往前挪着,刘滨咬着牙给他套上了手铐。
而达瓦先前肩膀上有枪伤,还没有愈合,又加上刚才的跑,一个跟头扎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往外喷着血沫子。格桑抱起他,是肺气肿。贡西掏出针头,却没有液体稀释药粉。马四的二儿子说要来试试。格桑犹豫地看了他一眼。马四也说,让他试试吧!他之前做过医生的。贡西把注射器交给他,他先抽取了半罐血,稀释了药粉,然后又打了进去,才渐渐止住了达瓦的疼痛。
格桑让气喘吁吁的刘滨带着达瓦回去看病,然后再带上给养赶回来。说着让阿旺给他拿钱,先是他们自己的经费,一叠零票,刘滨看了看,说不够。于是又把从前县里给的几十元经费也交给他,刘滨说还是不够。
格桑拧着眉头,像是下一个决定:“那就卖皮子吧!”
“我们去阿尔金山追他们,你到时候从花土沟进来跟我们汇合!一路保重!”
刘滨和众人一一告别。开足了马力返程。
送走了刘滨,平措悄声告诉格桑吃的已经没有了,油最多也能坚持三四天,卡车肯定带不上了。格桑说三四天应该能追上了,但是也仅仅是应该而已。
来到卡车旁,格桑让俘虏们从车上下来,他们都是格尔木的牧民,让他们各自回家。马老四抄着手,麻木地看着格桑:“你让我走,我走不出去了,我老了!”说完抽了抽鼻子。
“我油没了,粮没了,还抓你们老板。这到昆仑山口一百公里,到阿尔金山二百公里。你能出去!”格桑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马四摇着头:“走不出去了!”
“确实出不去,就是你的命,保重吧!”说完和阿旺几个人开上两辆北京吉普离开了。
僵立在寒风中的马四一伙人也只得迎着风走进了一场未卜的生死路上。
(九)
第十天,格桑的队伍来到布格达板峰。一辆车子停在了路边,机油没有了。格桑发了脾气,埋怨他们为什么出发前不准备好,但是一切都没办法挽回了,只能留下车上的平措三人在这里等刘滨过来接上他们。
西北风刮得紧,冷风席卷着地面的黄沙像刀子一样割着露在外面的皮肤。
格桑带着颜璞和扎西、阿旺四人驱车又钻进了黄沙中。
“刘滨能找到他们吗?”颜璞关切地问道。
“但愿不要下雪!”格桑在心里一遍遍祈祷着。但是事与愿违。
渺茫的群山中,孤零零的三个人挤在车厢内,天色越来越浑浊,西北风开始搅着盐粒一样的雪渣子落下来。
第十二天的时候,昼夜不间断疯狂开了三十六小时车的刘滨躲过牦牛群,在路边上停下来。已经精神恍惚的他扑倒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雪沫,后来干脆扎在雪堆里,让自己清醒些。然后抹把脸,看着不远处的村镇,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用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另一头拴在车顶上,以防止自己打瞌睡。
一大早,刘滨把车横冲直撞地开进了镇上的诊所,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已经发直了,他抽出刀子割断绳子,然后推开车门直接跌下车。两条腿已经不能动弹了,他使劲敲着车门高声叫着医生,好长时间,医生才出来。
当他被人摇醒的时候,才知道达瓦没事了,于是他又晃晃悠悠去了夜店。他要找冷雪要钱。
放着摇滚乐的夜店里,歌舞升平,这时候传来杯子的破碎声,刘滨拉着一个舞女就往外走。来到车上,冷雪看着他脏兮兮的脸,头上还有个红头绳的小辫,笑了。刘滨跟她说借点钱给队上买机油。冷雪哭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向她借钱了,她用出卖肉体换来的钱,全都交给他去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而他呢?不仅长期不在她身边,而且每次进山,都是命悬一线。她的难言苦衷,又向谁说呢?
早上,刘滨从睡梦中醒来,已经日上竿头,冷雪不再了,却留下了一叠钱和一个平安符。刘滨下车无可奈何地看着远处已经悄无声息的夜店,满心难过地敲了一下头,多糊涂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一卷皮子去黑货市场卖,好换回机油。成交后,他极为不情愿地把皮子交给老板,与其说是给,还不如说是老板从他手里夺过去的。皮货老板骂了句神经病就把钱丢给了他。刘滨魂不守舍地接过钱,像个游魂一样。在加油站,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又上路了。
(十)
第十四天,可可西里的风雪已经越来越大。马老四领着一帮扒皮子的人迎着强风一路而上,已经有很多人倒下了,倒下的人也就再也不會起来,像是死去的藏羚羊一样,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
而车子坏在布格达板峰的平措他们仨呢?再等下去只能冻死,于是三人互相搀扶着,开始寻着公路的方向走去。
已经没有希望了,格桑的车依旧在疾驰,可是下雪了。
“你们现在最大的苦难是什么?”颜璞问道。
“没钱没人没枪,一年没发工资了,县里又不发经费。”格桑长叹一口气。
“为什么?”
“因为没有编制!”
“那你们怎么处理缴获来的皮子?”
“大部分上缴。”
“你们会不会卖皮子解决经费问题……卖皮子是违法的……我真不知道这篇报道该怎么写?”
“这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这些记者保护着呢呗?!我可以进监狱,但我不会考虑你说的,我只考虑可可西里,考虑我的兄弟。见过磕长头的吗、他们的手和脸是脏的,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卖皮子?!我们没有办法!”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队长异常苦闷。
这时候,车子走不了了,机油用光。四个人只能下车背着枪钻进了风雪中。翻过雪山就是公路,格桑一行发现了盗猎者遗弃的越野车,他们就在前面,必须在他们上路前追上去。
而这个时候,刘滨的车却陷在了沙堆边,刘滨无奈地下车,一件件把车上的行李卸下来,散放在旁边,正当他要放下手里的箱子时,突然感到脚下一滑,空了一下,两只脚紧紧地被沙子咬住,刘滨心里咯噔一下吃住劲,陷进流沙了。来不及多想,他使劲撑着两边的硬地,试图从里边拔出来,可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沙子越积越多,他慌了,已经陷到腰了。他拼命地往外挺,尽管这样只能加速流沙的蠕动。但生的本能让他不得不这样挣扎着,容不得多想。沙子已经漫到脖梗,他只能张着嘴,已经不能呼吸了,瞪着眼睛,望着这片天,静静无边,恐慌亦或镇定,一切都无法阻止生命无情地下陷,眼神已经迷离了。流沙蠕动着,一点点、一点点下陷,那一刻如此漫长。流沙吞噬了最后一丝发梢,蠕动着,又和着北风,吹得平平整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留下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围绕在四周。
(十一)
格桑的队伍,只剩下他和颜璞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走在冷风中,其他的两位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圣地。翻过前面的山,应该就上路了,二人踉踉跄跄地走着。
突然,前方出现几个黑点,越聚越多,越来越近,他们手里握着冲锋枪,一个个也是准备往路上赶的,却有人发现了他们俩,于是掉转身围了过来。其间,就有抄着手,看上去老实巴交的马四。
“马老四,你到底是走出来了!”格桑冷笑道。
“我们的人也死了很多!这位就是格桑队长!”马四讨好地向领头的老板介绍,“这就是你一直要找的我们的老板!”
“队长抽颗烟吧!”盗猎者头头拿出一颗烟递过去,皮笑肉不笑地柔声说道。
“我抓你好几年了!”格桑面不改色。
“你抓我干啥子?我们又不认识!”老板一副无辜的样子。
“你打我的羊子。”
“青海打羊子的人多了,干啥子抓我们啊!”老板装得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管,就是要抓你。”
“那你想怎样?”
“跟我走!”
“队长,您把我放了,我给您两辆车。”
“少废话,把枪交上,人跟我走。”格桑蔑视地看着这趾高气昂的老板。
“那好那好,把枪教队长,我们跟着去巡山!”盗猎头目笑得牲畜无害。人群里也哄得笑开了。
恼羞成怒的格桑突然一拳打在老板的脸上,打得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在地上。
“砰!”一声枪响,格桑倒在地上,蜷缩着身体,老板捂着脸大骂谁开的枪,差点打到自己。那个年轻的枪手又怯生生地站出来,强巴被杀溅在他脸上的血还没有完全洗净。
老板一脚踹倒那孩子,从他手里夺过枪,冲着在地上抽搐的格桑就又是一梭子。
格桑死了。
其他几个盗猎者把拼命挣扎的颜璞拉到旁边。老板问是格桑的人不?马四告诉他不是。一伙人稀稀拉拉地又钻进了风沙中,鬼魅般消失了。
马四经过跪在地上呆了的颜璞的时候,低声告诉他沿着他们的脚印走,再不远就走出去了……
注:本文节选改编自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取材于可可西里索南达杰领导的野牦牛队巡山保护队的真实故事。导演陆川为完成此片,率领100多人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苦战120天,将屠杀和保护藏羚羊的情节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且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通过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讲述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挣扎和人与自然的相互抗争。该片被评论为一部关于信仰与生命的电影,是一部关注人类自我生存状况和自然环境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