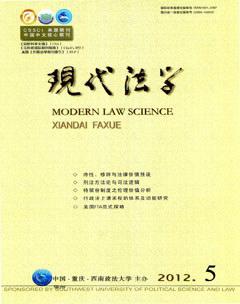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
摘要:法律价值预设作为法律中提纲挈领、统领全局的内容,在法律作为“制度性修辞”的命题、判断和架构中,有着独特的分析意义。法律价值的抽象性、统领性,提供了诗性思维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诗性思维也把法律价值预设结构在修辞世界。不论作为技术的修辞,还是作为本体的修辞,都对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起着论证作用。如果说法律和法治本身是一种制度性修辞,那么,通过法律价值预设能更好地证立这一判断。
关键词:诗性思维;制度性修辞;技术性修辞;本体性修辞;法律价值预设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5.01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预设,虽然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最终决定了法治,而不是法治最终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近代以来循着严格立法路径推衍的法治模式,决然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亦步亦趋。“法令改变不了社会” 参见: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张月,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的说法即便在终极意义上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在过程意义上或是一句十分正确的废话。因为我们在短短十多年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答应遵从其相关规则所带来的社会的巨大变化中,明显可见法令对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强力推动和决定性影响。但问题是,既然法律在改变着社会,改变着我们的交往行为方式,甚至也改变着我们的心理结构 说法律在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结构,在有些人看来或许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但我们所面对的日常生活事实业已表明,法律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已经让人们在交往中以主体身份进行参与,因之,权利不仅壮大利益,而且也壮大精神。经由现代法律的规划所展开的现代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让所有人以主体的身份结构在企业生产、管理和交易过程中。一旦这种主体关系被破坏,则任何一位主体皆可以法为据,诉讼于公堂,争辩于法庭。这正是法律对人们心理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结构的重要影响。这在最近围绕一起造谣事件,范冰冰、章子怡等都自觉地选择司法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行为中明显可见。它表明,有纠纷而寻找权力庇护的情形正在改变,寻找法律帮助的情形正在形成。(参见:中国网络电视台. 范冰冰状告影评人 毕成功称要和其“组团”告网站[EB/OL].(2012-06-13)[2012-06-26].http://news.cntv.cn/ent/20120613/106131.shtml;搜狐网.章子怡向香港法院递诉状[EB/OL].(2012-06-12)[2012-06-26].http://yule.sohu.com/20120612/n345358689.shtml.),那么,必然意味着它本身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导生的结果,反之,它在改变并导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而需要追问的是:以有限的法律规定(原则、规则),如何能调整或规范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交往关系?这种规范是一种科学的规范还是人文的规范?是理性的安排还是诗性的安排?是逻辑的诱导还是修辞的诱导?特别是法律和法治中的价值预设,又是根据诗性思维和修辞的原理,还是根据理性思维和逻辑的原理所得出的?这些问题,也是本文所拟展开讨论的一些话题。
一、法律价值预设作为一个诗性话题(一)法律与诗性思维
一般以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和人类交往的善良公正,但其自身是实现善良公正的技术或手段。 乌尔比安引用杰尔苏斯的话说:“法乃公平正义之术”,就典型地表达了对法律的这种见解。(参见:斯奇巴尼.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8.)任何技术手段,都必须置于理性权衡之下,否则,就不可能带来人们期望通过它获益(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的效果。尽管法律有其价值之维,但一般说来,法律的价值之维,存乎法律规定之外,即便法律原则的规定,在法律之内或许是价值问题,但逃出法律之外,它也是实现价值、追求目的的一种技术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把法律及其价值归于诗性话题之下,似乎不无浪猛、无比唐突。
是的,法律总是理性权衡的产物,即便是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地选择和形成的习惯法,也是人们在自发的行为中博弈选择的结果。这种博弈,有时候还不仅仅产生在自发的行为之间,而且自发行为还会面临与强大的国家组织行为的博弈。例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曾被国家大传统宣布为落后习俗,而要求人们“腊月三十不停工,正月初一照样干”,要求人们丢弃祖先崇拜、革除亡灵祭祀……可数十年过来了,上述习惯不但没有被国家大传统的禁令所销蚀,反而成为国家大传统必须尊重的习惯。如今,上述节日皆被规定为法定假日。再如一度在各地推行的燃放烟花炮竹禁令,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坚韧制约下,终于松开其禁止性规定,由禁放改为限放。这些都足以表明,国家法也罢,民间法也罢,都是在行为博弈和规则博弈过程中人们权衡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使法律似乎天然地连接着理性,关联着逻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排斥着诗性、规避着修辞。
然而,即使法律必然存在着理性之维,但也并不意味着它能摆脱诗性之维。在我看来,法律之于诗性,不是其拒绝与否的问题,而是其根本就无法摆脱的问题。这意在表明,诗性是法律的必要向度,尤其是当我们把法律连接到法治这个宏大而又不无自负的命题的时候,既显示了人类选择的一种抱负,也表达了人类行为的一种浪漫。经由这个词汇,可以把人们带入法治之瑰丽而生动的诗性世界。
行文至此,须要交代一下究竟什么是诗性,以及什么是诗性智慧和诗性思维。意大利人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描绘了一个独特的智慧世界。这种智慧是原始智慧,因此也是一种粗糙的智慧。这种智慧世界不同于理性的逻辑世界,而更接近于一种诗性的修辞世界。所谓“新科学”的命名,就是基于作者对以理性逻辑为特点的科学世界的反思。“新科学”的领域,毋宁说是艺术和美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具有完全不同于科学世界的思维特征和智慧内容,这便是诗性智慧。且看他是如何描述诗性智慧的:
现代法学谢晖: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
“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
“……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崇高到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写了些诗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却没有创造出比得上神学诗人们更好的作品来,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出现。”[1]
或许维柯这种对诗性智慧的发散性描述,尚不能满足中文读者喜欢准确地把握该词的习惯和嗜好(这已经流露出一种理性思维的特征),为此,我不妨把我国台湾学者林雪玲对诗性智慧或诗性思维的定义性描述引证于此: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合融的主体境界。”[2]
尽管诗性思维在上述作家笔下,皆被认定为是一种原始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后该思维方式便销声匿迹,反之,即使在今天科学如此昌明,理性如此受捧,逻辑如此发达的时代,诗性思维依然是人类追问价值、寻求美感、面对未知时必须倚重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能否这样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越来越远离其儿童时代,但并未因此而丢弃其原始思维。为什么会如此?其基本缘由是人类文明和理性本身的相对性。
常言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告知人们:在终极意义上,世界永远是不可知的,人类思维面对浩瀚的宇宙和无限的未来,无法清晰地运用数目、字全盘处理,于是,插上想象的翅膀,在诗性思维的视角衡度宇宙、考量人生、把握未来,是克服并补救人类理性思维有限性的重要思维方式。人类思维不仅在面对自然界时是如此,而且在面对人文—精神领域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人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神现象。这是何以“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思维前提,也是为何“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语言是存在之家” 上述语句分别为笛卡尔、贝克莱和海德格尔的重要哲学命题。也曾是一种“唯物史观”不遗余力地批判的靶子和对象。(参见:笛卡尔.笛卡尔:我思故我在[M].王阿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的存在基础。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就是依循精神现象而展开和深入的。甚至连牛顿在科学(力学)之后寻求上帝第一次推动的努力,也可看作是其从自然领域位移到精神领域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在结果上是无效的。为何牛顿的努力在自然领域会取得穿透历史、影响人类的成就,而在精神领域却寂寂无闻、甚至成为一些科学团体为圣人讳的缘由? 参见:百度百科.牛顿[EB/OL].[2012-06-26].http://baike.baidu.com/view/1511.htm.我想,原因可能很多,但不能不思考的是人类精神领域和自然物质领域相比较有更复杂、更深沉,甚至纯粹靠理性、逻辑和科学所无法解释和验证的内容。即使把精神世界限缩在人们日常交往的领域,也明显存在着和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的样态——恰恰是这种样态,让科学、理性和逻辑在精神领域的运用大打折扣。
在和自然世界比较的意义上,我把精神世界描述为“双重动态”的世界;而把自然世界描述为“单向动态”的世界。后者是指自然世界的运动,是机械的、内在的、可测的、可控的,而前者的运动,却是有机的、内外双重的、不可测的和不可控的。 参见:谢晖.法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所以,对已知的自然物质世界,完全可以代入公式、依循逻辑而在理论上解决,在实践中验证。但即使对已知的精神世界,人们也很难在一个公式所约定的框架和条件内进行解释。这正是精神领域完全有别于、并且明显复杂于自然领域的缘由所在;也正是对精神领域的认识完全有别于、并且明显复杂于对自然领域的认识之缘由所在。许苏民曾指出:
“民族的生存条件至少应该包括五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他人,人与社会群体,人与现存的传统文化氛围,人与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进程等。”[3]
如果许苏民的这种设证成立,则可以看出,在人(民族)所面对的五种“对象性关系”中,只有人和自然的关系才涉及物质自然领域,其他四种关系,无一例外都属于精神领域的“对象性关系”,或者把精神现象对象化后生成的人与对象的关系。这更进一步彰显了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在很多情形下的非逻辑性。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如何把精神领域的研究和自然领域的研究分开来,以方便地寻求精神领域问题的独特之处和规定之处,有效地阐释人类精神现象自有的问题,成为必要。这也迫使人们在科学(自然科学)之外,寻求精神领域研究的定位。这一定位,有些人称之为精神现象学,如黑格尔;有些人称之为精神科学,如狄尔泰;有些人称之为文化科学,如李凯尔特;有些人称之为美学或道德科学,如齐美尔;有些人称之为新科学,如维柯;有些人称之为诠释学,如伽达默尔;有些人称之为交往行为理论;还有些人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如当今中国学人……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M].童奇志,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凡此种种,都照应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精神领域不同于自然领域。精神领域具有更加复杂的特征,因此,要完全借用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无法胜任愉快地揭示精神领域的本质。于是,诗性思维在精神领域的研究上,理应出场、必须出场,并作为最重要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
可见,诗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一样,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两种思维向度。只要人类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自然领域的问题,同样,只要人类无法按部就班地解决社会—精神领域的问题,那么,也就无法摆脱对诗性思维的必然依赖。事实也证明,诗性思维是克服理性的机械枯燥,把人们带进那种“诗意地生活”境界的基本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法律价值预设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将通过如下一些问题的解决予以阐述。
(二)为何选择法律价值预设
何以在本文中要撷取法律价值预设来说明诗性思维与它的关系,并进一步说明其和法治的关系?法律价值是一个表征主体需要与法律供应之间关系的概念,是法律满足主体交往行为需要的状态。显然,它是介乎主—客体间的一个“关系性”概念。 笔者对法律价值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参见: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38-231.这样看来,法律价值未必等同于法律价值预设。前者跨越法律这一客体和人这一价值享有者(主体),从而是由法律内部而及于外部的概念,但法律价值预设却不同,它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或者说法律内部的概念,因此,它类似于法律的价值这一概念(应特别注意,法律价值不同于法律的价值[4]),但又不同于法律的价值。因为法律的价值在法律内部视角,是一个倾向于应然性和实然性同在的概念,而法律价值预设在法律内部基本上属于应然范畴。
法律价值预设在规范实证意义上,经常体现在法律原则的规定上。众所周知,对一部法律而言,原则既属于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内容,也属于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价值。它在表现形式上是高度抽象的,但在涵摄内容上又是广泛全面的。在多数条件下,这些规定只能是一种假定、一种预设。因此,它虽然具有现实的一面,但在更多情形下,它代表了人们对法律的憧憬和理想。这种憧憬和理想,就提供了诗性思维和法律价值预设之间的连接通道。
以婚姻自由这一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价值)为例,对任何一位青年男女而言,这是一个能把相互的爱情化作婚姻的原则保障。但究竟什么是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法律预设的实践场景是否只存在于自由状态下?没有爱情的自由结婚能否算作婚姻自由?类似如下的婚姻选择是否属于婚姻自由的范畴:
一对生活在北京且十分恩爱的男女,各自因为无房无车,在北京实在“无法”生活,决定分手。不久,两人又各奔前程,建立了自己有房有车的幸福之家。谈到以往的爱情,两人都表示那是人生的巅峰感受,可能此生不会有二。但谈到婚姻生活,两人都主张爱情不能当饭吃,婚姻还是要现实点。
在“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这一浪漫主义理念下,按理只有这两人之间才最适合建立婚姻,他/她们的婚姻,才符合婚姻自由的真谛,可吊诡的是两人都为了眼下实利,放弃了“价不低”的爱情,选择了“价更低”的房子、车子……
这一例证提醒人们的是,究竟应把婚姻法原则中的婚姻自由看作是心灵归宿的自由,还是行为选择的自由?如果从心灵归宿意义上讲,或许前述这对恋人之间更能够心心相印,他/她们之间选择结婚成家,或许更符合婚姻自由的价值真谛。但从行为选择的自由视角看,两人都没有选择自己的心上人作为婚姻伴侣,反而因为利益的自由而选择了爱情的不自由。那么,这种行为选择是否属于婚姻自由的价值预设范畴?倘若按照恩格斯有关“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会合乎道德”[5]的说法,那么,这种为了物质利益的自由行为选择,显然是对爱情和心灵自由的背叛。如果支持这种背叛,强调只要是当事人自主自愿的行为选择,则婚姻自由仅仅是结婚或离婚之行为选择的自由,不应当包含珍重爱情的心灵自由;如果反对这种背叛,则必须在婚姻自由的内容中嵌入爱情的心灵自由这一因素。否则,所谓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也就是某种意识形态说教,而不具有法律规范、乃至法律价值预设的条件。
以上讨论说明,作为价值预设的婚姻自由,究竟应表现为何种情形,人们既可以运用逻辑的、科学的手段予以说明,所谓婚姻自由应包含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陈述,就是这种科学意义上的逻辑归结。但借助这一原则,人们也可以想象自由缔结的婚姻该是以爱情为前提的结合,该是必然能够带给人们幸福和惬意的结果,该是两个相爱的人甘苦共尝、忧乐共担的人生过程。婚姻自由不应当有爱情之外的附加因素,一旦有这样的附加因素,婚姻自由便牺牲在物质世界供应的不自由中,从而婚姻自由这一目的屈从于外在的物质条件。
这样的分析使得婚姻自由这一价值原则即使有逻辑的归结和解释,但也不能排除人们对这一原则更高级的诗性想象:把人间男女的一切美好,都归置在婚姻自由原则的名下,让美好的想象借婚姻自由原则而驰骋飞翔——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婚姻自由的美好故事,一定是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婚姻,一定是牵手、私奔、终成眷属之类动人肝肠的婚姻。除此之外,一切斤斤于小利,萦萦于权术的婚姻,都不过是对婚姻自由的讽刺。这正是诗性思维在婚姻自由这一原则上的映照,也隐含着法律价值预设与诗性思维的关系。这也是在本文中我为何选取法律价值预设来说明诗性思维和法治关系的基本缘由。
(三)诗性思维与法律价值预设
前已述及,法律价值预设的内容大致上规定在法律原则之中。众所周知,在法律不同要素中,原则是最富抽象性、概括性和价值性的内容。如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人权保障等这类原则,尽管内涵具有一定确定性,但对其本身又可以做出多样的解释。 这或许最能表明法律和法学既有科学、逻辑的一面,更有人文、诠释的一面。(参见:谢晖.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J].法律科学,2003,(1):3-14.)尤其当这些原则和实践交汇的时候,人们考诸逻辑可以进行种种追问:主权在民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既然主权在民,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呈现的是公民权利因为权力的染指而被侵害?公民通过什么方式表达或体现其主权在民的事实?除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之外,还有其他方式以表达主权在民吗?代议制民主是否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的要求?人人平等指的是什么样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如果是机会平等,为何在一个社会失业的总是底层人士,而一个国家的权力拥有者为何鲜有失业者?如果是结果平等,为什么随处可见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形?人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利?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发展权还是自由权?究竟自由权高于生存权,还是相反,生存权高于自由权?如何确立基本人权的内容?为什么都声称要保障人权,可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如此明显,乃至于成为和平时代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最明显的对立之一? 众所周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近二十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就表现在人权领域。在西方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下,一方面,中国逐渐接受了人权观念,并两度确定了《人权行动计划》,分别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但另一方面,人权的主导内容究竟是自由权还是生存权,至今依然是中国和西方针锋相对的重大话题。中国的人权建设,可谓始终伴着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而展开。
对上述追问,人们或许能够给出一种逻辑上清晰圆满的说明,但更多的时候,却给不了逻辑圆满的说明,这一方面取决于原则及其价值预设本身的抽象性、主观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原则及其价值预设与实践结合时的复杂多样性。
一个事物的抽象性来自两种情形,其一是该事物表达了最一般的原理或者定理,并能通过数学的方式得到精确的验证。这种抽象,乃是科学的抽象。其二是该事物表达了人们最一般的关切和追求,但这种一般关切和追求只能借助经验验证,而无法完全获得数学上精确的科学验证。对后者的验证,在逻辑上可以通过经验归纳的方式进行,而无法运用演绎推理的方式从事。因为一旦诉诸演绎推理,需要首先把该原则及其价值预设代入到三段论之大前提中。而要作为大前提,又需要进一步证明该原则及其价值预设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里合理与合法的唯一表现方式就是相关原则及其价值预设所表达的内容是真的。
但实践证明,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并不能被经验完全证实,即便在号称真正民主自由的美国,诉诸其历史,人们依然能发现宪法原则中的平等内容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等深深困扰的情形。直到如今,失业、贫富差距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让法律上平等的宣告和努力在实践中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再进一步,当我们把这种事实放大到国际交往领域时不难看出,所谓平等,不过是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发达国家之间,即便存在所谓票决的平等,也存在事实的不平等。倘若再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位移到不同国家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则不平等反倒是一种日常的、绝对的、普在的事实,而平等反倒成为反常的、相对的、偶在的事实。这表明,在逻辑上很难周全类似平等、自由这样抽象的法律价值预设,不但如此,它们反而很容易被逻辑所撕裂和证伪。
不能被实践完全证实的基本原因在于法律原则所预设的价值具有主观性、模糊性以及它与实践遭遇后的复杂多样性。价值预设是根据人的好恶做出的。即使那种被宣布为人类一般价值或普世价值的法律预设,依然受一定利益关切的掣制,这正是任何一个国家无不从其利益关切出发,对国内外类似事情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运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处理的原因所在。 最典型的如美国对待塞尔维亚阿族分离主义运动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为了支持和保护阿族分离势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采取一场战争,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为了保护土耳其这一盟国的领土完整,美国则态度分明地站在土耳其当局一边,并把捕获的土耳其工人党领袖亲手交给土耳其处理。如此反差,不正表明利益对普世价值的左右和冲决吗?不正表明在实际行动选择中利益和价值的一般关系吗?因此,法律价值预设本身的主观性、模糊性以及它在遭遇实践之后更进一步呈现的主观性、模糊性、利益支配性和复杂多样性,更不能将其仅仅置于逻辑的框架中进行推论。
可是,尽管这些抽象的价值不能完全置于逻辑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推论,但这些价值本身却是现代法律所不能或缺的。那么,经由逻辑无法完美证立的情形应如何补救?应如何周全法律上这种抽象的价值预设?我以为,一种无法弃置、必须重视的方式就是通过诗性思维,通过理想陈述来周全法律的价值预设。这种诗性思维就是把法律的价值预设放在信仰的维度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等法律预设的价值,不仅是法律的宣告,也不仅是法律的一种抽象陈述,而且是人们在心理上和行动中必须承诺并予以践行的信仰。 尽管我所倡导的法律信仰理论(参见: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受到一些学者如魏敦友、范愉、张永和等学者的批评(参见:魏敦友.法理论述的三重话语[N/OL].法制日报.2000-5-28(03);魏敦友.再评“法律信仰”[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20-23;范愉.法律信仰批判[J].当代法学,2008,(1):10-17;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3):53-62.),但站在诗性思维的立场上理解法律,尤其是法律原则的价值预设,我认为法律信仰问题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旦把信仰因素纳入到理解并遵从法律的框架下,则意味着诗性思维和法律价值预设之间,就天然地有了勾连、贯通的管道。那么,诗性思维在手法上如何具体呈现出来?如何通过诗性思维的具体手法说明并理解法律的价值预设?这必须与诗性思维的表达手段或技巧——修辞相勾连。
二、法律价值预设的修辞证明诗性思维的技术之维就是修辞。诗性思维作为一种和理性思维相对的思维类型,是人们对类似思维方式的一般表达和概括。严格说来,诗性思维和理性思维都是人类思维的内在规定,这种内在规定只有具体地表现为某种外在行为或者技术手段时,才能发挥交往行为中理解和交流的效果。那么,诗性思维在人们的陈述、写作、讲演、交谈、对话、辩论等过程中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表现出来?如何把诗性思维的内心激情表现为外在的“煽情”,以便激起读者、听众们的共鸣,取得经由语言交往行为的实际效果?事实上,这种手段无外乎修辞。所以,修辞是诗性思维的外在表现方式。
(一)修辞的两个理解维度
修辞作为一种对事物认知的表达方式,既是抒发人们情感的主要的技术手段,也是支持论辩成功的重要的工具形式。所以,对修辞问题,既有人们在传统修辞意义上所作的理解,即把修辞主要作为润饰言语交往行为的一种手段,即技术视角的理解。这里的言语交往,既包括说话、讲演、对谈等语言性的言语交往,也包括书信、论著、词赋等文字性的言语交往。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和交往的发展,就是说和写的博弈史,或者说就是语言和文字两种交际工具的博弈史——口耳相传的语言史,给世人留下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规中矩的书写史,则把人类文明推进到经由记忆、拓向未来的创造性时代。直到今天为止,人类借助高科技手段的竞争,无非还是争取语言或文字两种表达手段的竞争。如书写出版的通行及其便利,就是对口耳相传语言交往的一次胜出;而录音、录像以及电视技术的发展,又是对文字书写交往方式的一次超越;至于现代互联网技术,更是将两者兼而融之、巧妙圆润地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方式。 参见:谢晖.游走在声音与象形之间[G]∥谢晖.法治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它成功地把以声音表达的语言交往和以象形表达的文字交往结合起来,使得人类文明从此由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到电与光的时代。可以说,离开语言和文字的纯粹行为交往,在人类的交往行为中早已退居其次,且其意义和言语行为交往相比较,要大为逊色。
言语交往行为的这种事实,本质上是把人们面对的对象世界——自然、个人、群体、文化、历史,甚至语言文字本身等等构织在符号形式下的活动,是用符号形式给一切对象命名的活动。有些命名,就在两种符号——声音和象形之间交替进行,如汉语拼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汉字的声音命名;而汉字作为声形兼备的符号类型,又是对声音现象的一种命名。这些命名活动,一般说来属于概念的逻辑范畴。但当人们运用这些命名开始交往行为时,词的多义性、模糊性和多变性,必然投射给人们交往的世界以模糊性的内容。对这样的内容,人们既不能规避,也不能做出清晰的逻辑回答,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诉诸诗性思维、诉诸修辞,以修辞的手段表明人们对它的基本印象——哪怕是模糊的印象。这种情形,具体地表现为所谓修辞格,如拟人、拟物、夸张、排比、比喻、比较、对仗、设问、双关、摹状等等。它们使得诗性思维的混沌美、抽象美、价值美具体化、形象化为修辞格下的生动美、具象美和事实美,从而使诗性思维由内在的规定外溢为外在的具体表达。所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夸张,把人面对庐山瀑布、陶情其中、物我两忘的诗性思维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形成想象世界中庐山瀑布银练千尺、恣肆泻流的美好印象。
当然,对修辞的理解,还有在增益于论辩、有助于逻辑推论和批评实践,并增进目的实现意义上所做的理解,即本体视角的理解。常昌富曾就此指出:
“如果我们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修辞这一概念界定在‘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的手段的能力的话,那么,修辞批评的对象主要局限在传统的演讲形式中;如果我们采用新修辞学和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定义,将修辞这一概念界定在运用话语和象征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话,那么,其对象则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现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象征环境,也就是一个修辞环境。”[6]
在如上这段引文中,似乎能够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说前种意义上的修辞,诚然是一种技术手段的话,那么,后种意义上的修辞,已然变成人类的一种本体追求,或者修辞就是精神存在的基本方式,人类的交往行为就是一个修辞本体性问题。这样,人们就开始对修辞做某种本体化的努力。我以为,这种对修辞活动的本体化努力,与卡西尔所言的“人是符号的动物”[7],从而把符号本体化的做法可谓一脉相承。也与存在哲学、诠释学、交往行为理论把人类的语言、理解和解释活动视为人的精神本体性生存的观点具有内在沟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借着主观理解给对象世界命名的一切言语行为活动,归根结底是人运用诗性想象,把自己的主观意欲加诸客观世界或对象世界的活动。虽然在某个环节上,人类的这种命名能够逻辑地、清晰地表达和说明对象世界,但在整体意义上讲,人类对对象理解和命名的冲突、矛盾,人类对对象世界认识的相对、有限等等,都决定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混沌世界之不可避免,也决定了一切命名,归根结底是修辞;一切理解,归根结底是修辞;一切存在(精神现象),归根结底是修辞。这或许正是上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科学理性的强光照应下,被淹没并沉积了许久的修辞学之所以重新焕发生机,并被本体化的缘由所在。
显然,上述两种不同的修辞观对于法律价值预设而言,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前种修辞对法律价值预设而言,可以增加法律价值理解和说服的技术力量;而后种修辞对法律价值预设而言,则决定着人们对法律价值预设的一种态度。因此,在此对两者分别叙述就有必要。
(二)修辞的技术之维与法律价值预设的论证力量
法律价值预设作为法律中主要运用原则所规定的内容,既是人们对对象世界、特别是对人类社会长期观察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人们在诸多观察结果中进行筛选和抉择的结果。以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都明令规定的民主原则为例,尽管在一般理念上讲,民主总是胜于专制的,但只要诉诸经济效益的考量,这种一般的理念会常常被证伪。如苏联曾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为什么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地成长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为何中国并没有普选的民主事实,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推行“党国体制”,但在近三十年来经济异军突起,从一个GDP总量排名世界靠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为何菲律宾、墨西哥等国都实行民主,但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不但停滞不前,反而不进则退?
这样的质问,显然使民主普世性的价值预设和约定,陷入一种模糊不明的状态。对它要做出逻辑的、清晰的说明,当然不是不可能,但只要在人类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民主反而利之所失、专断反而利之所得的具体个例,就必然存在人们对民主价值预设的质疑或不信任。在此情此景下,应对质疑和不信任的手法自然不是“武器的批判”,而只能是“批判的武器”。其中作为技术之维的修辞是充实批判之武器的重要支持力量。
既然法律预设了民主的价值,既然人们要依据法律来构织人间交往行为的秩序,并因之而摈弃人治,实现法治,既然民主的价值预设充分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那么,当民主的实践遇到与上述预设背道而驰、龃龉抵牾的情形时,对上述理念给出修辞性说明,以坚定人们对于民主价值的信念,强化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补救民主价值可能存在的缺陷等,自然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例如,一位论者可以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说明如下的观察结论:虽然专制体制有时能够实现经济上的高效益和高效率,但专制的本质必然使利益大河主要流经国库,最终流入个别人腰包,只有那潺潺小溪才可能润泽公民个人的钱袋。它形象地表明专制即使能带来效益,也不会是对公民普惠的效益,而只能是惠施于个别有权势者的效益。而另一位作者可以借助排比的修辞手法,说明专制体制在价值上劣于民主体制的事实:君不见苏联当年虽飞速前进,但公民生活却每况愈下的事实吗?君不见苏联当年虽经济指标高涨,但政治—社会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的事实吗?君不见苏联当年虽国库殷实,但却因国民经济体系严重失衡,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而带来的灾难吗?君不见苏联当年虽然在经济上一跃而成为世界二、三号角色,但对外穷兵黩武,挥霍纳税人钱财而争取一己霸权的事实吗?上述排比,一气呵成,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不但增加了修辞对于民主的法律价值预设进行论证之力度,而且由此提供了对民主的法律价值预设进一步进行逻辑论证之可能。
技术性修辞作为一种工具,对法律价值预设既可能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究竟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一是要看运用修辞的人在行文言语中针对法律价值预设想说明什么样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主题选择决定着修辞技术对法律价值预设的作用。倘若一位行文语言者的主题就是对法律价值预设进行贬抑,他可以运用修辞更有力地编排法律价值预设本身的种种不当和不足,强化修辞对法律价值预设的非议效果;反之,倘若一位行文语言者的主题就是对法律价值预设进行褒扬,他照例可以运用修辞技术,罗列并声援法律价值预设的种种好处,强化对法律价值预设的赞美、支持效果。
二是即便一位行文语言者选择了修辞技术以肯定法律价值预设的主题,但在字里行间能否妥当地运用修辞技术,是能否取得正面的支持、宣传并弘扬法律价值预设的关键所在。运用修辞技术说明法律价值预设,其实是对它的一种诠释。我们知道,有诠释,就可能有过度诠释[8]。诠释是对对象(文本、事实、思想等)的恰当说明,过度诠释则不但不能恰当说明对象,可能还会掩盖和遮蔽对象。以之为分析范例,作为诠释工具的修辞,当然在运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有修辞,就有过度修辞”的情形。对法律价值预设的说明、宣传、弘扬而言,修辞固然是必要的,但过度修辞可能会弄巧成拙,不但难以支持、回护和圆润人们对法律价值预设的理解,而且还会有损于法律价值预设。在这个意义上讲,行文语言者在回护法律价值预设时,不但要勇于运用修辞,而且要善于运用修辞。
修辞技术对法律价值预设的正面作用,或许主要体现在赞美、修饰、论证、慨叹、憧憬等方面。倘有人这样形容权利和人权:如果说权利是国王头上的王冠,那么,人权则是那王冠上的明珠。显然,这样的修辞技术对法律预设的人权保护价值而言,起着赞美作用。倘有人这样比喻: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它犹如朗朗天空中日行有常、周而不怠的太阳……不难发现,这是对法律正义价值预设的一种修饰。倘有人这样设问:何以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法治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它借助刚性的规则约定,可以尽量地摒弃一人之治的偏见、独断或者优柔寡断。这样的设问修辞,显然对法治这个法律价值预设而言,起着论证作用。至于在具体的修辞技术(修辞格)中,究竟哪些对法律价值预设可以起到赞美作用?哪些对法律价值预设可以起到修饰作用?哪些对法律价值预设可以起到论证作用?这是个需要把具体修辞技术(修辞格)运用到法律价值预设中时,才能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问题。显然,这是需要专文论述的话题。
总之,不论具体的修辞技术给法律价值预设以何种修辞效果,就修辞的技术之维与法律价值预设的具体关系而言,所有修辞技术对法律价值预设,只要运用得当,都会在技术层面强化人们对法律价值预设的认识、认同、恪守和追寻。透过上述论证读者不难看出,修辞技术与法律价值预设之间,有时是直接的、内在的关联,即法律价值预设本身即修辞;也可能是间接的、外在的圆润它的手段,即通过修辞强化对法律价值预设的论证。
(三)修辞的本体之维与法律价值预设的姿态定位
把修辞的本体之维运用到法律价值预设上来,则完全可以说,以符号表达的法律就是修辞,或者法律是一种制度性修辞。可以认为,法律是人类符号的高级形式,是符号的符号,或者是以符号为基础,修饰、加工而成的高级符号。我曾把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根据符号的难易程度分为3类:即行动符号的法律、语言符号的法律和文字符号的法律[9]。行动符号的法律乃是依据习得原则,根据“老辈子怎么做,后人们怎么做”的行为传承而展示其规范性的;语言符号的法律则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通过歌唱训话等方式传达给受众 在我国贵州苗族地区的一些村寨中,至今仍存在着把村落或山寨习惯法唱出来情形。歌唱者在唱诵中往往能通过“表情修辞”、“语气修辞”、“肢体修辞”,而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不容侵犯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有个山寨,笔者曾搜集到翻译为汉语的法律唱词《议榔词》,由唐德海唱诵,唐千武等释译。(参见:谢晖,等.民间法:第八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394.),并进而展示其规范性的。这两种符号形式的法律,都存在于初民社会或文字文明欠发达的地区。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作为文明标志的基本符号就是文字。一方面,人类的立法,就是经由文字符号而加工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系统;另一方面,如果放大规范的视界,完全可以将所有文字符号都纳入规范系统,因为文字既是人类主观世界对对象客观世界的命名,同时也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和约束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文字及其成果,都对人具有规范性,都可以被结构在修辞本体论所展示的境界中。而文字符号的法律,则是在文字符号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专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规则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符号的符号[10]。
任何符号面对浩瀚无垠、变幻多端、复杂多样的对象世界,都只能是近似的模拟,或最多只是仿真,而不可能是对对象世界的全盘复制。所以,文字符号自身就是对人类诗性思维的修辞表达,换而言之,它本身就是修辞,就被结构在修辞体系中。法律作为精致的文字符号,作为文字符号在加工后的行为规范系统,它企图用有限的文字规范,把无限的人们交往行为的内容悉数囊括在它的规制下,这本身就凸显了人类诗性思维的特质。尽管所有法律规范必须模拟人的行为类别而作出,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理应符合逻辑、符合理性思维,但在我看来,这里的理性思维、逻辑论证只能是诗性思维框架下的一种客观化的努力,它不可能取代人类法律的诗性维度,从而也无法取代法律自身作为一种修辞而模拟人类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行为。不但如此,符号及法律符号本身作为修辞,已预示着它被结构在人类精神本体世界,因之,我们应对这种修辞进行本体化的理解。这正是我强调制度修辞的缘由所在。 参见:谢晖《法律制度的修辞之维》,载《第二届全国法律修辞学论坛论文集》(尚未出版)。
可见,由修辞的本体之维投射到法律中时,把法律也结构为一个修辞成果这一结论中,可以进一步讨论它对于法律价值预设的意义。如果说法律在整体意义上,就是一个制度性修辞的话,那么,在法律构成要素的规范部分,应更多地表达规范和行为事实之间的契合,否则,规范对事实的调整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模糊之境,法律欲寻求一般调整的期许就只能落空。倘是这样,还不如一事一议、个别调整好了——既能实现实体公正,又能尽可能地在个别案件中得出个别的规范,实现规范符号世界和交往行为世界的真正契合。
和法律规则相比较,作为法律的另一构成要素,也是体现法律价值预设的一个要素——法律原则与主体交往行为间的具体关系就要疏离的多,给人的基本感觉是这样的规定,似乎和所有交往行为都相关,但又与任何具体的交往行为都不直接相关。从而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和人们具体的交往行为、社会关系之间呈现为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情形,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法律规范的重视,对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的相对忽视。
但作为法律人必须清楚:一般的原则及其价值,对人类交往行为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因其投射幅度和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而具体的规范及其调整,只对某一类交往行为具有投射能力和逻辑效力。当这种理念被树立的时候,事实上意味着人们对于法律价值预设的一种基本态度或者姿态。虽然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在日常实践中不能让人生发出须臾不可或缺的那种迫切感、紧密感,但无论如何,保持对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温情和敬畏,并捍卫法律价值在法律体系中统领全局、居纲守要的地位,是法治社会人们对待法律价值预设的一种基本姿态。
其实这种姿态就内含在对法律的有关修辞本体化的处理中。法律的修辞本体化表明:法律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一般规范体系,不仅是一种文字的组合形式,也是人类作为精神现象的本体存在形式。在修辞意义上,人们籍此可以将人类精神现象界定为符号修辞现象,从而“人是符号的动物”;在规范意义上,人们籍此可以将人类精神现象界定为制度规范现象,从而“人是规范的动物”。“人是规范的动物”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两个有关人类精神本质的命题,我认为事实上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不过前一命题更适合对法律和法治做本体性的说明;而后一命题更适合对人类交往符号——语言、文字、修辞、逻辑等做本体性的说明。对前一命题的论述,参见:谢晖.法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2.这样,修辞的本体之维就把法律、特别是法律的价值预设结构在修辞本体中。既然修辞是人们理解世界、认识世界、行进在世界、并因此被世界所结构的本体规定,那么,被结构在修辞本体之维的法律、特别是法律价值预设也就必然是人类精神本质的构成性因素。对它的遵从,乃是对人类自身精神存在价值的遵从;对它的蔑视,同样也是对人类精神存在价值的蔑视。法律的价值预设与修辞本体的人类理解同在,与人的精神本体存在同源。显然,从修辞本体视角看,遵从法律价值,就是遵从人自身的价值。这样,在修辞本体维度上就赋予给人们一种认识和理解法律价值预设的基本姿态。
三、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性修辞(一)制度性修辞中的法律价值预设
制度性修辞是我对人类制度,特别是作为大传统的正式制度所作的一种修辞处理和概括。这本来是个和诗性思维紧密相关的概念。如果说诗性思维是人类童年时代面对模糊性的世界所禀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继续说,不论人类文明行进到什么阶段,模糊性是永远存在的。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既上九天揽月、也下五洋捉鳖 这一点,或许当下中国公民更能感同身受。最近“神九”和“天宫一号”在万里浩瀚太空中的对接与游弋,蛟龙号潜水器在七千米浩渺海水中的成功下潜和试验,让当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奇思妙想、豪迈追求,已经不是遥远的梦,而庶几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但一方面,人们在深切感受生活世界的规范性、秩序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时候,同时也在深刻地体验现实世界的模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甚至这两种情形,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此情此景,必然导致诗性思维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基因,是人类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永恒思维方式之一。这也说明,诗性思维与主体作为精神存在方式的休戚相关。
但诚如前述,诗性思维的表达手段就是修辞。因为表达手段对人类交往行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失却了表达手段,人的存在就无法展现——因此,修辞手段既被结构在作为精神存在的人本质之中,同时又是令人异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前者说明修辞支配着、结构着作为精神主体的人。人的精神结构中失去修辞的面向,就意味着精神主体本身出现了缺损。修辞是充实精神主体的重要途径,也是精神主体的构成内容。后者说明人类精神的进化,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精神的异化和超越。如今提及异化,我们总是从负面意义——使人不成为人——这个视角去理解。这种理解在政治批判意义上是有效的,但在符号—文化批判意义上是无效的。因为在符号—文化意义上,异化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异化致人成长:异化缺位,也就进化不能。所以,我曾经把异化分为良性异化和恶性异化两种[11]。从人类精神发展的视角看,籍由符号所带来的异化,庶几可作为进化的代名词。
以法律为规范前提的制度作为人们交往行为的符号系统,表面看上去它是外在的,是社会或国家对人的一种外在强加,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结构的一种不当牵绊,因此,庄周在两千多年前,就著文反思这种情形,并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虚无主义”。 《庄子·马蹄》。但在实质上,所有法律总是根据人性制定的,无论是导向法治与民治的法律,还是导向擅断与暴政的法律,都是如此。只是前者面对人性恶的预设,采取了一种疏导人性,并把实在规范和人对规范的天然需求倾向结合起来,才创造了蔚为大观的法治文化。而后者面对人性恶的预设,采取了与人性相疏离的法律规范手段,因此,实在规范与人的利益取向一致,从而也与人的本性无法产生同构的效果,其结果是法律变成非法的工具,而不是依循人性的符号构造内容。
这种情形,其实反映了法律作为修辞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法律作为修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增强理解的效果,放大论证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法律作为修辞也夸大人们的误解,损耗主体交往的效果,缩减人们求证的力量。这样,在把法律视为修辞的时候,如何竭力扩大法律修辞的积极效应,让人们把法律自觉地作为主体交往结构的内在精神因素,就首先是立法者的基本使命,同时也是被结构在法律交往中的每位精神主体——公民的基本使命。否则,再完备无遗的法律,也只能作为外在于人们需要和精神存在本质的方式而被束之高阁,人们宁可在自觉的交往行为中选择一种自发的规范秩序。当代中国法律秩序之不彰,是不是和法律无法被内化进主体的精神世界,并为人们在行为上遵循关联甚密?是不是和法律无法化作人们内心的基本信任,更遑论信仰它息息相关?
如果把所有以规范(法律)为前提的制度统称为制度性修辞的话,那么,可以进一步讲,法律价值预设乃是制度修辞的核心所在。其原因既在于法律价值预设是统领法律全局的制度内容,一切法律问题皆可因价值预设的提纲挈领、统揽全局而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也在于和规则相比,原则在法律中是更抽象、从而也显得略为模糊的内容。这使得对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的解释余地更大、理解向度更多、提供给人们诗性地理解的内容更广,进而提供给人们运用修辞技术手段以描述的可能性也更宏阔。正因如此,如果说法律本身是制度性修辞,那么,法律价值预设就更能彰显制度性修辞的特征。
(二)技术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作为修辞
具体说来,制度修辞在技术意义上是指把一些修辞格运用在立法和制度运行过程中,以圆润制度设计、建立制度运行的理由,强化人们对制度的论证力量。如运用摹状修辞、设问修辞、比喻修辞、对比修辞、排比修辞等手段,让人们对法律有更为真切、形象和丰满的印象。一般说来,修辞不宜运用在立法中,因为立法本身必须以严谨的、逻辑的、明细的语言表达出来。一切立法安排的结果——法律都要具有预测性,即根据法律规定,必然能够预测在未来的交往行为中人们具体行为的一般逻辑后果。如果没有这种必然预期,则意味着立法所致的法律,纯粹是一种浪费。
但在立法中,以原则方式表达出来的价值预设,可以直接表现为某种意义上的修辞,例如前面提到的主权在民、社会正义、人权保障等原则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修辞预设。 对此,笔者在《法治预设与设问修辞》(未刊稿)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但技术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制度这一命题的各个要素中。
我把制度要素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即规范要素、理念要素、主体要素、行为要素和反馈要素。所谓规范要素,在正式制度中就是指国家立法。前面已有交待,它不宜过分诉诸修辞的方式来表达,尽管法律原则及其价值预设本身即可视之为修辞。
制度的理念要素预示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能够契合于法律的一般预设,显然,这是一个把人们复杂的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带入到法律图式的过程。不难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诗性意蕴、张扬修辞风格的过程。这犹如大自然把奔腾的江河,规范在河床和堤岸一般,也犹如大自然把汹涌的大海,规范在海床和海岸一般。要把云谲波诡、变动不居的人类思想规范在制度的逻辑之网和意义框架中,使人们的观念服从于制度规范所透露出的思想,这是文明时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政权形式和宗教教义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它既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必要代价。它可能会形成如秦皇那般“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带来的弊政以及对人的价值之扼杀,也可能会导致只有信仰并服从我们自己的法律,才能真正达致自由之路的理想状态。
但是,不论是倾向于以专断方式推行“我要你文明”、“我要你民主”、“我要你自由”、“我要你幸福”……的思路,还是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推行“你选择了民主”、“你选择了自由”、“你选择了正义”、“你选择了文明”、“你选择了幸福”……的思路,归根结底,都是让人的思想趋于齐一的过程,用墨子的话,是为了反对“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意见过分分歧所带来的种种困顿,而追求思想观念和交往行为之“尚同”的过程。 《墨子·尚同》。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把混乱的思想多元性变形为规范的思想“次多元性”的过程。 这里所讲的“次多元性”,意谓即使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世界不可能完全被一元化。更何况在现代法律中,思想自由还是一项重要的主体权利。故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之类的行为和口号,不过是多此一举。这种情形,可谓之思想的“次多元性”。它是对思想混乱的纠偏,但它不应、也不能消灭思想多元、观念多样和意思自治。显然,这个过程是充满了诗性想象和修辞的活动。在世界各国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教化(不论它是道德教育,还是法律教育;不论它是强制灌输式教育,还是循循善诱式教育;不论它是森严恐怖式教育,还是寓教于乐式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让人们的观念服从于某种观念和规范的大胆修辞过程。这种修辞,聪明的网民们以“洗脑”一词命名之,如果去除这一命名的贬义成分,把它置诸中性意义上,则可谓是对相关行为最妥贴、最形象、最简捷的修辞表达。而在形塑有关法律理念的时候,法律规范固然重要和必要,但由法律原则所预设的法律价值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修辞特质和具有情绪调动性、口号宣示性的文字表达,更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接受。
制度的主体要素预示着在一种法律管辖下的所有主体——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都必须被结构在法律的体系中。这样一来,人反倒成为法律的客体,法律反倒成为宰制所有人的主体。 参见: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461.因之,人这个在哲学上向来被作为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气的存在,反倒自觉地受制于规范的规训和异化。这种情形,可谓人类创生法律、提倡法治的作茧自缚效应。 这一提法,是参照了季卫东在《程序比较论》一文中所提到的程序的“作茧自缚效应”后提出的。进而考察,一切文明、规范和制度世界,对人而言都是一种作茧自缚,故我在前文中这样说:文明、规范和制度的进化,在实质上也是人的异化。(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2):1-46.)自然人暂且不论,法人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因为法人在实质上就是法律对一种外在事实的拟人化处理。通过这种拟人化处理,既没有统一肉身,也没有飞驰灵魂的单位,获得拟制的人格、肌体(场所、机构、人员)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讲,法人制度能较为典型地反映修辞与制度主体间的关系。而法律的价值预设作为制度的精神和灵魂,在法律把主体纳入其麾下,结构在其规范体系的过程中,扮演着更加独特的修辞角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价值预设中所关注的主体,一定是交往关系中的主体,而非离群索居、孑立孤行、自愿逃离人类交往关系的主体。正因如此,法律价值预设就在制度主体要素中更显其要。
制度的行为要素预示着要把形形色色的主体行为,纳入到整齐划一的法律逻辑系统。特别在现代法律中,这点尤为重要。这也是现代法律主要作为形式合理性的管道能够超越并取代历史上不断呈现的实质合理之个别调整模式的缘由所在。尽管把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法律的逻辑体系中,与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契合于法律制度相比,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安排,但同时,它也不无修辞的深刻意蕴。因为毕竟人们交往行为的世界和法律有限的言语体系相比较,乃是一个法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地调整的问题。或者说,当人们寄希望于法律能实现对人们行为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般的调整时,本身就把诗性和修辞代入到制度预设和人们的行为选择中。这其中,在法律价值预设的提纲挈领与人们对法律价值必须遵循的行为归结之间,能更加凸显人的诗性想象和修辞美感——这种修辞美感可以用一两拨千斤来形容,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表述,可以用一言立而天下定来说明……无论如何,把价值预设和价值规范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是种修辞的妙用。
制度的反馈要素预示着对所有的法律运作,必须置于某种检修机制下。这种反馈或检修机制,乃是在前述诸要素——即把人的理念、身份、行为等纳入法律规范规制的前提下,再检修法律的实际运作是否真能把上述事项纳入法律之彀,接受法律的调整和规范。所以,在实质上我更愿意把反馈机制作为法律与事实的再次对接,或者把事实再次装置在法律规范中进行过滤、淘洗并发现和提出问题。这种绵密的制度设计,本身意味着法律和事实对接中必然存在的模糊、错位和种种不足,因此,它也就提供着人们可以诗性想象的空间,也蕴含着人们借助修辞技术来进一步圆润法律运作的空间。就法律价值预设而言,在这里至少充当着宣教法律必须被尊重、法律不能废弛的意思。所谓“执法如山”、“信法为真”的口号和信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排比,昭告了法律价值预设在制度反馈要素中的修辞效果。
(三)本体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作为修辞
在本体意义上,制度修辞则指在把修辞假定为精神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把以规范为前提的制度,特别是以法律为前提的正式制度主体化的过程。诚如前文所言,对交往关系中的每个个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异化,因为它使人必须置诸法律的罗网,被法律所驾驭,成为法律的臣仆。但如果我们能换位思考,可能在这种人被异化,但人又在法律秩序下泰然处之、安然自若、悠然交往的情形中,获得另外的结论:人在本质上是规范的动物。规范的存在决定了人存在的基本精神价值。人的规范本质的沦丧,或许是人性的沦丧。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和结论,与“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以及“人是好利恶害的动物”等有关人性的界定,有着异曲同工的表达效果。
人在本质上是规范的动物这一界定,事实上通过本体性的修辞润饰,把规范及其制度人化,同时把人本身规范化、制度化——没有被结构在制度体系中的人,形同被放逐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只能孑然孤立、形同非人。古代的流放制度之所以成为对罪犯最严重的惩罚之一,就在于让人失去更广泛地交往行为的条件,从而也失去作为规范动物的依凭。 在非正式制度视角,这类制度至今仍然较广泛地存在,特别是在边远的社会。笔者在某省调研时得知,一个习惯上靠寨老解决纠纷的山寨,一例纠纷解决后,其中一位当事人不服而诉诸法院。该县法院曾多次赴村寨调研。最后一次村寨长老给法院下了“埃德美顿书”:如果村寨处理过的事情法院再要处理,以后村寨的所有纠纷就全交由法院处理,村寨不再处理了。法院一听,赶快动员当事人撤诉。当事人也审时度势,怕遭到村寨成员们的嫌弃和疏离,尽快撤了案。即使在城市中心地区,这类情形也依然存在,如罪犯出狱后就常会遇到“正常人”的白眼、歧视、躲避等另种方式的放逐。放逐后的人之所以会更加失落、更加孤独,主要在于他们失去了或被限制了与他人交往行为的条件,或者失去了、削弱了人是规范的动物之事实。可见,说人是规范的动物,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证立。
如果说人在本质上是规范的动物这一判断所表征的是一种有关人的精神存在实质的逻辑判断的话,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是一种修辞。这种修辞就是关于人存在的本质假设。它预示着作为人类交往行为规范的法律,本来派生自人的规范性,从而与人在本质上是规范地存在的动物这一对人的价值—修辞判断是同构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肯认一切法律不外乎人这样的结论。无论一家之法,还是天下之法,都是对人生存和生活之意义世界的规范和规制,更进一层,都是对规范的动物这一人类本性的经验归纳和制度抽象。所以,法律作为修辞和人在本质上是规范的动物这一修辞性判断,可以实现某种意义的互释和通解。
如果说法律作为修辞源于对人是规范存在的动物这一修辞陈述,那么,法律的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和本体性修辞,它既穿透在法律的其他一切规定中,也对法律的功能预设和过程预设等起着价值指导的作用。因之,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在法律制度中具有更独特的意味。法律价值对法律制度的穿透性,取决于法律价值往往是法律的指导思想、原则立场和精神导向。一部法律没有这样的精神价值贯穿其中,就如一位公民丧失精气神一样。
就法律价值预设与法律功能预设的关系而言,它预示着法律功能一旦出现模糊、紊乱和不足,需要法律价值来沟通。众所周知,法律作为制度性修辞,其功能预设并不是有了法律规定,就可以自足地实现的——因为法律肯定会出现预设有误的情形,否则,法官就不会解释法律、创造判例,立法者就不会修改法律、弃旧换新——这导致法律之外的解释者对完善法律而言,可以在实践本体意义上再次证成人是规范地存在的动物这一判断。但是,解释者完善法律不足——意义模糊、意义紊乱和意义欠缺 对在法律方法视角具体完善上述法律不足的机制问题,可参见:谢晖.法律哲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9-76. ——的基本根据,是法律的价值预设。因此,法律的价值预设不但是法律功能预设的价值指导力量,而且也是救济、补助法律功能预设不足的重要凭据。在上面的陈述中,或许能更进一步地说明法律价值预设与法律功能预设间的关系,并进而说明法律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预设必须被同构在本体性的制度修辞中。在这一修辞中,法律价值预设更高屋建瓴地作用于法律功能预设。
至于法律价值预设与法律过程预设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法律和法治本身当作一个程序或过程看待的话,那么,所谓“人在路上”的象征和隐喻,在程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印证和说明。换言之,程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就是对“人在路上”这一本体性、过程性判断的规范说明和逻辑表白。这种论述,已经把程序化的法律代入到人的本质存在中,为“一切皆流”的“在路上”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理由和通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法律的过程预设,就是法律的价值预设,或者至少在两种预设之间出现了叠合。在这里,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本体性修辞和法律价值预设作为修辞——制度修辞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国正在推进的法治,理应首先是一个逻辑体系,但与此同时,无论在立法上、行政上、司法上还是在公民的日常交往实践中,也应该关注诗性、修辞与法治的同构性。特别在法律信仰的形成、人们对法律的自觉皈依视角而言,如果不对法律做这种价值意义上与主体要求的规范同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尤其是中国文化向来被号称是“月亮文化”。关于“月亮文化”的论述,详见:刘成纪,章嘉年.月亮与中国文化[J].东方艺术,1995,(2):8-10.“月亮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关注诗、关注幻想并关注意向飞驰的修辞。这更需要我们研究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法治和吾乡吾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构性。否则,所谓的法治建设,就只能疏离于此邦主体交往的本体精神之外,也无法内化为其本体精神结构的有机内容。显然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思考和探寻法律价值预设和本体性修辞关系时不能忽视的问题。ML
参考文献:
[1] 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55,161,167.
[2]林雪铃.以启发诗性思维为导向的新诗教学设计[J].文传学报,2009,(8) :34-48.
[3] 许苏民.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5.
[4]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62-175.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G]//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6] 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7] 卡西尔.人论[M] .甘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3.
[8]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3-80.
[9] 谢晖.法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9-148.
[10] 谢晖.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
[11] 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468.Poetic, Rhetoric and Anticipatory Value of Law:
Study of Systematic Rhetoric (2)
XIE Hui
(Law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Being a key and pivot element in law, the anticipatory value is of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structure where law is held as a systematic rhetoric theme and decisive analytical basis. The abstractness and dominancy of the value of law renders a spacious space for poetic thinking while poetic thinking may well prearrange the position of legal value in the rhetoric world. No matter it is deemed as technical or ontological rhetoric, poetic thinking will surely play the role of justifying anticipatory value of law as a systematic rhetoric. If law and rule of law per se is an institutional rhetoric, the supposition might be testified by way of employment of anticipatory value of law.
Key Words:poetic thinking; systematic rhetoric; technical rhetoric; ontological rhetoric; anticipatory valu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