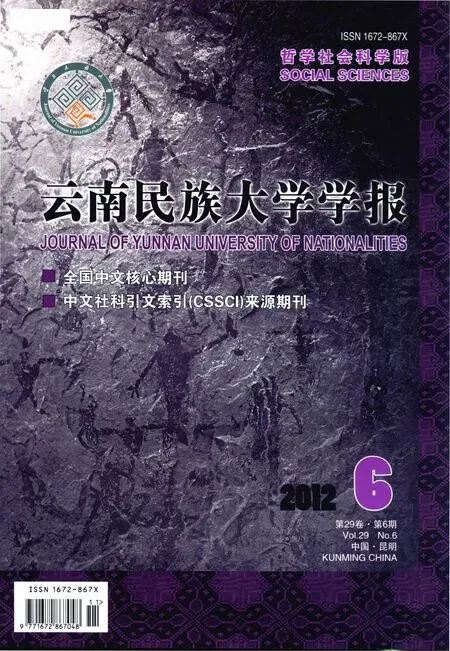旅游经济下的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以云南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为例
何 丽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云南省有25个少数民族,使用20多种语言,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地区,可与俄罗斯号称“语言山”的高加索地区媲美。在各民族的频繁交往与文化碰撞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不断受到冲击,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大理古城与丽江古城是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热点地,纳西族和白族这两个当地主体民族在文化上均广采博纳、兼收并蓄,呈现多元化。在旅游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两个民族其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悄然变化,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使语言关系呈现新的发展。
本文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以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为个案,特别关注大理古城洋人街和丽江古城四方街两个文化旅游热点区域,从新的角度来考察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当地语言接触和文化传承的影响,关注民族语言文化在经济大潮中的命运。
一
大理古城东临洱海,西倚苍山,已有悠久的建造历史。大理古城位于茶马古道的核心位置,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是藏汉民族通商的重要通道,并成为中国同东南亚诸国交流和贸易的门户.也是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通的地区。如今大理古城的贸易核心地理位置被逐渐弱化,旅游业逐步成为大理古城的支柱产业之一。古城内东西走向的护国路就是举世闻名的洋人街。洋人街属大理镇玉洱社区,包括东街和西街,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名叫金策的青年人,在招待所的对面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白族民居建筑“老木屋”里经营了大理第一家西餐厅——吉姆和平西餐厅。随着大理交通条件的改善,招待所和西餐厅所在的这条名叫护国路的小街,鳞次栉比地开起了酒吧、西餐厅和民族特色商品店,重新翻修改建后的大理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宾馆——红山茶宾馆,小街的名字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被各国旅游者熟知的“洋人街”。21世纪初,随着涉外定点接待的限制被取消以及大理市整个旅游大环境的日渐改善,“失宠”了一段时间的洋人街开始复苏,各式各样的酒吧、西餐厅、咖啡馆、旅游工艺品店和庭院式民居客栈从洋人街中心地段日渐向两头延伸,从洋人街“穿腰而过”的博爱路也成了洋人街的延长线,洋人街由原来的“一条”变成了“丁”字形。
丽江古城大研镇兴于元代,鼎盛于明清时期,是汉、藏、白、纳西等民族文化汇集之地,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重镇。至今,古城依然保留明清时期建筑三千余栋,八百余载岁月见证了本土纳西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水乳交融。[1]四方街是丽江古城的代表,位于古城的核心位置,是大约四千余平米的梯形广场,四周均是整齐的店铺,是丽江最具传统的购物集市,历史上也是滇西北地区的集贸和商业中心。从四方街四角延伸出光义街、七一街、五一街,新华街等四大主街道,又从四大主街分出众多街巷,蛛网交错,四通八达,从而形成以四方街为中心、沿街逐层外延的缜密而又开放的格局。丽江古城的旅游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2年玉龙雪山被批准为省级旅游开发区;1994年云南省政府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现场办公会议,提出“发展大理、开发丽江,带动迪庆、启动怒江”的思路;1997年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丽江旅游业获得巨大发展契机。近年来,旅游业从外事接待型转为经济产业型,成为丽江的支柱产业。
二
作为文化旅游热点地区,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自改革开放以来汹涌而入“淘金”的外来人口,不少当地少数民族也逐步加入这股经济大潮中。作为主体聚居民族的白族和纳西族,就在这股大潮中悄然发生着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上的变化。
白族是大理古城的主要聚居民族。[1]根据本世纪初的人口普查统计,80%的白族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的白语被认为较其他地区更为正宗。[2]然而我们对大理古城白族的调查发现,白语已经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至少50%是汉语借词。调查还发现,当地白汉双语状况稳定,白语的使用和功能尚未出现大规模萎缩。这个事实表明,大量借词的使用较好地保持了本地语言的使用活力,是少数民族语言得以保持和延续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使用上,白族内部交流大多以白语为主,在正式场合或与其他民族通话时,首选交际语言是当地汉语方言。[2]大理古城的洋人街由于受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浸染,其语言选择和使用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体现在对英语和普通话的认识和感受更真实,英语和普通话的普及率及认同度更高等方面。尽管当地人普通话水平有限,且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交际对象和话题的使用也十分有限,但是普通话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此外,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同度也体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调查中,选择“送子女去普通话授课学校”的被试比例最高。有一个家庭——白族母亲、汉族父亲和三岁的女儿,家里沟通以当地汉语方言为主,孩子不会说白语。这位母亲对于择校的态度非常明确:学好普通话非常重要,也要学好英语,如果有英语授课的学校,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类学校。
学好英语对于经商至关重要,但大多数人的英语表达仅限于经商用语。改革开放之初,上关沙坪蝴蝶泉附近的集贸市场开始接待外国游客,旅游业的刺激和商品交易的需要使得该地不少生意人积极学习英语。之后,村民追随外国人旅游的足迹逐步转移到洋人街。一位在西街酒吧兼职的服务生直接道出:“我们的普通话讲得都不太标准,是地方普通话和中国英语。”洋人街作为多民族杂相居住的开放地区,成长于此的孩子在语言习得和语言态度上较有特点,通常孩子首先学会的是当地汉语方言。通过访谈一位在古城长大的15岁的女孩得知:女孩父母是白族,在洋人街做生意,女孩成长中首先习得当地汉语方言,直到返回家乡大理才村读小学时依然不会说白语,同学们课余都用白语交流,于是她在和同学的交往中才逐渐掌握了白语。如今女孩的父母依然在洋人街经商,彼此依然用当地汉语方言交流,他们只有回到才村的时候才说白语。女孩表示非常热爱白族文化,很愿意学白语:“小伙伴都是白族人,不说白语就无法融入到同学中”。
和“洋人街”相比,丽江的“四方街”同样热闹繁华,纷至沓来的旅游团队和众多的散客充斥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在丽江商业街调查访谈的难度超出预料,这里商人和小工更加精明,他们可以热情地把你拉到店里,也可以拒绝访谈而冷漠地把你推出去。根据政府统计,大部分店铺由外来人口经营,其中一部分店铺聘请当地小工协助打理。部分古城商铺对当地人格外照顾,纳西语或者丽江话是砍价的筹码。一位纳西小伙子说:“古城人逐渐搬到了城外,住进了楼房,古城不少房屋出租给做生意的外来人口,本地人很少来古城逛街,嫌这里太吵,只有游客才会喜欢这个地方。”不少本地年轻人到这些店铺打工,纳西语只在同族人之间使用,有外人或做生意的时候,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汉语方言为主。一位来自河南的在玉器店打工的小伙子认为:在这里不懂纳西语不要紧,会说普通话一样通行无阻,来这个地方的多数是游客,本地人也很少来这里买东西。
对一位54岁的摩梭大婶的访谈反映出商业街语言使用的一些特点。摩梭人归属纳西族,大婶三年前来到四方街开了一家摩梭围巾织坊,摩梭语只在家里和丈夫、孩子交流时使用,出来做生意主要讲丽江话,还可以讲不太流利的地方普通话,针对国外游客,往往通过比划手势外加计算器来完成交易。大婶反复强调普通话的重要性,对英语的评价很高,认为英语对经商帮助很大,但对于学好英语没有信心。
无论是大理还是丽江,无论在村落还是繁荣的商业街,我们都必须承认,尽管白语和纳西语依然有相当活力,并有一定的通行度,但旅游业带来的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使当地汉语方言逐步代替白语和纳西语成为古城的主要交际工具。年轻一代的父母开始使用汉语教育子女,导致不少白族和纳西族孩子已不再学习白语和纳西语转而学习大理口音的汉话和丽江口音的汉话。父母尤其鼓励孩子学好普通话和英语。我们所调查的中年人群中,多数人能够在家中和工作地点熟练使用民族语与本民族亲属或同事进行交流,但对于和后代是否继续讲本族语,大部分人不能给出肯定答案,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态度不置可否。
作为旅游区,普通话在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被普遍接受并普及,但总体而言当地居普通话程度不很高,而且针对不同的交际对象和话题的使用有限;另一方面,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同程度高,行为倾向明显。在洋人街和四方街两个海外游客集中的旅游区域,英语认同感较高,尤其对经商者而言,英语的重要性和普通话相当,有一定的使用群体。在民族文字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白族文字的命运不如纳西东巴文。建国以后创制的白族文字是以拉丁字母为符号基础的拼音文字,“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58年制订,但未获推行。通过调查访谈得知,只有少数人知道方块白文的存在,对其由来和发展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在“本民族文字的发展前景”一题上,多数人表示“无法回答”,部分回答此题的被试对白文的发展前景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文化传承的影响和旅游经济的刺激使得东巴文获得了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扶持,也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凸现了商业价值。东巴文创制于唐末宋初。东巴文在比较文字学和人类文化史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1997年联合国将丽江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无疑是其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的契机。21世纪初,云南省立法要求对东巴文化采取“有效利用东巴文化学校和传习馆,培养东巴文化传承人并收徒授艺”[3]等保护措施。2002年,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与云南民族大学联合开办了民族文化学院纳西语言文学和东巴文化专业。当地政府还在部分小学开设了东巴文化课,并专门编写出版了东巴文化教材。丽江古城区人大通过议案决定,2003年9月起,古城区内的所有小学一到四年级都要恢复纳西语教学,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两节纳西文化课。[4]
三
对于旅游地区而言,文化旅游商业化在迎合游客体验过程中往往采取“舞台化”表现手法。如火如荼在旅游核心区重复上演的民族风情表演,向游客提供文化快餐服务,出现了旅游的“迪斯尼化”、“麦当劳化”,最终导致“文化符号本身在审美、精神需求方面的逐渐枯竭”,其结果是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化被同化,甚至消失[5]。表现在语言生活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必然会越来越局限于同民族、家庭等小范围使用,失去活力和影响力。就东巴文而言,口传心授的东巴经文随着老东巴的逐一去世而日渐濒危。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东巴文似乎又成为丽江古城的一种时尚,随处可见东巴文点缀的工艺品和饰品,外地年轻人尤有兴趣,把东巴文作为时尚图腾写在明信片上或者墙上,书写时融入时尚气息。这或许能对东巴文化的保护起一些作用。较之于东巴文,白文并未像繁复、神秘的东巴文那样引起商家的关注而加以开发利用。
语言文化的融合和变迁现象深层次上属于无意识表现,构成了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是能将此民族与彼民族区分开来的关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无意识,产生于民族集体历史活动过程,是后天形成、集体共有的。民族文化无意识的形成途径包括“适应”、“文化压抑或文化赞许”、“习惯”等。[6]无论通过哪一种途径,白族和纳西族在语言和文化上无不显示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影响。白语、纳西语中的汉语借词大量出现,反映了少数民族语言在优势语言包围下寻求生存发展的“适应”过程。白族、纳西族自古以来崇尚先进文化,尤其受汉文化影响颇深,谁在族中掌握汉语越好,就被认为有文化的人。这种“文化赞许”或心理认同,使得白族、纳西族在接受汉语词汇时没有过多抵触心理。在访谈中遇到有趣的一例,一些白族不大愿意子女同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通婚。访谈得知白族开放性较好,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热爱读书,他们认为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开放度较小,相对闭塞,因此他们更愿意同开放性好、文化发达的民族通婚。大理和丽江作为文化旅游热点地区,四面八方的海内外游客给该地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文化冲击,因此在语言的选择和认同上也逐渐发生改变。英语作为文化旅游开发后出现的交流工具,让古城的人们从陌生到逐步认识,继而争相接受,甚至期望学习、掌握。
各民族都致力于保护、传承、弘扬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提高语言文字地位,增强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各民族又都渴望冲破民族壁垒,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广纳百川、兼收并蓄。语言影响产生于不同民族文化接触过程中,其影响的速度是缓慢的,各民族语言在相互制约和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甚至基于自身特点发生变化和变异。一般说来,政治经济力量较强、文化水平较高、人口较多的民族的语言容易影响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如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都不同程度受到汉语的影响,一些民族语中出现了大量汉语借词,这不仅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也是该民族语言得以继续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人交往中,为了吸收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积极学习汉语、汉字,而文化旅游的推动,又使得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获得一定范围和相当程度的认同。由此看出,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1]郭品,褚昆雄.丽江古城——一部活的历史[J].云南档案,2004,(2).
[2]何丽.和谐社会之语言和谐:云南省多民族地区语言使用、语言关系与语言态度研究——昆明市沙朗白族乡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
[3]徐昕.世界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面临失真困境[N].安顺日报,2007-10-31(3).
[4]杨宁宁.论旅游与纳西文化的传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4).
[5]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民族研究,2006(2).
[6]杨连有.论民族文化无意识[J].心理学探析,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