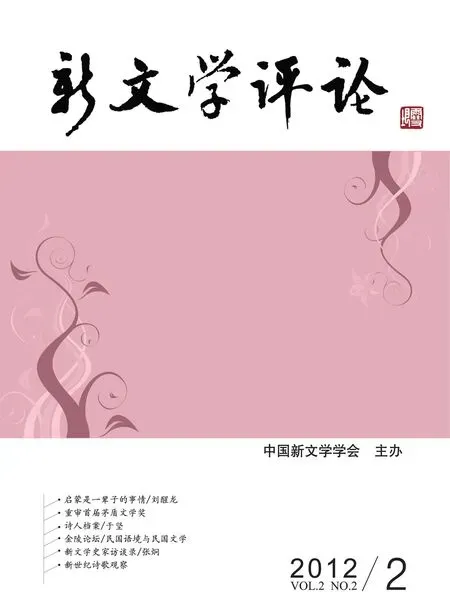“人民艺术家”柯岩和她的“人民文艺”
◆ 卢燕娟
“人民艺术家”柯岩和她的“人民文艺”
◆ 卢燕娟
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对中国现代文化最重要的创造与影响,是开创了“人民文艺”的传统。其核心有两点:其一是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外部颠覆既有的文化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文化权力向劳动人民的整体转移。其二是同时提出了“教育工农兵”的问题,从内部激发和塑造人民主体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五四”首倡“启蒙”,《讲话》继承了这一民族使命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即对鲁迅笔下的阿Q,不再仅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文化中将他们重构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英雄。
在这一传统之下,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人民艺术家,柯岩是其中一位。在《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内,柯岩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她不仅和其他人民艺术家一样,毕生坚持文化权力属于人民,艺术为人民服务,人民艺术应该书写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心声。因此,她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写出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样的作品,激荡起一个时代的共鸣。更重要的是,柯岩尤其深刻地理解,人民要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的主人,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和法律从外部颠覆旧的剥削关系,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更需要人民自身不断成长,不断荡涤自身的污垢,不断和人性的腐化、堕落斗争,在自己对自己的克服和超越中,获得当家作主的能力。人民艺术应该承担塑造人民主体性的使命。因此,她将儿童作为未来的主人,为他们写作;她在“文革”结束后,写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建设者,倡导理想和奉献;她为迷途的少年写《寻找回来的世界》,为迷惘的流浪者写《他乡明月》,为绝望的病人写《癌症≠死亡》。这些作品始终体现着柯岩对人民文艺塑造人民主体性使命的深刻理解。
所以,柯岩的意义,不是在某一种文学流派、语言风格上来说的。柯岩,也包括在人民文艺传统内坚持创作的几代人,他们的意义,最根本内在于《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中。这一传统是崭新的文化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崛起,也是崭新的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量涌现。人民艺术家产生于这一传统中,不仅为之正名,更为之奋斗。因此,理解这样的艺术家,首先要理解《讲话》,理解《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刻意义。
一、外部权力关系的重构和内部主体性的重塑——《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
《讲话》首先呼应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诉求:打破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重构新的权力关系。《讲话》集中阐述了文化权力格局的重构。重构的基础,是将劳动作为人创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本质活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取代了“财富”、“武力”、“知识”,成为文化赋权标准,劳动者随之获得文化权力和合法性。
在此之前,“文化权力”从来与劳动和劳动者无关。中国传统权力规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运作逻辑则是资本决定世界。在这两套权力秩序中,“劳动”都是被动的、受支配的甚至惩罚性的行为:是那些因为没有财富和知识而被划入权力结构“下层”的人们的标记,是他们为了偿赎自己来自血缘、知识、财富等等层面的先天或后天匮乏,所不得不担负的行为。劳动者也同时承担铭刻于“劳动”上的一切后果:身份上的无权者、知识上的愚昧者和道德上的卑贱者。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文化权力的下移,但都没有改变既有文化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排斥劳动和劳动者的实质。
第一次发生在唐宋之际。贵族政治没落,文化变成一种权力身份标识,普通百姓也可以获得。但是,文化只是向个体开放,而不是向一个阶层整体开放。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农民固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读书考试,进入文化精英的阶层。但是,这个农民一旦进入这一阶层之后,他就不再是“农民”,而成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依然被排斥在文化及社会权力之外。农民阶层内部不管出现多少人可以读书做官,都只是个人身份的转移,而不是阶层整体文化状态的改变。“田舍郎”阶层整体上始终与“天子堂”无关。
晚清以降,启蒙知识精英再次将文化权力向民众开放。这是一次更切实也更激进的开放,晏阳初代表的平民教育在今天仍广为人知。然而这一开放仍然以“精英与大众”权力二元结构为前提:知识精英作为教育者,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规定什么知识是有价值的,掌握什么知识的人可以进入现代文明世界。他们要求更多的个体转化为知识精英,不转化为知识精英的大众仍然被作为“麻木的看客”,摒弃于现代文化权力之外。因此,“启蒙”的实际结果仍是个体身份的改变,而不是阶层地位的整体提升。费孝通在考察国民政府体制下的文化教育时发现的情况是:农民的孩子在接受了现代知识教育之后,通常不能找到一种有效手段把他们学到的现代知识运用于家乡,“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即使是离村庄很近的农业学校,也无法让农民得到任何关于生产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想要改良村民种白菜的做法,被农民嘲笑为“种花”,“在学校和农民之间似乎有道无法跨越的鸿沟”①。
《讲话》则将劳动从下等的、惩罚性的活动,颠倒为最高级的人类文化。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要求成为根本问题,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文化向下移入人民整体之中,而不是人民中的个体向上进入文化权力结构中。
《讲话》将“知识”与“文化”区分开:前者仅指读写能力和借此获得的一部分既有知识,这些在旧的利益格局中,往往更容易为占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掌握;后者则是一种能力及与之伴随的权力,在《讲话》所建立的文化权力关系中,主要指劳动能力和劳动者因此获得的权力。在此前的传统中,知识与文化总是被视为一体:占有读写能力,懂得更多书本知识,就意味着占有文化,并可借此获得权力。工农兵群众在读写能力上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在此前一切文化秩序内,都是他们文化身份差别的前提。《讲话》取消了这一前提,“知识”的匮乏不再构成“文化”的障碍。通俗地说,即“不识字”不再必然代表“没文化”。《讲话》形象地表述了这一颠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干净”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他们因为掌握知识,可以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得以保持较为清洁的形象。而劳动则必然使劳动者“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呈现为不太干净的形象。但《讲话》却颠倒过来,将“干净”的评价赋予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干净”,正是因为“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证明了他们的劳动者身份。这不仅仅是对“干净”标准的颠倒,更是对整个文化秩序的颠倒。它意味着:从此以后,是“劳动”、而不再是读写能力、书本知识,成为最高文化赋权标准。拥有劳动能力才意味着占有文化权力,劳动者因此在新的文化秩序中成为主人。在这一新结构中,“田舍郎”个体既没有被转变为地主绅士,也没有转变为启蒙精英,而是依然作为一个劳动阶层,整体变成了文化权力的主人。
《讲话》在从外部赋予人民文化权力的同时,并不表示“人民”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定型僵化的概念。中国现代革命的残酷性,使那些在现实利益格局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首先作为一个共同利益群体被指认出来,他们需要革命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结构赋予他们前从未有过的权力。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此前革命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将这种外部权力的获得,与人民内部的改造、成长和重构结合起来。通过外部权力的获得,激发人民改造自身、成长为新社会主人的愿望和积极性;同时,新社会的最终到来,既不是一个神赐的、弥赛亚式的外部降临,也不是来自圣君贤臣或几个启蒙精英的赏赐或馈赠,而是人民自我改造、成长之后,自己不断牺牲奋斗而得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包含着改变不合理的外部权力结构的任务,也同时包含着改造人民这一更深层任务。人民需要从一个现实中因为被压迫、被剥削而联系起来的客观利益群体,成长为一个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实现劳动的尊严和劳动者的尊严而自觉奋斗、自觉奉献的主人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历史的轨迹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恰恰是启蒙与救亡在残酷的历史中被绑定为同一个问题,二者的共同完成赢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具体到《讲话》来说,它提出“服务工农兵”的同时,又强调“教育工农兵”,这是从内部激发和重塑人民主体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教育分两个层次:一为从知识分子处获得读写能力和相关知识;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中,获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的认识和所承担使命的觉悟。两个层次有着本质区别。知识分子对读写能力和书本知识的普及,仅仅是一种服务性工作。而作为权力的“教育”,只能由现代政党来完成。即,知识分子可以“普及”读写能力,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资格决定何为“提高”以及如何“提高”。这一点构成了《讲话》在教育人民问题上对五四启蒙传统的根本性超越,也只有这个层次的“教育”,才从本质上改变工农兵的自我意识,完成人民主体性的内在觉醒。同时,这一教育也指向知识分子。劳动者掌握知识文化,传统知识分子从劳动中改造世界观,在人民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人民化双向运动中,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大量生成。
二、从人民文艺传统的角度看柯岩的意义
柯岩一生,以其过人的才能和勤奋,可以被称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家、报告文学家、散文家、评论家等等。但她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人民文艺工作者”。这一自我定位不完全出自谦虚,更体现柯岩对自己价值的深刻理解。
首先,柯岩毕生自觉坚持的创作原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艺术来自人民,艺术家是人民的一员。她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抒发他们的内心情感。那些几千年来一直被摒弃在“文化”之外的人民,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从来不为笔墨的历史所关注。只有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讲话》才将他们确立为文艺的新主体。人民的情感、喜好不仅被文艺作品呈现,并且构成文艺的主要内容。艺术家只有深入人民之中,将自己的情感与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艺术,也只有得到人民的认可,才被认为是优秀的经典之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是这一标准之下的经典代表。这首诗歌呼应着一个时代人民的心声。柯岩作为诗人的艺术敏感性,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经典的阐释:这种敏感性不是对某种时尚风潮的追赶,也不是对某种流行观点的人云亦云,而是站在人民中间,感受到他们最真实的情感,最强烈的愿望,并且将这情感和愿望内化为自己的情感和愿望,形诸笔端。诗人放入诗歌中的个人情感是那么真挚又那么强烈,她“找遍整个世界”,一声声呼唤“周总理”;这情感从诗人心中喷涌而出,却又不只属于诗人自己:它同样属于收割谷穗的农民,属于松涛下的伐木工人,属于海浪中的海防战士。正是因为诗人的情感和亿万人民的情感融汇在一起,这情感才获得了巨大的强度和感染力,诗人的一声声呼唤才激荡起高山大地、森林大海的回音——这是时代的回音,也是人民的共鸣;也正因为诗人将这情感内化为自己内心的真挚体验,这情感的表达才如此强烈却又能如此朴素,如此直接却又能如此动人。这首诗歌再一次展现出人民文艺的独特魅力:艺术家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们忠于自我的情感与忠于人民的心声不但不构成矛盾,而且还从中获得艺术的强度和高度,展现出人民文艺独特的“大我”、“大情”之美。
柯岩在1983年重庆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更直接地表达了她对“人民文艺”原则的理解和坚持。当时,艺术为人民服务受到质疑,“表现自我”与“书写人民”被二元对立。针对这些问题,柯岩阐明了文艺经典的选择标准:“只有表达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自己时代声音的歌手才会为人民所拥戴,为后世所记忆。”②面对争论,柯岩表达了对人民的坚定信心:“我们还有人民呢,还有历史呢。而人民和历史都是公正的。”③她回答古往今来的大诗人为什么能不朽的一段话,也可以用来解释在人民文艺传统之内,艺术家对经典认定的标准,和对自己艺术努力方向的要求:“这些大诗人恰恰是因为对他们的祖国、他们的人民的忠贞不渝,才赢得我们的敬重,才唤起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生活,歌唱了当时人民中代表进步力量的思想感情,因诗与他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抒发了他同辈人的喜怒哀乐,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才成为不朽的吧!”④在柯岩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人民的心声”,始终是她坚持去感应、去书写的对象;而人民的肯定,对她来说,始终构成艺术作品评价的最高标准。一言以蔽之:在柯岩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艺术的主人。
柯岩作为人民艺术家,除了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之外,她对人民文艺更深刻也更独特的理解,是艺术要塑造人民,艺术家要承担为人民塑造心灵、为社会塑造良知、为民族塑造未来的使命。
怀抱着这样的使命感,她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儿童诗、儿童剧的创作中。她将儿童作为“小同志”,作为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怀抱着为民族塑造未来的高度责任感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因此,她既高度重视儿童的独特性,努力创作他们感兴趣的、能接受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她强调儿童剧同样是人民艺术的一种,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帮助了建设社会主义并教育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她反对把儿童剧简单化为“狮子老虎,小兔小猫,花卉虫草的世界”,也反对为迁就儿童而文法不通的牙牙学语,而是要将“社会主义艺术的一般要求和儿童观众年龄特点所提出的特殊要求”相结合,为“未来世纪的公民”创造能塑造他们美好心灵的艺术。所以,她主张探索儿童能接受的形式,将革命传统、劳动尊严等等严肃内容,都放入儿童艺术中⑤。正是怀抱着这样的责任感,柯岩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对孩子的爱、了解和尊重,用孩子喜爱的方式、熟悉的语言,把大到热爱祖国、继承革命传统的品质,小到不挑食、礼貌待人的美德,一点点塑造进孩子们的心灵。
作为人民艺术家,柯岩一方面站在人民中间,与他们呼吸相通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转折中,她又绝不迁就人民内部的倒退和堕落。今天,学术界常常在人数众多、非精英非官方的意义上使用“大众”一词,而在柯岩及其所坚持的人民文艺传统内,这个词是与“人民”有着本质区别。“人民”最根本的涵义,是作为劳动者所获得的历史主体性,是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主人意识。当柯岩在人民身上看到道德滑坡、理想丧失、人性腐化的时候,她绝不为了赢得大众的叫好而迁就,而是焕发出更大的使命感,更积极地发挥人民文艺教育人民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柯岩写了一系列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船长》、《追赶太阳的人》、《东方的明珠》、《美的追求者》。她自己说,之所以写这些报告文学,是因为看到“有的青年受了‘四人帮’毒害,什么都不信”,她很“着急”。这种“着急”,正是一个人民艺术家对自己责任的深刻认识。而因为着急,她写这些来自人民中的科学家、船长、农村税收员、刺绣女工、画家,他们的共同点是经历挫折而不放弃理想、遭受打击而不忘记人民。从这一系列报告文学中,可以看出柯岩努力的,是要为时代寻找向上的力量,为社会寻找美的形象,承担艺术家为人民塑造美好心灵的使命。
在这一视角下,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成为又一经典。这是柯岩的第一部小说,她自己说过写这部小说的动机:“青少年犯罪是世界性问题。不夸张地说,这写的是世界性的题材。通过对犯罪少年的中国式的挽救,我要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社会的本质。”⑥那么,柯岩对这一世界性问题作出的中国式回答是什么呢?小说开头呈现出来的,是一群病态、畸形的少年。这群少年绝不可爱:他们外形或凶蛮或匪气,自认为美丽的宋晓丽,在作者和教师们的眼中,也只觉得妖艳浅薄,并不能引起审美上的愉悦。他们的行为,野蛮、无知、麻木而愚昧。如果在启蒙文学传统下,他们只能是被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群。可是,作者和作者笔下教师们,却毫不保留、毫不虚伪地爱着这群少年。老师不是基督徒,没有上帝爱一切人的宗教信仰,这种爱从哪里来?为什么发生?小说通过白小远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光明美好的社会,不是那么容易到来的。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我们、校长、老师以及一切正直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都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代。”⑦这是小说中国式回答的第一个层面:他们爱的,不是这群少年身上呈现出来的堕落和麻木,而是这群堕落麻木的少年同样是祖国未来的公民,他们爱的,是自己民族的未来,是人民事业的明天。所以,小说将那些少年比喻为感染了病虫害的花朵,愤怒地谴责那些让他们感染病虫害的人和事,而正直的人们则不嫌弃这些污点,用自己全部的爱来打扫掉这些污点,为的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一个干净的明天。这种爱和恨,都因为深深植根于祖国人民中而显得博大坚定,也因为关联着人民的命运而显得深沉厚重。
这种爱充盈满整部小说,它使冷酷的少年冰河解冻,使扭曲的人性枯木逢春。但这种奇迹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转变了的谢悦回答外国参观者关于中国工读学校和国外感化院的差别问题时说:“我们靠的是集体、信念、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另一个少年小建国补充说:“还有——明天的快乐。”⑧这是小说中国式回答的第二个层面:这种爱不是西方宗教感化,不来自上帝,沾染了污点的少年不能通过把自己的罪放在自己以外的“天父”身上,而获得自身的净化。他们荡涤自身的污垢、重塑自己的灵魂,乃是在集体中获得信念和希望,这是一个从温暖的社会之爱中自我复苏、自我拯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的,不是以宗教忏悔的方式完成的灵魂拷问,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学校、社会的鼓励、引导也包括批评、监督下,重新培养学习、劳动的习惯,在学习和劳动中创造价值、收获尊严。小说描写工读学校的学生们,在为自己的校办工厂劳动时所焕发出来的热情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而小说更提出了这样的构想:在工读学校之外,再挂一块职业学校的牌子。让学生们从工读学校进来,从职业学校毕业。也就是说,作为有污点的少年进来,而作为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毕业。这一构想深刻揭示了:这群少年灵魂的得救,在于今天来自人民的爱,也在于明天他们将要为人民奉献的劳动,这种劳动向他们许诺一个有价值的、充满尊严感的未来。

注释:
①费孝通:《中国绅士》,第7章“农村社区的社会腐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②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李泱编:《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③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李泱编:《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④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李泱编:《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⑤此处引用观点参见柯岩《试谈儿童剧》,李泱编:《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72~90页。
⑥高洪波:《自幼诗心如烈火——柯岩访问记》,李泱编:《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版,第 48页。
⑦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⑧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