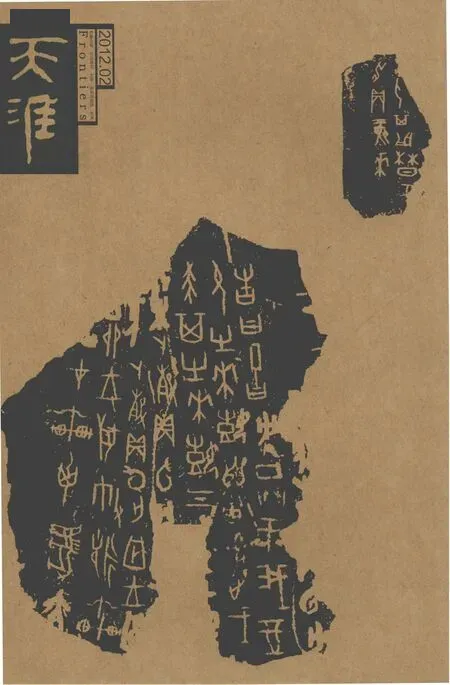风流事
周书浩
自从建了林场,冷冷清清的沙坝子就热闹了。
沙坝子坐落在佛山与神门山之间。两山呈“V”形对峙,沙坝子被夹在山底。一条不宽不窄的河从谷底曲折流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流沙淤积起来,形成了一个扇形的冲积小坝,沙坝子由此得名。早些年,住在两边山上的农户,嫌山高路陡,生产、交通不方便,便举家搬迁到沙坝子修房造屋。待沙坝子上有了七八户人家后,居住在山上的农户便陆续迁到山下,在沙坝子上定居。沙坝子上的住户便日渐有了规模,达到二、三十户人家时,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乡场。到现在,往沙坝子迁居的住户仍有增无减。
沙坝子山清水秀,男人长得壮实、健康,女人生得漂亮、体面。当地人说得益于神门山的荫庇。神门山的神门洞是天生的一个仙人洞。居高临下,俯视着沙坝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神门洞都像一个巨大的女人生殖器,扩张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沙坝子的人,世世代代都是神门吸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孕育的、繁衍的。生长在沙坝子的人,是神门赐予的自然美,原始、朴实,有着动物般的一股野性。
有了林场,沙坝子就多了百多号林场工人,沙坝子的人口就骤然增加,自然,沙坝子也就多了人气,充满生机。
白天,林场工人在山上干活,晚上,回到林场。晚饭后,工人们三三两两到沙坝子赶夜场。沙坝子土著的居民精灵得很:开茶铺、设牌局;摆食店,卖白酒、吃食;开小卖部,经营日用小百货,林场工人的腰包鬼使神差被沙坝子的小商贩洗劫一空。还有棋高一着、更厉害的整钱方法:沙坝子一些见钱眼开、不正经的女人靠色相把林场一些坚持不住原则的单身男人哄到床上,三下五除二,那些男人的钱包便瘪了下去。此等快活的事,男人也无怨无悔。所以,每日一到下班,林场的男职工就往各自相好的家里钻;没有相好的,就下酒馆喝酒或到茶铺打牌,猜拳行令,通宵达旦,乐此不疲,白天的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场工人大多是外地招工来的。他们见识多,眼界宽,善哄人。几年下来,沙坝子的女人大多被他们中的单身男人哄成了自己的老婆,剩下的就是一些年龄大的、长得有点丑的老姑娘和寡妇。饥不择食者见再不下手就无机会了,也纷纷出手,想方设法把她们之中的某一个搞成自己的老婆。这种择偶,并非林场男工人的一厢情愿,沙坝子的婆娘女子其实心里也春心萌动,心向往之:她们也恨不得找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工人过日子。在沙坝子,婆娘女子能找一个国家工人做男客,是祖宗八辈的福,体面得很、荣耀得很。
林场工人的到来,如一股新鲜的风吹进了封闭的沙坝子。沙坝子风气大变,沙坝子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早先,传统、守旧的沙坝子人刀耕火种、打猎捕鱼为生。有了林场,沙坝子的居民便开始从事贸易,林场工人是他们长期、稳定的消费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林场工人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沙坝子人也认可这一点,并且从内心感激林场,感激林场工人。如果说沙坝子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得益于林场工人,那么沙坝子居民风习观念的变化、思想的开放又从何时开始的呢?答案是明白的,显然也是有了林场和工人以后。以前,沙坝子的女子见到家里来了生人,说话都脸红,绝大多数基本上不说话、不打招呼,怕羞;就是性格稍为活泼一些、开朗一些的女子,最多也是三天说九句不痛不痒的话,算是出于礼节。那些妇女,更是不敢在公开场合或单独一个人的情况下与陌生男人说话,怕别人说闲话,招惹是非。自从有了林场后,自从街上有了来来往往的林场工人,自从林场工人先后一个一个把沙坝子的婆娘女子变成各自的老婆后,沙坝子的人就与林场工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人际关系交错,林场工人与沙坝子居民不是亲便是戚,瓜瓜葛葛,纠缠在一起,既有说得清道得明的关系,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大家彼此都是熟识的,知根知底的,没有了戒备、防御之心。
现在,沙坝子的婆娘开放得很。男人女人反正就那么回事,怕什么羞、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沙坝子的女人们集体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沙坝子的女人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引诱男人上床外,公开场合,沙坝子的女人大多敢在众目睽睽下坐在林场某个男人的膝盖或大腿上,打情骂俏或者撒娇。男人在这种野蛮行为的刺激和鼓励下,也敢象征性地隔着一层衣裤,浮光掠影地摸一摸女人的乳房或掐一下肥肥的大腿。这样的小动作往往总是在周围野兽般的浪笑声中转瞬结束,有逢场作戏似的表演性质,并不十分认真。沙坝子许多女人就坐过林场场长的大腿和膝盖。因此,场长也就顺水推舟摸过沙坝子许多女人的乳房和掐过许多女人的大腿——当然,是隔靴搔痒。这些女人的男客在场或不在场,并不计较。因为,这打情骂俏打得自然骂得随便,游戏似的,不是动真格,尽管是动真格的前提和预习。
沙坝子两边均是宜林荒山,山高坡陡,人迹罕至。林场对工人们的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男人在山上伐木,将参天大树砍倒,然后通过山上的“溜槽”,把原木放到山腰,载重汽车通过简易便道行至山腰,将原木一车一车运回林场的木材加工厂,要么成方成方地运出沙坝子,支援祖国建设;要么就地解成木板、木条,或制成成品卖出去。女人们在伐木的地方或没有树木的地方打窝,栽植从外地苗圃运来的树苗。树苗有杉树、柏树、松树,后续工作就是砍、抚、育。砍,即用长柄弯刀砍去地面的荆棘、杂草,不让它们荒芜了新栽的树苗;抚与育,就是精心照管树苗,包括浇水、松土、治虫等繁琐工作。她们要让一片一片再生林快速成材。
相对于男工人的工作,女工人的工作要轻松一些。全体工人每天一大早上工,由于上山的路途就耗费了时间,中午一般都不下山,在山上吃一些自带的便饭,到天黑才下山。在山上劳累一天,无论是男工人还是女工人,体力再好,下山回到林场都已是精疲力竭,都是早早吃了晚饭,带着浑身疲劳和腰酸腿疼上床睡觉。在沙坝子街上喝酒、打扑克、游手好闲的都是一些好耍的工人和林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这些人是:木材加工厂的工人、开汽车的司机、后勤人员、林场正副场长、会计、出纳等。他们有的是时间,特别是像林场的管理人员,他们夜里耍久了,第二天早上还可以睡懒觉。其他工人就没这个权力了。
与场长经常打牌的是副场长、林场会计和出纳。林场的会计是县城户口,当过几年知青,招工被分配到沙坝子林场。一到林场,他也是个普通工人,在山上伐木。他老婆也是城里人,长得细皮嫩肉,文文静静,平时不爱说话,见到人就像一头温柔的母鹿见到猎人一样,躲躲闪闪,有些惊慌失措。会计与她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当知青的第三年结了婚。婚后,她也被招工成了林场工人,随丈夫来到沙坝子林场。会计对林场的工人说:“她就那德性,念书时性格就内向。大家不要见外。”她在人面前虽过于拘泥、矜持,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温和、善良、敦厚,良家妇女的形象,干起活来也很卖力,不亚于林场任何一个女工人,场长曾两次评她为林场的“三八红旗手”,后来本可以继续年年评下去,场长却不评了,不晓得是啥原因。
林场缺少能写会算的人。会计是高中生,在山上干了两年活,场长就提携他当会计。平时,场长总当着会计的面夸奖会计的老婆年轻、体面、能干,会计的耳朵都听起老茧了,也没有听出个弦外之音,倒是听得副场长和出纳都嫉妒了。他们四人,没事就打扑克,玩一种“四人转”的游戏。开初,谁输了,谁就钻牌桌子,要不,脸上贴上纸条,用火柴点燃,俗称“烧胡子”,以示惩罚;后来,场长说要放点“血”更来劲,便提议赌钱。场长说赌钱,副场长、出纳、会计谁还敢说不?日后,一上牌桌赌钱便自然而然约定俗成,成了规矩。好在赌注不大,输了,一番输一毛钱;赢了,一番也就三毛钱,输输赢赢,有输有赢,就是玩一个通宵,手气好的话,也就是输赢三四元钱的事。大家并不在乎、计较,贵在参与,贵在牌桌上的气氛,贵在与场长之间的和谐,贵在打发掉林场一年四季枯燥无聊的漫漫长夜。
白天四人一般都不打牌。白天,场长打牌,影响不好。县林业局的领导知道了,场长要挨整,说严重点,要写检讨甚至撤职。晚上打牌,八小时之外娱乐一下,不说林业局领导,就是县长和中央都管不了。这一点,场长心里清明得很。白天,四人各干其事。副场长督察自己分管的工作,出纳、会计清点检查场里的账目,百十号人的工资、场里的各项收入等都丝毫马虎不得。场长先是在场里转一转,看看各个角落里特别是木材加工厂有没有火灾隐患,有没有工人在解木材卸木板时抽叶子烟。要是有人抽叶子烟,场长便上前训人:“日你娘,想一把火把场子烧光吗?”抽叶子烟的人便把烟灭了。场长便命令抽烟的人吐一泡口水在熄灭的烟头上,然后再用一只脚狠狠地踩烟头,直到地上留下一个脚板印、烟头被踩瘪才完事。有时,那烟头欲灭不灭,抽烟的人一泡口水浇下去,浇不准,场长便命令他吐第二泡口水,口水滴在烟头上,发出“咝”的一声响,烟头便不再冒烟,灭了。检查完木材加工厂,场长背着手,又去伙食团,看厨师炖砣子肉没有。场里百十号工人,工人在场里开垦了菜地,养了猪,自给自足。要是没有炖砣子肉,场长就会反复地对厨师说:“狗日的,挠肠寡肚,心里慌得很!”如果炖了砣子肉,厨师就说:“炖了,炖了。场长,今天的坨子肉四指宽的膘,肥得很!”场长就会接应道:“好!我就喜欢吃肥的。”要是没有炖砣子肉,厨师就会赔着笑脸说给他炒麂子肉吃、野兔子肉吃。佛山、神门山上的野物多得很。黑熊、野猪有时还出来伤人。出于自卫,林场工人自制了火枪和捕猎设备,没有打着它们,有时便附带地打一些麂子、野兔什么的带下山交到伙食团。
有时,场长心血来潮,也和女工人们一道上山砍抚育。男工人们不解,场长解释说:“伐木的体力活我干不了,总不至于轻松活也不干吧。当领导就要做个表率。”场长砍抚育总是和会计的老婆在一起。场长总是有话无话地关心会计老婆,说怎么握刀柄才不至于把手心打起血泡,脚下打一个稻草结,防滑,才不至于摔倒。会计的老婆一门心思放在干活上,开初,还认为是关心,后来,听的次数多了,便当成废话。因为她善使刀,手心从未打起过血泡;总是小心,从未滑倒摔过跤,只把场长的话当耳边风。到了夏天,场长到山上砍抚育的次数越发频繁了。其实,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场长砍抚育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是什么砍抚育。他总在会计老婆的身后、左右转,眼睛大多盯着会计的老婆,看她或者说欣赏她砍抚育的动作。夏天,女工人穿得单薄,身体的曲线起起伏伏,形成这个季节一道迷人的风景。会计老婆在坡坎上劳动,屁股随着劳动的节奏周期性摇摆。场长选择坡坎下的一个最佳位置,从下往上看,会计老婆的两个乳房在弯曲的身体的压迫下,左冲右突,如同两只活蹦乱跳的野兔子。场长看得心醉神迷,心旌摇荡。有时,会计的老婆一挥手使刀,腋下的腋毛便暴露出来,黑黑的,在阳光下分外醒目。还有,会计老婆的腿肚子,白白的,上面隐藏着几根暗青色的血管,一使劲,腿上的血管便微微凸起一下……会计老婆知道场长在注视她,她本来就有些矜持、害羞,便有些恼怒,但又不好发作,脸红红的,心慌意乱,快步换到另一个坡坎上劳动,场长就有些扫兴,没趣地下山。
晚上,会计老婆把白天在山上场长色迷迷地注视她的事给会计说了,会计说:“无中生有,疑神疑鬼。人家是场长,别多心了。”会计老婆说:“场长的一双眼睛看人时就像一双狼眼。我总觉得要出事。他没安什么好心。”会计安慰老婆说:“人家是场长,看得上你吗?”会计老婆反驳会计:“场长就喜欢女人。我听说,沙坝子好多女人都被他搞过。”会计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左右,捂住她的嘴,小声道:“莫乱说,捉奸要捉双,重要的是证据。别听人瞎说。”会计老婆说:“我总觉得场长砍抚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打女工人的主意。”会计老婆这么一说,会计不开腔了。老婆的话不是全无道理,这使他联想起打牌时场长常夸自己的老婆年轻、体面、能干的事。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后,以后就被其他女工代替了呢?林场的高中生多的是,场长为什么要提携自己当会计呢?场长为什么总喜欢与场里和街上的女人打得火热呢?想起这些,会计便隐隐地有了一种本能的担忧。但他在老婆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早早地吹灭煤油灯,上床睡觉。场长这时在屋外敲门了,会计扯故说头痛得很。场长在外面骂:“日妈的你不来,不是把牌场合拆散了?”会计装着病腔说:“场长,龟孙子哄你,我浑身无力,起不来。”场长在门外骂骂咧咧,临走时扔下一句:“要把身体当身体,莫把那事当成干饭吃。”会计明白场长说的“那事”是哪事,看来,场长确实是一肚子鬼主意。
老婆一上床就睡得一塌糊涂。听着她急促而轻微的鼾声,会计动了恻隐之心,她确实太劳累了。那砍抚育是女人干的活吗?会计只恨她命不好。想起自己前些年在山上伐木,一回家,晚上还不是睡得像一头死猪。能够当上林场的会计,平时与场长吃香喝辣,不多亏了场长吗?想起这些,会计对场长又陡然生出感激之情。目前,场长即或在打自己老婆的主意,只要自己和老婆多个心眼,提防着,也没什么。但是,万一场长公报私仇,不要自己当会计,自己岂不是又要上山伐木?那才叫人笑话呢。
会计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早饭,场长看见会计就问:“身体好了吗?”“好了。昨夜我焐了一身汗,没事了。”会计答道。“安逸!焐得安逸!”场长心猿意马地说:“你一个人头痛,害得我们三个人都没事做。下不为例。”“奉陪到底。”会计巴结着说。
春天来了。佛山、神门山上的再生林经过林场工人的精心培育、管护,都齐刷刷一片一片长成林了。初生的树叶泛出毛茸茸的银白色,远远望去,山上像盖了一层霜。那“霜”就要一天天地由银白色变成暗绿色直到深青色直到枝繁叶茂直到变黄直到憔悴直到凋零直到叶落归根,直到又一个春天来到沙坝子。那时,那些树的年轮又增加了一圈,树身又长高了一截。就像沙坝子人的生活一样,一切变化都是悄无声息的、自然而然的,也平平淡淡的。
一天傍晚,会计站在门前等场长、副场长和出纳到会议室打牌,这是事先约好了的。到林场会议室,场长、副场长、出纳都要从自己的住处经过,他在此等候他们三人。这之前,会计在灶上给老婆热好了洗脸水、洗脚水,把饭焖在锅里。因为劳累,老婆回了家,啥都不想做,吃了饭,就要洗脸洗脚,早早上床睡觉,第二天还得早早起床上山砍抚育呢。
会计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场长、副场长、出纳还未来。会计站在门口,朝神门山上望去,看砍抚育的女工人们下山没有。该是收工的时候了,有人仿佛在向山下走。会计企图从收工的人群中发现自己的老婆。可是太远了,看不真切,只是隐隐约约地发现有人在移动。落日从佛山顶上斜照到对面的神门山顶。天空云彩斑斓,变幻莫测,佛山、神门山落日光顾不到的地方,暮色弥漫,阴气沉沉,如同人心里挥之不去的忧郁。沙坝子的炊烟升起来了,它们顽强地向上生长,风一吹,有的曲扭,有的逸散了,最后无影无踪。
又一个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临。
场长、副场长、出纳、会计四个人玩的仍是“四轮转”。这“四轮转”的玩法是,分北、东、南、西四个方位,四人玩四番牌后,从北开始,三人开始玩牌,一人就在一边闲着,轮流进行。玩牌的人叫“上庄”,暂时三番牌不玩的,叫“下庄”。场长自然是坐靠北的座位。副场长靠东、出纳靠南、会计靠西。玩四番后,场长、副场长、出纳“上庄”,会计“下庄”,在一边闲着观看。轮到会计“上庄”场长“下庄”时,时间已是夜里九点多。场长吩咐把桌子上两盏煤油灯的灯芯拔长,让灯光明亮一些,今晚兴致高,要“战斗”通宵,说完,就要上厕所,说吃了伙食团放久了的野兔子肉,拉肚子。
场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正值会计“下庄”。场长说:“伙食团应该整顿了。再把放久了的野物肉弄来吃,就把厨师换了。”
到了深夜十一点,场长开始打呵欠。他看了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无精打采地说:“时间不早了,不玩了。”收场了,各自清理战利品,场长输了三元钱,副场长和出纳持平,会计赢了三元钱。
到了家门口,会计与同行的场长等三人打了招呼便径直推门进屋。会计夜里打牌,老婆不知他啥时回家,一般都不闩门。原因是自己懒得起床开门。会计就对她说,他去打牌,门就掩上,不闩,免得她起床开门,惊扰了瞌睡。会计进屋,灯也来不及点,脱了鞋就上了床。春回大地,草木发芽,动物与人都到了发情期。昨天夜里,屋外不知是谁家的猫“叫春”,叫得人心里痒痒的。会计触类旁通,便想起该与老婆温存了,她已睡了一觉,体力也许得到了恢复,疲劳应该说也有所缓解。善解人意的会计轻车熟路爬到老婆身上,正要进入,老婆睡眼朦胧,将他推开:“你行啊!刚才来了,又来?你吃了啥药?”会计莫名其妙,说:“才打完牌,刚回来。好久没有亲热了,我想你!”老婆一本正经地说:“当干饭吃吗?你已来过一盘了,还要来二盘?”会计说:“我还没来。”老婆大声说:“你不要脸,你刚才来的时候那么凶、那么狠,你快活了,又去打牌,我想不让你去,又怕把场长得罪了,就让你去了。”会计急了:“我没来,我真的没来!刚才是谁?你说!”老婆大声说:“你不要脸,你耍赖!”会计不说话了,瘫在床头,不动,如坠深渊。屋子里静了下来,空气凝固了一般,大团大团的夜色在室内钢铁一般不能融化。会计觉得这个夜晚比任何一个夜晚更黑、更暗。他想摸到火柴点燃床头的煤油灯,手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久,也未摸到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