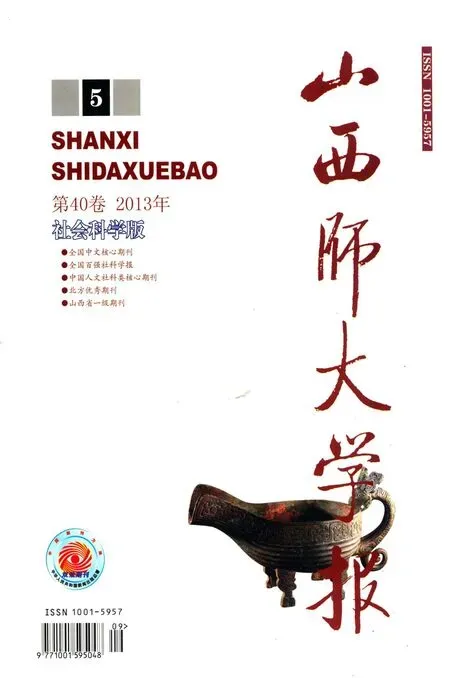中国民间狂欢文化溯源
骆 凡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狂欢一词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并不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狂欢文化的缺失,稍加识别,我们便可发现许多虽不以狂欢名之却深具狂欢精神的文献记录,文字中承载着的巨大热情让人感同身受。《礼记·郊特牲》中关于“蜡祭”的描述可视作最早记载中国古代狂欢生活的文字:“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146—147蜡祭是由天子主持的全民性大祭祀,以此感恩所有自然神的赐予。在这种场合下,上至天子诸侯,下至乡野村夫,中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有序生活,进入一个非常态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一反常态,我们可从这段话见出一二:“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238那么,这特殊的一天中有哪些内容呢?首先,有“观戏”之乐。苏轼认为:“‘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2]38苏轼之意即,蜡祭中尸乃由人扮演,类似于演戏。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的《补说》部分更是从蜡之对象尸、乐歌、舞踏,从狂欢证戏礼等诸多方面详细剖析考辨蜡祭之全部可能之细节以及与后世戏剧之关联。[3]据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蜡祭情形,整个祭祀包含着戏之因子。其二,有狂饮之欢。郑玄在为“一国之人皆若狂”作注时道:“蜡也者,索也。国索鬼神而祭祀,则党正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矣。” “蜡之祭,大饮烝,劳农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穑,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燕乐,是君之恩泽。”[4]1675蜡祭是庆祝丰收的典礼,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国家,广大民众长年劳作于土地之上,秉天时而作,生活平稳而单调,待到蜡祭,人们告别劳作的繁累,一切清规戒律都被暂时搁置一旁,尽情欢娱,达到了一种全身心放松的自由嬉戏状态。任半塘先生论及此处谈到:“孔子教之,所言虽仅及张弛协调、文武之道而已,而暗中则示礼教之藩蓠亦不妨及时一破,‘礼之用,和为贵’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泽’本意谓国人终年在礼教之缠缚中,实在太苦!蜡节狂欢,略可解除,才一日之暂耳。是年张而日弛,年守而日狂也,何过之有?”[3]1234可见,将“蜡祭”视作先民的“狂欢节”实不为过。[5]
又有《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6]733上古的桑林,是统治者祈雨之地,具有宗教的意义,人们采用交感巫术的形式,允许男女在桑林自由交媾野合,以影响上天布云施雨,并致孕育果实。这一天男女聚会,狂歌醉舞,放浪情爱,游欢作乐。《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即上文所说“桑林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7]105,这些被后世说成是殷纣荒淫,实际上表明了社会上层与百姓共同参加娱神活动的上古遗风。[8]34—35性爱的自由开放本身就颇有狂欢意味。帕特里奇写就的《狂欢史》中的狂欢就是专指这类宣泄性的纵欲行为,尤其是那种与性冲动有联系的群体性纵欲行为,并认为“这类狂欢对每个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9]1。帕特里奇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性本能与人欲的冲动从呱呱坠地的婴儿身上就有体现,但人类文明的规约使得这股冲动不能以社会允许的方式得到直接释放。所以人就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身体内既承载着文明属性也有着动物本性,人通过节制动物本性而使两者相协调,但这并不能解决不断增加的压力。于是,各式各样的紧张状态就导致了一种释放,即狂欢。然此类狂欢发生在礼制等级森严、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其冲击力可想而知,无怪乎孔子等圣人虽知是上古遗俗,但都“不欲观之矣”[10]26。故而,大规模的开放自由的性爱行为虽极具狂欢性质,但这样的行为随着文明的演进以及道德礼制的加强固化已经很难以社会允许的方式留存,由此也找到了后世的节庆欢会中两性交往相对自由的源头。

至唐代,金吾开禁的敕令使元宵节完全沉浸在了狂欢的氛围中,上元夜踏歌、观舞、观灯,官民同乐,彻夜狂欢不眠,除了打破平日的刻板生活之外,还打破了白天与黑夜的森严分界。先天二年(713年)上元节一连三夜,太上皇睿宗、皇上玄宗在安福门外和东宫延喜门外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这时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并妙选长安、万年县少女、少妇乃至侍婢、妓女千余人,其穿戴打扮每人要花三百贯到万钱不等,让她们在灯轮下踏歌,三日方罢,观乐至极。[14]69崔液的《上元六首》再现了这一壮观景象:“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15]183除了这些官方、半官方的节庆活动,由先秦蜡祭发展而来的民间迎神赛社活动也依然催生着民众的欢乐情绪。如汉代《淮南子·精神训》所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16]541《盐铁论·崇礼》也有这样的记载:“今富者祈狱,座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17]437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于东汉传入的佛教在中国民间狂欢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六朝时期中原佛寺兴盛,僧人从印度学来演奏梵乐的伎能,并逐渐融入土著的百戏内容,如景明寺内“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18]99,僧人们在设斋行像时进行表演,用以吸引人众。寺中设斋是经常性的仪式,而“行像”则是每一年度的大礼。《洛阳伽蓝记》记载:“长秋寺四月四日,此像长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火吐刀,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18]36—37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每年释迦牟尼诞生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出行时,佛像有时多达千余尊,以避邪、狮子等兽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伴以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且由宗教性发展为全民性,由酬神活动向文化娱乐、商业活动方面发展,逐渐世俗化。寺庙的大量兴建也为民间狂欢聚会提供了宽阔、固定的场地,唐代长安之慈恩寺、青龙寺、保国寺,宋之相国寺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民众娱乐欢庆之所。
至宋代,由于城市的发展、政治控制的相对松弛、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懈,民众生活的自由度有了较大的增加,民间文化的发展也有了很好的基础。民间节庆欢会也由此达到空前繁荣,娱乐色彩更加浓重。除元宵节、腊八、除夕等原本狂欢氛围就十分浓厚的节日,连传统中较为肃穆的节庆也被感染。宋代以前的元旦,“除鬼驱邪、禳灾避瘟”为其主要内容,至宋则已为饮宴游乐所代替,“细民男女亦皆新衣,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19]1;宋代以前的寒食习俗禁火,上坟祭扫,至宋禁火习俗趋于淘汰,与清明节融合,成为人们“寻芳讨胜,极意纵游的踏青之日”,大家“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锣鼓喧天”,“游手末技为尤盛也”。[20]41在这些丰富多彩的节日里,民众们倾城而出。在欢庆的人群中,不仅有各种美食巧玩供应,更重要的是还有各种名目的表演混迹其中,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至节(元夕)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上千百队。……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担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萧鼓振作,耳目不暇给”。[20]3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宗教祭祀色彩的淡化,包括百戏在内的各种表演在民间欢会中呈现出越来越显要的位置,戏曲杂剧、说书弹唱等逐渐成为节庆、庙会的重要角色。如《东京梦华录》载:“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赦赐神保观。二十三日,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栅、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二十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生、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掉刀装鬼、鼓牌捧、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拽呈不尽。”[21]212—213陆游在《春社》中亦写道:“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22]1883“比邻夜出观夜场,老稚相呼作春社。”[22]2465“空巷观竞渡,倒社观戏场。”[22]3660在社日这样的狂欢氛围中,本想一心“幽居”的老诗人也耐不住寂寞,跟随观剧的人流“巷北观神社,村东看戏场”[22]4318去了。
至元代,狂欢集会热度不减,《元典章》五十七“刑部”卷十九记载:“朝酒暮肉,每次祈赛,每日不宁,街衙喧哄,男女混杂。”[23]463《析津志辑佚·岁纪》载每年二月初八日西镇国寺之盛况:“寺之两廊买卖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大佛游于城外,极其华丽。”[24]214—215明清时期,全民参与的戏曲表演更成为狂欢活动的中心。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倭乱后,每年乡镇二三月间迎神赛会,地方恶少喜事之人,先期聚众搬演杂剧故事。……至万历庚寅(1590年),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每镇或四日或五日乃止,日费千金。”[25]93庙会中所费惊人,挥霍无度,民众挈家来观,情绪狂热,是区别于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一种狂欢生活。在苏州东岳神会中,“在娄门外者,龙墩各村人赛会于庙,张灯演剧,百戏竞陈,游观若狂”。[26]97“吴下风俗,每事浮夸粉饰,……如遇迎神赛会,搭台演戏一节,耗费尤甚,酿祸更深;此皆地方无赖棍徒,借祈年报赛为名,图饱贪腹,每至春时,出头敛财,排门科派,于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哄动远近男妇,群聚往观,举国若狂,废时失业,田畴菜麦,蹂躏无遗”。[25]99此虽为汤斌禁赛会演戏之言论,但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民众的狂欢情绪,无论远近,男女皆群聚而观,而且他们把据以生计的田地农活抛诸脑后,不理农事,专事娱乐,彻底沉浸在“举国若狂”的赛会气氛中。
从以上的粗略勾勒中,中国民众狂欢生活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出来:它以节庆为主要依托,主要发生在庙观、街市等地,欢会中民众聚集,肆意饮食、两性开放、歌舞喧哗、百戏竞集,其重心从以“神、祀”为主,逐渐倾向于“艺”,百戏、戏曲演剧等更成为承载民众狂欢情绪的主要载体。中国民众的狂欢生活也是全民参与,颠覆常规,富于狂欢精神的。
[1] 陈灏注.四书五经(中)[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
[2] 苏轼.东坡志林[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
[3] 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 孔颖达著,吕友仁点校.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 李慧玲.试说中国古代的狂欢节——蜡祭[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3).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 孙其刚.嫘祖养蚕和桑蚕的宗教意义[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2).
[9] 伯高·帕特里奇.狂欢史[M].刘心勇,杨东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2]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 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6]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8] 周祖谟校.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 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20] 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西湖书社,1981.
[21]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商务出版社,1959.
[22]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祖生利,李崇兴点校.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4] 熊梦祥.析津辑佚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25]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6] 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