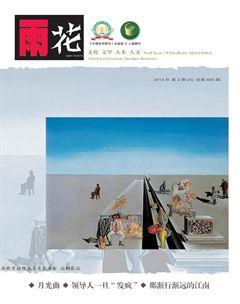我之画画
张震
中国画,中国书法都是一个道理,摹只是求形,只有“写”才会彰显真我!“写字”,“写画”,只有深知和了悟这个道理,你才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小时候不喜欢画画,不像王冕、任伯年、丰子恺都从小酷爱画画,我之画画更像“扬州八怪”的金冬心、汪近人,临近中年才当回事。我小时候画图课总是不及格,人家会画树了,我才勉强能画片叶子;人家会画军舰了,我才知道,那根拖下来的链子叫锚。我小时候画图不好,但我不觉得我是最差,我总认为还有一个人不如我,他叫达芬奇,他只会画圈,而且越画越不圆,我要好点,能画树叶,能画红灯笼;能画日本人的仁丹胡,能画王二小的红缨枪。
稍大些后,我开始有点喜欢画画,不过我不喜欢老师的画,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粉笔,一根线一根线地往上搭,老老实实,千篇一律,实在没啥意思。我的启蒙老师是街头艺人的画,是卖狗皮膏前抓一把白砂撒在地上,是手里拿个铜匙在大理石板上画糖画。多冷的天都赤裸上身,把手伸进小铁桶里,抓一把白砂,一边口若悬河,一边在地上画画;多冷的天都坐在那里,手里端着个糖匙,永远低着头,沉默着坐在那里画画。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入迷这两个艺人,他俩走哪我都跟到哪,为的就是看他俩画画。看他手里攥一把白砂,手指稍稍一松,白砂便流下,一会儿工夫便把一个人体画在地上,那人体栩栩如生,仿佛一个骨骼健全,肌肉丰满的人睡在床上。然后,他便开始讲膏药应该贴哪,如何神奇。那时候,我身体哪都不痛,我不太关心他的“后半段”,更看重的是他怎样将一把白砂变成一个活人,这对我而言,是神奇的谜。
至于那个永远沉默,永远低着头画糖画的人,我更是喜欢,他永远戴一顶军绿的“雷锋帽”,像写毛笔字一样悬着腕,倾斜着铜匙画着他的糖画。在我眼里那洁白的大理石,是一个真正敞开的万花筒,一会儿一头鹿,一会儿一条龙;一会儿麻姑献寿,一会儿韩湘子吹箫。我一直在想,他本事太大了,他怎么不需要对照书?他肯定能画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想拜他为师,我逃学三天,随他一起穿街走巷,一路兜售糖画,结果我为他熬了三天糖,他教会了我树叶的画法。后来,他对我说:孩子,学什么不要学糖画,学会了就意味着一辈子要穿行在风雨里。成年后我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多冷的天都必须挑着沉重的担子,必须坐在那里,必须接受寒风的问候,飞雪的敬礼,那绝对不是一项甜蜜的事业。
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第一个师傅,虽然他从没认过我这个徒弟。
我十六岁开始迷上文学,开始写诗且热情万丈,我一天能写八首,没地方发表,就念给蓝天听,念给大地听,蓝天大地不回话时,我就在工厂里逮谁念给谁听,说我好,说我丑,无所谓,我只要能把诗发表在别人耳朵里就行。时间一长,我有一点小名,全国各地都有诗友,我开始写信,坚持用毛笔写信,这样几十年下来,我的墨线还是有劲的,无形之中我完成了中国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画其实就是“写”,只要坚持用写的方法去做,画里就一定会有你的魂魄。中国画,中国书法都是一个道理,摹只是求形,只有“写”才会彰显真我!“写字”,“写画”,只有深知和了悟这个道理,你才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几乎与文学同步,我也钟情于绘画,虽说落在纸上更多的还是诗歌和散文,但空余时间我还是坚持观看和研究绘画,把绘画当做文学之外的第一修养。若干年下来,我几乎把中国画从古至今所有的名作名家都研究了一遍,殊途同归,其实文学与绘画从宏观上讲是一样的,都是开拓和塑造人类情感的艺术,都是用手中的笔去构写人类情感的形态。绘画与文学也非常互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你看到以这两句为题精湛的绘画,你就会觉得这两句写得多么鲜活和精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如果你觉得这两句费解,你就可以在古人的绘画中找到这两句惟妙惟肖的意境。我研究绘画,它也使我的文学创作变得更加生动和丰满,使我的文章更加笔下有物,我曾经坚持数年对着无数幅优秀画作进行写作练习,按照一幅画的起笔和终笔进行再次文学创作,我称之为“文学写生”。这样,既可以背出每一张画的景物,又可以非常有特色地进行文学描写(因为每一幅优秀画作都是独具匠心的),还可以锻炼自己写文学评论和美术评论的能力,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美妙的经验,是最好的基础练习,一举多得,一箭多雕。
苏东坡这样评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早年认识肤浅,只是以为王维诗好,写的像画一样漂亮,现在才深知,王摩诘是诗画一体,一种魂魄,一种精髓,只是艺术式样不一样。由苏东坡评语,我也悟得无论文学、绘画,还是音乐、舞蹈,到高境界时都是在做同一篇文章,在登攀同一种高峰,至于这“同一篇文章”,究竟想表达什么?怎样表达?运用什么形式?凡集大成者皆有各自独特步伐。不过,画画与文学相比,达到化境,达到高标,画到似又不似而又相似的人较多,而文学写到高标,达到收放自如大开大合的人较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探求文学的奥义最难,它对人的要求更高,它与绘画的承载量不一样。
三十出头,我开始买纸买颜料了,我觉得我应该像苏东坡,像黄庭坚,像王世贞,像傅青主那样,以水墨养养自己的性情,让自己的灵魂接受一下水墨的滋润。三十出头起步晚吗?郑板桥四十以后才专事兰竹,吴昌硕五十开外才一心丹青,我何晚之有?我之画画,对我而言是补气,是用另一种修养来支撑文学创作。我不太在乎有多少人捧场,我游戏笔墨是属于文人在书斋里的秘玩和雅玩,只为脱尽尘心。吴昌硕说越无人识越安闲,扫叶楼的龚贤也有类似的诗篇——扫叶何时尽,秋风秋雨多。四山声不断,一树寂如何?
自从把毛笔在笔洗里化开,我几乎每天都保持两小时的水墨功课,我喜欢用淡墨抒写古代人物,用行书和草书的笔法描绘古人的逸和趣。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白墨在中国画中的作用,一直在寻找古代人物画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一直在捕捉中国文人画的趣味和雅意。无趣不生动,无质不大气,我一直在宣纸上锤炼着线的质量,墨的韵味。在中国山水画中一直有“白龚贤、黑龚贤”,“白宾虹、黑宾虹”之说,在人物画中尚没有“白人物”,我一直在尝试不用重墨,把墨色降到极限,用白墨表现人物的清雅和神逸。我画面中的人物,几乎都著着白衣,都有超凡脱俗之态。这是白墨带来的视觉效果,我也愿意在这条路上走走看。
画画和其他艺术一样,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什么独特的秘笈,即使有也早在书里了。我始终认为中国画就是画“水”,“水”在中国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水”决定着画面的品质,画意的变化。中国画不在乎大小,只看重笔墨是否隽雅,是否精到,你画一座黄山也行,你画一块石头也可,关键在于好。一座黄山并不见得比一块石头更具价值,其实所有的艺术皆一样,都推崇力作,崇尚精品。
画好画,在于勤奋,在于思悟,在于审美,在于肚子里有没有货。我小时候见过程十发在裱画店里画画,裁一叠纸,一画一大堆,画完之后,人就像站在云里,值得他留的,也就一、二张。中国画都是纸头喂出来的。我也见过林散之、黄永玉、亚明画画,基本上亦如此,一天不磨斯功,一日等于虚度。我之画画,是养闲、养气,是文学写作的另一种形式,是把文学装进美术的容器,进行重新编排,重新组合。艺术是养人的,不仅养自己,也要养他人,艺术创作的目的也在于此。近年喜欢我画的人渐多渐隆,索画者也不断,我只要有暇,尽力满足。淡墨写出心中事,只为激赏报知音,像版画大师黄丕谟,散文大家董桥都是我的忘年知音,他们尤爱我这个小朋友,赞扬我的画打通了文学和美术的界线,也属“另类”,有生活的真趣,文人的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