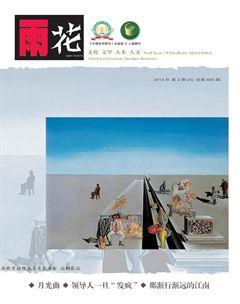那渐行渐远的江南
宁默
奶奶有好几件这样的青布褂子,她轮流着穿。脏的褂子洗好晾在竹竿上,方正而肥大,躲猫猫时我常钻在里边。
银杏
常州的老银杏树不多,城北的陈家祠堂门前就有两株,须双人合抱才能围拢来。却只长叶不结果,阿姆爷叔都说它们是金刚罗汉,雄的。
每年春夏,银杏长新叶时分,成群结队的姑娘嬷嬷们跨着篮子来采杏叶,配药,熬汤,煮粥。我记得年轻的女子都爬在银杏粗壮的枝丫上,纷披的绿叶间,东边垂下一双绣花红鞋荡啊荡,西边两只蓝布裤腿飘啊飘,隔了二三十年回忆,依然鲜活如昨。有时荡得飘得幅度大了,树下的嬷嬷便嚷起来:嗐!轻骨头郎当的,别嫁不了人家。年轻的便在枝丫间吃吃地笑,腿上的动静小下来。
东街的仇和尚也常过桥来树下和人吹牛皮,说到苏东坡,他就摇头晃脑地背诗:四边封山,嬷嬷亲手撕画,一树惊天,圈圈点点文章。我依样画葫芦回家背给阿爸听,他犹豫了好几次,有一回终于问我:你念的是什么?我说,是夸银杏树“一树惊天”的。阿爸想了想说,哪有这样的对子!我其实也疑惑,嬷嬷为什么要亲手撕画呢,仿佛该有个曲折故事。
两株银杏树先被雷劈伤了一株。阿姆说,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她娘家的大河庙前就有一棵银杏,有一天她亲眼看见银杏在震雷的电光中燃烧起火;临河巷那边也有棵大银杏的,后来被雷劈个贯心透,当中全空了。她的经验是,银杏寿命长,容易惹上妖精,雷公公最容不得妖精的。那是不是妖精也喜欢银杏树呢?我又开始瞎想。劈伤了的银杏一副恹恹弃世的样子,我每天上学从它身边走过,下学也从它身边走过,有时摸一摸它枯黑的树皮,像过年蒸馒头时灶膛里的焦木。阿姆爷叔都说没用了,肯定是树心被劈烂了。然而过了好些年,它居然挣扎了过来,仿佛一夜间,断枝上就绽出茸茸的叶芽,新鲜的绿色点点滴滴地覆在黑色的焦皮上,害得老得不能动的陈阿姆在树下掉了一回泪。
都以为从此又可以成双结对地活了。哪里知道镇里要铺水泥路,来了十几个带电锯的男人,一天工夫就彻底放倒了它俩。
那时候啊,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把长长的石板街塞得水泄不通。银杏树被分成大大小小的树段准备运走,仇和尚从人群里挤出来,绕着小山样的树段转了两圈,用衣袖擦擦眼睛,仰天大笑三声,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又念起当年的句子:“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这回我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字都没听错。
仇和尚
仇和尚最怕他老婆。传说仇和尚四十多岁的时候被扒了庙,他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声音嘹亮地刺穿了一个镇,把镇西河边玩耍的鸟儿惊得扑簌簌飞。仇和尚白天被拉着游了一天街,晚上就挣脱了绳索跑回他的庙,去看倒了一地的泥菩萨。他在庭院当中挖了个大坑,一趟趟地往坑里搬运那些菩萨的残肢碎骸,但是没来得及搬完,来人了。他们把他关进猪圈,一个月后放出来,塞给他一个女人,让她负责监督他的一切生活。
这个女人就成了仇和尚的老婆,她比他小二十岁,是个哑巴。仇和尚往老庙跑,她就抱住他的腰;仇和尚喝酒,她就揪住他耳朵往干部的办公室拉;仇和尚昂首背诗:“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她就拿烫山芋堵他的嘴。到后来,仇和尚就在家里规规矩矩坐着,哑巴一样,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活也不干。倒是身上干净利落了好些,袖子口不再有鼻涕的污痕。
再后来,哑巴老婆难产死了。仇和尚就照样喝酒,背诗,用袖子口擦眼泪鼻涕,只是不往庙里跑了,庙没了,成了大晒场,人们在上面摊晒稻谷麦子。
仇和尚经常穿一件麻布灰白长褂子,哐当哐当地罩到小腿,一条看不出颜色的布巾绑着裤腿,脚上总是黑圆口布鞋,他的哑巴老婆别的没留给他,就留了几十双这样的布鞋。个子又高,黑地里看见他,还以为是无常鬼呢。大人就警告哭泣的孩子:再哭!再哭就让仇和尚带了你去。孩子便噤若寒蝉,连呼吸都屏住了。
其实仇和尚人很和气,从不大声呵斥淘气的孩子们。有次我拿竹竿去敲枣树上的枣子吃,他看见了,捋捋袖子,朝手心吐口水,噌噌地上了枣树,摘了一兜的枣子送我。那时仇和尚已经有点老了,不过我说不准他的年龄。
仇和尚一天只吃两顿茶饭,早上在石桥下的麻糕店吃早饭,一碗豆腐汤,一块大麻糕;午饭时我到他家隔壁的小店里买盐,总看见他坐在自家门口的矮凳子上咪一盅黄酒,面前的小木桌上只一碟酱黄豆。他说“过午不食”。每到年脚,仇和尚最是紧俏人物,家家都要他写门联。他握着毛笔在红纸上写字时,两条眉毛几乎攥在了一起,看起来非常吃力。右手的袖子黑了一半,都是墨汁。
但是仇和尚从不写“山清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多”这样的对子,他的对子人家大多看不懂,比如“沾墨才题梅似雪,挥毫又赋柳如烟”,“晴绿乍添垂柳色,春流时泛落花香”,就嫌不够喜气,背后嘀咕。后来镇里调来一个干部,也会拿毛笔写字,慢慢地仇和尚就没生意了,人家大门上又恢复了“山清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多”的喜气。
孩子们却依旧喜欢拾仇和尚牙缝里的句子回家炫耀,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阿爸再三关照我:不许跟仇和尚学说话,晦气的!我心里悄悄地想,管他晦气不晦气呢,有学问总是真的吧。
我到现在都这样认为。
南街
街镇被石桥分作南北两块,北街只有一个菜场,南街有很多店铺。南街不大,丁字形的两条路,青石板的地面保存得很好,一条条横铺着伸向拐角。走着走着就会被它们打乱了脚步:一步跨两块石板呢,步子太大,不雅观;跨一块半正好,可是要费心测算,下步犹豫;就一步一块石板吧,悠悠地走,像过去小脚女人的细碎步子——只要你走上这样的青石板路,旧时江南就从你脚下开始了。
街道两边是各类店铺,都有桐油漆过的暗金色木板门。早上木板门陆续移开,露出里边装着各式货物的柜台。裁缝铺子里是一张堆着布匹的大工作台,小徒弟打着呵欠烧水,掸尘,然后将头歪进隔壁的南货店里朝里看,摆着油盐糖酱醋的柜台遮住了一个俏俏的身影,她正踮着脚用鸡毛掸子掸货柜上层的灰,脑后的一条辫子甩来甩去。小徒弟咳嗽一声,她便转过脸,两只毛乎乎的黑眼睛一亮一亮地看向门外,抿着嘴没有声音地笑。
那时候人们都说开南货店的薛老板新招了一个四川的徒弟。我见过几次,她在柜台里,我在青石板的路上。有次她在埋头打算盘,白生生的手指有时弯有时翘;有次她用牛皮纸给人包红糖。有时会听见隔墙里边喊:阿莲,痰盂还没倒呢!她便脚步咚咚地端着痰盂走出店门,钻进对面杂货铺边上的小弄堂里去。走过我身边的时候,闻见一股酱油混合着潮湿的红糖的味道,每一家南货店里都有这股味道。她比我高半个头。
南货店对面的杂货铺是南街生意最好的一家店,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他家都有。我喜欢去他家买头花和胸花,我平时并不戴的,但是学校里每逢劳动节或者国庆节要排节目,老师们规定辫子上必须扎上粉红的头花。我每次都是去茅老板的店里买,五角钱一对。有次我在学校里和女同学一起折腾头发玩,把扎辫子的皮筋绷断了。老师不喜欢蓬着头的学生,就趁着下课的一丁点时间冲到杂货店,跨进它高高的门槛,用两角钱买了长长的一根红皮绳。我并没有见过茅老板,但是胖墩墩的老板娘始终在柜台里。她对气喘吁吁的我说,丫头,弗要跑啊,我忒你扎册来再走(丫头,不要跑,我给你扎起来再走)!
老板娘给我扎辫子的时候,裁缝店里的小徒弟和南货店里的阿莲就坐在他们各自的柜台里看着我。
我过十二岁生日,母亲带我去南街照相馆里照相。照相馆在街道的最边上,石板路到此为止,接替石板路的是一片青森森的榆树林。照相馆进门就是一团黑咕隆咚,母亲带我穿过一条长长的漆黑的过道,来到拍照的暗室,那里更加黑,仿佛走进了一团墨汁。照相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一盏灯亮了,我才看清屋里的摆设,一张旧的写字桌,一张椅子,靠墙摆着几张大的风景画布,有天空,有湖水,还有一张画着漂亮的白色房子,房子前是碧绿的草地。风景画前有一张骨牌凳。
我在白房子前拍了两张照,一张坐着,一张蹲着。出来的时候看见店铺的墙上挂着很多素描人像——此时眼睛适应了昏暗,所以看得见了。大多是只画到胸部的人像,母亲说,这个照相的还负责给死人画遗像。可是,我分明看见有一张画,里边的姑娘有手也有脚,膝上还有一只猫。我敢肯定画的是阿莲。
阿莲当然不是死人。我外出上学前还看见过她,正坐在馄饨店里喝面汤。她往汤里舀了两匙子辣酱,喝得额头和鼻尖都是红红的。坐在她旁边的薛老板娘的碗里却是白汤的三鲜馄饨。
她一定是吃不惯馄饨,她一定还在想家。
斜襟褂子
那时候我家大门对着德胜河的河堤,河堤很高,高过了我家的两层青砖小楼。河堤内侧种着槐树和柳树,外侧被农人耙作高田,种着绿叶蔬菜。河堤上人来人往,都是赶集的走亲戚的办事的。奶奶对着河堤坐在门前,膝盖上一只竹笸箩,里边一团白棉乱线。她仔细地理着那团乱线,从里边寻出一根线头,抽出来,一边理一边绕成个线团。有时一抬头,看见河堤上的行人,扬着声招呼:双喜家的,急急忙忙囊头气啊(急急忙忙哪里去啊)?来坐坐!
河堤上的行人也扬着声和奶奶寒暄,吃啦,坐啊,来啦,去啊……走得不见了。
奶奶撩起斜襟褂子外系着的围裙,用边角沾沾眼睛,叹着说:老了,眼睛不好了。
我至今不晓得她是哪里来的那么多乱线,她又为什么总是在理这些乱线。
然而我总是不能忘记奶奶坐在门口理线的样子,青布的斜襟大褂,水溜光滑的发丝在脑后挽成一只髻,如她一生妥帖而安详的时光。奶奶有好几件这样的青布褂子,她轮流着穿。脏的褂子洗好晾在竹竿上,方正而肥大,躲猫猫时我常钻在里边。
那时年轻的女子是不肯穿这样的褂子的,嫌老气,她们都喜欢胸前有扣子或者拉链的衣衫。可是过年时的龙灯会上,唱小曲的姑娘们也穿这样的斜襟褂子,不过裁剪很贴身,颜色也大红大绿起来。
母亲也有青布的斜襟褂子,她结婚时的陪嫁,可我未曾见她穿过一次。母亲说,光是扣腋下的布扣就麻烦得不得了。尽管她不穿,然而作为陪嫁的“箱底”,外婆是不能不给她准备的。甚至到我堂姐结婚时,箱底依然铺着一袭这样的斜襟褂子。它老气,所以它传统,有底蕴,是守规矩的象征;它是青色的,江南人一向认为青色的物事可以避邪,譬如外出时常在口袋里放一根穿着青线的针。
奶奶很老的时候,斜襟褂子腋下的布扣终于让她感到了为难,她的手抖得扣不住它们。我每天不仅要帮她扣上扣子,还要帮她解开扣子。有时天气潮湿,盘花的扣头怎么也塞不进扣袢,她抬着左手坐着,一声接一声地喘,我钻在她腋下,越是心慌就越扣不住,央求她换上对襟褂子穿,她会皱着眉说:小佬真没用啊,我自己来扣。
终于有一天,斜襟褂子的扣子扣上后就不必解开了。奶奶躺在那里,安详得不动声色。青布褂子将她包裹得凛然而决绝,她什么也不用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