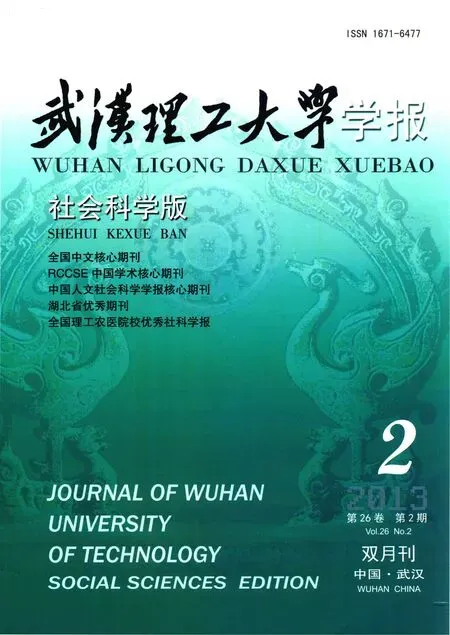从隐逸观念透视帝制中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朱 雄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在帝制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寒窗苦读,不断坚守的动力。但是,在帝制中国却存在着隐士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隐士不热衷于仕进,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甚至对现实政治予以批判,折射出知识与权力的某种张力。
一、士与隐士
阎步克从训诂学及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认为,“士的最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并由于一个近似社会分工的过程,它逐渐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统治部族成员之称、封建贵族阶级之称、受命居职之贵族官员之称,以及贵族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等等内涵”,并将士大夫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1]30。既然士大夫是居官的知识分子,那么隐士即可定义为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
在帝制中国,个体的士非隐即仕。钱穆认为,“(先秦)初期之问题中心为礼,中期之问题为仕,末期问题为治”,中期“所讨论者,质言之,即士阶级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应抱若何之态度”[2]。因此,关于“仕”这一问题,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思想家们普遍讨论的问题。
仕之所以成为普遍讨论的问题,是与先秦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周代采用的是分封建制的基本政治结构,官吏都是世卿世禄,各级官员是世袭的。正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所讲:“世禄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孙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则官之。”[3]218因此,只有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动摇,诸侯国自主性加强,士人可以选择君主时,仕与隐才成为需要士人考虑和选择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由于‘师道’的独特形态,学士文人们还面临着‘仕’与‘隐’的两难。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学士文人面临的特有问题”[1]402,并将仕与隐的冲突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政治或文化性的紧张之一。
二、儒道仕隐观念分析
先秦时代的学术活动已然奠定了帝制中国的思想基础,是学界普遍的共识。正如钱穆先生所讲,“中国民族的‘学术路径’与‘思想态度’,也大体在先秦时代‘奠定’”[4]。因此,本文将从先秦儒道的隐逸观念出发,从儒、道的经典文本出发,来分析仕隐观念的主要内容。
(一)儒家的隐逸观念
儒家怀有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儒家思想在帝制中国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那么,为何还存在着隐士这一群体呢?对儒家仕隐观念的剖析,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论语》和《孟子》都有精辟的论述,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论语》认为仕是士人的职责与义务所在。“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3]185。《论语》认为士人入仕是其职责与义务所在,是行其“义”。“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3]266孟子将士人之仕比作农夫之耕,认为是天经地义,职责所在。
其次,《论语》认为邦有道与否是仕与隐的前提。“笃信好学,死守善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3]106;“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163《论语》中所说的“邦有道”的内涵,可以从“问政”的语录中分析得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136-137。由此可见,《论语》所主张的“邦有道”,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仁政与礼治的一种伦理政治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穴隙之类也”[3]267。孟子将不由道而仕的人比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两情相悦,因而“父母国人皆贱之”。[3]267孟子进而指出,士之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道,以区别于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3]211。这里的“有恒心”就是对道的坚守。
最后,儒家仕隐观在内在逻辑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论语》中孔子将有道与否作为仕隐的前提。另一方面,孔子将道的实现与否归之于天命,“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3]158。而士人应该抱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对待入仕,“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3]185。如此,孔子则将“邦有道”与否作为入仕的准则弃置一旁,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模糊对待将有道与否作为仕隐的取舍标准。孟子同样也认为道之行否在于天命,“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3]226
从对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儒家仕隐观念的总体特征如下:其一,主张积极入仕,并认为是士人的职责所在,不仕无义。其二,士人应该坚持其政治理想,“从道不从君”,并且高扬道尊于势的大旗。道的内涵主要意指儒家仁政及礼治的伦理政治观。其三,儒家以有道与否作为仕隐与否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并非刚性的。孔子提出了道之行否在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观念;孟子借孔子的行为道出了“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3]320的“三仕”说。而这些又是与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主张相矛盾的。
(二)道家的仕隐观
相对于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则明显表现出出世倾向。有学者就认为隐士产生于道家,“这些隐者是‘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远离世俗,遁迹山林,早期道家大概便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5]57。《庄子》一书便集中表达了道家的隐逸思想。
首先,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与其哲学主张相联系的。庄子认为万物的本性和天赋的能力各不相同,强求一致是徒劳无益的。《庄子》中有一比喻:“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6]317因此,庄子认为自然本身就是完美的,反对人为的对自然的改造。一切体制、政府、法律、道德,在庄子看来,其所求达到的便是强求一律和压制差异,这对于万物自然本性来说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庄子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宥之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6]364。
其次,庄子的隐逸观念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重生”,归隐的目的是“存身”。“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6]323。《庄子·让王篇》所载,尧以天下让许由,舜以天下让子州支伯,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而皆不受。其理由也是一致的:不以天下害其身,以天下之大器不易生。以“天下”与“身”相比,就是要以人的本真的生命为重。
最后,庄子认为隐而不仕的另一个目的是个人的“自得”。“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裳葛绀希;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6]966。在善卷眼中,顺应四时变化,逍遥自得,天下只是负累了。庄子还借颜回之口,道出隐居而“自娱自乐”是为“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6]78。庄子所谓的“自得”、“自娱”、“自乐”突出了自我的主体价值,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一种肯定。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庄子的隐逸观念如下:自然是完满的,一切政治安排是违反自然天性的,主张在宥天下,返朴归真,远离政治生活,为“重生”和保持个人的独立性而当隐居不仕。
抛开儒家和道家的具体价值追求与内在逻辑的不同,其隐逸观念的共同特点就在于要与帝制中国的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隐逸心态在帝制中国的士人中是普遍存在的。冯友兰先生就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5]7
政治行为是受政治观念所支配的,隐逸观念影响下的隐士群体的政治行为就必然表现为疏远现实政治的行为方式。在帝制中国,王权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刘泽华先生就将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王权主义”社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7]。隐士是知识的传承者和保有者,但又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因而,从仕隐现象考察隐士与王权的内在张力,就成为透视帝制中国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极好视角。
三、隐逸观念折射的知识与权力关系
隐士在帝制中国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义与文化蕴含。士与政治的关系表面上看是“仕”的问题,其实是关乎“道”的问题。其所谓“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351。从一般意义来理解,士人所遵循的“道”是广义上的“知识”,主要包含增量意义上的学问,更包含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承担。隐士作为“从道不从君”原则的坚守者,隐与仕也就转化为知识与权力的问题。隐逸现象彰显出在帝制中国所呈现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
(一)知识对权力的软性制约
“从道不从君”是隐士坚持知识高于权力的依据。知识士人将自身作为道的坚守者,并对权力占有着价值评判的高地。从中国漫长的传统政治社会实践来看,隐士群体显然是张扬了士人对于道统的坚守,这也是士人对于隐士为何普遍持褒扬态度的原因。隐士成为士人仿效的对象,隐逸心态在士人阶层普遍存在。封建帝王对于隐士的礼遇有加,成为历代史书大书特书的事件,并被传为美谈。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被后代儒者尊之为“素王”,其所修订的《春秋》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孟子·滕文公下》言道:“世衰道微,邪说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戄,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272在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看来,孔子就是“素王”,是“无冕之王”,孔子所作之《春秋》就是为天子立法,为后世政治立法,使乱臣贼子惧。由此,权力对知识也表现出尊崇与礼敬。儒家学说是帝王统御万民的工具,也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如达尔所言,当一种意识形态被整个社会广泛接受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提倡者本人也会受到其约束,成为它的“囚徒”[8]。否则,即使是帝王,也无法找寻其价值归属,而成为道德、信仰和精神上的孤魂野鬼,无可依托。正因为此,在帝制中国,权力对知识的尊崇也在政治运作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无论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俗语,还是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加封,对祭孔活动的重视,对经筵制度的完善等等,都可以看出对读书人及对知识的尊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士人取得官职且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时,这种知识对权力的张力仍未消除。一方面,君为臣纲,君主作为最高权力的享有者对官僚拥有无上的支配权。但另一方面,士人取得官职,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官僚组织。有学者指出,“这种对君权的依附性和从属只是官僚制度的一个方面,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全成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官僚制度的实际运行(而不是从专制制度的规定性)情况来看,它还具有不受君主意志所左右,自行其是的自主性的一面”[9]。
自从汉代帝王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独尊儒术”以后,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化身为道统的承继者,面对权力时保持着清高与尊严,甚而对现实政治实行猛烈的批判。西汉“虎臣”盖宽饶曾指责当时圣道寝废,儒术不行,而面对东汉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士人的愤起指斥最能显示士阶层对道统的坚守。然而士人的指斥并不能带来对现实政治的实质改变,也就是说知识并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制约。东汉士人抨击宦党之祸的结果却是士人被杀戮,士人的无可奈何:“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10]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衡关系,知识对权力的制约只能是一种软性的制约。正如刘泽华提出的“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织结构的概念”[11],认为从道不从君、道高于君是一组概念,是属于阴性的;另一方面,君又是道的体认者、裁判者是另一组概念,是属于阳性的。在这样的阴阳组合结构中,阳性概念居于主导地位,而阴性概念处于附属地位。这当然是一种学理上的高度概括。我们透过隐士群体的具体分析也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特征。隐逸观念的存在及流行反映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但是并不能对封建王权进行制度化及组织化的有效制衡,只能是一种软性的制约。隐士归隐只能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绝异于西方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之争。隐士群体的存在至多也是象征意味的,知识对权力并不能形成实质性的制约。
(二)权力对知识的刚性压制
中国传统社会下,专制主义的倾向由秦汉而至明清逐步加强已成为学者们的基本共识。这一过程也表现为权力对知识的压制逐渐加强。隐逸现象的流变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趋势。
我们从隐逸观念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出,帝制中国专制主义逐渐加强的趋势,权力对知识的刚性压制逐步加强。正如前文所讲,“仕”的问题在战国中期一直是士人所广泛讨论的问题,并且儒家鲜明地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主张。然而到了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士人的仕隐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政治环境的变迁。孟子所谓“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3]291。这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士人可以自由选择入仕的诸侯国。当秦汉一统之后,政治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国时士无常君的政治现实在秦汉一统后完全不存在了。在新的天下一统的政治现实下,隐逸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朔提出的“避世于朝廷间”的理论,“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12]。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出现在隐逸理论的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竹林七贤纵情山水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他们在一套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的思想观念下的特立独行。竹林七贤的独立特行行为背后所秉持的思想已经直接质疑了王权的现实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林七贤传承了隐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态度。然而,从嵇康的被诛,以及司马氏政权对七贤中的山涛、向秀、王戎等人待以高位的现象来看,则又明白地昭示了专制主义容不下隐逸观念的直接挑战的现实。面对逐步强化了的专制主义,隐逸理论也不得不进行自身的调整,发展到唐朝就成了白居易在其《中隐》诗中所阐明的“中隐”说:“大隐在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官司……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13]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归隐的形式。例如禄隐、洒隐、半隐等等不一而足。明代李贽更是将隐士分为时隐、身隐、心隐、吏隐四类。
从专制主义的本质来讲,它是以在社会各个领域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为特征,不可能妥协于任何意识观念或政治行为对这种支配地位的挑战。作为专制主义的王权,虽然有时礼贤下士,对隐士优待有加,然而,在残酷的政治以及专制主义的本质驱使下,这种优待勿宁是君主的一种统治术。这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待隐士的两面态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朝初期大兴优礼隐士的作法。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九月,朱元璋下《谕隐逸诏》[14],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隐逸之士的尊崇与优待,天下之治要与“天下之贤共成之”,谕请岩穴之士辅佐朝廷。然而针对元代遗民不仕新朝,明朝以刑法直接制裁隐士行为。《明史·刑法志一》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罪至抄札”[15]。当统治者举起屠刀之时,隐士并无丝毫反抗之力。朱元璋对隐逸之士的两面做法,突出地显示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谕隐逸诏》表现出了权力对知识只是表面的、象征性的尊重。
从朱元璋对待隐逸的两面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王权尊隐常常只是充当了帝王的一种统治术而已。所谓“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16]。正史当中,也时有类似的观念:“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17]隐士们对现实的不合作态度,常被社会看作是清廉刚正的符号,也成为统治者稳固统治的可资利用的资源。那就是通过尊隐,厉浊激贪、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净化官场贪渎习气,稳固统治。此外,统治者尊崇隐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成就君王的美名。范仲淹在其《严先生祠堂记》中一语道破了隐士严光是如何成就光武帝美名的:“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18]
四、结 语
隐士群体突显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从道不从君”的儒家政治原则成为士人疏离与批判专制王权的依据。尽管是一种知识对权力的软性制约,但是对于遏制王权的专制独断无疑是有益的。儒家所尊崇的道,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仁政、礼治的伦理价值观,表现为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这无疑也消解了家天下背景下以一姓之私与一已之欲所造成的对百姓利益的戕害。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历史总是以某种形式影响着当下。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也必然受到历史上的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影响。话语体系虽然已经改变,但是知识面对权力时仍应保存一份清醒与尊严,仍应保持对“道”的坚守。当然对于“道”的内涵的理解肯定是异于帝制时期的了。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也正是知识与权力张力问题的现实追问。这一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本文所探讨的范畴。若本文能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探讨作出一个历史的注脚的话,也就达到其价值与目的了。
[1]阎步可.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钱 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2.
[3]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钱 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5.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8]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0.
[9]张星久.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J].政治学研究,1997(4):61-69.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820.
[11]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33-35.
[12]司马迁.滑稽列传[M]∥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90:906.
[1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4991.
[14]王恩俊.隐士与明初政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1):118-120.
[15]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26.
[16]皇甫谧.高士传[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8:1.
[17]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15.
[18]吴楚材.古文观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