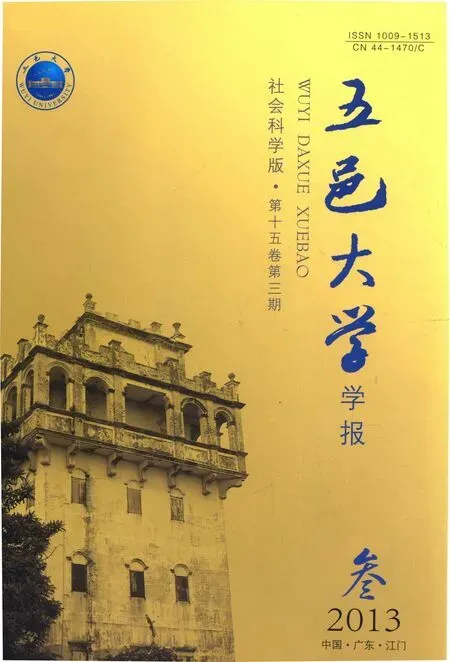论梁启超 《新民说》的国家主义倾向
揭 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其中 《新民说》尤其受重视。《新民说》对国民素质的重视和思考成为中国近现代国民道德教育的里程碑。目前,学术界对梁启超《新民说》中国家主义倾向的研究主要侧重以下两方面:一是探索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来源。如张衍前的 《近代国家观: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理论学刊》,1995年第5期);二是探索国家主义思想倾向的主要表现。如陈雅琴的 《浅论 “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对于 《新民说》中的国家主义倾向,前人着重从梁启超对新民提出的政治要求入手,而对其中的道德要求及国家主义倾向关注得较少。在 《新民说》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倾向既体现在他对新民提出的政治要求中,也体现在道德要求中。其所谓的 “新民”是集道德人与政治人于一身、以利国为最主要人格特征的国民。 《新民说》的目的就在于将 “臣民”改造成“国民”。
一、国家主义倾向的体现
在 《新民说》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他的 “新民”理想人格中。在国民的人格重塑上,梁启超以培育公德为新民的精髓,以利国为公德的根本;以具有国家思想为国民的灵魂,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国家思想的核心。
首先,国家有机体思想。在梁启超看来,一方面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统一整体,国民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与其他国家相对立而存在,并具有独立并超越所有组成部分的目的和精神。整体的目的和利益大于任何个体的目的和利益。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本国利益至上;在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中,国家优先于个人,国家利益至上。
关于国家起源,梁启超认为:“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己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利益之道也。”[1]68国家的结成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难以独立自存,需要与他人相互帮助,来抵御侵害,满足需要,确保自身的存在。国家的建立在于维护国民的利益,确保国民的安全。就国家构成而言,梁启超将其比作身体与各器官的关系,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统一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46各构成部分的素质直接决定了整体的实力。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1]56因此, “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46只有改造国民性,培育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梁启超指出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不能再指望一时的贤君相、横空出世的英雄,必须着眼于兴 “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1]51。
国家作为国民组成的统一体,一经产生,对外则与其他国家相对立而存在,对内则具有独立并超越所有组成部分的目的和精神。对于国家间的关系,梁启超提出:“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1]69各个国家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如何处理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关键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1]69面对当时外交上列强林立、危机四伏的形势,梁启超强调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民族主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对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梁启超一方面承认“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1]69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国民的公有财产。政府或者朝廷只不过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1]145国家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只有兼爱才能为我,只有利国才能利己,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 “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以拥护未来公益。”[1]145在此,梁启超用类似于功利主义的证明方法实现了由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个人主义使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国家主义使个人利益的实现成为可能。
其次,新民以利国为最主要的人格特征。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他的 “新民”理想人格中。
《新民说》以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为主要纲领,其中又以新民德为核心和根本。在梁启超看来 “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1]121,“智之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1]209国民道德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梁启超以 “利国”为最大的公德。他将国民道德分为 “公德”和 “私德”两个部分,承认公德与私德 “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62,但更强调公德,将公德的缺失视为导致中国日益衰弱的主要原因,强调实现国民性改造、培育新民的根本在于提高公德。梁启超的 “公德说”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或群体主义倾向。“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1]65“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1]66德的根本在于利群,在于维护国家利益。群体 (国家)的利益是道德善恶判断的标准,有利于国家的即为善,无益于国家的即为恶。因此,可以说利国就是新民的最大公德、最主要的人格特征。为了强调国民利群、利国的义务,他甚至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认为 “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1]64家与父母一样,对个人恩重如山,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对于个人而言利国是天经地义的。“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当其二者不兼之际,不爱己不利己不乐己,以达爱群利群乐群之实者有焉矣!”[1]104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个人应该做出自我牺牲。
梁启超指出 “有国民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1]68只有具有国家思想的人才能称为国民,也只有国民才能组成国家。对于什么是国家思想,梁启超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68在个人之外还有国家,个人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朝廷之外还有国家,朝廷并不是国家,而只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要严格区分朝廷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国家是人类群体的最高形式,国家高于世界。自私也应私于国家,博爱也限于国家,一句话,人们应将情感全部寄予国家,并献身于国家。由此可见,梁启超的 “国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国家至上”和 “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理论。在 《论权利思想》、《论义务思想》和 《论政治能力》等篇目中,梁启超也是以国家主义思想作为立论依据。总而言之,梁启超对新民人格的塑造完全以 “利国”为灵魂和精髓。
在此,梁启超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强调,对国家理想的信奉,已超出权宜之计的考虑。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被颠倒,作为目的的个人利益不再具有独立价值,而被完全消解在国家之中。不过,正如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所言:“概而言之,梁的阐述以个人为出发点,以国家之优位为归结。由于国家与新民并无矛盾,当他的国权和民权论从 ‘国民’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民权主义,从 ‘国家’展开时就倾向于国家主义,可以说有两个轴心,正像椭圆有两个焦点一样。”[2]国家主义思想和民权主义思想并存于梁启超思想中,只不过救国图存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国家主义必须优先。只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存在,民权主义也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
二、国家主义倾向的缘起和归旨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缘起于他对救国图存、兴邦振国之道的探索,发轫于流亡日本期间受到的理论和现实的冲击。在此期间,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从民主共和到开明专制、从卢梭 “民权主义”到伯伦知理 “国家主义”的转变。
首先,时代背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正值中国文化衰弱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取经,探索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良方。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争取民权,维护人的自由、平等。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惨死,使得梁启超看到了清政府顽固派的腐朽与残暴。流亡日本期间,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代,此时日本高昂的民族主义精神震撼了梁启超。按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所言,1903年历时7个月对美洲大陆的考察,不仅没有加强梁启超对民主共和制度的信心,反而让他看到了民主共和制的各种弊病,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实行必须有其产生、发展的条件。此外,他在北美考察海外华人社团时所看到的状况,如家族主义和政治冷漠等,又使他对华人在民主社会中所可能的作为感到失望。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使得梁启超失去对民主共和制的信心转而 “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3]169。梁启超在对中西竞争本质进行分析时,认为欧洲国家及日本崛起的根源在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将民族主义视为实现国家复兴的原动力,更将实行民族主义视为本民族抵抗列强的唯一对策。
其次,理论背景。近代意义上的新民思想,最早由严复提出。1896年严复在 《原强》中提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4]严复的观点,可以说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先导与基础。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得自于 《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描绘了一幅近百年来西方各民族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的历史画卷。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大量接触和阅读西方的书籍译作,吸收了很多西方启蒙思想。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观点成为他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5]而对于新民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倾向,学界普遍认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经历了一次由卢梭的 “民权主义”到伯伦知理的 “国家主义”的思想转变。如张朋园、张衍前认为,1903年10月前梁启超主要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而游美归来后,思想突变,转而支持与民权主义相对立的国家主义。张灏认为在1903年2月赴美之前,梁启超思想中已经有了国家主义倾向,而游美之后对国家主义的热衷,不过是 “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最终发展”[3]169。笔者赞同张灏的观点。根据对梁启超著作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几乎是同时接触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学说,只不过在赴美之前对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视,但不能否认没有国家主义思想倾向。
对于卢梭的思想,梁启超在 《卢梭学案》一文中,有过明确的解释:“卢梭以前诸学者,往往以国民之主权与政府之主权,混淆为一,及卢梭出,始别白之。以为主权者,惟国民独掌之,若政府不过承国民之命以其意欲之委员耳。”[6]而对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的认知是 “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7]显然,“转向”发生在两种国家观之间,一种是主权在民、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民权主义”,另一种是国家至上、权威主义取向的“国家主义”。对于这两种思想倾向,梁启超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做出了评价和取舍,指出两种学说是相对立的,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时代。相比较而言,伯氏的国家主义思想更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并大胆预言国家主义学说乃未来大势所趋。当然,这种思想转向,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完全放弃了 “民权主义”。在 《新民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权主义的痕迹,看到他对自由、平等、民权等思想的肯定和认同,对专制、集权的批判。民权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时并存于梁启超的思想中,两者处在不断的矛盾与冲突中,而这种矛盾冲突正体现了历史的尴尬和矛盾。
三、国家主义倾向的价值与意义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既保有中华民族的优秀特质,又具有近代公民的基本品格;既具有民权主义的思想倾向,又具有国家主义的人格特质。《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初的 “人权宣言”,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道德革命历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首先,梁启超所设想的新民是集道德人与政治人于一身的国民,而由之组成的国家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以民族认同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时过境迁,民主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主体,国家主义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民主、自由等理念相悖,但它对民族认同、对政治德性的强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梁启超对公德的强调,某种程度上使 《新民说》成为一种道德论,使新民成为一种道德人。然而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使得他所提倡的公德并不是纯粹的伦理德性,还是一种政治德性;新民不仅是道德人,还是政治人。梁启超对新民这一理想人格的塑造,既有对西方民主社会公民理念的借鉴,又因其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强调而有所突破;既有对儒家 “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批判与否定,又因其对私德、对儒家修身养性之道的肯定而有所继承。新民不仅要具备独立的人格系统,更要具备政治素养,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独立的人格系统的培养只是手段,国民的爱国心、责任感亦即公德的培养,才是最终目的。因而,梁启超所设想的以新民为主体的国家,既区别于传统儒家以仁为中心的道德理想国,也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为中心的公民社会;它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确切地说,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以民族认同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
其次,国家主义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近代中国,内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部列强林立、丧权辱国,急需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以国家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第一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个人的自由与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中。抽象地脱离于国家的个人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作为生活在专制制度羁扼下的国民,不能不要求民主和自由;而作为面临西方列强侵略、面临亡国危险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国民,则不能不急切地要求国家的强大。不实现我国民 “固有之民族主义”,则无以抵制他人的帝国主义。实行国家主义并不意味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不重要,而是跟国家的统一与秩序相比较,应该处于次一级的地位。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国家主义的正当性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国难当头之时,国民自当为国尽责。但在和平时期,尤其是现代社会,只有当国家能够真正代表国民的利益和意志、也即具有政治价值和正当性基础时,国家利益至上才是合理的。
[1]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86.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M].崔志海,葛夫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4]严复.严复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88.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8.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89:88.
-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梁启超社会公德思想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