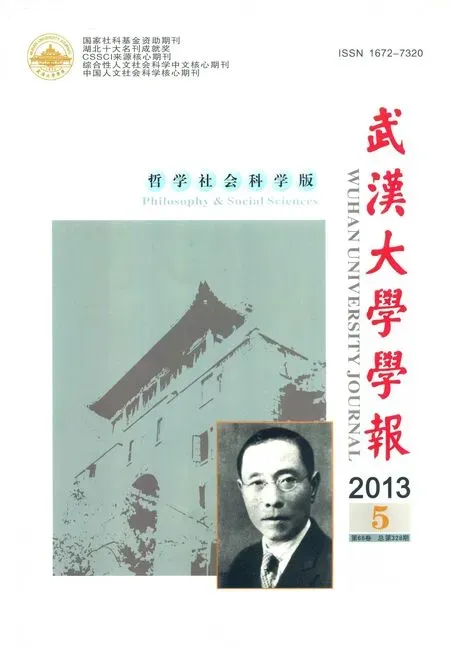“资源诅咒”:资源丰裕地区的社会稳定困境——以X矿区为例
曾 明 夏毓璘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资源丰裕的地区,可以依靠其资源优势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发现,资源丰裕的地区,它的发展水平反而会比那些没有什么重要资源的地方要差。这一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资源诅咒”,即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大多从事对自然资源的简单加工,仅仅靠发展初级产品就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因而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经济的长远发展方面都不及资源贫瘠地区(Auty,1994:11-26)。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资源丰裕会产生荷兰病(Corden & Neary,1982:825-848),产生经济停滞(Sachs &Warner,1995:5398)、社会冲突(Fearon & Laitin,2003:75-90)、脆弱的政治制度(Collier & Hoeffler,2005:625-633)等。中国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资源诅咒(Zhao & Xing,Li,2008:7-29)。在资源丰裕地区容易产生一种“小富即安”的社会文化,导致该地区的居民难以接受新事物、缺乏竞争意识(付英、靳利飞,2011:6-11)、寻租腐败现象严重(徐康宁、王剑,2006:78-89)等。这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现象引发我们去思考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资源丰裕会带来社会稳定问题么?即在社会稳定中是否也会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
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当今中国,它还有着特定的政治含义和政治背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①详见2006年10月18日新华社发《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各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维护稳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项,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学术界也对此极为关注,有关社会稳定方面的学术文献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对群体性事件、抗争政治等的研究。大量的文献集中在对社会稳定产生机制和维护稳定中的参与者,如上访人员(胡荣,2007:39-55)、各种抗争性事件中抗争者的研究(于建嵘,2010年),也有学者关注边疆地区(胡联合、胡鞍钢,2008:164-174)、农村地区(温铁军、郎晓娟、郑风田,2011:66-76)的社会稳定状况。
有些文献关注到了自然资源对社会稳定的影响。Paldam的研究表明,资源产业的繁荣使得该产业出现高工资和高福利,从而挤压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甚至引发罢工运动和政治派别的争斗,带来不稳定(Paldam,1997:1-43)。Welsch利用1989-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矿产资源禀赋增加了国内暴力冲突的风险(Welsch,2008:503-513)。但 Wick和Bulte认为,自然资源与暴力冲突密集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自然资源既可能加重也可能缓和暴力冲突(Bulte & Damania,Deacon,2005:1029-1044)。
在中国经验研究中,刘燕舞通过对中国一个村的农村集体行动个案的研究发现,土地本身并不是引发农村矛盾的关键,而是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利益才真正触动了农民利益诉求的冲动(刘燕舞,2009:59-63)。吴毅通过一起石场采石权的利益之争,发现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吴毅,2007:21-45)。Zhan用比较案例分析方法对贵州瓮安事件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县域治理中确实存在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现象(Zhan,2010)。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文献中仅有的把自然资源当作社会稳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我们将采用过程追踪的个案研究方法,以江西省X矿区为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即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自然资源的丰裕是否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它又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呢?
一、过程追踪研究方法与X矿区介绍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中的过程追踪方法,即通过考察个案中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个案结果来探究系列事件或决策的过程(Alexander &Bennett,2005)。通常做法是将连接自变量(原因)与因变量(结果)间的因果联系的中间环节分解成更小的步骤,然后寻找每一环节在个案中的可观察到的证据(Van Evera,1997)。如果现实中能够发现这一因果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则可以从经验上来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文将提出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理论,即在资源丰裕和社会稳定压力间建立一个因果联系,然后分解这一因果联系间的中间过程,也就是资源丰裕是如何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我们把社会稳定事件作为结果,而把资源丰裕作为它的原因,通过了解从原因到结果的一系列过程的中间机制来考察资源丰裕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预言与个案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否一致或是不一致①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成果有scokopol对社会革命的研究以及Collier &Collier对劳工组织的研究。详见Skocpol,T.(1979).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ollier,R.B.& D.Collier(1991).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Critical Junctures,the Labor Movement,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资料的收集采用深度访谈和文献收集法,作者和南昌大学研究生肖清丹、祝晓辉、饶磊于2012年3月底多次到X矿区,对矿区的矿务局领导、矿区信访办主任、工农办主任、综治办主任、社区管委会主任等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本文的相关资料都来自这些调研成果。
X矿区属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地处江西省F市,由河西、河东两大矿区组成,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周边有ST镇、QJ镇、SZ镇以及T乡,是大型国有煤炭企业。X矿区现有6对生产矿井,年生产能力280万吨,1对90万吨在建矿井将于2014年上半年投产。属传统资源型优强企业。2011年,矿井年生产原煤在300万吨以上:全年工业产值为26.87亿元,利润总额为4.06亿元;全年应缴税费总额为4.21亿元,其中增值税2.4亿元,营业税25.91万元,资源税672.71万元。按照税收属地化原则,矿务局所有应上缴税费都算作F市的财政收入。
X矿区局机关所在地ST镇,1971年划归X矿区管辖,在2008年时划归F市管理。该镇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在未移交给F市管理之前,一直是由X矿区进行管理,ST镇周边所属村民的管理工作也一直由矿区进行。农业税未取消时的2005年以前,X矿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所属村民的农业税一直由企业代缴,同时企业还负担了附近村民的工作安排。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得周边村庄的生活负担明显比其他村庄要低。自X矿区1950年代建矿以来,兴建了学校、公路,提高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即使在划归地方后,矿区仍一直担负着为周边村民低价供水、供电的任务。
X矿区大部分矿工属合同制职工,收入水平根据工作种类的不同,差距非常大。除矿工一般在外省招聘外,地面单位的工人、管理人员一般都是职工子弟,会在规定的范围内给职工子女就业优惠。
由于开采时间长,X矿区的表层煤矿已经开采完毕,煤炭挖掘已经进入了深度挖掘的阶段,较浅的深度也有500-600米,最深的深度已经到了地下1000米。小煤窑不具备深度挖掘的实力,因此近年来,未出现与小煤窑之间的冲突。
二、资源丰裕到社会不稳定的中间过程的理论分析
本节将要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资源丰裕地区会产生因资源禀赋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的中间过程。这一中间过程是:X矿区的矿务局作为国企,与政府一样承担着维稳的属地化管理责任,刚性的维稳压力成为一些农民要挟政府和企业的砝码,大型国企成为“唐僧肉”,矿区农民因此产生了“吃资源大户”的心理。同时,煤矿生产可能引发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更使得矿区容易发生维稳事件。
通过严厉的政绩考核机制来实施的刚性维稳制度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矿区维稳的压力。这种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的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不稳定现象,如社会抗争等行为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措施进行压制(于建嵘,2010:38)。追求晋升是中国官员最重要的效用函数,在当前“向上负责的层层委任制”的官员晋升体制下,上级政府通常会通过政绩考核来实现对官员能力的甄别(周黎安,2007:46)。而“一票否决制”是其中最严厉的官员晋升门槛。虽然政绩优秀者未必会获得升迁,但“一票否决”制度的要义就在于一旦属于一票否决考核的工作内容出现问题,将直接导致该年度或以后的绩效考核和晋升考核无法通过,被一票否决者将不能升迁,这对官员行为会产生非常大的约束作用(曾明、任昌裕,2012:4)。当前,中国的维稳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要求尽可能地将社会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基层,强调“谁的孩子谁抱走”,各级政府为应对维稳压力,对社会稳定采用“一票否决”制,而且实行了严格的量化考核制度,使得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这样的政策压力会迫使基层政府、官员对社会稳定和综治工作极为谨慎和重视,尽量调解与群众间的矛盾。但当矛盾难以调和时,地方官员奉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做法,会迫于上级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压力而选择 “赔钱”妥协(曾明,2011:81)。
从近年来各种上访、缠访、闹访的案例来看,虽然不排除很多群众上访是由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直接侵害他们的利益而产生,但也有很多信访群众已很好把握了中央的维稳政策和地方官员的“不出事”逻辑(贺雪峰、刘岳,2010:36),因此只要地方政策不合意、各种矛盾处理不合理,他们就有了上访理由,很多上访群众会选择向更高级别的县-市-省-中央进行上访,或者采用更加激烈的上访手段比如静坐、游行、自焚等方式以博得媒体的报道、网民的支持和更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有时上访已经成为了某些闲散人员谋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他们认为官员迫于民间舆论压力和上级晋升压力并不敢把事情扩大化,也不会“难为”他们。很多上访专业户甚至以此谋利(贺雪峰,2011:71)。
在这种刚性维稳模式下,自然资源的丰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中间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矿区企业一业独大带来的“吃大户”心理。自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本,但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并不能够使其他生产部门共同分享它所带来的利益,反而会因为它的繁荣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因为它会提高同一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抬高物价水平,形成经济发展中的“荷兰病”,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影响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诅咒,Sachs和 Warner对1970-1989年间世界石油资源国家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Sachs & Warner,2001:827-838)。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经济丰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低于资源贫瘠地区(Zhao &Xing,Li,2008:7-29)。而经济发展的差距势必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特别是直接产生矿产资源部门与其他部门,比如农业生产部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收入差距容易使低收入人群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对于一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来说,往往是矿区一业独大,特别是在中国,国有矿区的规模都比较大,很多矿区都是国家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资产雄厚,下属企业单位众多。而矿区经济发展的收益大多归属政府和企业,地方公众受益有限。即使在X矿区有多种对周边群众的补偿方式,但他们的收入与矿区相比还是有差距。周边群众很容易产生“吃大户”心理,即国有企业规模巨大,资产雄厚,产权又归属于国家,国企负责人只是作为代理人角色出现,这种缺乏明晰产权的巨大国有资产就成为周边一些群众心目中的“大户”。这种心理与居民对政府官员的 “一票否决”维稳压力的了解、对官员心理的掌握相结合,维稳就成为居民上访、闹访进而获得利益补偿的筹码。如在X矿区,访民的上访成本并不高,而只要无止境的上访下去,官员迫于晋升考核、业绩考核压力,终究要做出让步、赔钱解决的。因此,上访对访民而言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第二类是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产生的居民利益受损。矿区周边居民的利益受损主要有两类,一是环境污染影响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二是矿产资源的开采产生的地面下陷等引发的房屋开裂。自然资源在开发、开采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灰尘,都是影响着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污染源。当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污染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健康和农业生产时,居民通常会通过上访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双方立场不一致,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往往会采取越级上访或者更加过激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从而对该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产生强烈的冲击。
从制度角度来看,关于资源收益的分配安排会对社会福利的产出产生重要影响(Bulte &Damania,Deacon,2005:1029-1044)。按照中国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安排,所有的自然矿产资源都属于国家。在1994年新的《矿产资源法》实施以前,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企业都属于国有,这些国有企业并没有对当地居民提供补偿(张文驹,2000:4)。由于自然资源收益无法在当地居民之间进行平均分配,但当地居民要承受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污染,必然会心生不满。再加之自然资源在开采的过程中势必会对居民的生活、生产活动产生影响,产生社会冲突在所难免。胡联合等人关于社会稳定矛盾变化态势的实证研究就发现,环境污染是主要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胡联合、胡鞍钢,2008:170)。孙庆刚、秦放鸣以新疆为个案研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现象时也发现资源丰裕会带来环境生态的恶化(孙庆刚、秦放鸣,2010:74-79)。
三、资源丰裕到社会不稳定的中间过程实证检验
本节将通过对X矿区维稳现状的实证分析,说明在矿区,因环境的破坏、污染和周边村民存在的“吃大户”心态影响着矿区的社会稳定。
X矿区在地理环境上被ST镇、QJ镇、SZ镇、T乡包围着,与周边村庄的纠纷、冲突十分常见。这些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十分广泛,开采造成的污染、沉陷、房屋开裂是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偶然事件引起的纠纷,像医疗纠纷、基建工程等。这些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村民由此而产生的利益诉求有些确实是矿区的责任,有些可能与矿区无关但也会向矿上寻求补偿。用矿区工农办主任的话说,“那是小事天天有,大事三六九”①局工农办主任访谈时原话(访谈纪录12-3-26-11)。。每天应付工农纠纷成为矿区工作的常态。
从管理体制上来说,X矿区的处境十分尴尬。由于是国有控股企业,因此国家对矿区的社会稳定也有硬性规定,也是按照“一票否决”制对矿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考评。但矿区隶属省煤炭集团,而周边乡镇目前都隶属于X矿区所在的F市。X矿区对周边乡镇已经失去了行政管理权力,对与村民产生的各类矛盾需要通过镇政府及村委会协助进行处理。而F市和各乡镇同样面对维稳的考核压力。对于F市来说,最大的稳定就是不产生越级上访。为避免激化矿区与村民之间的矛盾,F市通常对与X矿区有关的社会矛盾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矿区不属F市,所以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或上访事件,不管是否属于矿区的责任,F市政府一般都会要求矿区进行适当赔偿,以化解矛盾。这一方面增加了X矿区处理这类工农关系的难度,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村民的“吃大户”行为。
为应对第一类情况所引发的矿区维稳压力,X矿区每年用于村民补偿方面的费用通常在1000万元以上。矿区每年按照农作物市价给予三镇一乡村民污染减产补贴,每户按照所拥有的稻田亩数和减产数量核算,补贴款由矿区直接转账给乡镇,再由乡镇、村小组按照每村的人数、土地亩数、受污染情况进行分配。矿区周边农村的农田抛荒问题十分严重,尽管农民不种地但矿区每年仍然要进行赔偿。事实上,X矿区的环保投入每年都以高额的数目增加,很多矿井的污水已经达到了能够循环利用、零排放的水平,灰尘、烟尘等污染也并不会对粮食生产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但是,矿区也不能因此不给或者少给周边村民污染补贴,否则村民会以污染土地无法耕种为由向矿区要求补偿,很可能发生不稳定事件。矿区电厂每年的烟气污染补贴42万元,由X矿区补贴给乡镇再由乡镇按照每户受污染影响的情况下拨。对于不同的区域,矿区也有不同的赔偿标准。就河东、河西的乡镇来说,河东村民民风比较剽悍,因此赔偿额度也就较高一些,按照680元∕平米核算赔偿;河西乡镇按照480元∕平米进行赔偿(对于不同的受损程度还有不同的认定)。河西的村民们原来也想按照河东的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但矿区工农办的态度坚决,一直没有妥协,“河西的村民民风要纯朴些,闹了几次没效果后也就不闹了”①矿区工农办主任访谈(访谈纪录12-3-26-10)。,所以还是按照比较低的标准进行赔偿。在处理赔偿的过程中,赔偿的额度不能轻易变动,因为各个村庄、乡镇的村民会自发地对赔偿额度进行互相参照、攀比,稍有不同对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带来更大的危机。
在这些常规的赔偿之外,矿区还要面对由于房屋开裂、下沉、污染等原因引起的赔偿事件。如2010年矿区开采造成QJ镇敬老院房屋开裂,由QJ镇政府出面协调,要求矿区赔偿180万元,经过工农办工作人员的现场勘查,发现该敬老院房屋陈旧年久失修;且房屋质量不好,没有地基和屋梁,但敬老院的房屋开裂确实是由矿区煤矿开采带来的地壳变化而造成的。由于房屋本身质量就存在着问题,经过工农办与QJ镇政府的协商和调解,最终矿区向QJ镇敬老院赔偿了65万元。
为应对矿区复杂和经常性的社会不稳定形势,矿区专门成立了处理矿区与周边乡镇农民关系的工农关系办公室。目前,全矿区从事工农关系工作人员有29人,局工农办8人,其他的各矿、公司共有21人。一般工作流程是农民向相关单位的工农办反映问题,矿工农办报告到局长,局长再签到分管副局长,再由分管副局长交由局工农办处理。工农办的最重大职责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在解决好群体性事件或是村民上访事件的同时,尽量降低企业的赔偿额度。在整个协调的过程中,工农办需要详细了解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整体判断,在协调和沟通的过程中寻找降低赔偿金额的突破口,如果无法避免赔偿就要将赔偿额度控制到最低,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第二类维稳压力主要来源于X矿区附近乡镇居民对矿区存在的“吃大户”心理。一种是直接向矿区企业要补偿。因为X矿区是周边地区,也是所在的F市最大的国有企业,职工众多,占地也广,经济效益又不错,这就成为周边村民心中的“唐僧肉”。他们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要求赔偿、资助。
另一种“吃大户”方式是在矿区欺行霸市。本地村民多在矿区开店、接工程、建打渣场、搞煤炭运输等获取收益。矿区筹建的道路、房屋工程,在附近村民眼中也是炙手可热的“生意”,时常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承包。通常由附近村民承包的项目,不仅工期长、质量差,而且要价也十分高,所以矿区并不愿意与其合作,一般都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建设,因此附近村民也常常因为接不到工程而在矿区打架、闹事。矿区为职工建设的棚户区改造房,本地村民就时常强行要求职工必须雇用其装修和搬运队伍。
据矿区职工小区四期正在装修的职工L女士说②与矿区社区办主任的访谈(访谈纪录12-3-27-9)。,她的房屋在进行装修时由于材料是由朋友帮忙搬运的,附近的C村村民就曾经找到她,要求她支付搬运费。L女士当然不同意。C村村民称小区的土地是C村的,所以装修的搬运工程必须由他们来做,即使不是他们做的也需要向他们交费。C村村民的搬运费用比一般的搬运工要贵上许多,在搬运时对货物也很不注意保护,经常撞坏、摔坏,所以职工都并不愿意与他们合作。L女士反映小区里很多家庭装修碰上了C村村民的阻挠,如果不交钱给C村人,他们便天天上门妨碍装修,很多人家迫于这样的软磨硬泡都交了钱。
以上的分析表明,由于资源开采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矿区的维稳压力和成本非常巨大。另外,矿区确实存在村民把矿区当作“唐僧肉”吃大户的现象。
四、结 论
通过过程追踪的个案研究方法对江西省X矿区的社会稳定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资源贫瘠地区相比,自然资源丰裕的X矿区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工农矛盾更加激烈。由于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了“资源诅咒”效应,即资源的丰裕使得该地区的社会冲突更多。
X矿区与周边村民有邻里关系,出于对维稳的考核和生产的需要,矿区十分重视与周边三镇一乡的工农关系,会主动对他们进行制度化的补偿。由于开采导致周边乡镇居民房屋塌陷、下沉、开裂的,矿区都会对村民房屋进行估价赔偿。在考虑社会稳定和生产顺利进行的情况下,X矿区时常还要做出让步。矿区职工大多愿意配合周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但是,矿区的社会稳定状况仍然极为脆弱,任何涉及利益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矿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这样的社会稳定状况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有着必然联系,资源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诱饵”,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多对利益渴望的眼睛,他们时时想获得资源开采的收益。X矿区的大多村民认为现有的利益分配不合理,他们无法享受到自然资源应有的收益,因此都有“吃大户”心理。在矿区刚性维稳的压力下,他们会通过影响矿区维稳考核的方式,希望以污染赔偿、房屋损坏赔偿或其他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会在生活中搜寻一切能为他们带来好处的“项目”,通过各种途径向矿区施压,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会通过闹事、上访等影响社会稳定考核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对于矿区的社会稳定问题当地政府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要求矿区让步,甚至周边乡镇政府本身也有吃大户的心理,期望从矿区获得利益。这进一步增加了矿区维稳的压力。
[1]付 英、靳利飞(2011).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社会学解析.资源与产业,2.
[2]贺雪峰(2011).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以农民上访为问题意识之来源.天津社会科学,4.
[3]贺雪峰、刘岳(2010).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6.
[4]胡联合、胡鞍钢(2008).民族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分析.人文杂志,2.
[5]胡 荣(2007).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3.
[6]刘燕舞(2009).农民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一个分析视角——以豫东曹村8队农民集体行动为个案.长江论坛,3.
[7][美]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
[8]孙庆刚、秦放鸣(2010).“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传导机制研究——兼评《“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经济问题,9.
[9]温铁军、郎晓娟、郑风田(2011).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基于100村1765户的调查分析.管理世界,3.
[10]吴 毅(2007).“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5.
[11]徐康宁、王 剑(2006).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1.
[12]应 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
[13]于建嵘(2004).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
[14]于建嵘(2010).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15]张文驹(2000).我国矿产资源财产权利制度的演化和发展方向.中国地质矿产经济,1.
[16]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7.
[17]曾 明、任昌裕(2012).政绩晋升效应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一个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3.
[18]曾 明(2011).稳定压倒一切下的乡镇政府——江西省J镇的经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9]Alexander,G.L.& A.Bennett(2005).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MA:MIT Press.
[20]Bernstein,Thomas P.& Xiaobo Lv(2000).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Peasants,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163.
[21]Bulte,E.& R.Damania,R.Deacon(2005).Resource Intensity,Institutions,and Development,World Development,33(7).
[22]Chen,Feng(2003).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Resistance in China”.Modern China,29(2).
[23]Collier,P.& A.Hoeffler(2005).Resource Rents,Governance,and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49(4).
[24]Fearon,J.D.& D.Laitin(2003).Ethnicity,Insurgency,and Civil Wa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7(1).
[25]Mcadam,Doug &John Mccaethy,Mayer Zald(1996).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n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O’Brien,Kevin J.& Lianjiang Li(2006).Rightful Resistance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Paldam,M.(1997).Dutch Disease and Rent Seeking:The Limits to Growth Revisite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
[28]Pei,Minxin(2003).Rights and Resistance: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In Perry,Elizabeth J.&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 Curzon.
[29]Auty,R.M.(1994).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Six Larg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World Development,22(1).
[30]Sachs,J.D.& A.M.Warner(1995).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31]Sachs,J.D.& A.M.Warner(2001).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45.
[32]Tilly,C.(1976).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n Modern Europe.In Spielberg,Joseph &Scott Whiteford(eds.).Forging Nations:A Comparative View of Rural Ferment and Revol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33]Van Evera,S.(1997).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4]Welsch,H.(2008).Resource Abundance and Internal Armed Conflict:Typ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Incidence of“New Wars”.Ecological Economics,67(3).
[35]Corden,W.M.&J.P.Neary(1982).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The Economic Journal,92.
[36]Zhao,Dingxin(1998).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3(6).
[37]Zhao,X.B.& L.F.Xing,X.P.Li(2008).Resource Abundanc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Economics of Transition,16(1).
[38]Zhan,J.V.(2010).Natural Resources,Local Governance,and Social Instability:A Comparison of Two Counties in China.APSA 2010Annual Meet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