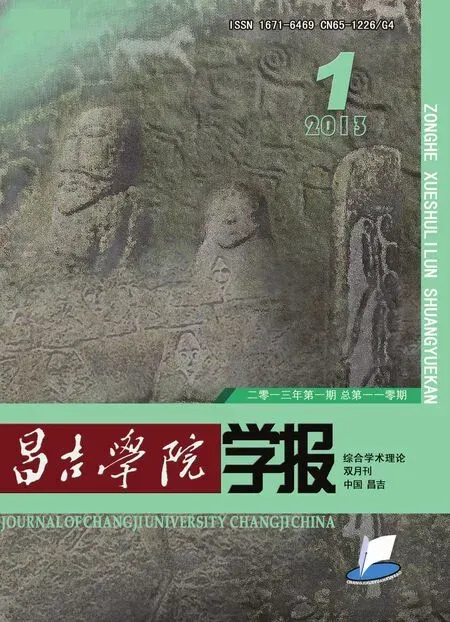真实的荒诞——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吴艳艳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8月7日,刘震云推出自己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再度成为文坛焦点。这两部号称兄妹篇的作品,让刘震云一度成为了近年来文坛的焦点人物。对其书、其人的评论也纷至沓来。白烨的《刘震云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越绕越丰富》、徐兆寿《人学的困境》、黄德海的《平面化的幽默陷阱—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等等。几乎每篇文学作品一出版发行,它的评论便随即而来,褒贬不一。笔者认为每一部新作出来都会遭遇这样的待遇,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一个叫李雪莲的农村女性二十年上访的故事:李雪莲与前夫秦玉河为了生二胎躲避计划生育的罚款,两人决定先假离婚,等孩子生下来再复婚。但离婚后,秦玉河娶了新的妻子,抛弃了李雪莲和亲生女儿。李雪莲为了把这一件事情说清楚,引出了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上访一圈没有结果,李雪莲回头找秦玉河,却被前夫冠上“潘金莲”的恶名。正是这句话造成了李雪莲后来二十年的上访结果。先前为了讨一个说法,现在转变为要还自己一个清白,遂把上访告状当成洗清不白之冤的惟一手段,成了一个不屈不挠上访二十多年的告状专业户,从镇里到县里,从市上到省上,各级领导都被她不时牵动,成了地方的“老大难”。故事很简单,刘震云却用17万字来讲述这个简单却又不简单的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
我们说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却往往比现实更有真实感。刘震云就是在这种理想化的虚构中,在严肃与荒诞、真与假、虚与实的交错中,用这个荒诞不羁的故事来塑造真实的社会生活,展现底层社会的生活境遇与尴尬。
一、结构的布局
褚斌杰在他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道:“作为一种文体的序,其性质或功能是对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作说明,或以议论为主,或以叙述为主,或二者兼备;其名称尚有“引”、“题词”等。【1】正常情况下,序言要少于正文的字数,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序言:那一年;序言:二十年后;正文:玩呢。令读者惊讶的是序言部分占据了文本的十八分之十七,正文只有十八分之一,完全颠覆了正常的文本结构方式。在序言部分,作者讲述了导致李雪莲上访的各种原因及最后上访的结果。正文部分,作者讲述史为民的一个生活小片段。在读者的观念里,这种结构是不能运用在文本中的,但在刘震云这里,颠覆了固有的文本结构格局,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结构,令读者眼睛一亮。不管这种结构会不会在以后的作家创作中成为摹本,但至少现在,成为刘震云文本一个新的标志。正文部分的标题为:玩呢。更出乎读者意料范围之外,具有明显的荒诞意味。其正文所讲述的就是用荒诞的方式来对付生活中荒诞。史为民成功地在回家高峰期没票的情况下舒服地回到家,打上了麻将。为了“玩”麻将采用上访的伎俩,果然是不一样的玩。刘震云用这种别具一格的结构来讲述生活中遭遇的无可奈何,来告诉读者要用玩的态度来对待生活,这才是生存之道。
二、独特的标题
《我不是潘金莲》,初次见到此名称,读者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的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而一路读下来会发现文本与潘金莲几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就是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的一句话:“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2】也就是因为这句话才有了后来李雪莲20年的上诉生涯。新书发布会上刘震云自己也谈到书名的问题,他坦言到,“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反应,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我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书不好卖,出版社不干。”【3】一方面为了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刘震云借用这个书名,用深入浅出的形式来消解生活中的无可奈何。上访是件严肃的事,但故事的书名却取自古书中一个荒淫的女子姓名,通过这种对比,以此来表明人的生存之尴尬处境。全书只有几处提到“潘金莲”的字眼,而且是谈话中夹杂的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一路读下来,可能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李雪莲的上访,而是书目的名称。刘震云就是用这种荒诞的命名书名的方式来展示现实中的黑白颠倒的生活,用丑陋的名称来唤醒人性中的美好一面。
三、内容的理想化
前面说过,文本序言部分讲述一个农村妇女李雪莲的上访是为了把离婚这件事说清楚,讨个说法。结果为了讲清楚一件事要先讲清楚8件事,一件离婚案件扯出了其他的不同的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脱离了离婚原始事件。虚构的故事加上理想化的事件,刘震云将乡村民众生活的处境、遭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首先,从李雪莲自身考虑,她有儿子,还有个3个月大的女儿,孩子小,根本离不开母亲。另一方面,20年的上访生活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坚持下来几乎不可能,女性的韧性大大扩张了。其次,文本中李雪莲20年的上访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避免,先是董宪法的“刁民”、“滚”惹恼了李雪莲,接着是荀正义喝酒、史为民为了剪裁选择躲避,其中关键人物是秦玉河。在找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均无结果后,李雪莲重新回头找秦玉河,只是为了一句话,“世上有一个人承认她是对的,她就从此偃旗息鼓,过去受过的委屈也不再提起。”【4】但秦玉河为了一己的利益,没有顾念往日的夫妻之情,打断了李雪莲的唯一念想。本来可以避免,可以简单说清楚的一件事,刘震云却没有让它简单结束,绕出了后面的17万字的故事。20年后李雪莲决定不再上访,但王公道、郑重却不相信这是真的,硬是把一个人真实的内心颠覆了,把一件假想中的事情变成真的,逼着李雪莲将上访的事情进行到底。李雪莲上访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赵大头。他为李雪莲的上访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在以后的20年里,他仍然是上访的关键人物之一。赵大头帮助李雪莲逃跑上访,在读者和李雪莲的眼里,赵大头是真心为了李雪莲,但刘震云却笔头一转,写了赵大头是为了一己之利帮助李雪莲。故事的结局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处于情理之中——秦玉河死了,李雪莲上访的最初或者最终的被告对象不在了,这个上访便不了了之。秦玉河的死、赵大头的欺骗让李雪莲踏上了自杀的道路,自杀未遂的原因却是果园主人希望李雪莲帮忙,到其竞争对手的果园自杀,李雪莲的自杀的念头在果园主人荒谬的要求下烟消云散。
看过文本的人,都会发现另一个特别之处,文本中人物的名称。法院院长:王公道、法院的专任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等。他们在各自的职位上,结果却并没有像他们的姓名那样解决李雪莲的问题,只是徒有虚名。作者用这一反讽的手法来讽刺当前的社会问题,用一种非严肃的方式来讲述生活中严肃的问题。
故事的正文部分与李雪莲却无任何关系,讲的是史为民的故事,他用上访的理由成功地在春节高峰期回到家里打上了麻将。假的上访却成功地帮助了史为民解决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刘震云用这种荒诞的方式来解释如何对付生活中种种无可奈何,如何消解现实的困惑。
四、另类的叙述方式
读完《我不是潘金莲》,记忆中留下的不是故事的发展过程,而是关键性的几个事件。刘震云采用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讲故事。这里没有背景交代、没有环境和景物描写,也没有除事件相关人之外的多余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刘震云淡化了其他一切背景,只对故事的发展展开叙述,且故事没有高潮,一路平铺直叙下来,语言简洁流畅、对话风趣生动,人物形象简单明确,在主要人物之间来回旋转来讲故事。故事的连接靠各个片段直接拼凑起来,原生态保留各个片段,不加任何修饰。他用这种冷静、客观、旁观者的清醒来揭露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生存状态。
五、真假难辨
在一次访谈中刘震云说他想写的是“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用乡村的叙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虚拟的背面给出了一个真实的解释,以此来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却被前夫及老张等一伙人默认为是“潘金莲”,并且20年的上访也没有“洗刷”这个所谓的“恶名”。20年后李雪莲放弃上访,但没有人相信,非得把这件真事说成是假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真的,李雪莲再次踏上了上访的列车。上访中李大头对她本来是真的喜欢,可喜欢却最终变成了假的。秦玉河的死、赵大头的背叛,带着孤单和失望,面对无望和无可眷恋的人生,李雪莲选择了自杀,当初想让秦玉河死结果阴差阳错,自杀的是自己。李雪莲真上访,20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为民的史为民一次“上访”便得到自己想要的——回家赶牌场。这些黑白颠倒的事件和结局就在刘震云的笔下一一展示在读者们面前真假难辨,真可谓“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
六、荒诞的背后
荒诞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产物。它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现实中的荒诞是审美活动范畴中荒诞的根源,荒诞审美形态是对现实中荒诞人生事件以审美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尤奈斯库认为:“荒诞是指缺乏意义……他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意义,荒诞得无用”【5】。萨特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我们应该力求若不是维护它,就是改变它,——从而向未来继续前进。”【6】刘震云就是用这种荒诞的、戏谑的、真假难辨的叙述角度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思索。
序言部分李雪莲最后如何没有结果,刘震云给读者留下了一片空白,留给读者自己补充。让读者自己去填补这片空白的结果和意义。刘震云的作品多围绕历史、乡村权力、故乡展开,《我不是潘金莲》也不例外。刘震云用一个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揭露了乡村文明的破败:一、人性的缺失。秦玉河的不顾念旧情、老张一群人的默认让李雪莲感觉自己是孤独的,是异类,所以她必须把自己融入进这个世界,消除这种荒诞感。二、权力的滥用。从法院到镇长到县长到市长甚至省长、领导人,不作为的不作为,作为的却是一件荒唐的政治事件。人性一直是颇受关注的方面,刘震云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呼吁人性,来揭示人最根本的生存状态。他在沧海一粟的民众生活中挖掘出了人的生存本质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生活背后的人类生存的尴尬和权利的异化。“存在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是世界荒谬、人生孤独。每个自为的人在世界中遇到的常常是障碍、限制和奴仆。每个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生存境遇说。认为人的生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境遇中的存在,人并没有选择他的那种特殊境遇,但是发现自己受到一个陌生而敌对环境的压制和包围。在试图控制自己的境遇时,会碰到新的顽固限制。当人可以成功地改造并控制个别环境时,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他所不能应对的最基本界限,例如痛苦、孤独、罪恶、死亡。”【7】这位被称为“中国生活的批评家”的作家,就是用他过人的体悟和深刻的洞察来表达了人性丰富的内蕴并用他独特的笔成功地塑造出戏谑的效果。他用拧巴的故事来讲述扭曲的人生道路,揭示当下的现实问题,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痛苦和对现下社会的思考,为读者、更为社会提供了思索的平台。
[1]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78.
[2][4]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J].花城,2012,(5).
[3]刘震云新书发布会访谈
[5]伍蠡甫,林骧华.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林出版社,1983:358.
[6]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05.
[7]万海洋.荒诞境遇下的存在状态——刘震云小说的存在意义[J].名作欣赏,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