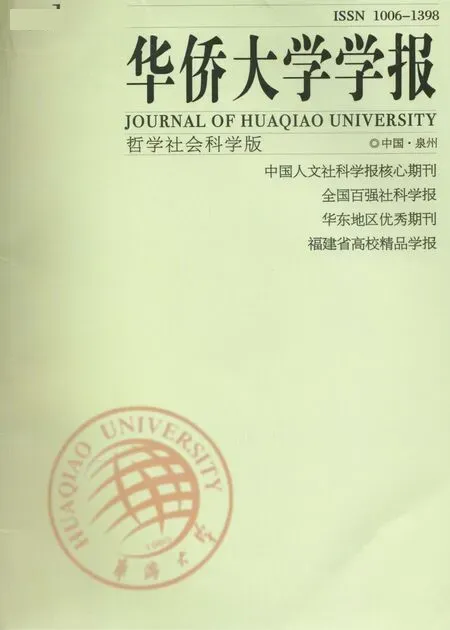《论语》诗“兴”之境的现象学解读
○李 乐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875)
诗,或者说《诗经》在儒家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推崇礼乐教化,先民诗乐舞完全一体,而诗在非舞蹈化的时代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墨子·公墨》批评儒家“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其语或有夸张,但《诗》在孔门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孔子看来,诗教是最好的教化方式。《礼记·经解》篇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而诗之所以用于教,根本原因在于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是《诗经·鲁颂·》中的一句诗文,孔子引之以为《诗经》乃全为真情流溢之作,是情感的最真诚的表露。所以孔子会用“不学诗,无以言”来勉励儿子孔鲤,还将“可与言诗”作为对弟子的最高称许。
每每孔子谈及诗之用,总将其与“兴”共论。《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兴”是最重要的“用诗”方式——诗歌之于人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通过“兴”来实现的,且这是人的自我完成的初始,“兴”于诗方可依“礼”而立,依礼而立方可在“乐”中获得人性的完足。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解释“兴于诗”云:“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1]104-105可见诗歌在个体成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价值就在于诗能够兴发人性向善的一面,使之自觉地艺术化地成人。张祥龙先生甚至认为:“孔子哲理的源头恰在于‘乐作’和 ‘诗兴’。”[2]69
一 “兴”的起源
在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兴的基本含义为“起”。《尔雅·释言》将“兴”释为“起也”,许慎《说文解字》说与《尔雅》同:“兴 (興),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在甲骨文中,兴写作,像四手共举一物,罗振玉最初将其释作“与”,商承祚与其意见相左,以为当释作“兴”,“乃兴字,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3]829。可以想见“兴”原是原始时代初民的集体活动:几个人合举着盘状物,绕其旋转,初民的身体也在旋转扭动,口中可能还呼喊着号子。这或者也是某种巫术形式的体现,是颇具神圣性的,因为上古时期巫术活动一般都是大型的载歌载舞,而参与进舞蹈中的人们则“如火如荼,如醉如狂,虔诚而蛮野,热烈而谨严”[4]11。故而兴的初义或是从上古时期的巫术中来,更确切地说是从巫术中娱神的原始歌舞而来。
巫术的舞蹈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初民内心情感的表达,是最原始的抒发胸臆表现自我的方式。《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说明舞蹈是最能全方位宣泄人类情感的方式。因此,兴是远古的生命力爆发,具有初步的艺术形态。故兴者,起也。兴,有感而起也;兴必与情感紧密关联。二是原始的舞蹈服务于神秘性的宗教活动,如《尚书·益稷》所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每一个舞蹈都折射着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诉求,所以在这种宗教仪式中舞蹈常常是具有情节的:或是对人间世的模仿,或是初民对神的活动的想象;因此舞蹈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象征意义。“兴”在舞蹈中的原始意象即是众人合力举起某物,故兴可得意“共举”,后来又获得了发端、发动、喜悦之意。
简言之,“兴”的意义在上古时期源于原始的生命活动及意识冲动。《说文》所谓“兴者,起也”,指的正是情之起——情感于自然万象而生,感于外物而起,且这种“升起”的情感,夹杂着原始宗教的成分,透露着最初的艺术精神,酝酿着中华民族将天地万物与人的情感合一的独特的艺术性思维方式。
二 《论语》中的诗“兴”
从文化溯源中我们得知“兴”乃情起之状,而回归到孔子的语境中,兴为何意?它乃是和孔子的诗教思想紧密相连的。在孔子的哲思中,诗歌之外是礼乐之境,是道德之境;而学诗正是通达礼乐道德之境的重要途径。《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教弟子:“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郑玄以为“歌《诗》,所以通礼意也。作乐,所以同成礼文也”。孙希旦更从《诗》之用的角度说明:“古人行礼之际,每歌《诗》以见志,不能《诗》,将有赋‘相鼠’、‘茅鸱’而不知者,能不缪于礼乎?”[5]1272这里我们如果忽略郑玄的过度分疏以及孙希旦对于《诗》通礼意这一层面意义认知的不足,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在礼乐文化中,《诗》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诗》的吟诵充当着催化剂的效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外交、礼聘等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从《礼记》中大量引《诗》为证、为兴的手法,我们可以看到《诗》与礼相通的一面。正如焦循《毛诗补疏序》所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6]689正是因为诗具有“感人”的效果,注定其于人发生作用的方式不是对象化的说教,而是润物细无声,是潜移默化。所以,孔子才教导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告诫自己的弟子即使熟悉《诗》,但如果“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希望弟子通过读《诗》引发对礼乐之境、道德之境的领悟,通过《诗》而彻悟诗外之世,这是他诗教的大意境,即是“兴”的大意境。
《论语》历代注疏对“兴”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立身成德来展开的。“兴于诗”一句邢昺疏云:“此章论人立身成德之法。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学《诗》。”[7]2487他认为“兴”于诗歌之兴为起始之意,即学诗是修身成性的初始。朱子《论语集注》讲“诗可以兴”时,“兴”被解为感发志意、涵养性情的接受活动。郑浩《论语集注述要》则以为:“兴之为义,因感发力之大,沁入于不自知,奋起于不自已之谓,是惟诗歌为最宜,教者宜如何慎重选择。”[8]529郑氏以为,《论语》教人学诗,必定除去不关教化之淫诗。兴于诗,乃是指诗歌之教孝便可以兴于孝,教贞便可兴于贞,兴于善则恶不期远矣。兴在此被理解为感化熏陶,导引人的精神方向。从各家解读我们可以看出,《论语》中的“兴”是复义的,其意义指向涵括三个重要方面:“怡养性情”、“激发心志”和“教化善恶直曲”。
我们仔细揣度就会发现:无论“怡养性情”、“激发心志”还是“教化善恶直曲”,讲述的都是诗“兴”于人可达成的效果,可是“兴”和“立”、“成”、“观”、“群”、“怨”一样,在《论语》中都是以动词形式出现的,它的含义中必定暗含人直接遭遇诗时那个充满意趣和动态感的过程描述。“兴”的过程是人面对诗歌的时候当场生成的,而性情得以怡养、心志得以激发、人们懂得善恶曲直在时间轴上都在那个充满意趣的过程之后,是人们对“人遭遇诗”这个过程做出反思后注入“兴”的阐释里的,但最原初的过程“兴”总是充满当场构成意味。
三 现象学启示下的“兴”之反思
现象学是一种方法,其基本态度是无立场、无预设判断,回到事物本身进行直观。其代表人物胡塞尔在讨论人的认知时指出,我们所关注的东西,焦点旁边总是有个边缘域。我们去审视去认知某个对象时,总比任何实在的当下能够内在感知的那个东西还要多。这种边缘境遇是由时间意识造就的,因为时间总是在流动中,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因了自身的时间意识也是成“思想流”状的。我们所感受的当下并不能被孤立地抽象出来,这个当下一定是和一段预持——即将要到来的一个将来的事态——和一段对过去的保持——也就是一段越来越浅的曾经存在着的保持交织在一起。所以,任何的当下,都不单单是当下那一面,是由当下这一维、过去这一维和未来这一维三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的。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比当下更多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更边缘化,更匿名化,但不是消失,不是没有,而是会融入到我们巨大的下意识的背景里面,在那里于我们的意识发生不易察觉的却十分深刻的作用。[9]229-297
而在前文我们已经揭示:诗兴于人的是以对诗歌的体验来展开的。故而我们带着胡塞尔的体验思想,重新回到“兴”作用的具体情境里,探究“兴”的原初意义域。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 “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诗经·卫风·硕人》(“素以为绚兮”为逸诗),意思是说庄姜笑起来很美,眼睛黑白分明很漂亮。子夏不明白这句诗何意,夫子答以“绘事后素”。“绘事后素”①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对“素以为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不同于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窃谓《诗》云‘素以为绚兮’者,言五采得素而始成文也。今时画者尚如此,先布众色毕后,以粉勾勒之,则众色始绚然分明。《诗》之意即《考工记》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独以素为绚,故以为问。子以绘事后素告之,则素以绚之理不烦言而解矣。子夏礼后之说,因布素在众采之后而悟及之者也。盖人之有仁、义、礼、智、信五性,犹绘之有青、黄、素、白、黑五色也。礼居五性之一,犹素为白采,居五色之一也。……故《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也。’然则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本非深文奥义也。”参见陈大齐.论语辑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4.是说先用其他色彩绘画,最后再用白粉勾边,这样原本的色彩会更整齐更绚烂。这时候子夏忽然就明白了,说礼就跟素一样,即所有的行为若加上礼的勾勒,一下子就有美感了,就完整了。本来只是说诗,结果孔子由诗一下子跳到了绘事,这是第一重兴;本来是言绘事,子夏一下子就说起了“礼”,这是第二重兴:经过“兴”,“诗”和“礼”瞬间就贯通了!故而孔子称赞子夏说“始可与言《诗》已矣”,这在孔门是极高的评价。
对于诗的“兴”的机制,《论语注疏》引孔安国解释称为“引譬连类”[7]2525。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兴于诗这一过程,不难发现引譬连类只是“兴”的一个阶段。所谓的引譬连类,我们权且将其理解为诗歌是一种譬比性的言说,召唤着譬比性的领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诗经》,而诗是传统文化意义的贮藏器。我们面对诗句时,诗歌的“引譬连类”是指引导人们领悟诗里所描绘的情境和当下情境的相似性,或言找出传统与当下因为情境相似而产生的关联。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也。”[10]451-452但这种相似是意蕴上的,精神指向上的,而非经验上的相似。女子“素以为绚”与“绘事后素”、礼后于行,三者在气韵上相似,道理上相贯通,但是未必有逻辑上的关联,这种引发是出神入化的,甚至是靠“悟”的。如同子夏与孔子谈论诗歌本身即是借用诗的语言,通过兴发的途径来达到思想的认知,从而具有非概念的人生情感的心理内容,从而具有一种超脱当下时空的哲理诗意。
引譬连类完成,兴,并没有戛然而止,明晓一种情境的相似性,知晓传统与当下的关联,可称是“兴”的最核心构成,是“兴”的焦点。在焦点之后,这种领悟将转化为人们的思考方式和现实中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使得性情得以怡养,心志得以激发,明辨善恶曲直。这个过程如按时间序列是跟在刚刚那个引发过程之后的,按现象学的思路来讲,后续的过程是“兴”焦点后的晕圈。焦点时刻和后续的晕圈,完整地构成了“兴”。但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域”,一个长久的时间序列。
诗之于人的“兴”发作用是在时间之流中产生的。读者遭遇诗的那个当下是“兴”的焦点,诗瞬间引发相关之思,力量是凸显且强大的;可是“兴”并不止于此,即便没有了与诗面对面的遭遇,在“兴”焦点处所引发的思也会随着时间之流继续以边缘化的状态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慢慢融入我们庞大的下意识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着我们后续的思想和行为、性情、心志。我们从引譬连类中得到的领悟,会被糅合进我们个体的创造性,参与到后续的生活经验中,所谓明辨善恶曲直、性情得以怡养,所谓心志得以激发,都是我们从诗得到引譬连类的领悟加之个体创造性以适应了新情境的结果。所以,“兴”并不是诗意单向度的传承,而是让意义潜势凸显,再以创造性的方式适用于新的情境。
简言之,“兴’在时间之流中把我们的生命体验纳入其中。“兴”是有焦点的动态域:其焦点是用诗开启新的领会之境,是人遭遇诗的起始态,就像《论语·八佾》中描写的乐“始作,翕如也”的状态,一下子就将人纳入了发生的纯气势,诗歌意义瞬间激发出来;那瞬间的激流如同乐音,在演奏过后仍以余音态存在于人的下意识中,对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而“兴”并非是单次的,初始的“兴”在时间流上的后续会成为下一次“兴”的“前时间之流”,成为“前景”,人们在前一次“兴’时所获得的礼乐洞见、道德洞见及其践行洞见后的生命体验都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下一轮的诗“兴”之中,使得下一次的“兴”在诗与人遭遇的那个当下更加风起云涌。人就是在这样的“兴”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向至高的礼乐境界和道德境界迈进。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释[M]∥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3卷.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
[5]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宸,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清]焦循.毛诗补疏序[M]∥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三联书店,1990.
[7]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清]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 钱 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