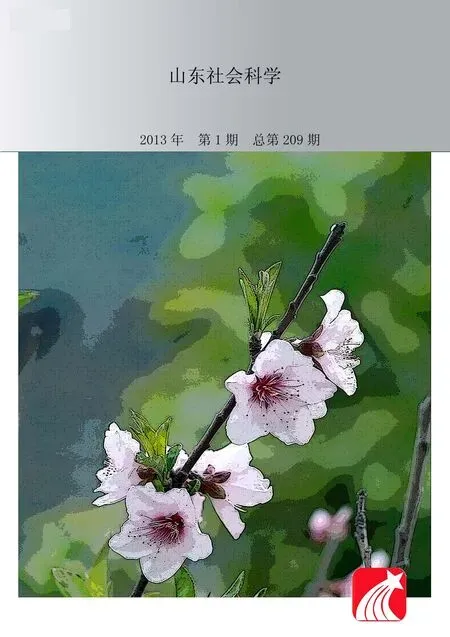一部点校水平颇令人失望的古籍
——简评《廖燕全集》
刘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4)
近年来,古籍的整理出版方兴未艾,一些地方出版社为弘扬地域文化,以地方文化名人为对象,整理点校出版了不少古籍,如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浙东文化特色的《吕祖谦全集》,齐鲁书社出版的反映齐鲁文化特色的《王世禛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廖燕全集》。这其中有点校水平颇高的古籍作品,实为学界和出版界的幸事。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点校水平不高,令人遗憾,《廖燕全集》即属于后者之列。该书最早有清乾隆本,为廖燕的诗文集汇编,廖燕诗文集即颜之曰《二十七松堂集》。后有日本的和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之文久二年[1862年]的全本十六卷《二十七松堂集》),台湾和大陆上海(远东出版社)均有铅印翻刻本存世。200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年刻本《二十七松堂集》为底本,参校诸家版本,点校整理出版排印本,连同后人对廖燕的研究成果,裒集成册,是为《廖燕全集》(上下两册)。
廖燕(1644-1705),字柴舟,广东曲江人,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家族毁于清初三藩之乱。他以一介布衣寒微之躯,虽身处庙堂之外,却时时针砭时弊,屡有惊世骇俗、曲高和寡的高论,发前人所未发,诸如脍炙人口的《明太祖论》、《高宗杀岳武穆论》等,其学识远远凌驾于时人之上,却被当局视为“异端”,所作所为颇与魏晋之际的嵇康和阮籍同道。廖燕早年辞去诸生,绝去功名,落草于岭南一隅,所以不仅生前潦倒,身后也鲜为人知,至今仍名在扶桑,未闻于中土。日本人谓廖燕的文章为“朱明三百年之殿”,极尽颂扬之辞。作为亡国的明朝遗民,尽管一生穷困潦倒,饱尝屈辱,默默无闻,怀才不遇,却誓不食清政府的饩廪,其风骨意志实令后人景仰;作为体制外的一名草根学者,始终能够保持思想独立和批判精神,见解犀利,以柴舟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深度,在中国古代灿若星辰的众多著名学者中,完全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斥资出版《廖燕全集》,实乃学术界一大幸事,对廖燕生平及其思想的推介和研究,功德不浅。但遗憾的是,该书问题不少,概括起来大致有二。
一、书名称呼不规范
《廖燕全集》分上下两册,下册通篇都以附录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近现代大陆、台湾和日本学者研究廖燕生平传记和各种版本学研究成果的资料汇编,并无廖燕本人的一首诗文,而全为后人且多为现代人的评论文章,而以《廖燕全集》的形式附之骥尾,简直可以视为《二十七松堂集》的附赘悬疣。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对廖燕的评论文章何以非要硬塞入《廖燕全集》之中呢?而且分量与廖燕本人的文字几乎相等,所谓的下册竟被颜之曰《廖燕全集》,如果下册不存在,只留上册,难道就非《全集》了吗?如此搭便车的做法实为不妥。为何不将下册另以《廖燕生平著作研究资料》为名,名正言顺地另册出版呢?这本下册,本无廖燕的任何作品,却也在封面上堂而皇之地印上[清]廖燕著;本无标校问题,亦一如上册一样印上点校者的大名,这种做法岂非名不副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行事,将《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以《红楼梦》署名,那将是个一个怎样的局面?这个问题不能不成为引发读者对此书质疑的一大阙失。其实,将后人的研究成果以附录的形式一并在《全集》中出版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亦有先例,但须标注清楚,以廓清主次。如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李渔全集》,凡20 卷之巨。在其最后的两卷中,点校者分别在封面上以大号字印有“李渔年谱”、“李渔交游考”、“李渔研究资料选辑”、“现代学者论文精选”和“李渔研究论著索引”等字样。此种做法即属于规范的做法,读者并无异议。
二、点校中出现的问题屡见不鲜
概括起来,问题多出在点校者对生僻词汇、历史人物和典故不熟悉。因廖文全部集中在上册,与下册无关,引文出处做简化处理,只标明题目和页码。现择主要的问题按上册页码前后顺序大致胪列如下:
《卷一·性论二》(第7页):毛会侯先生曰:前篇论质不是性,此篇论情不是性,俱发前贤所未发。中间提出‘復性’二字,使人有下手处方,不是鹘突学问。
原文并没有“处方”一词的语境,这段话是不通的,恐怕标点者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逗号应该点在“处”与“方”之间,“处”读chù,“方”为副词,应属下句。
《卷二·烈女不当独称贞辩》(第47页):予谓六女罹难捐驱,于例称烈为宜,因为一诗并书后一篇,以正其义焉。
“驱”字应为“躯”字之讹,非通假字。这是中学生都可能看出的问题。
《卷三·春秋巵言序》(第53页):况《春秋》以美刺兼《诗》,以政令兼《书》,以权变兼《易》,以会盟征伐兼《礼》、《乐》,其理显,其词微,虽遊、夏不能赞一词,而后世诸儒辄以管窥之见解之,至以春王正月为周之十一月,即此正朔月数与春夏秋冬四时之不辨,又遑问其褒贬予夺之大也耶?甚矣。
“遊”应作“游”,指孔子的弟子子游。子游(前506-?),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吴国人,与子夏、子张齐名,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曾为武城宰(县令)。名从主人,就如陆游不能写作“陆遊”一样。在《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字子游是千真万确的,后人不大可能擅加改动。下文还有:《卷九·与黄少涯书》(第199页):仆则答云:本章所称门人者,岂非子遊、子夏诸贤与冉有、子禽之徒欤?按:在一本书中竟至少出现两次“子遊”,如所依据的古版本确属如此,这两条就应该出校记,以正视听。
《卷三·荷亭文集序》(第67页):酒似无与于文章,然当其搦萤欲书时,不得一物以助其气,则笔墨亦滞其难通。
“搦萤”应为“搦管”,执笔之意。
《卷三·人日遊紫微巖听弹琴诗序》(第73页):韻者,所以节嚣也。于是挈榼携琴,越溪陡峦,行二十里,至紫微巖,洞屋轩廠,可容数百人。
“轩敞”亦可作“轩廠”。“轩敞”为高大宽敞之意。“敞”与“廠”互为通假,应出校。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卷七·芥堂记》(第131页):兹堂幽僻轩廠,旁多余地,可池可墅,予亦得饮读其中,意欣然乐之。
《卷六·祝圣庵募缘疏》(第111页):庵左有流泉,清可鉴髮,予尝吟咏其上,遊鱼数十,立波际不动,突而腾跃嚅唼不已,似喜予吟者。
“嚅唼”为“唼喋”(shà zhá)之讹,“唼喋”,形容成群的鱼、水鸟等吃东西的声音。
《卷六·会龙庵募建接众寮房疏》(第115页):丹霞为吾郡名胜,僧俗往来,靡不籍此院为居停。
“籍”为“藉”之讹。两字有时可通用,读jiè 时,不得用竹字头的“籍”。
《卷六·资福寺募修佛殿疏(代)》(第116页):今此刹日就颓败,若不急为修葺,则将来不无倾圮之虞,堕前人之功而失相资之义,莫此为甚。
“堕”应为“隳”(huī),通假字,应出校,否则容易误读为duò。
《卷六·募建芙蓉庵疏》(第117页):而回视一身,亦如僧之萍踪无奇,太息久之,以为非佛莫能销此肮脏耳。
“奇”为“寄”之讹。从上下文关系来看,萍踪无奇没有道理,居无定所才符合原意。
《卷七·鱼王泷神庙碑记》(第129页):行数里,前舟已泊岸候,其奇险遄急如此。
“遄”为“湍”之讹。“湍”(tuān),湍急,水势急;“遄”(chuán)为往来频繁之意,用在溪水河流中实为不妥。
又(第130页):维此乡庶,以嵩代耒,履险而安,神功是著。遗庙江湄,奠斚品奏词,刻之滩石,千古于斯。
其中的“品”、“奏”或“词”三字中必有一字为衍文,因其为《记》中结尾的四字一句的“铭”,其中一句竟排出五字,该如何交代?
《卷七·乐韶亭记》(第135页):无簿书讼嶽军马之繁,以扰其心思志虑。
“讼嶽”非词,乃“讼狱”之讹,“讼狱”义为诉讼。嶽,读音为yuè,简化字即“岳”。
同页,“宜其有可乐者在矣,而况乎山川蜿蜓而俶诡,为古名贤往来乐遊称道而不置者又比比也。“蜿蜓”乃“蜿蜒”之讹,“蜓”的读音为tíng,为蜻蜓之“蜓”。
《卷七·修路碑记(代)》(第136页):惟自部署至风度楼,出相江门至关廠亭,及汲道阶磴,予榷关朝暮出入,必经由此,视他路为有缘,今昔倾圮已甚,而不急为修葺整理,致行旅有蹶趋挫折颠僕之患,忍乎哉?
“颠僕”为“颠撲”之讹。“颠撲”的简化字作“颠仆”,仆有两个不同的音义:1.pú 音,①仆人;②古时男子谦称自己;③姓。2.pū 音,向前跌倒。
《卷七·改旧居为家祠堂记》(第138页):东向,背山临溪,浈水来朝与武水汇于址,而南去无所见,左右环抱,静好如立,玦外而望其内。
“玦”(音jué)为古代环形有缺口的佩玉,古代常用以赠人表示决绝;另一义为戴在右拇指上用以钩弦之器,俗称扳指。用在这里均讲不通,疑为讹字,只能核查原刻本才能解决。若原刻本确如此,应解释“玦外”究竟是什么意思。
《卷七·遊丹霞山记》(第148页):僧屋皆傍江就巖磊成。
“磊”通假“垒”字,堆砌之义,宜出校记。
《卷七·朱氏二石记》(第162页):毛会侯先生曰:绝不写二石形状何似,但将灵璧、英州较量一番,用意蕴藕之甚。
“蕴藕”为“蕴藉”或“蕴蓄”之讹,蕴藏,积蓄之义。
《卷八·哭澹归和尚文》(第163页):美恶莫辩。
此处“辩”宜作“辨”。本书目录最后出校谓“辩、辨古通”,本不必苛求,凡遇较难的通假字,似以出校为宜。
《卷九·吴少宰与翁源县张泰亭明府书附》(第177页):惜行色勿遽,无暇请教,转觉瘐岭一行陡增尘容俗状耳。
“瘐”应为“庾”字之讹。大庾岭亦称庾岭、台岭、梅岭、东峤山,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位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为南岭的组成部分。
《卷九·吴少宰与翁源县张泰亭明府书附》(第178页):接见惟恐不及,尤为之竭力揄扬,如二书之肫挚恳侧者乎?
“恳侧”本为“恳恻”,诚恳痛切之义。“侧”与“恻”可通假,似宜出校。
《卷九·复邹翔伯书》(第182页):自念业已身为废民,廓庙之谋本非其任,时俗之好又非所乐,所剩残书数卷,灌园之暇时或披阅,间有亲知以名酒相遣,欣然取醉,复有所作,得尽所怀。“廓庙”应是“廊庙”之讹。“廊庙”,书面语,指朝廷。
《卷九·与陈崑圃书》(第198页):然二公所重又不在此。燕思稍欲立言,接二公武于唐、宋、元、明之后,别具一种幽泠笔墨,使后人读之领悟不尽。
“泠”字应是“冷”字之讹。泠只有两音,一读líng;一读lǐng,没有lěng 音,可与其通假的字有“令”(命令,仅见《庄子·山木》)、“零”(泪泠,涕泠,滴落)、“伶”(乐官),用在文中不搭配。难道堂堂一个出版社只有“泠”的铅字,而独无“冷”的铅字?这样一个普通常用字竟误排有七、八处之多。
下文还有:《卷十一·续师说一》(第248页):魏和公先生曰: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一经妙笔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文。至泠潮(校勘者在排版时误将“嘲”排成“潮”)热骂,不顾庸师面皮,尤见持世辣手;《卷十一·别号说》(第253页):朱藕男曰:别号至今日已成滥觞,此文泠嘲热骂,提醒此辈不小;《卷十六·朱吟石像讚》(第345页):是殆与吾辈同一副冰泠面孔,只可于一丘一壑中安置者耶?《传奇三种·新琵琶》(第594页):泠落已堪羞;《卷二十·平南夜泊谢友人招饮又》(第519页):深山初觉早寒添,手倦抛书曝短檐。万顷平畴翻麦浪,三叉斜路滑松鍼。坐临水石心俱泠,卧入烟霞梦亦甜,闻道长安尘十丈,从来足迹不曾霑。
“鍼(zhēn)”即简化字“针”字。在这首七言诗里,“鍼”字与其他句的最后一字(an 韵)不协音,疑为讹字,须核以原刻版。
《卷十·与仞千上人》(第211页):前惠片楷,居然名宝,上逼钟精,下该储妙。
“楷”字疑为“楮”(chǔ)字之讹,指纸墨;“储”疑似为“褚”(chǔ)。“钟精”指三国曹魏时期的钟繇书法之精;“褚妙”指褚遂良书法之妙。
《卷十·与萧絅若》(第215页):著书饮酒,足遗穷愁,燕与吾兄须罄生平气力,为此一事。
“遗”应是“遣”字之讹。遣,打发,消除,发泄。“遗”字则与原文逻辑关系相矛盾。
《卷十二·书邑志宋特奏科后代》(第278页):士人读书一生,上之不能致身庙廊,下之不能安心岩壑,束發受书,白首无成,亦可悯也已。
“發”应为“髪”。点校所用之底本不可能是简化字本,所用之版本中,“發”与“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不可能相混淆,错误只能出在校勘者手上。属正体字与简化字转换过程中的常见错误。
《卷十四·南阳伯李公傅》(第297页):姚彙吉曰:绝去支蔓,独书大节,是得龙门神髓者。中间描写亡国诸臣形状,千古一辄,令人不寒而憟。
“憟”为“慄”字之讹。憟(sù),阿谀逢迎之义。慄(lì),发抖;哆嗦。
《卷十四·丘独醒傅半醒附》(第305页):尤善画虎,尝结屋深山中,观生虎形状,得其神,苍忙返舍,取笔就粉壁图之,犬一见皆惊僕,为之遗矢。
“苍”为“仓”字之讹。“苍”有颜色之义,亦指天空。“仓”才有匆忙、仓促之义;“僕”字应为“撲”字之讹。“惊僕”说不通。“撲”才符合文义。
《卷十四·高望公傅》(第307页):望公嗔目不视,既而曰:“我要画一个若有若无的高望公。”
《卷十五·待赠文林郎文学张君墓志铭》(第318页):君长嗣拱极惊起,见墙正压君卧榻,徨遽莫知所措。
“徨”应为“惶”字之讹。“徨”,彷徨,犹豫不定。“惶”,恐惧,惊悚。很显然,从文义上看,“徨”字是错误的。
《卷十六·程子牧像讚》(第342页):修髯炯目,芒履布襟,传神正在阿堵,抱臂还思入林。才不可象而象之面,德不可见而见之琴,胡为乎,独抱而不鼓,默坐而沉吟?岂黄山歙水,既无识者;今来韶石,又鲜知音。
“抱”应为“把”,“把臂入林”为常见之句;“独抱”应为“独枹(桴fú)”,鼓槌。
《卷十七·程子牧像讚》(第357页):今云性即理也则穷理不必尽性,尽性不必至命矣,岂不与《易》相刺谬耶?
“刺”为“剌”字之讹。“剌”(là),乖戾;违背;悖谬。《卷十七·读韩子》(第387页),就有点校正确的“剌谬”。
《卷十七·答客问五则》(第361页):客问:宋钦宗北狩,决无复辟之理,若岳忠武之死,则秦桧杀之也。今坐首恶于高宗,而未减秦桧,可乎?
“未减”应为“末减”。末减:从轻论罪或减刑;末,薄也;减,轻也。“未减”则不是词。
《卷十七·记张献忠卒语》(第381页):予闻之,心知其然,尽杀运方开,人心俱变,妖星下降,孽狐陛座,屠毒成风,心狼手滑,日习一日,遂有如张卒所云者,天下事尚忍言耶?
“狼”当系“狠”之讹。
《卷十七·重修曲江县志凡例代》(第390页):……亦概从删,例殊不可解。
标点错误,应为:亦概从删例,殊不可解。
《卷十七·永曆幸缅始末》(第398页):太常博士邓居诏一本,为停止不急之务,仰祈修省等事,内有责吉翔及各员自媒自衔等语。
“衔”为“衒(炫)”字之讹。“衔”,动词,1.以嘴含;2.存在心里;3.接受;4.相连接。从上下文文义看,“衒”应为夸耀之义。
《卷十八·丙子夏自圆通蘭若移寓报本庵赠鹤洲上人》(第422页):悟对各冥冥,齐心满寥廊。
“廊”应为“廓”字之讹。“寥廓”,高远空旷。“寥廓”同“辽阔”。
《卷十八·沧浪亭歌呈某中丞》(第432页):苏子遗踪亦已烟,依稀惟剩沧浪水。
“烟”字原稿可能为繁体字“煙”,音yān,为“湮”字之讹。“湮”,埋没。
《卷十八·石龙池歌》(第441页):迅雷突震谁惊觉?矢矫雲中露头角。
“矢矫”为“夭矫”之讹。“夭矫”,形容姿态的伸展屈曲而有气势。郭璞《江赋》:抚凌波而凫跃,吸翠霞而夭矫。
《卷十八·荔枝歌留别》(第441页):芒种才过夏至前,千株万树糖方满。
“糖”为“塘”字之讹。
《卷十九·十六夜坐月》(第446页):鹤唳犹闻影,萧声只隔篱。
“萧”为“箫”字之讹。
《卷十九·坐西禅寺万佛阁同胡而安太仆》(第449页):楼高成寂寞,恋静客时登。
“恋”为“峦”字之讹。
《卷二十·霁后登广州府城东战台》(第500页):避世高僧浮海云,从军好寄书回。
七言诗脱漏一字,“寄”与“书”之间似脱一“家”或其他字,须核查原刻本。
《卷二十·梅影》(第510页):绿萼依稀镜里攒,天然雪幹欲摹难。
“幹”(gàn)应为“乾”(gān)字。“幹”为动词义,“乾”为形容词义。
《卷二十·山居三十首》(第514页):到来丘壑雜忘处,正值春风蕨笋肥。
“雜”疑似“难”字。
《卷二十·平南夜泊谢友人招饮又》(第515页):几年避迹卧崆峒,茅屋高低竹树中,未学谁堪称隐逸,有才人始许贫穷。
“未”疑为“末”字。“末学”为谦词。
《传奇三种·新琵琶》(第598页):适蒙概诺,还要借重。
“概”为“慨”字之讹。
以上是《廖燕全集》上册中出现的明显的点校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只是参考了以往的诸家版本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点校本,并不是笺注本。目前,国内还尚未看到有详细考订和注释的笺注本问世。古籍整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阐发作者的微言大义,一切研究成果均须以过得硬的考订本为基础,否则,很难避免有南辕北辙之虞。为了更透彻地研究廖燕作品,出版廖燕诗文集的笺注本已是当务之急。很明显,学界目前对廖燕原著的研究仍显不够,至少是不太重视。举个例子,卷七第136页之《卷七·修路碑记(代)》开首一句话“予奉命榷关来韶,似除徵税譏人外,皆非予责也”,其中的“譏”字,有稽查,盘问之义,即便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中也未有见到,更何况现在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都未必讲得出它的确凿涵义。这个任务的解决就要靠校注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