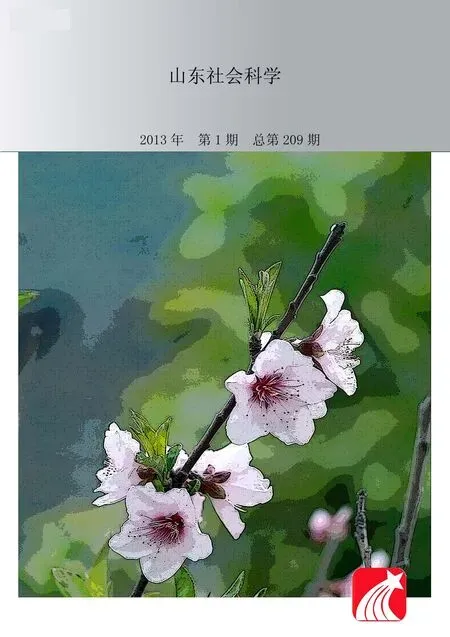国家、个人及民间社会的内在秩序
——试论天津皇会中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
蒲 娇
(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 300072)
妈祖作为民间神受到百姓信仰崇拜,对天津本地的城市文化性格产生重要影响,是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载体,被亲切地尊奉为“三津福主”,本地更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为妈祖诞辰举行的大型祭典仪式——皇会,也在天津地域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谓记录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信仰、风俗及社会变迁的活化石。妈祖信仰在天津的扎根并非偶然,一方面,作为一位外来之神,妈祖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神性与天津百姓的人格模式不谋而合,很快便融入包容性极强的天津本地文化中;另一方面,庆典仪式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有组织的活动往往需要调动地方社会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才可完成。因此,妈祖庆典仪式便具有了广泛吸引社会力量、促成社会各阶层频繁互动的特点。不同群体的加入壮大了皇会的势力,但矛盾也相应产生。如何协调好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并运行一套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内在秩序,都是在皇会各阶层关系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
妈祖信仰在天津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逐渐完成由单纯的护航神到万能地方神的转化过程。信仰的生发及传播必定同此区域内社会人群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某种民间信仰的发展或消亡,极大程度是社会自主选择的结果。①具体见郑振满、陈春:《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最初妈祖祭典仪式处在“娘娘会”阶段时,多半是民众自发组织参与,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虽然常有官员参与,但大多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官府操持的情况较为罕见。清康熙年间,因娘娘会已具较大规模,引起了政府关注,逐步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与宣传。妈祖作为神祇,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起便多次受到皇封。天津的乡绅与官员自妈祖入津伊始,便为此具有文化正统性、符合儒家教义的神明扎根天津而苦心经营。当妈祖信仰被当地民众普遍接受后,所传递的有关于“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官员、民众和地方精英对待妈祖的态度随之产生微妙变换。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多次改朝换代,但对于专制政权的掌控权却没有一刻放松过。统治阶级反复强调“礼”的教化,利用“儒学”为统治工具的同时,也力图在民众心中营造“礼治社会”的假象。然而,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松散关系,致使在某些历史阶段内中央集权阶层的权力被架空。因此,必须出现一种能被各阶层所接受、能平衡各阶层关系的交流方式。显而易见,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参与只是一袭华丽的外袍,获取民众对国家的支持和忠诚才是统治阶级的真实目的所在。这或许才是皇会能得到国家重视,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的真正原因。此类事件在清帝的加封、赏赐物品,甚至亲自参与等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正是利用了有良好群众基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活动,将本阶级的意识渗透其中。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适时调整政策,通过主动示好来达到笼络民众、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以1936年皇会为例,从组织筹备到具体实施都由官方出面全盘布置,甚至天后出巡散福的路线也由政府定夺。官方介入皇会筹备会,意味着皇会受到官方的实际控制,成为传达统治阶层意志的载体。
妈祖信仰的在地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同“碧霞元君”信仰的融合,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妈祖保持了独立神格而未被碧霞元君同化,甚至民间出现了将碧霞元君讹传为妈祖娘娘的传说。通常而言,在强势信仰的已有神灵空间内,外来神灵会被同化。但妈祖信仰在天津的发展状况却截然相反,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妈祖信仰特性的保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众心理的基本需求。天津地处海运与漕运的双重要塞,本地居民家中大都有从事航运和脚行的人,因而妈祖佑护水运安全的核心神职显然是必需的。至今尚存的天后宫“海门慈筏”牌坊,以及配殿内所供奉的木船模型①天津本地由此传说:面对神灵许愿必定还愿,否则就会遭受报应。商贾如在出海前对妈祖许愿祈求护佑,必须要在平安归来后到天后宫还愿,并进贡一条小船模型,意为将整船的宝物都献给娘娘,日积月累,天后宫内的小船模型越来越多。就是历史见证。其次,从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妈祖是经历代王朝政府封赠而进入国家“正祀”体系的民间神,这对于保持其独立神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妈祖频受“敕封”这一点,在其传播过程中被大肆宣传。民众相信,被统治阶级认可的正祀威灵更强。而从妈祖被加封的过程与天津民间信仰逐步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来看,二者基本是同步的。因此虽然经过历朝更迭和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但在乡民对文化价值的认知层面上,对于“正祀”的信念并没有产生动摇。历次皇会出巡,队伍最前必定要挂一条写有“上造娘娘敕封,世人念到,就知娘娘常常显圣,才受敕封”②据西码头百忍老会时任会头殷洪祥先生口述。的门幡。这些举措在强调妈祖信仰灵验的同时,也是国家传递阶级意识的过程,通过在文化意识方面的反复加强,使得人们对既定秩序产生自然认同。
二、妈祖信仰与民众之间的互动
妈祖信仰在天津地区的发展传播,经历了一个“民众出于不同的心理需要赋予天后多种职能,并在其神灵谱系中加入不少天津本地的世俗神灵”③侯杰、李净昉:《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的过程,这同民间信仰的实用功能密切相关。中国民众的信仰大抵限于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原因,所表现出来的趋利效应严重。通过对信仰体系的改造,不仅巩固了妈祖的基本神职,更派生出了许多更广泛、实际的功能,如繁衍求子(“拴娃娃”功能)与祛除疾病(斑疹及天花等疾病)方面。在妈祖神职扩大的过程中,盛大的皇会仪式无疑起到了一种最为直观、立体、真实的宣传作用,民众对其产生的强烈认同感与好感便不足为奇了。
皇会中的玩意儿类花会表演,不仅为民众带来娱乐效果,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人们对神灵的认知,为他们亲近神灵提供了一条捷径。在皇会仪式中,常有数目众多的“巡风会”、“愿心会”、“顶马圣会”、“宝塔花瓶”等会种参与,此类花会都是以答谢神灵庇护、宣扬神绩为主要目的。“与日常祷祀仪式不同,庙会活动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向社会公众集中展示神灵及与神灵有关的各项内容。”④吴效群:《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在行会过程中,一方面进行表演,另一方面向民众传播妈祖的灵应事迹。这种宣扬效果直达社会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角落,无论是政府官员、地方绅士还是民众,都会被神通广大、普济天下的神灵所感染。
诚如刘魁立先生所言,民间信仰构成了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参见刘魁立:《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在民众心中,能参与酬神、敬神、敬神的演出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仪式过程中,民众在身临其境享受表演乐趣、满足自身兴趣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情感之中对妈祖强烈的归属感与贡献感。这些平时处在社会最下层的百姓,终日辛苦,很难有机会参与到社会集体文化活动中。但皇会的狂欢正可以创造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以神的名义发出呐喊,发出内心深处的自我宣泄。“在他们的世界中,民众的文化活动能够被纳入到皇朝的仪式范围,自身的价值追求能够得到皇朝政府的认可和赞赏,这不啻于证明了自身的追求和行为的合法性。”①姚旸:《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在现实世界中,统治阶级的地位不容质疑,大部分民众过着屈从、忍耐的生活。但在皇会仪式所营造的第二世界的理想生活中,民众可以在表演活动中打破等级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众参与皇会是渴望获取社会地位、平等自由的一种表现。
皇会的参与者中,有部分人身份特殊,被称为“吃会儿的”或“扒会儿的”。此类人不参与演出也不出资,甚至并不信奉妈祖,作用却十分重要。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无正式职业,但却精通皇会中的仪式、礼仪、会规、人情及忌讳等事。每逢会期,他们便借办会之名四处筹备资金、募捐银两,然后私藏部分收归己有。这些人没有固定收入,但是所获“报酬”却极为可观。虽然社会各界对这些人的行为心知肚明,但对他们却睁只眼闭只眼。据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来看,出现“吃会儿”群体是时代的必然。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粗放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生活与生产问题大多依赖宗族互助解决,社会联系的渠道方式相对缺乏。因此,这种能自如游走于社会各阶层、社会交际能力强大的群体,所发挥出来的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他们的活动虽是利益驱动,但最终使得皇会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故而,在经济匮乏的时代,生活在下层的贫困百姓,为了现实利益而加入某种团体或宗教组织也是常见之事。此类现象的产生,也可认为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中,一种实用特征和功利性格的异化表现形式。
三、地方绅士在皇会中的价值实现
皇会在清康乾年间的兴盛,与天津民众对妈祖的笃信、地方经济的繁荣及国家的统治意图几方面都有极大关系,但兴办与停办却与地方绅士②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费孝通将中国的绅士阶层定义为:绅士阶层有时也叫士大夫,“学者——官员”。的态度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民间社会集中崇拜某一官方认可的神祇时,也就等于国家间接地控制了地方信众的宗教及社会行为。”③迪生:《香港天后信仰》,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天津皇会因统治阶级的认可,打上了标志性的正统符号,描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成为地方绅士阶层参与其中的源动力。
皇会是地方绅士阶级表现及确定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与有效方式。地方绅士试图进入皇会的组织管理机构,进而构建一个由管理皇会的精英团队与普通信众共同参与,并达成自身目的的社会组织。在皇会中,绅士群体所掌管的组织被称为“扫殿会”,他们所重视的是如何靠近地方政治及博得社会声望。普通民众所参与的组织称为“花会”,他们所关心的是会与会之间的关系、村落之间的关系及村落中人与人的关系,并注重内心宣泄的实现及对妈祖信仰的虔诚。此外,参加扫殿会的绅士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参加花会组织,扫殿会却绝不允许处于社会底层的花会成员随便参与进来。从另一个角度说,参与花会活动的民众比绅士们在行动上可以更为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参加皇会或者不参加,可以选择改为参加其他庙会,如碧霞元君庙会、妙峰山庙会、葛沽皇会等。但绅士们却要对自己的行为深思熟虑,他们的离开可能会导致皇会在资金方面的瞬间垮塌、组织系统混乱、安置工作失灵等后果,进而影响到他们在本地的社会声望。因而,其自身所背负的道德、信义方面的责任便更加重大。虽然在行为上受到极大的约束,但绅士阶层也绝不轻易放弃参与皇会的机会。“众位爷,每多有举、监、生员人物上会,俱是袍套靴帽,各有顶戴职分,尊为会中领袖。”④许青松、郭秀兰:《天津天后宫行会图》,香港和平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202页。清代以后,扫殿会全部是由身有功名的官、商两界的上层人物组成,这个阶层的人群在本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相对疏离,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声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⑤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在当时的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名誉直接决定了其社会关系的广博度、精神满足感和各阶层人群的认可度,但最终还是归结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绅士阶层依靠自身在本地的声望广泛吸纳各类组织力量,募得最佳、最为广泛的社会资金支持。因而,扫殿会在皇会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会中领袖”,可谓皇会真正的领导者、策划者及组织者。
综上所述,虽然各个阶层参与的是同一场皇会,但管理者和参与者所处的社会阶层与政治范畴却是截然不同的。为妈祖诞辰举行的皇会祭典仪式,可以认为是绅士阶层所操控的一个集体符号,但并不是所有民众都会认同这一符号,民众之间、民众与精英之间、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扫殿会领导地位的确立,对于保障皇会组织的凝聚力、执行力方面的确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方面,还加强了官、商阶层对地方社会事务的渗透能力和处理能力。如:行会过程中,若各花会之间产生矛盾摩擦,负责协调解决的是扫殿会成员,一般情况下,各会成员都会服从此类安排。此外,随着皇会繁荣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一些皇会外的民间组织深感身单力薄,积极向皇会靠拢,也希望籍此平台提升社会名望,使自身组织得到更好发展。在皇会举办的过程中,扫殿会成员能够与各类人群产生接触,从而促进了官与商、官与民、民与民、民与商和会与会等不同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
四、皇会对世俗社会秩序的重构作用
庙会的普遍社会功能在于——酬神、谢神、贿赂神灵。据人类学仪式研究学家特纳的仪式理论,这些仪式活动反映了古代民众在特定时节,对过渡阶段、对自身生存状态所作出的调适性努力,反映出民众企图通过人类自创文化体系来驾驭宇宙、实现愿望的不懈追求。①参见[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往深层功能意义方面探究,群体性的祭祀仪式在乡土社会中还具有对社会秩序网络的消解与重构作用。只是这种暂时的、颠覆性的文化展演被有效整合在高度秩序化、整肃性的祭典仪式中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有组织的仪式活动往往需要调动自上而下的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因此,皇会中各阶层人士的有机聚合,导致了地方社会秩序在建构和维持上所产生系列的变化。
妈祖信仰深切地植根于天津民众心中,这是皇会生发、繁荣及相关民俗活动有机传承的动力源泉。但由于中国民众的信仰意识较为不自信,他们认为普通人与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直接交流是不可实现的事情。这时,在民众与妈祖之间就自然引入了沟通媒介——道士。早期的道士是沟通世俗与神圣仪式的执行者,又是现实生活中民众信仰生活的引导者,同时也掌握着较多的文化知识,因而在民间社会受到尊重。虽然在皇会的决策层中逐渐加入了官府、商人,但调度、请会、提会、派帖和张贴黄报等一系列的联络协调工作仍需要道士来完成。作为皇会的重要参与者,在建立民众和神灵联系的作用中,道士阶层也可归为社会精英的范畴,对建构世俗社会的秩序也有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女性信众的作用。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女神的数量占据了很大比例。女神及女神信仰的存在与中国妇女特殊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需求关系密切,女神也就相应地被赋予了满足与女性需求相关的职能,其中保佑生育是最重要的一项。受传统伦理的影响,中国妇女参加社会交往和公开娱乐活动的机会十分有限,但若是替家庭成员的平安祈福、为传宗接代祈祷的宗教活动就变得十分合理。事实上,在对待皇会中是否允许女性参加的问题上,一直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女子不能抛头露面”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女性不成文的道德观约束,皇会期间众多女性的涌入,无疑是对“男女授受不亲”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挑战。但女性群体作为妈祖信众中的主体,是妈祖信仰在天津地区得以存续的关键力量。这也是妈祖信仰扎根天津后,派生出其他分身娘娘功能与各种民间生育民俗的主要原因。因此,皇会组织者对于女性信众的参与始终是不鼓励也不禁止,而持无奈又容忍的态度。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分析,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约束,学习与交流的机会较少,合理的出行可以使她们广博视野,获得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
皇会的举办,直接受益者当属商人。他们既从皇会中获得了经济方面的实惠,又通过对皇会的热心参与和鼎力支持,获得不同程度的社会声望与号召力,巩固和提高自身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当然,这其中不乏别有用心之人,某些怀有政治理想的商人借参与皇会的机会,作为与官方靠近的手段,最终达到官商勾结、赢取私利的目的。但正是因为商人阶层对于皇会的热情与动力,才最终形成皇会刺激经济、拉动商业,商业资助皇会的独特运作模式。最终,商业的发达及商人的社会角色“善”化,必然会对天津地域文化、城市性格、民间风俗造成一定影响,传统的社会秩序也会受之影响,作出相应的调整及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