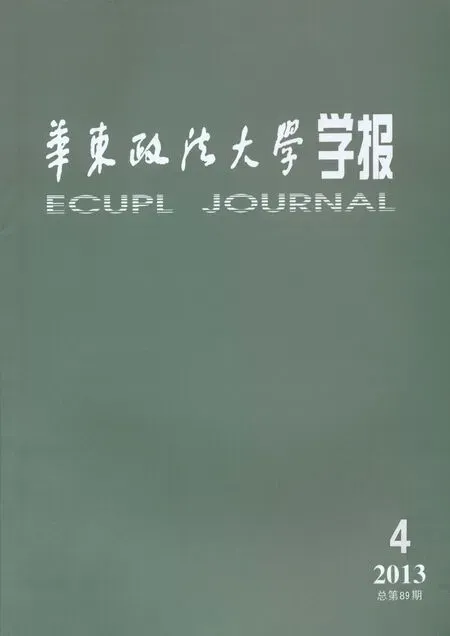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
陈 玺
流刑萌于夏商,立于秦汉,北魏、北周之际正式成型。隋《开皇律》始定流刑三等里数,唐律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完备的流放制度,并为后世宋元明清历代沿袭,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大清新刑律》颁布,沿用数千年的流刑方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唐代是中国古代流刑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学界对此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注]主要研究成果有:刘启贵:《我国唐朝流放制度初探》,载《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郝黎:《唐代流刑新辨》,《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张春海:《试论唐代流刑与国家政策、社会分层之关系》,载《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王春霞:《唐代长流制度研究》,载《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23期。关于唐代流刑的研究,必然涉及一项重要制度——长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唐代长流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仍甚为匮乏。
作为一种不见于律典明确规定,却又在唐代长期行用的流放制度,其发展演进与具体施行对唐代政治与法制构成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专文阐释,以期全面认识唐代刑罚之实际执行状态,以及唐律对于后世立法之影响。
一、唐代长流制度之创制
关于长流制度之创制,史籍文献记载甚略。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长孙无忌”条引《朝野佥载》,“长流”由宰臣长孙无忌奏请设立: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注](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长孙无忌”条引《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50页。长孙无忌长流事,在唐代已为时人关注。今本《朝野佥载》记“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氊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见(唐)张鷟撰:《朝野佥载》卷一,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戴建国先生据长孙无忌案,将唐代长流创立时间确定为贞观时期,[注]戴建国:《唐代流刑的演变》,载《法史学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此说或可商榷。唐代流刑源自杨隋,其刑罚位阶仅次于死刑。《开皇律》规定流刑分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贞观修律,概遵隋旧,惟“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7页。是为“常流”。[注]唐律规定之“三流”,概称“常流”。据《唐六典》:“流刑三(原注:自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皆役一年,然后编所在为户。而常流之外,更有加役流者,本死刑,武德中改为断趾。贞观六年改为加役流。谓常流唯役一年,此流役三年,故以加役名焉。)”见(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6页。又因唐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流犯应配”,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页。一般流犯需于配所服役,因而唐代流刑又有“配流”之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事,后经八座集议,改断右趾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注](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九《议刑轻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6页。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正月二十三日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要之州。”[注](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59页。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永徽律疏》继受贞观修律成果,在规定三等“常流”的同时,又增列流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等条目。而《永徽律疏》之领衔修订者,即为赵国公长孙无忌,若“长流”为无忌于贞观时奏请设置,则永徽修律之际,理当将其与加役流等一并纂入律典,然今本《唐律疏议》之中,并无“长流”之条。由此,“长流”制度的设立时间,或在高宗永徽四年之后。[注]据《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功第一,始封齐国公。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官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因许敬宗诬构谋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戊辰,流于黔州。关于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两《唐书》、《资治通鉴》及《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颇有出入:《旧唐书·高宗纪》言:“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带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依旧准一品供给。”而旧书本传又言“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亦作“流黔州。”《大唐新语》卷十二《酷忍》言“配流黔州。”《册府元龟》记“帝竟不引问无忌,便下诏廷斥之,仍发遣次州府兵援送于黔州。”见(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九《宰辅部·忌害》,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0页。《资治通鉴》曰“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4页。清人沈家本认为“安置”即流刑。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页。张春海则以此案作为唐代“安置刑”之始,见张春海:《论唐代的安置刑》,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其实,“安置”与“长流”在适用主体、施行程序、执行方式等方面颇为相似,长孙无忌案即是唐代“安置”之肇端,亦为“长流”之滥觞。两种刑罚在其后互相交织,并存不悖。
上述推断还可于史籍文献中求得印证,目前可见最早关于长流的案例,为前述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流黔州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四月右相李义府因厌胜、赃贿等事下狱,三司杂讯有状。戊子,义府“除名长流嶲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70页。同月壬辰,右史董思恭以知考功贡举事,因预卖策问受赃断死,“临刑告变,免死,长流岭表”。[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明罚》,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9页。此二例为唐代有确切记载“长流”案例之始。
长流人犯因逐至边裔,谪于蛮荒,就其刑罚性质而言,无疑属于广义流刑范畴。然与“常流”相比,“长流”不受律令里数限制,刑期不可预见,设计初衷即有终身不返之意,且为常赦所不原。然史籍文献中关于唐代“长流”之具体表述并无定制,往往与“流”、“配流”、“流贬”、“安置”等互文通用,兹举数例为证。其一,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张易之诬奏魏元忠与司礼丞髙戬谋反,引凤阁舍人张说指证未果,张说以忤旨“长流钦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07页。对此,《旧唐书·张说传》记“配流钦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51页。《新唐书·张说传》则概言“流钦州”。[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06页。《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台省部·正直》又记“配岭南”。[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台省部·正直》,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8页。其二,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七月,高力士与内官王承恩、魏悦等因侍玄宗登长庆楼,为李辅国所诬,“除籍,长流巫州”。[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七《宦者上·高力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60页。关于高力士长流一事,相关资料之记载略异:《旧唐书·高力士传》言“配流黔中道”。[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高力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9页。《资治通鉴》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七月“丙辰,高力士流巫州”。[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肃宗上元元年七月丙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95页。郭湜《高力士外传》则云力士“除名,长流巫州”。[注](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柳珵《常侍言旨》又作“于岭南安置力士”。[注](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五《常侍言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其三,天祐三年(公元906年)闰十二月乙亥,兴唐府少尹孙秘因兄孙乘赐死,《旧唐书·哀帝纪》言秘“长流爱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09页。《册府元龟》则云“宜除名,配流爱州,充长流百姓”。[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五《总录部·谴累》,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35页。
作为唐代法制研究的基本资料,两《唐书》关于长流案例的记载也存在重大差异。《旧唐书》中本纪、列传对于长流事例多有记载,仅本纪部分就记述崔湜、第五琦、杨收等长流事例二十宗,其他散见与列传者亦不下三十余事。《新唐书》修订时因遵循“文省而事增”原则,对原始资料进行大幅删削,本纪部分长流事例或径行略去,或省称为“流”,列传部分明确记述的长流事例仅见十余条。《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资料中也以长流、配流、流贬等不同方式记述多宗案例。基于典籍文献著录之现状,对于唐代长流案例的蒐集与认定,必须予以严格限定,非有文献记载明确记载为长流者,概不收录,以免将“长流”与“常流”等混同。
据史籍文献综合统计,共检得可确证之长流案例64件。其中高宗朝4例(李义府等、董思恭、郑钦泰等、皇甫公义等);则天朝2例(裴伷先、张说);中宗朝2例(沈佺期、桓彦范等);玄宗朝14例(崔湜等、来子珣等、迴纥承宗等、齐敷等、魏萱等、薛锈、薛谂、卢晖、韦坚等、彭果、鲜于贲等、宋浑、王准等、李彭年);肃宗朝7例(李白、张均、高力士等、李逢年、侯令仪、孙蓥、第五琦);代宗朝3例(程元振、裴茙、来瑱);德宗朝5例(黎干等、萧鼎等、郜国公主子位等、王定远、崔河图);宪宗朝5例(崔简、于敏、韦正晤、李宗爽、权长孺);穆宗朝3例(于方等、李元本等、唐庆);敬宗朝1例(李训);文宗朝7例(石雄、柏耆、杨叔元、萧洪、吴士规、王晏平、萧本);武宗朝2例(李珏、李宗闵);懿宗朝3例(李鄠、严譔、杨收);僖宗朝2例(路岩、田令孜);昭宗朝1例(宋道弼等);哀帝朝3例(李彦威、柳璨、孙秘)。以安史之乱为界,高宗至玄宗朝共检得长流事例22件,所占比例为34.4%;肃宗至哀帝朝则为42件,所占比例为65.6%。长流作为常规刑罚得到日益普遍的适用。
唐代长流刑所涉罪名甚为繁复,赃污贿赂者计15件(李义府、董思恭、沈佺期、卢晖、彭果、宋浑、李彭年、李逢年、崔简、韦正晤、权长孺、唐庆、吴士规、王晏平、路岩),所占比例为23.4%;朋比交通者8件(郑钦泰等、皇甫公义等、崔湜等、齐敷等、魏萱等、鲜于贲等、王准等、李宗闵),所占比例为12.5%;事涉反逆者4件(李白、张均、程元振、黎干等),所占比例为6.3%。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因宫闱争斗或臣僚倾轧而蒙冤长流者甚众(桓彦范等、迴纥承宗等、薛锈等、韦坚等、高力士等、侯令仪、孙蓥、第五琦、来瑱、崔河图、石雄、柏耆、李鄠、杨收、严譔、宋道弼等、李彦威、柳璨,共计18件),所占比例竟至28.1%。此外,又有杀人(薛谂)、私通(萧鼎、李元本等)、厌祷(郜国公主子位等)、肢解(于敏)、伪造(于方)、诬告(李赏)、诈伪(萧洪、萧本)、株连(李宗爽、孙秘)诸多罪名与长流相关,于兹不赘。
二、唐代长流之放逐区域
唐代流人之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江南等六大地区和北方的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注]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在上述长流案例64宗之中,涉案长流人125名,可查明具体长流州郡者86人,其余多称长流岭南、领表或远恶州郡。唐代长流区域主要集中于剑南、黔中、岭南三道,而这三个区域接纳长流人的具体情况又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长流剑南道者凡6例,流配地点相对集中,其中流嶲州者有4例(李义府、薛元超、刘祎之、李善),流廉州者2例(卢幼临、张均)。长流剑南事例主要集中在唐前期,流嶲州者4例皆发生在高宗时,流廉州者玄宗、肃宗朝各1例。安史乱后,则鲜有长流剑南事例见诸史书。其次,长流黔中道者凡8例,分布地域较为分散,其中溱州2例(彭果、程元振),夜郎郡1例(李白),巫州1例(高力士),播州2例(孙蓥、来瑱),夷州1例(第五琦),费州1例(裴茙)。黔中道是中唐时期长流的热点区域,除天宝六载三月戊戌,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溱溪郡(溱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帝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1页。以外,其他7宗案例均集中在肃、代两朝。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岭南道,始于龙朔,讫至天祐,这一区域一直是唐代长流人犯最为集中的区域,涉及梧、振、横、钦、瀼、崖、泷、环、古、藤、琼、崖、白、窦、富、封(临封郡)、龚(临江郡)、端(高要郡)、峰(承化郡)、贺(临贺郡)、康、雷、昭、潮、新、象、爱等27州,其中尤以流配瀼州、驩州、崖州三地者居多。唐代对于流配剑南、岭表者之隶属管制有明确规定:据开元《狱官令》:“江北人配岭以南者,送付桂、广二都督府。其非剑南诸州而配南宁以南及嶲州界者,皆送付益州大都督府,取领即还。”[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5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流人押解至诸道之后,当由当地都督府统一编配,发遣所辖诸州配所安置服役。
据《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临潭郡,乾元元年,复为瀼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48页。领临江、波零、鹄山、弘远四县,距离京师约六千二百里,是岭南地区长流罪囚的重要区域之一。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驸马都尉薛锈因李林甫、武惠妃诬奏,“长流瀼州,至蓝田驿赐死”。[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帝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8页。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有尚衣奉御薛谂因杀人事泄,“长流瀼州,死于路,其党十人并杖”。[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三百六《外戚部·专恣》,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1页。
崖州,隋称珠崖郡,武徳四年(公元621年)平萧铣置,领舍城、平昌、澄迈、颜罗、临机五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珠崖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旧,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冬十月辛未,兴元严砺希监军旨,诬奏流人通州别驾崔河图,“长流崖州,赐死”。[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3页。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前寿州刺史唐庆因违赦敕科配百姓税钱,及破用官库钱物等事,“除名,长流崖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七百《牧守部·贪黩》,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8090页。
驩州,隋为日南郡。“武德八年,改为德州。贞观初,以旧驩州为演州。二年,置驩州都督府,领驩、演、明、智、林、源、景、海八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4页。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日南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旧。至京师陆路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万七千里,是岭南道最为僻远蛮荒的流放地之一。中宗朝即有长流于此者,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坐赃,“长流驩州”。[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沈佺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49页。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八月甲辰,前鄜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事觉,流驩州,于道赐死”。[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文宗开成元年八月甲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926页。至晚唐,仍可见长流驩州之事例,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六月乙巳,因遭宰臣崔胤诬告,枢密使宋道弼流配于兹,行至城东灞桥驿赐死。[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昭宗光化三年六月乙巳”,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31页。
司法实践中,为打击家族势力或官僚交结,对同时长流之亲属或同僚,往往采取异地安置的保安处分原则,[注]齐涛:《论唐代的流放制度》,载《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依托地理隔绝之天然障碍,切断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最终达到预防与惩戒并重的刑罚目的。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丙子,兰台左侍贺兰敏之获罪流雷州,“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高宗咸亨二年六月丙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67页。尚书右丞兼检校沛王府长史皇甫公义以託附敏之,长流横州。太子中允刘懿之“私托敏之,共母相见,配流康州;弟右史祎之知情,配嶲州。蕲州司马徐齐聃前任王府椽,与敏之交往左道,除名,长流岭外。前泾城令李善,曾教敏之读书,专为左道,长流嶲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五《总录部·谴累》,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32页。嶲州属剑南道,距京师三千二百三十里;横州隶岭南道,距京师四千七百五十五里;康州亦隶岭南道,至京师四千五百二十五里。玄宗时,凉州都督王君,诬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瀚海大都督迴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得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眀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六《将帅部·生事》,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2页。瀼州隶属道里如前所述,吉州隶江南西道,距京师三千六百五里;滕州隶岭南道,距京师五千五百九十六里;琼州亦隶岭南道,距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天宝六载,李林甫等诬告御史中丞杨慎矜心存异谋,克复隋室,妄说休咎,十一月二十五日,杨慎矜兄弟赐自尽,其党范滔决杖六十,长流岭南临江郡;太府少卿张瑄决杖六十,长流岭南临封郡。[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六《政事·诛戮上·杨慎矜自尽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78页。临江郡即龚州,距京师五千二百七十里;临封郡即封州,距京师四千三百八十五里。流犯身陷绝域,天各一方,在当时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极为不便的条件下,各个政治集团之瓦解遂成必然。
三、唐代长流之施行程序
唐代长流具有“不忍刑杀,宥之于远”[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8页。的意涵,作为死刑之减等,其具体施行程序较为严格。司法实践中大致遵循除名、发遣、安置等环节,其间又涉及决杖、程粮等相关问题。现存文献中缺少唐代长流制度的完整规定,纪传、诏敕中处置长流人的相关记述则成为研究该制度的基本依据,而《唐律疏议》与《狱官令》令中关于流犯与左降官的原则规定,也应成为长流制度的直接法律渊源。
(一)除名
除名是拟断长流之先决程序。由于长流人多为官僚贵族,流配之前须先褫夺犯官出身以来所有官爵,以流犯身份投诸远恶州郡。据《唐律疏议》:“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除免官当叙法”,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许敬宗希武后旨,构陷上官仪与梁王忠通谋,仪下狱死,家口籍没。十二月丙戍,上官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左肃机郑钦泰、西台舍人高正业、司虞大夫魏玄同、张希乘、长安尉崔道默等因与仪结託故,“并除名,长流岭南远界”。[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百三十三《总录部·诬抅第二》,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2页。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六月,江淮都统李峘畏失守之罪,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令仪坐除名,长流康州”。[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肃宗上元二年六月丙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14页。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新州刺史路岩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长流儋州”。[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僖宗乾符元年正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69页。罪臣免官长流后,其身份即同庶民,“长流某州百姓”的表述时常见诸唐代敕令之中。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魏州刺史卢晖坐赃,玄宗诏“特宽斧鑕之诛,俾从流放之典,可长流富州百姓”。[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七百《牧守部·贪黩》,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7页。开成元年(公元736年),前鄜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洪“长流驩州百姓”,洪男恪、女壻万缜等决杖流岭南崖、象等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四《总录部·诈伪》,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8页。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冬十月,朱全忠以主典禁兵,妄为扇动等罪名,将崖州司户李彦威“配充本州长流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88页。长流缙绅士族在完成向庶民身份转化的同时,其即有之议、请、减、赎、当等法定特权至此均告丧失。
(二)决杖
自武后朝始,罪臣长流开始附加杖刑,惟其决数虽时有更易,然基本未突破律文规定之上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太仆寺丞裴伷先因谏言忤旨,“於朝堂杖之一百,长流瀼州”。[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丙申”,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8页。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魏萱、前睦州桐庐县尉王延祐与武温眘相为党与,朝夕谈议,“宜各决一顿,长流窦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明罚》,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2页。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七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一万三百余贯断死,宪宗愍其母耄年,长孺“杖八十,长流康州”。[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帝王部·宽刑》,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5页。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八月,李元本为京兆府参军,与士族子薛枢、薛浑俱得幸于襄阳公主,驸马张克礼上表陈闻,穆宗“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后,得减死,杖六十,流象州。枢、浑以元本之故,亦从轻,杖八十,长流崖州”。[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李宝臣附元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71页。值得注意的是,决杖并非长流之必备要件,是否附加决杖,均由法司秉承圣意权断施行。
(三)发遣
唐开元《狱官令》对于递送流人设置了差使防援制度,派遣专人押解流人:“诸移流人……具录所随家口、及被符告若发遣日月,便移配处,递差防援。(原注:其援人皆取壮者充,余应防援者,皆准此。)专使部领,送达配所”。[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5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负责押解递送流犯者,“皆令道次州县量罪轻重、强弱,遣人防援,明相付领”。[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6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对于“稽留不送者”,唐律规定“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徒流送配稽留”,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9页。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兴州别驾麻察漏泄禁语,贬浔州皇化县尉,其党齐敷量决一百,长流崖州;郭禀量决一百,长流白州,“仍并差使驰驿领送”。[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明罚》,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2页。
唐代押解流犯以“长解”与“递解”[注]陈光中、沈国锋:《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相互配合,即原判法司差人押解,沿途州县协助完成辖内押解任务。司法实践中,长解事务多由两京诸司派员施行。广德二年(公元766年)春正月壬寅,前右监门卫大将军程元振变服潜行,将图不轨,“长流榛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纲递送。路次州县,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许东西。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程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3页。
(四)锢身
部分长流要犯在长流之际,须着械具,锢身遣送。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春秋左传》曰:会于商任,锢栾氏也。则禁锢之事,已见于春秋之时。故汉末有党锢。今以盘枷锢其身,谓之锢身,盖出于此。”[注](宋)髙承撰:《事物纪原》卷十《律令刑罚部》,(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3页。唐时实施锢身之械具当不限于盘枷一种,白诗即有“锢身锁”[注](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六《半格诗·闲坐看书贻诸少年》,朱金成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7页。之谓。枷、锁当均为押解流犯之法定械具。《资治通鉴》载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始定械具规格。法司采取强制措施时使用之械具,如枷、杻、鉗、锁等,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罪轻重,节级用之”[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9页。关于唐代强制措施的相关研究,可参阅陈玺:《唐代诉讼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6-71页。:“械其颈曰枷,械其手曰杻,钳,以铁劫束之也。锁,以铁琅当之也”。[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26页。开元《狱官令》还规定徒流人犯服刑期间,“皆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21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由此锢身押解长流人之具体法则,当据此施行。
锢身递送在唐代流配中得到广泛适用,元和八年二月,太常丞于敏肢解梁正言家僮,弃于溷中。事发,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5页。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三月己丑,又诏“兴元监军使杨叔元宜配流康州百姓,锢身递于配所”。[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6页。据诏敕中除籍为民的表述推断,本案所谓配流之性质,当属长流无疑。
(五)程粮
流人起解后,应驰驿前往流所,不得无故稽留。依开元《公式令》:“诸行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卅里”。[注]〔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公式令第二十一“马驴江河行程”,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唐律疏议》录此令文字略异:“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见(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流配人在道会赦”,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流人食物应由沿途州县提供,“每请程粮,停留不得过二日,其传马给不,临时处分”。[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7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秋七月六日,又敕流贬人不得在道逗留,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注](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0页。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除名配驩州,充长流百姓。敕言“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仍锢身,所在防押,递送至彼。具到日申闻,仍路次县给递驴一头并熟食。”[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大臣·宰相·贬降下·杨收长流驩州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9页。依旧制,流人不得乘马,[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八《薛收子元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92页。此处特谕递给脚力、熟食,当属法外开恩,而一般长流人犯只得步行跋涉,奔赴流所,且在途交通、饮食、医药等均无从保障,其处境之悲苦自可想而知。此外,《狱官令》中关于流犯沿途之生育、婚丧等事项之规定,长流人犯亦当一体遵行。
(六)著籍
一般流犯在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当处无官作者,听留当州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20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唐律疏议》规定,凡有官爵之流犯,除名至配所,均免居作:“除名者,免居作。即本罪所应流配而特配者,虽无官品,亦免居作”。[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应议请减”,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由此,长流犯官虽已除籍为民,并于当地著籍,仍享有免除居作劳役之特权。然长流人须接受当地政府严格管束,无故不得擅离配所。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二月丁酉,南海太守彭果坐赃,长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驰驿,领送至彼捉搦,勿许东西”。[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明罚》,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3页。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庚戍,或告宰臣第五琦受金,琦坐除名长流夷州,肃宗即诏“驰驿发遣,仍差纲领,送至彼所,勿许东西”。[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七《大臣·宰相·贬降上·第五琦长流夷州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3页。至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四月,又敕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流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同年十月又规定“流人不得因事差使离本处”。[注](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2、863页。然因唐时领表、剑南等地烟瘴寒苦,流犯逃归乡里之事时有发生,光宅元年裴伷先流瀼州后,“自岭南逃归”[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睿宗景云元年十一月甲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58页。,后复杖一百,徙于北庭。
四、唐代长流人犯之处置
(一)长流政策之变迁
长流制度创立之初衷,欲使流犯至死不回。由此,长流人非经特赦,勿得放免。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春正月戊辰朔,高宗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47页。长流不赦的原则在武后《改元载初赦》仍有所体现:“ 亡官失爵,量加叙录。长流人、别敕流人、移贯人、降授官人及役缘逆人用当,及造罪过特处分者,虽未至前所,并不在赦限。”[注](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三《翰林制诏四十四·诏敕五·改革》,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360页。
开元天宝之际,朝廷还多次发布诏敕,将长流作为减死一等的易科措施,在岭南等地大量安置长流人。据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四月二十日《孟夏疏决天下囚徒敕》:“其天下囚徒,即令疏决,其妖讹盗贼,造伪头首、既深蠧时政,须量加惩罚,刊名至死者,各决重杖一百,长流岭南,自馀枝党,被其诖误,矜其至愚,量事责罚,使示惩创”。[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八十五《帝王部·赦宥第四》,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40、941页。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二月敕曰“其犯十恶及伪造头首,量决一百,长流远恶处”。[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三《政事·恩宥一·以春令减降天下囚徒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79页。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四月丁丑又敕“天下见禁囚犯,十恶死罪及造伪头首、劫杀人,先决六十,长流岭南远恶处。”[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八十五《帝王部·赦宥第四》,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43页。上述流人非逢特赦,不得量移、叙复。
另一方面,唐代诏敕中又时常包含宽宥长流人罪责之意涵,这些诏敕因具有普遍意义,遂成为量移或放免流犯的直接依据,长流人终身不返的司法惯例渐被废弃。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壬辰,改元大赦,首次规定“天下长流人并放还”。[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八十四《帝王部·赦宥第三》,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页。,李义府妻、子即在当年放归。[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70页。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甲申,韦后临朝,改元唐隆,敕“长流任放归田里,负犯痕瘕咸从洗涤”。[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页。同月甲辰,相王李旦即位,大赦天下,诏“流人长流、长任及流人未达者并放还”。[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页。开元十七年(公元731年)十一月丙申谒桥陵,又敕“反逆缘坐长流及城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八十五《帝王部·赦宥第四》,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页。
长流制度经过长期运行,终身不返的旧制因赦令频发而渐成具文。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王播为刑部侍郎奏请“流人及先流人等,准长流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百十六《刑法部·议谳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4页。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王播奏请内容相关史料记载颇有出入:《唐会要》作“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见(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2页。宋本《册府元龟》、点校本《册府元龟》及《全唐文》卷六百十五《请放还配流人奏》均作“流人及先流人等,准长流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这里提到的“长流格例”值得特别重视,其中规定流人满六年放还,正与《狱官令》“六载后听仕”的时限一致。[注]据《宋刑统》引开成四年十月五日敕节文:“从今以后,应是流人六载满日放归。”见(宋)窦仪撰:《宋刑统》卷三《名例律》,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页。唐代法司或在此前编修格例,对长流人放还问题予以专门规定。至晚唐,对于长流人的诸多限制进一步松动,长流犯官之量移与叙用均被提上议事日程。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大赦文规定“左降官并流人,元勅令终身勿齿,及长流远恶,并云纵逢恩赦不任量移者,并与量移”。[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政事·恩宥四·咸通七年大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9页。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月九日懿宗《嗣登宝宝位赦》亦言“流贬人中从元敕云虽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或长流及充百姓,终身勿齿者,并与中书门下量与收叙处分,及量移近处”。[注](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百二十《翰林制诏一·赦书一·登极赦书》,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125页。
(二)长流人叙用转迁
唐代一般流刑以六年为限,流人至配所“六载以后听仕,即本犯不应配流而特配流者,三载以后听仕”。[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9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然长流多在常流三千里上限以外,其流配时间不恒,非有赦令豁免,终身不得返乡、叙复。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九月,司农卿李逄年以贪冒黩货,“除名,长流岭南瀼州百姓,终身勿齿”。〔[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五《卿监部·贪冒》,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4页。点校本《册府元龟》误断为:“(敕宜)除名,长流岭南瀼州,百姓终身勿齿。”语义未恰,当改。,即永不叙用之意。
同时,禁锢诏敕之效力往往还及于犯官子嗣,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秋七月,武三思阴令人疏韦后秽行,牓于天津桥,请加废黜。御史大夫李承嘉诬奏桓彦范等人所为,中宗以彦范等五人因拥立之功,尝赐铁劵,许以不死,“乃长流彦范于瀼州,敬晖于崖州,张柬之于泷州,袁恕己于环州,崔玄暐于古州,并终身禁锢,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岭外”。[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十一《桓彦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31页。禁锢者,“勿令仕也。”唐孔颖达言“禁人使不得仕官者,……谓之禁锢,今世犹然”。[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页。可见,至唐代,禁绝人犯入仕之意犹存。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二日《开元格》规定: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等二十三人,因残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状尤重,“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远处。纵身没,子孙亦不许仕宦”。[注](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刑八·峻酷·开元格附》,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31页。
唐代司法实践中,“比年边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注](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2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流人犯几乎皆属衣冠士族阶层,与一般流人相比,长流人并无戍守边塞或居作役使之法定义务。移居远恶州郡后,伴随国家政治形势变化以及个人身份因素影响,特赦放还或起复叙用者皆不乏其例。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因上官仪案长流远恶者甚众,简州刺史薛元超于“上元初,赦还,拜正谏大夫”。[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八《薛收子元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92页。司虞大夫魏玄同亦于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七《魏玄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49页。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尚书右丞卢藏用坐託附太平公主,长流岭表。“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04页。前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铁福建院官权长孺以坐赃杖八十长流康州,“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注](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百一“权长孺”条引《乾馔子》,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17页。武宗初立,宰臣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会昌三年(公元843年)长流驩州。至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崔铉、白敏中逐李德裕,征入朝为户部尚书”。[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05页。此外,亦有长流人赦免后返乡定居,不再入仕。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泾城令李善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曹宪附李善》,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6页。
(三)流人滞留与赐死
“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注](唐)宋之问:《宋之问集校注》卷三《诗·发藤州》,陶敏、易淑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56页。中国农耕文明条件下形成的安土重迁思想,对长流人的精神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流人由于苦闷失意、贫病老衰,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若未能及时获得赦宥,长期滞留贬所,甚至客死异乡之流人不在少数。长流人李义府《嶲州遥叙封禅诗》曾云:“触网沦幽裔,乘徼限明时。周南昔已叹,邛西今复悲”。[注](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1页。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大赦,惟不及长流之人,义府忧愤发疾而卒。[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70页。唐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同欲随者,听之”,随流家属须于当地附籍,但“不须居作”。“若流、移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流犯应配”,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为保障人犯妻妾随行,《狱官令》专门规定“流人科断已定,皆不得弃放妻妾”。[注]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开元狱官令复原清本》第13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5页。据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今后有配长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减等者,并勒将妻同去,有儿女情愿者,亦听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并许东西。州县不任勾留,情愿住者亦听”。[注](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5页。
由然受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仍有大量长流人及家眷长期滞留贬所,甚至终身不返,客死异乡。安史乱后,朝廷曾十余次发布诏敕,责令地方官长协助流人归葬。肃宗元年建辰月己未诏:“流贬人所在身亡者,任其亲故收以归葬,仍州县量给棺榇发遣”。[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八十七《帝王部·赦宥第六》,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70页。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二月册皇太子,敕“左降官及流人,并与量移,亡殁者任归葬”。[注](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皇太子·册太子赦·长庆二年册皇太子德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又敕“如已亡殁者,并许归葬,如缘葬事困穷,不能自济者,委所在官吏量给棺榇,优恤发遣”。[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政事·恩宥四·咸通七年大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9页。
先天至天宝时期是唐代长流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长流时常作为死刑减等之处置措施,同时,赐死在途长流人的现象亦时有发生。部分流人名义上被流于边裔,实际上却在未达流所之前,于沿途驿站实施死刑,而长安东郊通往领表之蓝田、灞桥等驿,往往成为诛杀流人的首选场所。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丁卯,崔湜附太平公主,除名,长流岭表。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酖,乃追湜赐死,缢于驿中。[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崔仁师孙湜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23页。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王銲与故鸿胪少卿邢璹子縡潜构逆谋,侄王鉷男“准除名长流岭南承化郡,备长流珠崖郡,至故驿杀之;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五《王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32页。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秋七月乙酉,襄州刺史裴茙“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驿”。[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0页。此外,亦有长流人行至贬所后赐死之例,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七月,括苍太守韦坚为李林甫所陷,“长流岭南,杀之。坚弟将作少匠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及男河南府尹曹谅,皆贬远郡,寻又分遣御史并赐死,诸子悉配隶边都”。[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五《总录部·谴累》,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32页。此条史料点校本《册府元龟》误断为:“坚弟将作少匠,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及男河南府尹曹谅,皆贬远郡。”据《旧唐书·韦坚传》:“坚弟将作少匠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24页。韦兰、韦冰名讳、官制皆误,且所谓“尹曹”当为“户曹”之讹,皆当据改。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十月,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严譔因广补卒,擅纳缣廪长流岭南,次年二月,赐死于流所。[注](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七《政事·诛戮下·严譔赐自尽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5页。
五、长流制度的后世影响
五代、两宋时期沿袭唐代长流政策,时常将犯官除籍为民,放逐荒远地界。长流人非经特赦,不再量移放免之限。后唐庄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秋八月丁亥,诏“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等可并自长流,后纵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十三·明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07页。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十一月癸未,祕书少监于峤为宰臣赵凤诬奏,“配振武长流百姓,永不齿任”。[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四十《唐书十六·明宗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55页。这一时期,朝廷发布特赦诏敕的原因也基本与唐代相同。后梁末帝龙德元年(公元921年)五月丙戌,改元。敕“长流人各移近地,已经移者许归乡里。”[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十《梁书十·末帝纪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8页。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八月戊申,册尊号礼毕,制“长流人并诸色徒流人,不计年月远近,已到配所并放还。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一切不问”。[注](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九十三《帝王部·赦宥第十二》,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5页。司法实践中,特赦放免长流人的制度在五代仍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如天成中,秘书监兼秦王傅刘赞因秦王得罪,长流岚州。“清泰二年,诏归田里。行至石会关,病卒”。[注](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八《唐臣传十六·刘赞传》,(宋)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7页。
唐开元时期逐步形成的赐死长流人犯的司法惯例,亦为五代长期继受。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八月癸未,河南县令罗贯坐部内桥道不修,“长流崖州,寻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顿处死”。[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三《唐书九·庄宗纪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4页。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秋七月,曹州刺史成景宏坐受本州仓吏钱百缗,贬绥州司户参军,“续敕长流宥州,寻赐自尽”。[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十九《唐书十五·明宗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4页。后周广顺四年(公元954年)十二月辛未,邺都留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削夺在身官爵,“长流登州,寻赐死于北郊”。[注](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十三《周书四·太祖纪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00页。
宋代在继受唐《狱官令》的同时,尤其关注长流刑之易科功能。[注]对照天圣《狱官令》与开元《狱官令》可知,宋代流刑皆以唐令为蓝本损益而成。如宋令仍禁流人放妻妾,然“如两情愿离者,听之。”(宋第10条);北宋递送流人“其临时有旨,遣官部送者,从别敕。”(宋第12条);流移人在路“每请粮,无故不得停留。”(宋第13条)凡此诸条,皆与唐令有所异同。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狱官令卷第二十七,中华书局2006年版,415、416页。判定长流者,多为原免减罪之例,长流作为死刑贷命措施被广泛适用。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因贻误战机,减死,削夺在身官爵,“并其家属长流房州”。[注](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七十九《傅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74页。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十月已未,殿中丞童静专坐赃,“削籍,长流郴州,不得叙用”。[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已未”,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98页。徽宗末,户部尚书刘昺坐与王寀交通,“开封府尹盛璋议以死,刑部尚书卢致虚为请,乃长流琼州”。[注](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刘昺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07页。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八月戊午,朝散大夫洪刍等三人因奸赃等事“贷死,长流沙门岛”。[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戊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95页。宋辽之际,长流刑又渐具军戍意涵,《辽史》有兴宗重熙年间,永兴宫使耶律褭履减死“长流边戍”[注](元)脱脱等:《辽史》卷八十六《耶律褭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207页。的记载。
长流属封建闰刑性质,其刑罚位阶恰介于流、死之间,承担减死贷命之重要功能。沈家本考唐宋以降流配、充军诸刑嬗变历程,言“宋沿五代之制,于流罪配役之外,其罪重者刺配充军,始区分军、流为二。元制,盗贼合流者有出军之例……明制颇有沿于元者,充军即仿出军而变通之”。[注](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充军考上》,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2页。配役、充军等皆为死刑降等,据律不在正刑之列。与长流相比,其内涵与适用更为复杂。两宋配役源于唐五代流配刑,多附加黥刺与决杖;配役有军役、劳役之分,且刑期不恒;放逐区域有沙门岛、远恶州军、广南、邻州、本州牢城等十余等。充军则始于宋元,至明清方为常刑。刑期分终身与永远两类;放逐区域分极远、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和附近,合称“五军”。因后世配役、充军之法日善,至宋元之交,长流刑渐趋衰微。总之,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既是对传统“三流”制度的完善,更促进了死刑易科制度的发展,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宋元明清配役、充军等同类刑制之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