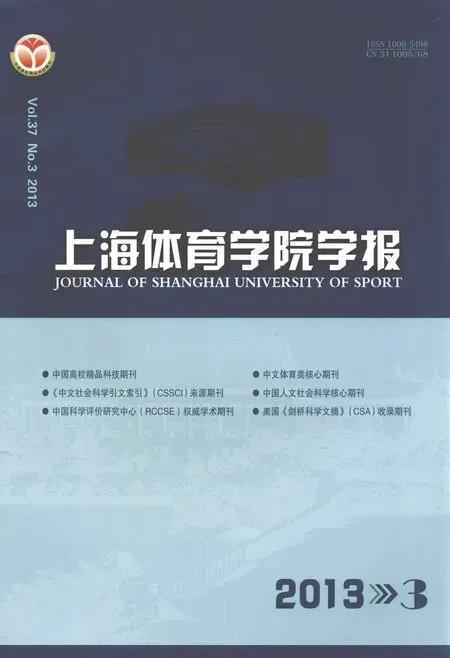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盛与殇
——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与对“现代解读”的反思
高 强
(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241)
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盛与殇
——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与对“现代解读”的反思
高 强
(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241)
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之间存在着以现代视角返观的“现代解读”方式。以哲学人类学的追问方式重新梳理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繁盛和殇落过程,阐明它与古希腊游戏传统之间的此消彼长,从中挖掘古希腊竞技运动中蕴含的身体技艺之知及其在经历古希腊传统社会、中世纪直至现代的过程中,身体和技艺逐渐淡出社会的历程。解析“现代解读”方式存在误读的因素,提出哲学人类学追问中体育的“在世”概念。
古希腊竞技运动;现代解读;哲学人类学;在世
Author’s address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Health Assessmen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1 问题与方法
1.1 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现代解读” 现代奥运会是否继承了古希腊的竞技精神、兼备了其中的宗教与文化气息?“竞技者”是否在现代重现[1]?这一系列的问题体现在对古希腊竞技运动是否为现代体育起源的争议之中,其中以西方体育起源的教育说和闲暇说最具代表性:持此教育说观点的法国体育社会学学者Henri-Irénée Marrou和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家Jean-Marie Brohm就认为,在体育之中存在着超越“社会和伦理局限”的本质[2-3],能在历史变迁中保持其本质,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希腊青年尤其是希腊贵族青年的各种身体教育的方式形成了现代体育的起源;而持闲暇说的法国体育社会学学者Pierre Parleras与德国社会学家Norbert Elias就反对前者,认为现代体育是来自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休闲活动。他们在反对古希腊竞技活动和现代体育一体同流的基础上,认为体育是现当代欧洲政治议会化和社会生产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调节机制而非宗教仪式[4-5]。
Norbert Elias和Eric Dunning比较分析了古代和近代搏击运动,发现2种运动在规则、训练方式中都对暴力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6-7]。究其本质,上述2种观点就是对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之间是沿袭抑或割裂的争论。笔者将这2种观念称之为“现代解读”,并不仅仅意旨这2种观念产生于现当代的一个时间概念,而认为它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体育中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基础上的“返观”,是一种现代观念下的“投射”。
在对“现代解读”进行反思之前,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是在何种社会观念下得以繁盛的这一问题应得以厘清。大卫·勒布雷东指出,古希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存在着对身体活动影响最大的2种社会观念——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在古希腊传统社会中,身体整体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倾向于将个人的身体、自我、社会、世界整合为一体,在仪式的过程中形成交互作用[8]13-21,而身体的个人主义则是反其道行之,主张将身体与自我、社会、世界中割裂开来的观点[8]65,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观念便是心物二分,即认为人的身体是一种生理基础上的肉体,而心灵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的身体结构与社会结构既不存在显性的联系,也不存在隐喻式的社会仪式层面上的联系,仅将身体做一种机械论层面上的解读[9]。本文所致力批判的便是这种忽略古希腊身体整体论观念,而仅在现当代身体个人主义观念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竞技运动作出的“现代解读”,甚或说“现代误读”。不立不破,首先要实现的是一种“立”的方法,所以本文希望回到古希腊竞技运动和古希腊社会之中,在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的流变过程中寻找古希腊竞技运动由盛到衰的过程,进而反思“现代解读”的误读所在。为展开这一义理,一条哲学人类学思考的路径是上佳之选。
1.2 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 哲学人类学的思考方式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智者派“以文化哲学的观点发现人”,从“文化习俗”的视角探讨人的“创造文化的力量”[10]36-37。在现代,海德格尔于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亦有论述[11],但是它的真正兴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舍勒的工作。哲学人类学的考察对象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形成人之为人的知识,同时质疑了有关于人的、“科学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知识”[10]4-5。由此哲学人类学有以下基本观点:人类一方面有“一种稳定遗传的天性,才能赋予人类以最一般的结构、特殊的知觉和行动方式等等。在此之上,产生了不决定于天性而决定于人自己创造力和决心的第二方面”;这第二方面正是包含了“文化”——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等,所以兰德曼就认为“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了人自己去完成”。基于研究对象和基本观点,哲学人类学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它“通常是从显著的人的特征出发,由此追问:如果在一个存在物中,这种特征起着有意义的和必不可少的作用,那么怎样构成这个存在物”,所以在哲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会关注“直立行走”“劳动”等人类特征,由此来解释人类的本质[10]47。
哲学人类学的方式首先悬置了定义的问题,转而向“特征”进行追问,以此考察问题的本质。当这一方式转向古希腊竞技运动时:首先需要的是回到古希腊竞技运动之中,回到古希腊社会之中,而不是用近现代才拥有的观念、概念重构古希腊竞技运动;其次要发现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特征,研究这些特征并不需要穷尽所有的特征,而是更多地梳理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的兴衰浮沉,从而形成对古希腊竞技运动的返观。
在当代体育哲学的争论中,对于体育的本质争论莫衷一是,但是身体和技术这2个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体育的2个重要特征[12]。同样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这2个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此要作一个概念上的修正。根据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区分:“‘技艺’通常是说一组动作、行为,一般来说是手工的,有组织化和传统的,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的生理性和肢体性的目标。”[13]而“‘技术’指向那些被认为是现代的、复杂的、精巧的、基于知识的客观现象”[14]。可见在古希腊时代,技术这一概念还未被完全展开,而更多的是一种技艺。更进一步,莫斯又在对游泳动作的学习中提出体育的艺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身体的技艺”[15]。本文关注古希腊竞技运动的身体和技艺这2个特征,勾勒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运动,阐明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繁盛与殇落,展现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在其中的此消彼长。
2 古希腊竞技运动之盛与殇:身体与技艺的繁盛与退隐
由于古希腊竞技运动中蕴含的身体与技艺这2个特征的繁盛与退隐并不能直接体现,需要以史为据才能从中透析出身体与技艺的扬抑过程,而由古里奥尼斯所挖掘的古希腊竞技传统与游戏传统的此消彼长正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2.1 隐于语词之中的历史:竞技传统与游戏传统 身体技术视角下Suits在现代英语中区分了竞技、体育和游戏这3个概念,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和差异[16];但由于缺乏历史的视角,并不能为解释古希腊竞技运动提供有益的帮助,而希腊学者古里奥尼斯在希腊语中对现代英语“sport”一词翻译的词源分析揭示了一段被语词遮蔽的历史。在现代希腊语中,将“sport”一词翻译成“αθλοπαδια”。通过对构词的分析,古里奥尼斯认为,其实“αθλοπαδια”是由2个单词“αθλο”和“παδια”组成的,分别对应着古希腊时代的竞技运动和古希腊时代的游戏活动。对于前者,古里奥尼斯[17]41认为,竞技运动是人用“睿智、独特”的方式驯服人的“攻击性本能”“是通过比赛,以文明竞争的方式追求第一或胜利”[17]8,追求人与自然和群体的和谐共存[17]105;但是针对古希腊时代的游戏传统,胡伊青加描述道,“游戏比文化更古老”“动物则无需人教也会游戏”,游戏既是“自然冲动和习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构造”[18]1-5。古希腊人严格区分竞技与游戏,认为游戏本身存在着欺骗,仅仅为了追求胜利[17]43。
古里奥尼斯对语词的词源分析揭示出蕴涵在古希腊时代2种不同的身体活动传统,一是竞技运动传统,二是游戏传统。在他看来,即便这两者之间在外表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却有着本质的不同[17]119。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繁盛与殇落也正是蕴含在这2种传统的此消彼长中。
2.2 古希腊竞技运动之盛:身体技艺之知的“习得”古希腊竞技运动是“美德”(arete)与“竞技”(agon)的并举,对于这2个词的阐释有助于理解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繁盛。根据Miller[19]47-48对希腊语“美德”即arete一词的解析:“勿庸置疑,美德一词是与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在此Miller用的是athletics一词,有运动的意味,却不完全是现代的田径运动,所以翻译为竞技运动)不可分割的,也承载了太多的内涵”“包括品德、技巧、力量、荣誉、优秀、勇敢和高尚,但是这些词无论是单个还是整体都无法完整地体现美德。美德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每个古希腊人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是一种万物融通的状态,而对于“竞技”一词,R.A.Mechikoff[19]48发现,在《荷马史诗》中“竞技”一词直接被解释为“竞技场”,但是之后“竞技”一词的解释被逐渐丰富,音乐、诗歌、公开演说都能成为竞技的内容。可见,虽然竞技运动并非美德的全部,却是古希腊人习得美德的一个途径。
对于“美德”和“竞技”之间所形成的“习得”关系,在众多对古希腊竞技运动进行研究的论文中并不鲜见,有从德性角度赞赏这一“习得”关系的[20],也有研究从古希腊竞技中挖掘了古希腊美德之中的身体性[21]。在这些讨论中,往往缺乏了在历史变迁层面上的论述,无论是在其中的竞技活动,还是其中的身体概念都是相对封闭和固定的,无助于分析古希腊竞技运动由盛转衰的过程。延续在导言中所提出的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在身体和技艺这2个特征上,挖掘古希腊竞技传统的繁盛之因由,从一个侧面可以解释“美德”与“竞技”之间的“习得”关系,了解身体整体论对“习得”的重要意义。
2.2.1 古希腊竞技运动中身体整体论色彩:“习得”关系形成的可能性 古希腊社会具有身体整体论色彩。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身体的形象是自我的形象,由构成大自然和宇宙的原材料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塑造而成”[8]13-21。在古希腊时代,身体、个人、社会、大自然等,在社会观念中都是一体的。由此,亚里士多德崇尚“身体的善”[22]13,认为首先身体的善是一种美德,其中包含了“健康、强壮、健美、敏锐”和“节制”[22]140[23]。这样个体才能通过身体的行为[22]13,实现“个人的善”,才可能进入政治和公共活动,实现更高的“国家的善”。可见,在古希腊身体是实现美德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身体整体论的社会观念下,古希腊竞技运动中“美德”和“竞技”之间的“习得”关系具备了可能性。
希腊竞技运动中包含的“习得”可能性展现为“自然隐喻”和“国家隐喻”。针对“自然隐喻”,英国体育哲学家C.Jane和Darwin认为,古希腊奥运会的很多项目都是在模拟自然界的天体(太阳、流星)、神圣生物(公牛、骏马)的运动,实现个体与自然的融通[24]。以“自然隐喻”为中介和基础,个体在竞技运动中找到身体的美,形成一种以身体形象为主导的[6]、古希腊式的个人的善。在古希腊竞技运动的“国家隐喻”中蕴含了高于个人的善的“社会的善”。竞技运动的“国家隐喻”主要体现在公正理念和教育理念之中:在公正理念中,古希腊竞技运动的开展必须有公开的场地,有日光的见证,让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无差别”的比赛,都体现了正义的社会展示,以构建国家和维持社会群体[24];在教育理念中,竞技体育的训练强调一种“全才式”的教育,而不是仅仅接受某项训练,这样才能转变个体的身体私人性,而成为国家的公器[25]。
正是“个人的善”和“社会的善”形成了古希腊时代“美德”的主要内容,而只有在古希腊传统社会所具有的身体整体论社会观念下,古希腊竞技运动中才能蕴含着“自然隐喻”和“国家隐喻”,从而在身体的竞技中渗透了“个人的善”和“社会的善”,实现了“竞技”和“美德”之间“习得”关系的可能性。
2.2.2 古希腊竞技运动中的“技艺之知”的分殊:“习得”关系形成的必然性与蜕变的伏笔 在苏格拉底时代,“美德”有着宽泛的含义,如“美德即知识”,其中包含了知识的内涵,也包含“善于做某事”,这种“善于”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艺”[26]。如果从这一层面上理解,知识也是宽泛的,不仅仅是指理论性、书面性的理论知识,同样也包含着实践性、操作性的技艺知识。之后亚里士多德将这一宽泛的知识概念区分为3类:“理论知识或者科学知识;实践的智慧、实践的知识或明智、审慎;技艺、技巧或生产的知识、制作的知识”[27]。技艺在亚氏处被专门地划分出来以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28]。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承认技艺是一种知识,区别在于前一种的“技艺之知”是宽泛的,实现着美德,后一种的“技艺之知”却是区隔的、特定的。
在“美德”与“竞技”之间存在着“习得”关系的古希腊时代,“竞技”是为了实现一种“技艺之知”而存在的,即便是2种区别的“技艺之知”。就第1种宽泛的“技艺之知”而言,古希腊竞技运动中对“特殊化”的拒斥,对其他技艺的包容就体现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就反对音乐教师和体操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区别化的训练,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应当接受所有种类的体育运动,而不是某一项运动的训练”[25]。同时,让现代体育无法理解的是,古希腊时代的竞技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展开哲学论辩,学习算学、修辞学等其他知识(其他技艺)的场所。就第2种区隔的、特定的“技艺之知”而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对宽泛的“技艺之知”的蜕变。这一蜕变来自于公元5世纪的竞技运动的“特殊化”和“商业化”。McIntosh[29]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大众英雄已经变成了‘赏金猎人’”“‘运动员’这一称号已经不再是荣誉的象征,而是一个在饮食、训练都不同于普通公民的职业”。可见在这一时代,已经独立形成了“竞技技艺”,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关的训练手段和生活方式,虽然是之前宽泛的“技艺之知”的蜕变,但是仍不失为一种知识的形式。
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存在的2种不同层次的“技艺之知”,同时也为构建这2种“技艺之知”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较为具体的训练手段、生活方式,为“美德”和“竞技”之间的“习得”关系建立形成了一定的必然性,使古希腊竞技运动——一种身体的技艺之知繁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2种“技艺之知”仍然实现了身体与知识、社会的融通,是身体整体论的具体体现,但是在它们之间的蜕变关系中存在着身体整体论崩塌的隐患,也埋下了古希腊竞技运动殇落的伏笔。
2.3 古希腊竞技运动之殇:身体的技艺之知的衰落与游戏传统的兴起 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潜在的游戏传统的逐渐展开促使了古希腊竞技运动的殇落。这些因素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下,以身体和技艺这2个特征为线索,身体整体论和它在竞技运动中的表现——“技艺之知”呈现出以下衰落特征。
2.3.1 身体整体论的殇落 桑内特区分蕴含在古希腊传统社会中的2种语言:一种是理性的语言,也可以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理论性知识”;一种是神话的语言,这是维系古希腊传统社会身体整体论的根基。在神话中,充满着神、奇幻的人和神迹,是通过“仪式”进行具体化,而“在仪式中,话语是借由身体的动作来传达的”[30]79-80,但是这一仪式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和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中形成了衰败之势。如在克里特岛的“抚牛腾跃”活动向伊利亚特半岛的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就是仪式语言衰败的表征。在克里特岛的“抚牛腾跃”中,只是翻越公牛[17]18。在伊利亚特半岛上,模仿了“抚牛腾跃”,但以杀死公牛为结束[17]46。在公元前430年发生的瘟疫中,构成仪式的社会组织、政治机制遭到破坏,人染病的身体也成为了秽物[30]81-85。
随着身体整体论的仪式语言逐渐淡化,古希腊城邦间为了实现政治利益和影响力对古希腊竞技赛会主办权展开了争夺[31],其中包含了仪式语言淡出的过程。在早期的主办权争夺中,神话起源一直是实现主办权的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如伊利斯人和皮萨人之间的争夺就集中在赛会的神话起源究竟是赫拉克勒斯还是赫拉女神与英雄珀罗普斯。在举办公元前364年的奥运会时,伊利斯不顾奥运会“神圣停战协定”的约束,向奥运圣地进攻,并在血腥中重获奥运会的主办权[31]50-54。从这一过程中便可以看出,神话与世俗生活之间的联系被逐渐打破。古希腊的神话中神多以自然神为主,这一神话与世俗之间联系的断裂也就标志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断裂。古希腊竞技运动得以繁盛的身体整体论基础被削减。
2.3.2 从技艺到技术:“技艺”的殇落 在古希腊竞技运动繁盛的时代,同时也是身体整体论繁盛的时代。即便在柏拉图的身心二元(将身体与心灵区隔开来)的理论中,虽然强调了“精神(笔者认为即心灵)来自一个更高的世界,只是暂时把自身合并入生命之中”,但是精神从“那个较高的世界带来了寓于其中的法则,尽力追求真理”,在人的生命之中就驻留了“追求真理”的法则。在那个时代的人是“智慧的人”[10]116-117,人的技艺也是一种获得了更高世界真理法则的知识,是为技艺之知。这一状况是与古希腊时代手工业较为发达密切联系的,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手工制作业逐渐没落,形成了技艺与技术的分化。“技术则同成批生产产品的机器操作活动联系起来”,是“不自由、受约束的活动”[32],而技艺更多地和“锻炼性”“表演性”活动联系在一起[33],和现代的艺术活动有了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竞技活动仍然处于“技艺”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在技术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从古希腊晚期开始,身体整体论的坍塌,个人与自然、世界的逐渐剥离,古希腊时代“智慧的人”逐渐转化为“制作的人”,知识便与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与技术密切相关。由此,知识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所区别的“理论之知”“实践之知”和“技艺之知”只在知识体系中存留了“理论之知”(即与仪式的语言相区别的理性语言),技艺已不被当作一种知识的形式存在,因而“技艺之知”也随之殇落[10]117。正如前文所述,“技艺之知”的存在是古希腊竞技体育中通过“竞技”习得“美德”的关键所在,而“技艺之知”的缺失打断了“美德”与“竞技”之间的联系,那么古希腊竞技运动的文化本质就缺失,古希腊的竞技运动无奈地走向衰落。
2.3.3 游戏传统的存留与繁盛 古希腊的竞技传统随着身体整体论的坍塌及“技艺之知”在知识论体系中的淡出逐渐失落。根据上文中古里奥尼斯[17]84所作出的竞技传统和游戏传统的区分,古希腊的游戏传统并未在这一过程中消失,却在中世纪的过程中得到强化。
首先“球类比赛”和“血腥的骑士比武”是中世纪流行的“身体锻炼形式”[17]88。虽然这些锻炼形式与古希腊的竞技运动极其相似,而吉列特指出,古希腊的竞技运动是一种竞技,“是平等的比赛,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免于争斗和冲突”;但是在中世纪的球类比赛和比武运动中将“竞技”误读为“竞争”,充斥对立、敌视,要求消灭对手[17]89。
在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彼得拉克等人文主义的复兴者一直试图重读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再现“美德”[17]97;但是他们的做法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中国哲学先人庄子就曾在其作品《天道》中批判过这一错误。庄子借工匠轮扁与齐桓公之间的对话,认为一些能够记录下来的手工业的一般原则可以被人熟记,但是那些“得心应手而口不能言”的技艺无法被以熟记的方式进行传递[34]。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者只复兴了古希腊的文本,而没有复兴古希腊文本之中的精神内质,更甚,他们将古希腊时代简单的表达方式转变为花哨、含糊、误导的鼓动方式,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理论——不存在客观真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真理,这一理论表现在竞技场上为那种“不择手段、以胜利为唯一追求目标的冲突式竞争”[17]97-98张本。
在上述2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希腊意义上的竞技者消失了,竞技传统也隐而不现,随之出现的便是“游戏者”的登场,游戏传统的繁盛。游戏传统与现代的竞技体育有着极大的亲缘关系。由于本文意旨阐明古希腊竞技传统的盛衰变迁,游戏传统作为一个更为宽广的概念则不在本文中赘述。
3 对古希腊竞技运动“现代解读”的反思与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
3.1 对古希腊竞技运动“现代解读”的反思 在哲学人类学式分析中解析了竞技传统和游戏传统的此消彼长,以及其中身体与技艺这2个特性在历史过程中的跌宕起伏,从古希腊竞技传统的盛与殇之中解读“身体的技艺之知”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遭遇。如本文开头时所提及的教育论和闲暇论观点,这一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现代解读”的反思。
若要分析“现代解读”的误读所在,需要明了在古希腊竞技运动殇落后主导身体活动的2个主要因素,一个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游戏传统,另一种则是“试图将人类的身体转变为创造纪录的机器”[17]163的锦标运动。古希腊竞技传统的社会观念已经消失,而古希腊竞技传统的躯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但是对这一躯壳的应用被深深打上了游戏传统和锦标运动,及其蕴藏在这两者身后的社会观念的烙印,由此“现代解读”才得以出炉,所以剖析“现代解读”中存在的种种预设是形成反思的必要条件。
3.1.1 “现代解读”中的身体个人主义色彩:“投射”的误读 身体个人主义是在古希腊传统社会的身体整体性坍塌后的一种社会观念,也是在本文开头所提出却未加甚解的。勒布雷东在《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在以身体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身体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孤立见证了一种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分离的社会秩序”“身体作为社会、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个人化因素,从主体上游离出来,被视为主体的属性之一。身体成为一种所有,一件附件”,而人是“一个脱离于自我的人,脱离于他人的人,脱离于宇宙的人”[8]65。在这种社会观念下,现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整合自我、他人、宇宙的“完整的人”的教育,培养的是受到无形的社会权力制约的人,所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现代教育便是“一种符号暴力”“教育行动的目标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35]13。
在古希腊竞技之中,或者以竞技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古希腊教育是为了习得美德,而古希腊时代的美德是一个身体、人、社会、宇宙相整合的最高存在,并非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古希腊时代,体育教育和当代的教育、体育教育和竞技运动有着社会观念上的本质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古希腊竞技运动殇落的过程中被打断。可见,法国体育社会学学者Henri-Irénée Marrou和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家Jean-Marie Brohm等人将古希腊竞技运动与现代体育在体育教育层面上建立联系的教育说,是以现代教育中蕴含的身体个人主义观念“投射”古希腊竞技运动,是一种在现代观念下的解读;所以是一种“现代误读”,而对古希腊竞技运动中所深藏的、富含了身体整体论色彩的“技艺之知”的“习得”关系毫无触及。
3.1.2 “现代解读”对古希腊游戏传统的旁落:“忽略”的误读 坚持现代体育起源于英国休闲运动的闲暇说,尤其是Norbert Elias对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中身体暴力的容忍程度、操控程度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古希腊的竞技传统与现代体育竞技有着质的差异。借此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体育与古希腊竞技运动虽然有相似的身体活动方式,但是其中蕴含的社会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闲暇说以此为依据,完全割裂了现代体育与古希腊身体活动方式之间的联系。
闲暇说只是着眼于现代英国休闲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对现代体育形成的影响,只是着眼于古希腊的竞技传统与现代体育之间的差异,而未意识到蕴含在英国闲暇运动背后的古希腊游戏传统的存在。胡伊青加以人类学的方式,论证了“游戏是生命的一种功能”,文化只是一种“亚游戏”的存在这一思想,继而以此为出发点,梳理了游戏形成于文化之前,发展于古希腊时代,繁盛于中世纪并同时超越古希腊竞技传统,最后繁盛于现代社会的过程,充分描述和论证了游戏传统与现代体育之间的亲缘关系[18]7,而这点恰恰被闲暇说所忽略,形成了一种忽略古希腊游戏传统的“现代误读”。
3.2 哲学人类学式的追问:体育的“在世” 以特征追问古希腊竞技运动,反思教育论与闲暇论中的现代性观念投射,这种哲学人类学的追问方式是否为体育哲学的研究带来几许新意,仍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逻辑分析方法,而是将具体的历史事实与哲学概念进行有机整合而成。在当代体育哲学研究之中,对体育概念的定义调动了多种哲学定义的方法。大多有着明确定义的体育概念都符合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而如背景发生了转变,就会产生一种概念上的纷争。可以想象,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绝对不会发生极限运动是否属于体育这一概念的争论。在体育的发展史上,新的运动方式层出不穷,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观念的变迁风起云涌。哲学人类学的追问方式就是深入了这种运动方式的改变和社会观念的变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概念逻辑层面上的纠缠,但是这种跳出的方式究竟是一种哲学的规避还是新的研究思路需要思考。
其次,在认识论层面上,可以认为,各种体育概念的定义都是对于体育的认识,是一种知识的形式。罗蒂认为近代以来,对知识的认识有着浓重的表征主义色彩,即认为“知识的本性是内在心灵对外面对象的表征”,所以就形成了主体与客体,内在和外在的分离[36]。当代对体育概念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这一方法。体育运动的历史可以被认作是一连串历史的事实,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秉承一种抽象式的分离,即用一个概括的、抽象的方式对事实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体育概念的定义脱离了对体育历史的考量。
海德格尔就认为当人们能够自如地应对世界的活动时,是不会形成这种抽象式的分离,只有当应对世界的活动受阻时,才有分离出来的概念存在,所以这种知识形式无疑不是“探本之见”,由此形成的体育概念也属“皮相之见”[35]2。海德格尔除对这种分离的认识外,更强调一种“在世”的方式——“存在者总是以另一种方式处于世界之‘内’。作为一个行动者,他正致力于实现某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首先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如果将体育也看作为一种“存在者”,那么要对它进行完整的理解,阐明其“在世处境”[35]2就是必不可少的。哲学人类学的方式就是在挖掘、描述体育的某种生活方式,即一种“在世”的方式。哲学人类学追问的并非单纯的体育概念,而是更为丰富的体育“在世”方式,这样既能规避在概念定义讨论上所形成的分离式的误区,也能充分展现体育运动的丰富性,形成从特征的描述到对体育“在世”方式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路径。同时哲学人类学追问方式的进一步展开也是当代哲学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考方式进行反思的趋势,是体育哲学能进一步与当代哲学发展进行深入对话的契机。
[1] 王苏杭.体育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229
[2] Marrou.Histoire de l’éEucation Dans l’Antiquité[M]. Pairs:Seuil,1948:242
[3] Brohm JM.Le Mythe Olympique[M].Pairs:Bourgeois,1981:242
[4] Elias N,Dunning E.Sport et Civilization[M].Paris:Payard,1994:34-43
[5] Pociello C.Sport et Société[M].Paris:Vigot,1981:25
[6] Elias N.Sport et Violence[J].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76,2(6):2-21
[7] Defrance J.Sociologie du Sport[M].Paris:DéCouverte,1997:13
[8] 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9] 高强.西方体育起源之争与身体维度的解析[J].体育学刊,2010,17(12):24-29
[10]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11] Schacht R.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What,Why and How[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0,50:155-176
[12] Tamboer JW I.Sport and Motor Actions[J].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1992,XIX:31-45
[13] Mauss M.Le Travail et Les Techniques[J].Journal de Psychologie,1948,numéro spécial:71-78
[14] 莫斯.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2
[15] Mauss M.Les Techniques du Corps[J].Journal de Psychologie,1934,XXXII:5-9
[16] Suits B.Tricky Triad:Games,Play,and Sport[J].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1988,XV:1-9
[17] 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9] Mechikoff R A.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 to the Modern World[M].New York:McGraw-Hill,2002
[20] 刘欣然,陶国新.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体育竞技[J].体育学刊,2009,16(1):95-99
[21] 谢光潜.古希腊体育与身体意识的觉醒[J].体育学刊,2006,13(2):79-81
[22] 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2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
[24] Gregory C J.Hypothe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ZEUS
The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of Sport in Ancient Greece—Reflections on“Modern Interpretation”and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GAO Qiang
There is a“modern interpretation method”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ve activity in ancient Greece and modern sport.The paper proves into the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of competitive sport with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method,as well as the shift with game tradition in ancient Greece.Thus the skill know ledge about human body in athletic sport in ancient Greece has been sorted out.On the other hand,the paper describes the diminishing process of the two factors,body and skill,in the cours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to medieval age till modern times.The paper finally states the misinterpretation in“modern interpretation”and puts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existence”of sport with the enquiry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competitive sport in Ancient Greece;modern interpretation;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existence
G80- 05
A
1000 -5498(2013)03 -0013 -07
2012 -12 -20;
2013 -02 -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2CTY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10&ZD052)
高强(1980 -),男,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博士,西方哲学博士后;Tel:13761150837,E- mail:gaoqiang.ecn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