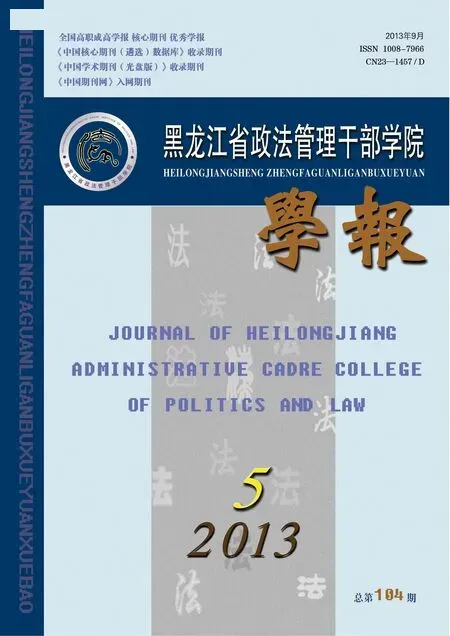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及其发展
何冻民,李 平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及其发展
何冻民,李 平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是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是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部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其权力组织形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被动实施了法治改革。法治改革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能否在法治理论上作出创新是考验法治改革的核心因素。
法治改革;社会改革;被动实施;党的理论
一、转型中国法治改革的背景分析
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法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系统的子系统,但是中国缺乏进行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本土文化土壤。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这场转型必须也必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来进行。中国共产党需要以法治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来获得和巩固其自身权力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且法治的理念和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排斥①《中国共产党党章》序言中已经明确表述其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法治的理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一部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有无足够的动力将法治的理论包含到其党的理论之中。
(一)中国缺乏转型的历史文化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邓小平先生1992年南巡以后开始流行的,到今天用“转型”来形容中国已经足足21年,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已经意识到处于转型形态,并且这个转型形态至少一直持续了21年。转型最早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最后发展到“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1]。而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法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系统的子系统。
中国缺乏一种温和改革的历史文化,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大多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博弈改革,最终演变为激烈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被称为“转型”抑或“改革”的历史阶段,著名的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至近代“戊戌变法”。按照上述“转型”的定义,这些时期都可以用“转型中国”来形容。中国历史上这种“转型”抑或“改革”最核心的特征是由一开始当时的权力阶层主导,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最终丧失了主导权。
从这些历史上的转型来看,这种转型的局限性在于: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当权者缺乏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底层,而改革却又依赖于当权者来进行。比较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在转型的前期,转型的社会需求已经出现,由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主导转型,这个时候的当权者利用其固有的权力完全可以引导转型,而且代价是最小的,但是当权者缺乏转型的动力甚至缺乏转型的意识;在转型的中期,由于当权者没有回应社会转型的需求,这种转型的社会需求会在社会寻求支点外部表现出来,一般会在社会秩序和经济中表现,这个时候外部环境的压力压迫当权者进行社会转型,但是当权者不会主动去转型,而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举措;转型后期,由于前期和中期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当权者的临时举措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转型的需求程度,民间社会不再相信当权者,这个时候当权者会丧失其主导力。经过这三个阶段,温和的社会转型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权力阶层变更,也许新的权力阶层会引导一场新的社会变革,但这种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转型了。
(二)法治改革依赖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法治改革,必须要先承认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如果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一切将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臆想而已。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社会制度的构建都是通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构建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宪法和法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运行通畅,中国的社会也就可以运行通畅。在1949年至1954年之间并没有《宪法》,但是中国的社会秩序运行良好,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时期,整个社会完全脱离法治,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下社会也可以运行。中国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行和运行的形态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只要执政党运行良好,社会秩序就会运行良好。
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权力,然后再利用掌握国家权力这个事实行为不断巩固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社会转型来获得和巩固其自身权力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也必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来进行,作为社会转型核心内容的法治改革当然也必然会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这是因为进行社会转型是需要权力资源来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合法性地占有了整个社会权力,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具有进行社会转型的资源。而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场对权力的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分配,所以中国共产党会本能地禁止由其他社会主体来进行社会改革的。综上,中国的社会改革必须也必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来进行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改革所需要的权力资源已为中国共产党所独占;第二,中国共产党不允许脱离其控制的社会改革的出现。
(三)党的理论可以包含法治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虽然其原旨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理论,但是其实际上已经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中国共产党也将区别马克思的行为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由此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然后通过这种“中国化发展”的包装将各种理论混合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当中,甚至是价值冲突的理论也被包装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当中。
法治的理论也可以成为党的理论的一部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是否意愿将法治的理论包含到其党的理论之中。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种理论修改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法治的理论也随时可以被排除在党的理论以外。而且法治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部分内容并不相容,甚至是排斥的,法治是保障自由和规范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在于控制和中央集权。当然法治也有控制的含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可以选择性地采取法治内涵的控制的部分,而摒弃和其党的控制不相容的部分,这种有选择的选取法治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党的执政是有帮助的,虽然党称其为法治,但是其已经脱离了法治的含义。在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而可以随意摘取内容并冠其名为“中国化”模式下,“法治”只不过作为控制和执政的工具。通过法治改革进行党的改造,将党改造为宪政内涵的现代型政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唯一缺乏的是动力。
二、转型中国需要通过法治改革来解决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需要通过法治改革来回应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更益义于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法治改革来回应社会的变革。
(一)社会阶层出现分立
目前,中国的社会已经出现分立的迹象,这种分立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密不可分。党的组织架构是以控制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形态,而且这种架构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领导人觉得“适当”的人通过组织部门考察然后委以重任,但是“适当”的选择标准却由领导层自己界定,这样就形成一个弊端,领导人容易将自己的亲属界定为“适合”的人,这样就会出现“权力的世袭”。目前这种“权力的世袭”已经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国的语态中已经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以及“穷二代”等词汇。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形态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其本质类似封建的皇权结构,最为明显的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官员的任命都是通过上级任命的形式产生的。具体到任命的选择标准却由“经党组织研究决定”的形式予以任命,从外观形式上在封建社会官僚由皇帝凭个人喜好直接任命,而在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则有领导层开会任命,似乎这种开会带有选举的性质,但是这根本不同于选举,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经党组织研究决定”的开会形式是在室里秘密操作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操纵整个密室运作,这种黑室的秘密操作顶多可以称为权力阶层的政治平衡。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60余年以后,其组织架构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架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权力世袭”,外部表现就是由绝对的权力所滋生的腐败。现在愈演愈烈的是共产党内权力阶层的权力世袭,这种权力世袭的规模越来越广,原来只存在高层的领导之间的权力世袭,逐渐发展到底层权力阶层的权力世袭。最近从中国新闻中得出的湖南27岁县长、26岁市长就是典型的实例,而且更为恐怖的是,以前这种权力的世袭一般是不合法的不正当的途径进行的,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权力的世袭已经通过合法的途径表现出来。
(二)社会规范出现失调
历史上看,中华文明中一直存在其特有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强调责任和道德,而且中华文明自身孕育出了道德和行为的规范。但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利用国家机器进行以“社会改造”的形式“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①参见吴邦国:《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虽然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而且正在发展和恢复之中,但是短期内无法形成系统的社会规范。在缺失传统文明等固有的社会规范的情形下,那么只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
规范失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中国之所以社会秩序还能保持完整,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在于其已经建立了一套社会行为法律规范体系。但是这套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具体而言,这个规范体系的特点是理论上全面规范的,但是实际上只针对一般民众适用,对于社会顶层却不适用。所以在目前的中国,以《物权法》、《侵权法》为体系的民法规范得到全面的实施而且和国际上接轨发展的很好,但是相关的涉及顶层设计的如关于政党的立法却一直不存在,作为一国核心的《宪法》只是一个“祖宗牌位”被顶层限制发生效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规范失调的形态,这种规范的设置模式典型的特点就是民间社会得到规范,但是公权力没有规范,所以在现在的中国随处可以看到公权的滥用。这种底层有规范而顶层无规范的社会形态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为底层会向顶层效仿,而顶层没有规范那么也就意味着当权者不受约束,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强权欺凌,由此社会秩序也是不稳定的。
(三)法治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以法治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改革解决这些危机。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现阶段面临的社会危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苏醒以及民间社会组织能力在逐步加强,也就意味着民间社会的组织架构越来越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依赖性降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能力在下降;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架构所出现的危机,主要权力世袭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第三个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民主浪潮。
中国的法治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来推动的,中国共产党将其法治改革表述为“依法治国”。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依法治国”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才予以确定的,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才明确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的基本动因是一个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的选择过程,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和长治久安等现实社会问题而启动的[2]。从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来推动这场法治改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回应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挑战,而这个社会变革的挑战凭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架构无法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也出现了变化,尤其突出的是和中国负面官僚制度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出现了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自身最大的危机是因为由于腐败所出现的政治信任危机,正如其官方表述“腐败亡党”,“腐败”可能会使其“失去执政地位”。
三、转型中国法治改革的路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法治”本质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以法律为工具的社会管制。这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法治改革虽然具有局限性的,但是法治文明具有它自身的生命力,这场法治改革已经将法治的火种播在了中国的社会。
(一)转型中国法治改革的特点
“法治”对于中国而言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并且并不是抽象的、缥缈的,它拥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规范,而且经历了西方国家数百年历史的实践。但是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并没有用“法治”这样一个概念,而是采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概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
“法治”经过数百年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其已经具体化,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中明确法治的含义包括三层:“第一,法治意味着法律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或压倒一切的地位,它排斥专制、特权甚至政府的自由裁量;第二,法治意味着各阶级、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宪法性法律在由法院解释和实施时,他们不是法律规范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的结果。”[3]显然如果按照西方法治的定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合法性和正当性明显受到了威胁,而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力避免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自己掌握对“法治”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以便将自己的利益贯穿到“法治”当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西方法治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吸收,融合其党的理论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特别是和党的理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早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通常被理解为“依法治国”,并具体化为人民主权、宪法和法律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制约公权力五个方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将依法治国完全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二)转型中国的法治改革的现状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的社会改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法治改革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这场社会大变革改变了中国,中国的经济活力得到发展,中国的社会也得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虽然存在很多局限性,但是中国的法治改革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法治的内涵,这场法治改革带来的正面效果是巨大的和革命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显示了法治文明本身的生命性。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才首次提出和法治相关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口号,然后不断的丰富和增加其内容,2008年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②。按照中国官方对“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解,其主要内容为“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4]而有法可依的“法”则大量借鉴了西方法治文明的成果,通过宪法、民法商法等具体规范,大量的法治内容在中国的社会中发展并和中国传统文明进行融合。
三十年的法治改革基本最为突出的是建立了以《物权法》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体系,官方表述为“至此,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5]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其主要划分依据是历史渊源、体系特征以及司法技术三个因素。[6]通过这个法律体系,中国民间社会的社会规范得以确立,经济发展得到保障,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明的自我更新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法律规范体系,结合中国自身文明,法治的理念不断深入社会。
四、转型中国法治改革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法治改革目前是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必须依赖于中共的组织架构来进行,这种情形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中国法治改革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党的理论能否在法治理论上作出进一步创新是考验法治改革的核心因素。
这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法治改革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法治改革对中国民间社会影响的程度。法治改革和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的更新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法治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于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并已经将法治文明的火种传到了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发生了变革,而党的理论为回应这种社会变革也作出了法治理论上的选择。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程度无法通过量化的形式表述出来,但是我们愈来愈明确法治改革的速度已经落后于中国社会对法治改革的需求。中国法治改革的最核心就是公权的规制,公权限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公权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以中国法治改革的核心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法治的关系的设置。
随着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以及民主化浪潮等因素不断加大,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改革力度一旦无法满足这种需求,那么党很可能丧失法治改革的主导权,并且很可能党和法治之间发生冲突,而这场冲突的结果则在于法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和中国共产党组织架构之间力量的大小。中国共产党期待通过法治改革实现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党主导的法治改革根本上还是为了秩序,所以,中国的法治改革的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和正义,弥合社会分立的阶层,维护分裂的社会形态,避免社会秩序发生混乱。
[1]宋林飞.中国转型社会的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9.
[2]李林.法治与宪政的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41.
[3]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w of the Constitution.8thd[M].London:Macm illan,1915:120-12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王新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N].检察日报,2008-04-24.
[6]孙国华,冯玉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23-24.
[责任编辑:杜 娟]
LegalReform and Developing of China’s Transition
HEDong-m in,LIPing
CCP led Legal Reform to China’s Transition from top to bottom,which is a part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society.Fac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CCP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crisis of its powers tissue morphology,passively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Reform.Legal Reform depends on the CCP,whether or not the CCP’s can mak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a core element to test the rule of law reform.
Legal reform;Social reform;Passive implementation;CCP’s theory
DF02
A
1008-7966(2013)05-0005-04
2013-07-05
何冻民(1986-),男,湖北鄂州人,2011级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平(1987-),男,湖南邵阳人,2011级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