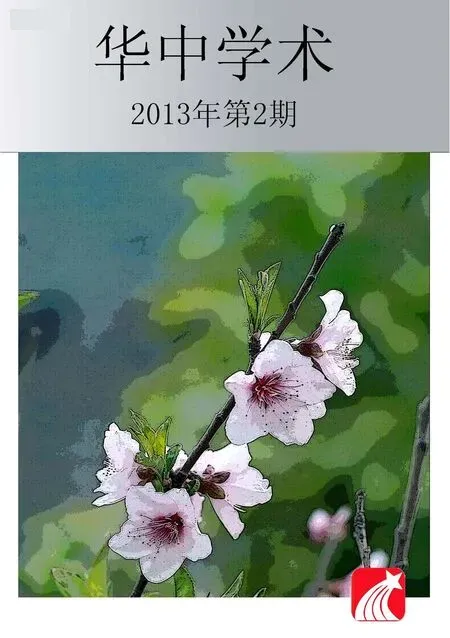华语游戏的跨媒介文化传播
李 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当代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不同的媒介里使用相同的形象,形成具有相关性的多重文本,跨媒介现象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潮流。其中数字游戏与影视、文学乃至其他文本的跨媒介互动,在当下中国的文化传播现象中尤为引人注目。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由游戏玩家引发的群体效应吸引了文化制作者将游戏中的形象、场景以各种不同媒介加以延伸、扩展,不仅仅出现了大量的游戏文学作品,由游戏改编的电影及电视剧也逐步增多,还出现了其他各类衍生产品及相关文化活动。这种跨媒介互动不仅促进了文学、影视样式的革新,给传统的文学叙事、影视叙事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变化,也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和琢磨的范例。探究当代华语游戏的跨媒介文化传播现象,分析其产生背景,比对游戏、影视、文学等不同媒介的叙事特质及其间的互文性,是我们在网络、纸媒、影视、手机等多媒介并存的时代正视并研究文化文本在不同媒介间整合这一跨媒介文化趋势的重要内容。
一、概况:华语游戏的多重跨媒介互动
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游戏已经成为当下主流的娱乐形式之一。数字游戏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手段设计开发,并以数字化设备为平台实施的各种游戏,包括PC单机游戏、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视游戏和掌机游戏等,其共性是在基本层面均采用以信息运算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
数字游戏的跨媒介转换在国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并且有成功的范例,最为突出的转换形式便是电影与文学。《最终幻想》《古墓丽影》《生化危机》等经典游戏都被翻拍成电影且票房不俗,由暴雪娱乐从1994年开发至今的全世界最火爆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也出了系列官方小说并预计在今年开拍电影。就华语游戏而言,由游戏发端而改编成文学作品的例子不胜枚举,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也逐渐增多,比如《轩辕剑》被改编为电影,但若论及多重跨媒介互动,在PC单机游戏与网络游戏中最为典型的范例便是《仙剑奇侠传》与《摩尔庄园》。
(一)《仙剑奇侠传》系列
《仙剑奇侠传》(以下简称《仙剑》)系列被公认为是华语世界的经典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简称RPG游戏),是由台湾大宇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电脑游戏,故事以中国古代的仙妖神鬼传说为背景、以武侠和仙侠为题材,已发行了7代单机角色扮演游戏、1款经营模拟游戏、2款网络游戏和1款网络社交游戏。系列首款作品发行于1995年7月,最初是单机游戏。单机游戏(Console Game)是区别于网络游戏而言的,指仅使用一台计算机或者其他游戏机就可以独立运行的电子游戏或者计算机游戏,模式多为人机对战,也可以通过局域网的连接进行多人对战,相比网络游戏而言互动性稍低。《仙剑》第一代单机游戏的主角李逍遥出生在余杭县的一个小渔村,因缘巧合结识了酒剑仙并学会一式御剑法。有一天婶婶突然生病,李逍遥前往仙灵岛求丹,巧遇正在莲池沐浴的赵灵儿,并在姥姥的胁迫下与赵灵儿成亲。第二天早上,李逍遥回到盛渔村,却因服了黑苗人给的忘忧散而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事,仙灵岛被黑苗人血洗,赵灵儿被虏,几经波折后李逍遥救出赵灵儿,并与她踏上寻找其母之路。之后,李逍遥游历到苏州遇到林月如,由此展开了曲折故事。该游戏设计了复杂的迷宫,采取了全动态回合战斗模式,画面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无论是构图还是音乐与音效在当时同类游戏中都极其出色。第一代作品荣获两岸当时诸多游戏奖项,被誉为“旷世奇作”。
在影视改编方面,2005年第一部由《仙剑》系列单机游戏改编的电视剧上映,由上海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CES)出品,大陆版为38集,后被改为34集,台湾版为34集,剧情是根据1995年原版本游戏的情节和故事改编而成。电视剧的情节有较多改变,但主线没变。2009年第二部由《仙剑》系列单机游戏改编、由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3》在大陆、马来西亚及台湾地区播出,共37集。《仙剑奇侠传3》电视剧集因为没有保留游戏中重要的剧情、融入了大量现代道具及名词,而在仙剑迷中遭到不少批评。
在纸媒方面,2000年台湾青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漫画家易水翔麟编绘的同名漫画《仙剑奇侠传》,当时新仙剑奇侠传并未推出,因此剧情以1995年版本的游戏情节为主,漫画连载至2002年结束,共9册。2001年8月台湾的第三波信息公司出版了由楚国执笔的小说《仙剑奇侠传》,共5册。内容虽为改编《仙剑奇侠传》的版本,不过剧情主轴完全跟新版一样。2002年5月该书在大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新仙剑奇侠传》。2012年10月、12月,由管平潮撰写、“仙剑之父”姚壮宪监制的《仙剑奇侠传》小说之一、二部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正式发售。2012年11月,《仙剑》五的同名漫画《仙剑奇侠传5·青荷镇篇》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也有仙剑发烧友自行制作的游戏续作或改编的小说在互联网上流传。
(二)《摩尔庄园》系列
《摩尔庄园》是由上海淘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于2008年5月正式上线的基于WEB网页的网络游戏,是国内首款定位于儿童的网络虚拟社区。摩尔是英文“mole”(鼹鼠)的音译,儿童用户以一个个可爱的虚拟鼹鼠摩尔形象在庄园里进行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深入研究6—14岁年龄段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教育情况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摩尔庄园设计了摩尔城堡、爱心教堂、阳光牧场、开心农场、淘淘乐街、咕噜艺术街、交通署、拉姆学院、西部游乐场、摩尔足球场等20多个不同的活动场景,儿童用户或是直接参与游戏,或是在庄园中遇到各种人物,与他们交谈,得到一些信息线索或者任务,然后采取行动,玩游戏、学习各种技能并比赛。自2008年5月上线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儿童网上乐园,曾荣获腾讯2010年中国网游风云榜最佳社区网游,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1年文化部中国优秀儿童作品奖。该游戏在全国约有1.6亿用户,除小朋友外,还有一些“80后”“90后”玩家热衷于此[1]。
影视方面,淘米公司在网络游戏之后,又推出了《摩尔庄园》电视动画片,以虚拟网络社区的经典形象为原型,创作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主题是一个普通的小摩尔——摩乐乐如何在变身精灵拉仔的帮助下,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变身乐乐侠,对抗邪恶巫师库拉,保护庄园。动画剧每集约12分钟,于2011年6月由北京卡酷卫视首播52集,目前已播至第三季。2011年8月电影《摩尔庄园冰世纪》上映,是国内首部儿童网游动画电影,2012年7月《摩尔庄园2·海妖宝藏》上映,这两部电影都票房成绩不俗,影片均以原版网游和电视动画片中的角色为基础,展开了一个不断演绎发展的童话故事,同时更好地发挥了电影的优势,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视听效果,比网游和动画都更加细腻和精彩,也让摩尔庄园的公众知名度更高。
在纸媒方面,摩尔庄园的系列图书在网游有了不断增长的用户群之后,便推出主要有《玩转摩尔庄园》、《摩尔庄园:神奇道具完全图鉴》、《摩尔庄园》杂志系列、《我爱摩尔时尚》系列、《摩尔庄园》小说系列、《摩尔庄园超级明星总动员》系列、《童趣摩尔庄园》系列,以及《摩尔庄园迷宫大冒险》《摩尔庄园之摩摩拼图追逐棋》《摩尔庄园口袋日记本》等。这些出版物包括了网游指导、小说、纸媒游戏等各种不同类型。在电影上映之后,《摩尔庄园冰世纪》同名电影连环画、电影原版小说《勇士之书》和《圣熊之书》等系列图书也迅速出版。电影小说《海妖宝藏》、电影连环画及全明星图鉴也同期出版。总体来说,摩尔庄园系列纸媒出版物市场火爆,在中国图书零售排名中稳居前列。
从电脑屏幕迈向其他媒体介质,“《摩尔庄园》品牌已经完成了从单一网络游戏到跨媒体儿童娱乐体系的蜕变”[2],《仙剑奇侠传》也同样如此。我们从这两个系列的转换传播,以及其他诸多正在进行中的文化运作,可以预见由游戏发端的多重跨媒介转换将是当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模态之一。
二、语境:新媒体变革与“融合文化”
以数字游戏发端的跨媒介文化现象何以出现并蔓延?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探究论及这一现象的语境,从而厘清其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乃至相关的受众心理层面的因素。
以数字/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变革,昭示了媒体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在传统的文字、声音和图像进行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并产业化,传统的单一媒介形态已经不能满足新技术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必然要进行资源整合,多重媒介的不同形态融合已经成为消费时代的一种趋势。
数字游戏本身也是基于屏幕的,“游戏在视觉风格和叙事意图上和它的电影‘先祖’之间存在派生关系”[3],因此游戏与影视的相互转换显得更加顺理成章。目前与游戏相关的纸媒出版物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与游戏直接相关的出版物,比如游戏画册、游戏指导,游戏背景介绍等;第二种是在游戏基础上的相关动漫纸媒出版物;第三种是游戏文学,指的是由以数字游戏为创作背景、创作素材或者其他与数字游戏相关的文学类作品,主要以改编小说为主。
数字游戏的兴盛,是游戏文学、游戏影视及图书诞生和发展的母体。一个成功的游戏所累积的影响力,本身就增加了改编作品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对于之前没有玩过游戏又被电视剧或小说吸引的观众而言,也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游戏用户,从而带动经典游戏或是后续游戏的销量。在游戏与影视、文学作品的互动中,影视、文学有时比游戏火,有时游戏比影视、文学爆,有时又旗鼓相当。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游戏文学《龙枪编年史》,本是为了配合光盘游戏上市而制作的附属产品,然而没想到上市后,卖得比游戏本身火得多。于是单独出版,成为一套经典的“游戏文学”奇幻小说[4]。“仙剑奇侠传”现在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限于游戏,其改编成的电视剧、动漫、小说在国内拥有诸多“粉丝”。在第一部《仙剑》电视剧播出后,大宇公司特意为电视剧修改游戏程序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XP,以电视剧主角人物重新包装,出版了“新仙剑奇侠传——电视剧纪念XP版”。《仙剑2》小说的宣传语是“为了仙侠奇幻小说爱好者的仙侠之梦;为了游戏玩家重拾仙剑最美好的回忆;为了电视剧观众感受仙剑的原著故事!一次游戏与文学的完美结合,献给所有故事爱好者的顶级文字盛宴!”[5]这也很能说明游戏的跨媒介版本之间互为宣传、互动搭售的现象。
“摩尔庄园”系列的文化运作显然是更有系统的、强调时效性的规划,其多重媒介产品在影视及纸媒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以电影上映期为例,为了回报众多《摩尔庄园》的游戏玩家,电影片方为观众(玩家及潜在的玩家)提供了二重大礼:电影主题限量版的“白熊天使”、摩尔庄园游戏神奇兑换卡和礼盒套装限量珍藏版“麦塔精灵魔力水晶球”。在摩尔庄园的纸媒出版物中往往会附赠和游戏相关的来信、密码卡,后续还会上市升级版配套图书,与游戏有关的游戏书,包括对战卡牌、对战图鉴、对战棋、对战益智游戏书等。影视及纸媒出版物,反过来又会推动游戏玩家的增多。这种扫射式的互动营销方法在跨媒介文化传播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内容生产、媒体传播、市场营销是文化产业的三大环节,从游戏开始的跨媒介文化制作施行的是全方位的经营与推广,其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各种不同媒介产品的互为宣传及搭售。从“仙剑奇侠传”“摩尔庄园”系列在文化市场上的成功我们看到了一条逐步成熟的文化产业链,这种制作模式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显现出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与市场潜力。跨媒介形成了文化制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品牌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成为相关从业者的共识。
事实上,新媒体变革逐步改变了文化制作和消费的方式,促生了融合文化。“亨利·詹金斯声称,现在我们都生活在一种‘融合文化’中。他指出,这代表了媒介所有权的转移,媒介巨头正在‘控制整个娱乐工业的利润’,媒介消费的方式也正在改变。发生在技术、内容和商业层面的融合,提供了一个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某些文化和工业实践融为了一体。数字时代因为提供了更灵活和更具参与性并赋予消费者更多权利的媒介而受到称颂,然而融合的兴起却使得‘专营权’成为许多媒介和娱乐巨头行销策略的中心问题。分离风险往往是这一战略的一个积极方面。在许多不同的市场尽可能使用相同的知识产权(IP),其目的在于赢得更多的成功机会且具有更少的风险,而且也能够维持一个品牌的知名度。”[6]融合文化意味着制作者能够倚赖上一级文本的知名度,各种不同媒介的激烈营销,使得跨媒介转换成了当代文化的一个潮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坚持在跨媒介转换中使用稳定的角色形象,非常有益于一个品牌知名度的长效性,能控制生产风险,可以不断地推动已有产品和正在制作产品的传播和普及,这是品牌理念的传承与发展,也是能保证跨媒介文化制作成功的核心竞争力。
还要指出的是,游戏的跨媒介转换之所以兴盛,除了以上谈及之外,玩家的主动性需求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游戏现今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而玩家群体对一个游戏的支持度,时间上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游戏本身呈现的是一个虚拟世界,玩家主要通过电脑屏幕以及网络来投入。而影视作品、小说、连环画等,由于有了确定的情节线索及走向,无疑将游戏的虚拟空间及故事更加具象化,在情感的表现上也更具力度和张力。因此,不少玩家对于游戏的跨媒介呈现抱有期许的心理,这也促进了制作者的进一步行动。
三、互文性及差异:从源媒介到目的媒介
关于游戏的叙事,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副教授、游戏研究所指导Chris Swain有过这么一段论述:“当想到故事,我喜欢在今天的游戏和20世纪初的电影之间作个类比。早在1910年代,电影是无声的、黑与白的,故事的讲述几乎完全借用来自于戏剧的技巧。那些电影真的并没有建立与人们之间的情感连接。如果你告诉别人电影将成为20世纪的文学,他们会笑着让你滚出房间。但是,电影不断发展并成为通过技术(声,色)和创造性的突破(特写,闪回,相机移动)转化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讲故事的媒介。我认为今天的游戏就像1910年以来的电影(讲故事的角度粗糙,无法作出与人的真实的情感连接),我看到他们通过技术和创意的突破,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的讲故事的媒介。……今天我也许会被嘲笑滚出房间,但我仍然要说,游戏将成为21世纪的文学。”[7]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说辞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当代不少游戏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讲故事的媒介这一观点却毋庸置疑。小说、电影、动漫都是出现在游戏之前的讲故事的媒介。通过分析比较相关范例的互文性及其他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媒介叙事的特质及跨媒介互动中从源媒介到目的媒介的转换规律。
(一)叙事主题的普遍性与一致性
纵观当下的各类跨媒介转换实例,尽管不同的媒体介质给出了丰富多彩的情节场景,然而在从游戏到其他介质的转换过程中,叙事主题或意义仍然保持了一致性。
《仙剑奇侠传》之所以在玩家中获得极高的评价,与游戏本身的叙事性及对人物情感的着力展现刻画是分不开的。一位玩家在论坛里写道:“你不能拒绝仙剑,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在仙剑之前没有游戏可以使我流泪。”而有“仙剑之父”之称的游戏制作者姚壮宪则如此论说《仙剑》:“严格地说,《仙剑》并不是一款单纯的中文武侠游戏,它更像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蕴涵了丰富人文及情感的传说故事。”[8]众多的玩家乃至研究者都认为,《仙剑奇侠传》延续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剑仙文化,在游戏中体现了侠、道、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深层文化心理,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绝对自由的永恒追求[9]。仙剑系列对古代神话进行了深入发掘和演化重组,仙剑游戏中的女娲神话可谓贯穿始终,赵灵儿的故乡南疆是苗族聚居地,而苗族尊崇的大神又是女娲。作为女娲的后人,赵灵儿人面蛇尾,最终为天下苍生而死。这些都是在古代神话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而仙岛求药、仙女沐浴、比武招亲、仙妖报恩、六道轮回等也是来自于中国民间古老的神话传说与典故[10]。救护苍生的侠义与凄美悲伤的爱情,这种内在的精神与文化,不仅对于游戏玩家而言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渊源和动人力量,对于各种媒介而言都是极好的表现主题,奠定了跨媒介转换的基础,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延续。
《摩尔庄园》作为儿童网络游戏,一开始就有着明确定位,要求寓教于乐,在摩尔庄园的虚拟社区里,由儿童用户化身的每个小摩尔都要像小鼹鼠一样勤劳、善良、勇敢,具备了这些品质并行动,才可能赢得奖励。健康、快乐、学习、分享是这个网上乐园的主题。在游戏基础上发展的各个媒介文本延续了整体定位,张扬着正面的价值观念。电影与动画片包括小说也既充满童趣,又不乏积极向上的意义,勇敢、诚实、正义等美德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丰富展现。在其改编文本中,情节大多都属于典型的正义与邪恶对立的斗争、危机与英雄的类型化叙事,张扬积极正面的品质与价值观作为核心理念贯穿始终。
选取具有普遍性的叙事主题并将之贯穿于各个不同的媒介产品之中,是跨媒介系列文化产品能够成功运作的王牌。
(二)从游戏到影视小说等的叙事逻辑化与情节增删
对于数字游戏尤其是RPG游戏而言,本身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主要角色都具有叙事形象上的延展性,这正是其成为改编源文本的前提,因此现在我们所见的数字游戏改编为影视及小说的,都是PRG游戏。游戏中也有一定的因果叙事设置,但更为特殊的特征是,“在叙事上它打破了单一轨迹的“走廊式”叙事,取而代之以更为灵活的‘花园路径式’叙事策略”[11]。对于游戏玩家而言,选择不同的角色,在虚拟场景中买卖物品、学习技能,根据游戏中设定的任务进行通关战斗,是玩游戏的主要进程。完成众多的任务的同时,复杂的情节也会展现,玩家必须通关才能达到最后的结局。玩家(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中往复参与,是RPG游戏具有的特点。最常见的有代表性的就是玩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对象重用——一种妖怪被反复杀死,一种招式被反复使用,一个角色反复与之说话,一种药反复吃,等等。“打怪——升级——打怪”体系就是RPG游戏中常见的对象重用体系。而且游戏根据玩家的进程,也可能给出几个不同的结局。《仙剑1》采取的是悲剧性结局,基于玩家对美好结局的强烈期望,2001年推出的《新仙剑奇侠传》特别制作了隐藏结局,采用了分支结局制。
但对于影视观众及小说读者而言,文本首先是一个故事,是一个能被大众而非仅仅是游戏玩家能理解的故事。麦克卢汉早就提出,媒介是积极的、能动的,决定了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因此,游戏被改编为影视、小说时,目的文本等必然会对源文本进行增删的工作尽可能地进行优化,并要加强叙事之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尤其是电视剧,因为采取了分集播出的形式,更加注重这一层,强调线性叙事。《仙剑1》电视剧就删除了游戏中纯功能性的人物比如妖怪,将反面角色(如拜月教主)突出,将感情线作为跨媒介转换后的叙事主线。《仙剑奇侠传3》电视剧因为加入大量疑似现代道具及名词,有些情节没有逻辑,没有保留游戏中重要的剧情、元素而备受诟病,就可以见出在由游戏到影视作品的跨媒介转换中叙事逻辑的重要性。文学的内在叙事机制与影视的内在叙事机制是有区别的,影视以场或者剧集为叙述单位,而文学则相对自由一些。关于仙剑小说,作者管平潮就表示,小说内容基本忠实于游戏,创作部分只占30%,保留了游戏中大量的经典支线剧情。“小说要从文学角度出发,把它写成完整的故事,并且还要加入人物的恩怨情仇。”[12]
尽管故事从细微上千差万别,但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游戏及其所涉及的多种不同平台(电影、文学作品、漫画、图画小说等)间,“这些各不相同的媒介中所描述的世界和故事情节的基础结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或至少不是彼此矛盾。它们的目的在于维持某些被策划的、不断扩展而无休止的宏大叙事,与那种更明确的、严格的文学作品相比,这种故事更像是一种肥皂剧”[13]。因此,从整体上而言,“游戏作为‘原文本’,提供了基本的人物形象架构,而电影、动画系列剧、纸媒出版物则将叙事的背景故事及各个形象深化、细化,衍化出更为复杂的故事。不同层级文本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延展、扩散、推进,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叙事体系”[14]。
(三)从动态机制到固定模式的差异
游戏都包含着相互作用的意义,麦克卢汉说:“任何游戏,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样,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是使群体或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15]对于数字游戏来讲同样如此。游戏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它是经过设计师精心结构的、由程序控制的动画和文字,但它仍然提供了一种代言的感受,它极大地促发了玩家的主观性。竞技性元素在游戏中是主体,玩家通过操作角色完成任务并代入体会角色的情感,尤其是根据角色的自行选择所见所感的差异性,让玩家能够沉浸其中。“数字游戏常常利用电影的各个层面,为玩家所进行的活动制造更多的意义并促进共鸣。然而,通常用来定义游戏,把游戏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的,就是游戏必须被玩。”[16]这种交互动态的机制在观看影视作品及阅读纸媒文本中是没有的,相对而言游戏的受众更加积极主动。单机游戏存在着人机互动或是局域网进行多人多战,大型的网游都存在着不同玩家之间的互动,在一个虚拟环境中实则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动态机制。
但语言差异恰恰反映出了游戏相对其他媒介的薄弱之处。RPG游戏中人物的对白相对其他游戏而言较多(无人声,仅用字幕),而且情节主要通过角色与人接触过程中的对白来进行交代并向前发展,包括人物的情感很多也只是少量的字幕交代。同时游戏中也存在着不少游戏专有名词。但文学及影视作品、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不同于游戏中玩家控制角色的语言及非玩家控制角色的模式化语言,它显然更加丰富,更加富于变化,也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个别游戏名词对于非玩家而言会造成理解障碍的可能性,这些又会在跨媒介转换的过程中被舍弃。
同为有影像视听画面的媒介,游戏与影视作品在具体的取景上也有差别。电脑游戏中全景居多,且多从角色视点出发,借助字幕来进行说明或展现,而影视作品中则可以采取多变的视角及中近景、大量的运动镜头来充分展现各种场景。而且影视作品可以充分地运用闪回等技巧来增加剧情的曲折性或表现人物的情感意识,包括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这些都是电脑游戏所不具备的。
但我们也知道,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叙事几乎有着一种本能的接受方式,一种顺应了该媒介本身叙事特质的接受方式,这种心理机制确实存在——受众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接受默契与要求。对于那些对游戏主体完全不了解的观众和读者而言,改编后的影视及文学动漫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文本,是用一种媒介讲述的故事,和其他类似作品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而对于之前已经玩过游戏的玩家,他们会不自觉地将之与游戏进行比较,以此来评价改编作品的优劣,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每一种不同媒介的文化产品都是作为新的形式而存在的。原媒介的叙事就是素材,需要按照目的媒介创作规律来进行重组创作,在共通的基础上其实更强调各种不同媒介艺术的独特性。管平潮想把仙剑系列小说打造成经典剑侠作品:“我的目的是让即使没玩过游戏的读者,也能在阅读时感到非常的享受。”[17]这无疑正是作为一个改编者应有的态度。好莱坞著名编剧家悉德·菲尔德指出:“进行改编意味着从一种媒介改变成另一种媒介。改编的定义是通过变化或调整使之更合宜或适应的能力——也就是把某些事情加以变更从而在结构、功能和形式上造成变化,以便调整得更恰当。”[18]这话对于任何改编都适用。真正成功的游戏跨媒介转换,应考虑到一般观众或者读者不了解游戏名词、游戏场景的现实,追求好看易懂、打动受众,市场收益也必然不俗。因此,是否尊重或者完全和原作相符并不重要,而是在不同的媒介属性的制约下,如何发挥目的媒介的优长,避免目的媒介的不足,呈现一个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体系。
从当代文化的发展来看,不仅仅是游戏与影视、小说、动漫之间,话剧以及手机等新媒体与影视、纸媒之间的跨媒介互动也越来越多。可以预见,一个日益扩展的宏大跨媒介体系时代很快就会到来。作为目的媒介文化产品的制造者,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形成一个具有长效性的品牌以及文化产业链,保持稳定增长的利益循环,更应当把握不同媒介的属性及其特殊的美学要求,以期在多级文本之间取得理想的平衡与价值双赢。
注释:
[1]新浪游戏:《〈摩尔庄园冰世纪〉7月公映网游动画起航》,2011年06月24日(http://games.sina.com.cn/w/n/2011-06-24/1749508986.shtml)。
[2]新浪游戏:《摩尔庄园:航母级新媒体儿童娱乐品牌开启新航程》,2011年8月31日(http://games.sina.com.cn/w/n/2011-08-31/1514526995.shtml)。
[3][美]詹米·M.珀斯特:《电脑游戏中的观看与行动——影像的“玩耍”与新媒体互动》,经雷译,《世界电影》,2009年第4期,第4页。
[4]傅秀宏:《游戏文学踏上开往春天的地铁》(http://www.chinapostnews.com.cn/b2009/865/08650501.htm)。
[5]当当网《仙剑奇侠传2》图书售卖网页:http://product.dangdang.com/23160605.html。
[6][美]道格拉斯·布朗、[英]谭雅·克里兹温斯卡:《电影—游戏与游戏—电影:走向一种跨媒介的美学》,范倍译,《电影艺术》,2011年第3期,第102页。
[7]Jeannie Novak,GameDevelopmentEssentials(Third Edition),NY :Cengage Learning,2011,p146.
[8]野花等:《宿命的情感,轮回的宽恕——永远的仙剑奇侠传》,《大众软件》,2003年第4期,第116—125页。
[9]牛景丽、于丹:《〈仙剑奇侠传〉的文化传承》,《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8—120页。
[10]相关阐述详见野花等:《宿命的情感,轮回的宽恕——永远的仙剑奇侠传》,《大众软件》2003年第4期,第116—125页。
[11]彭骄雪、王进:《电子游戏与美国当代动画电影的崛起》,《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第152页。
[12]人民网:《〈仙剑〉小说大卖 新结局将不同于游戏》,2012年12月3日(http://game.people.com.cn/n/2012/1203/c48627-19769376.html)。
[13][美]道格拉斯·布朗、[英]谭雅·克里兹温斯卡:《电影—游戏与游戏—电影:走向一种跨媒介的美学》,范倍译,《电影艺术》,2011年第3期,第102页。
[14]李炜:《从游戏到动漫影视及其他:跨媒介文化现象论析》,《中国电视》,2012年第2期,第89页。
[15][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00页。
[16][美]道格拉斯·布朗、[英]谭雅·克里兹温斯卡:《电影—游戏与游戏—电影:走向一种跨媒介的美学》,范倍译,《电影艺术》,2011年第3期,第100页。
[17]人民网:《〈仙剑〉小说大卖 新结局将不同于游戏》。2012年12月3日(http://game.people.com.cn/n/2012/1203/c48627-19769376.html)。
[18][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鲍玉衍、钟大丰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