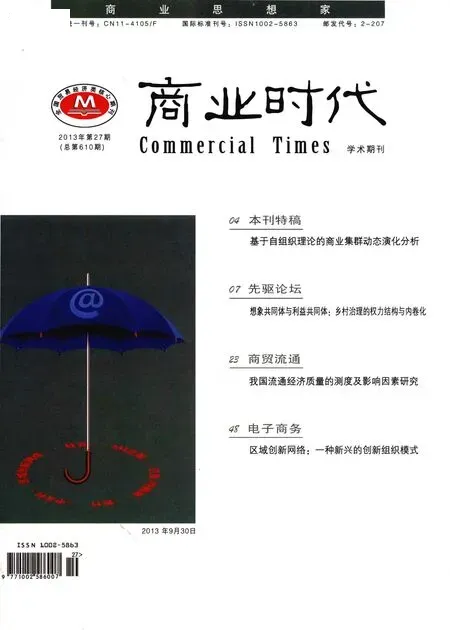想象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与内卷化
■ 吴 娜(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哈尔滨 150001)
引言
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演绎着“进入”与“退出”的循环,而这一系列循环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之间力量的消长都影响着乡村的发展。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逐渐减少了对乡村的管控,乡镇基层政府也逐渐由“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转变(周飞舟,2006),这使得乡镇基层政府与乡村村民的关系变得疏离。在“压力型体制”下,更多的基层政府选择了“不出事”与“做作业”的治理逻辑(欧阳静,2010)。此外,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国家惠农、富农、支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的土地资源与各种惠农政策项目成为各方行动者“交易”的对象,城乡交界地带的村落成为各方力量博弈的场所。乡村治理呈现出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是由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市场经济理性的渗透以及传统礼俗的沦丧所共同引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逻辑共同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生态,可以说转型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生态是丰富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更是复杂多样而难以厘清的。以权力结构的视角去剖析乡村治理可以从根本上厘清乡村治理的复杂格局,把握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
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乡村治理“体制外”的三股力量
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不同的权力主体,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乡村发展中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模式与行动方式。乡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缺乏行政力量介入的场所,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是以礼俗与宗族等传统力量作为规约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使得拥有土地资源较多的地主和宗族势力较强的大户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强势行动者,很长一段时期他们既充当着“保护型经济人”的角色,又通过一系列手段获取声望、地位等传统的中国人较为注重的价值诉求。在明清及其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众多研究表明,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共同治理乡村的(吴晗、费孝通,1948;郑振满,1992;赵秀玲,1998)。肖唐镖认为,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明清时期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到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持续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初的毁灭期。此外,从当前的趋势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宗族势力重新崛起,宗族势力在传统型乡村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治理称为复兴期。
随着国家政权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中权力的介入,乡村逐渐成为“谋利”的场所。无论是民国时期乡绅角色从“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的转变,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而使得国家对乡村的汲取能力日趋加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干预达到顶峰。随着政治浪漫主义的退潮,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一大批经济能人的产生,他们在乡村经济发展乃至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苏南的很多乡村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从“村庄型公司”向“公司型村庄”的转变(郑风田,2011),苏南模式中值得称道的企业家“经营”村庄的特征使得乡村治理日趋呈现出“公司”或“企业”的特征。这与戴慕珍、张静等学者所论述的“地方法团主义”有着类似的特质。村支书与村长作为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体制内”代理人,开办乡镇企业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经济发展的亮点。21世纪以来,这些乡村的“公司”已经逐渐嵌入乡村的治理结构之中,形成“公司型村庄”。
而在一些“原子化村庄”,有限的社会流动、革命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村庄集体对农民控制力的下降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秩序现象。乡村混混从改革开放之初通过身体暴力积累名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综合治安治理运动的开展后逐渐开始利用早起积累的名气经营实业。一定意义上而言,乡村混混的身份转换过程是国家与乡村关系演变的产物,而这也进一步影响着乡村混混和乡村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对乡村控制力的降低而实现了“弱”混混“强”治理组织到“强”混混“弱”治理组织的转变,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的关系也从“相互疏离”走向“利益联盟”,乡村治理呈现出“内卷化”的局面(李祖佩,2011)。
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介入日趋减少、乡村治理组织权力的弱化以及资源下乡的开展,乡村治理中“体制内”精英日益不能单独承担乡村治理的功能。宗族、混混与经济能人等“体制外”力量从乡村治理的“幕后”走向“前台”,使得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与力量消长又构筑了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宗族势力、乡村混混和经济能人的角色受制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等一系列关系变迁过程的制约。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尤其是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的政策举措极大地拓展了乡村社会的生长空间。显然,乡村混混与宗族势力由于不同地区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经济基础的不同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治理力量的对比关系或乡村治理格局也都各有特色。
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当前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由于不同的知识渊源与地域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质甚至“学派”。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社群注重“田野调查”,他们通过一系列实地考察对我国的乡村治理的新特征进行分析。例如,他将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称为“半乡土社会”以区别于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而在有关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研究中,贺雪峰以村庄权力结构为基础,建构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权力结构,并以经济分化、社区记忆为变量,区分了不同类型村庄中精英的互动逻辑。他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划分形成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的分野。然而,对于精英的界定以及不同地域精英类型构成状况缺乏研究。因此,构建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理想类型是对我国乡村治理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厘清权力结构类型的基础上,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理性对乡村治理的深刻影响,则是基于权力结构嬗变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运行机制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乡村治理三种“体制外”力量的考察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总体上形成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共同治理乡村的格局且总体的趋势是“体制内”精英权力弱化,“体制外”精英权力得到强化。以往的研究也大多侧重于“体制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的关系,而忽视了对“体制外”精英内部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状况的研究。显然,宗族、乡村混混以及经济能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不是线性的、单一的与绝对的,而是变化不定的、复杂的与多样的,正因为如此形成了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三种权力结构。
传统文化的印记、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及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都在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中“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共同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宗族势力乃至乡村混混都在乡村治理中充当“谋利”的行动者。不同地域乡村状况的差异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宗族式治理”模式
国家主义退潮后,传统宗族文化回归与复兴形成“宗族式治理”模式。肖唐镖教授对于宗族势力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多,他撰写的《村治中的宗族》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农村地区传统宗族势力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民国初期以前,乡土社会是没有国家权力渗透的场域,乡绅与宗族扮演着“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国民党统治时期,乡村社会逐渐受到国家的控制,传统的乡绅与宗族也开始充当“赢利性经纪人”。无论是民国以前还是民国时期,宗族势力几乎垄断了乡村治理,一系列乡村事务都由村落中的大族或有名望的宗族去把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力的下降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熟人社会的逻辑得到了“创造性转换”,在一些地区传统的宗族势力开始成为影响当地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温州商会其实是传统宗族与关系网络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宗族势力的复兴则代表着国家主义退潮后,乡村治理“空壳化”状态中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的侵蚀。例如,一些地区乡村选举中,宗族势力的干预则是这方面的典型。总而言之,传统的宗族势力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影响的提升主要受益于国家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变化,半乡土社会的“关系”逻辑与“文化记忆”依旧支撑着这种传统的力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二)“公司型治理”模式
经济能人从乡村治理的辅助性角色转变为主导性角色,从而形成“公司型治理”的乡村治理模式。赵树凯关于公司型基层政府、郁建兴关于发展型政府以及郑风田关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转变过程的研究都在印证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经济理性与市场力量逐渐赢得主导地位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公司型治理”模式在苏南地区的某些乡镇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能人在乡村治理中从辅助角色转变为主导力量与国家财税制度的变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税制度。这种财税制度极大的挫伤了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此时的政府更多扮演“管制型政府”的角色,地方政治精英的升迁与任命主要靠政治忠诚实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实施“财政包干”的财政制度。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大批“村庄型公司”应运而生。然而,由于“财政包干”的财政制度使得中央的财税汲取能力下降,中央政府的财税收入占国家财税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化。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地方政府对于兴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降低,很多乡镇企业开始转制。正是在分税制实施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村庄型公司”逐渐发展为“公司型村庄”。
(三)“灰色化治理”模式
乡村混混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最初通过暴力活动积累名气,到税费时代的运用暴力资源“收费”获得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资源,再到后税费时代成为乡镇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谋者”。乡村混混的角色转换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力的转变的产物,当前一些地区乡村混混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导致乡村治理“灰色化”。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治浪漫主义与革命主义思潮的影响,乡村混混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农村税费改革以前,税轻费重、缺少规范是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的主要特点,乡村混混往往充当乡镇政府征收相关费用的“工具”并从中获得利益。一些乡村混混在这个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并逐渐开始兴办实业,成为当地的经济能人,而他们与一般经济能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的暴力资源与名气去攫取公共资源。总而言之,乡村混混伴随着国家体制变革的历程成长,实现了多次角色转换。一些村庄尤其是城中村或城郊地区的乡村由于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以及“资源下乡”而更多的受到乡村混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乡村治理的“灰色化治理”模式,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呈现即非黑又非白的灰色状态。
从想象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传统的乡村治理中乡绅与宗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一系列仪式与乡规民约使得乡村治理呈现出“想象共同体”的特征。乡村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更像一个有着共同观念或想象基础的“共同体”。普通村民认为乡绅与宗族的代表可以为自己谋取权益,而在现实中传统的乡绅也确实扮演着“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所谓“想象共同体”,主要是基于地域、宗族以及婚姻等关系而形成的观念、想象乃至信仰上的有机联结,并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共同体。我国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乡村社会是充斥着人情、礼俗与关系的社会,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是村落的主导逻辑。
然而,随着科层制与市场力量的介入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村人际关系以及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乃至村民的行动逻辑一时间都呈现出较多新的特征。传统的乡绅作为一种历史而淹没,“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变,乡村社会也由于经济理性的充斥而变得淡漠,人际关系正在从“熟人逻辑”走向“利益逻辑”。伴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行为逻辑的消解,乡村治理的支配规则正在由传统礼俗与规范向经济理性转变,而乡村治理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在由“想象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变。传统力量的消退与新兴力量的崛起使得一些旧有的观念成为历史,而新兴的经济理性则成为主导观念。尽管,在传统的我国也存在着经济理性,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经济理性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巨变。
这种经济理性的迸发与崛起使得乡村治理变得缺乏“人情味”而更多的由利益所主宰,乡村治理成为“谋利”的场所,体制外精英作为强势行动者通过影响甚至直接参与乡村治理而获得更多利益。乡镇一级基层政权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转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渠敬东,2002),各类强势行动者围绕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市场扩张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展开争夺,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构建其“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无论是宗族式治理、公司型治理抑或灰色型治理都蕴藏着巨大的利益谋取空间,国家资源、公众利益被强势行动者通过一系列“合法化”外衣的掩饰占有。普通村民则成为“边缘人”,村落公共资源乃至国家的资源投放沦为强势行动者的“私有物品”,乡村治理呈现出内卷化的局势,乡村治理亟待重塑。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民上楼”、“土地征收”等成为乡村中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普通村民的讨价还价能力有限,而国家的法律又没有进行具有强制性的约束,这使得“土地财政”的生财之道逐渐从城市及其郊区转移到农村地区。而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村民与基层政府以及经济精英等行动者的复杂博弈,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困境以及基层政权的内卷化。
如何摆脱乡村治理的困境,改变乡村治理中普通村民的弱势局面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命题。反思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反思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建设,并进而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正如前文所述,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等制度安排都将对乡镇基层政权的行动逻辑产生深刻影响,也将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因此,推进乡村治理发展,必须调整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改变国家“项目治国”的方式,在集权与分权中寻求平衡。例如,在环境保护、司法体制等领域实行垂直管理,将权力重心上移。而在财税权力上,则可以通过省管县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更大的权力,从而避免由于地方财政吃紧而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此外,由于项目治国所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即国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可能无法到达基层社会的困境,需要调整项目治国的方式,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的同时探索更为高效的资金配置方式和渠道。
通过有限的权力介入,社会资本的重塑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等方式重新架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强化对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力规约以及道德约束。乡村治理内卷化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经济理性的充斥所引致的权力的寻租等腐败行为。因此,实现不同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良性运作并不在于重新回归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强力控制的“老路”,更不能无所作为的走任由“体制外”精英谋取公共利益的“邪路”,而应该走出一条“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在法律与道德双重约束下多元共治,最终实现“善治”的“新路”。
1.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5)
2.谭同学.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J].学习与实践,2006(6)
3.肖唐镖.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J].东岳论丛,2008(5)
4.郑风田,阮荣平,程郁.村企关系的演变: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J].社会学研究,2012(1)
5.陈柏锋.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J].青年研究,2010(1)
6.肖唐镖.乡村治理中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7.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8.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
9.高红波.作为村庄纠纷处理人的乡村混混探析—兼论小戚族的村庄基础[J].青年研究,2010(1)
10.宋宝安,赵定东.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J].长白学刊,2003(3)
11.欧阳静.“做作业”与事件性治理:乡镇的“综合治理”逻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