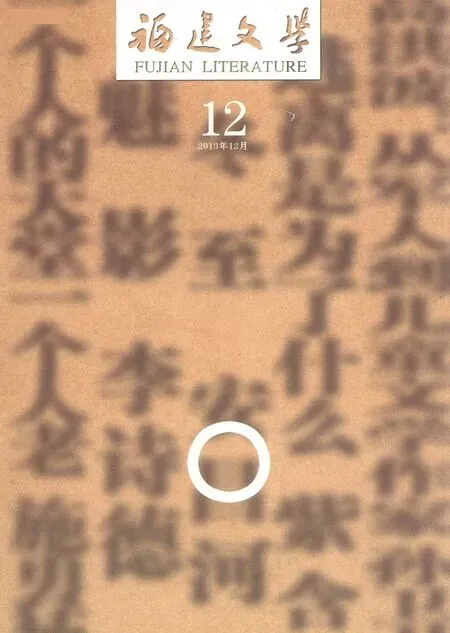煤棚里的陌生客
□孟学祥
□罗龙海
散文空间
煤棚里的陌生客
□孟学祥

老式楼房的一楼,是各家各户的煤棚。购房时,原屋主把我带到楼下,指着一间潮乎乎黑幽幽的小屋对我说:这就是煤棚,现在归你使用了。煤棚正对着我七楼的主卧室,从一楼仰望上去,全封闭的主卧室阳台就像一个凌空吊着的阁楼,悬悬地坠在煤棚的上方。
各家各户的煤棚都是关着的,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铁锁。属于我的煤棚因为其原先的主人长期不在这里居住,疏于管理,铁锁早就不见了,门也朽烂不堪,里面更是尘埃遍地,垃圾成堆。把家搬过来后,我和爱人嫌一楼的煤棚与七楼间相距太远,也就没有把煤棚清理使用起来。
响声从楼下传来时,我正在炽热的屋子里烦躁不安。炎热的夏季打乱了我的生物钟,白天烘热,夜里闷热,让人无法安坐和入睡。刚用冷水冲刷过的身子不一会儿又变得汗津津潮乎乎,这个时候我对任何声音就特别敏感,一点点轻微的响动都能够引动耳膜的共鸣。
响声又传了过来,听起来特别清晰特别刺耳,我站在窗边,声音透过洞开的窗户如雷鸣般灌进屋子里,回响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下意识地往发出声音的楼下看去,各家各户飘出的灯光摇曳在街市的夜空中,除了这些或闪现或隐退的灯光外,什么都看不见。声音仍锲而不舍地飘过来,清晰地响彻在寂静闷热的夜空中。
我提着应急灯向楼下走去,烦躁的心情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去寻找声音发出的地方。楼道仍然很黑暗,从七楼到一楼,如果不是提着应急灯,我是很难摸得下去的。
一楼的背后,卧室的阳台下,应急灯指引我找到了声音的来源。雪亮的灯光下,正在忙碌的一对中年夫妇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迅疾地停了下来。我感到两双胆怯的目光在我的身上迟疑了一下,或者说留驻了一下,我愤怒起来。这是关键的所在,因为面前这两个人,因为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我知道了眼前的情形,知道了有人在动我的煤棚。我虽然一直没有使用这间煤棚,但这是属于我的财产,是我房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它在我的房屋中属于不可用的一部分,我也不会允许别人占有。
男人首先反应过来,叫了我一声大哥,我没有理会,女人也叫了我一声大哥,我仍然没有理会,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接着他们又叫了一声,这次我用鼻子一哼,算是做了回答。在应急灯光的照射下,煤棚里点着的那支小蜡烛就失去了应有的光芒。煤棚已经被打扫干净了,垃圾被清理出来堆放到了距煤棚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几块木板支撑的一张床占去了煤棚的大半个空间,朽烂的门被钉上了两块新木板,还有几块木板散落在地上。男人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捏着几颗钉子,女人的手上拿着一块木板。我在楼上听到的声音就是他们修理木门发出来的。看到男人的斧子,我的心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心中集聚的愤怒慢慢荡漾开来,粗重的鼻息也渐渐平复下来,因为愤怒而捏紧的右手拳头也像落入水中的土块,缓缓地摊散开来,不再凝聚,不再有力。

知道我是煤棚的主人后,男人放下斧子,从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谢绝了,我说我不会抽烟。男人递烟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抖着,那不光是一种慌乱的抖,更是一种恐惧的抖。男人的慌乱让勇气又重新回复到了我的身上,我质问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动我的煤棚。男人点着了烟,抖抖地抽着,烟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笼罩在他的脸上,也笼罩在暗夜的灯光里,让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孔。男人说他们是进城找活干的,他白天就守在街边找活干,女人就挑着菜走街串巷去叫卖,由于赚不了几个钱,没敢去租房子住,晚上两口子就在街边胡乱找个地方挤一晚。女人到这里卖菜时发现了这个空着的煤棚,门也没有锁,是一个理想的遮风挡雨的地方。天黑了,他们从街边挪到了这里。也许是怕我听不明白,男人停顿下来的时候,女人就急急忙忙地补充。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诉说,急急忙忙地诉说,急急忙忙地补充,可怜兮兮地恳求。说话的同时两双眼睛躲躲闪闪地不停地在我的身上扫描。他们的诉说、他们的恳求让我由愤怒转为平淡,由平淡转为同情,由同情转为可怜。
我似乎看见了白天,看见了那些蹲在街边等活干的农民工,看见了挑着菜担与城管躲着迷藏的小贩。每一次与这些人相见我的心就没来由地有种酸涩的疼痛。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中,这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啊?这道风景表面上与城市生活共融,但实际上却一直与城市的文明格格不入。因为晚上很少出门,我就很少看到那些居住在城市屋檐下的农民工。他们或许睡得很晚然后又起得很早,就像在家干农活一样,把睡眠的时间都挤在了劳动上。他们不像其他城市流浪者那样,在我去上班的时候还在某一个屋檐下呼呼大睡,给人留下恶心的印象。我无法想象一对夫妻相拥在屋檐下的情景,更无法想象在城市因噪音、因治安等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干扰下,他们会睡得踏实吗?我不会再责备他们了。我把手上的应急灯递给那位妇女,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按在门上坏了的地方,叫男人把钉子钉上去。男人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丢掉手上的烟头,拿起斧子把钉子敲了上去,那一刻我看到男人和女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女人说太脏了,叫我不要动手,由她和男人干就行了。我没有理会女人的话,一边替男人打下手,一边叫他们赶快把活做完,不要影响楼上人家休息。
朽烂的木门修好了,把门关上后煤棚里俨然成了一个家,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站在这个家里面,我感觉这里竟比我七楼的房间凉爽得多,这种凉爽让我找到了一个清静的理由,不再烦躁,不再坐卧不安。我不知道这种安宁和清静是因为没有了响声还是因为刚刚的经历所带来的,当我的感情接受这对夫妇在属于我的煤棚安家的时候,这间低矮潮湿的煤棚和至今仍回响在耳边的声响,使我仿佛感受到了雨丝的清凉,其实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雨丝,煤棚外只有闪烁的城市灯光和飘浮在城市上空的闷热。我一时竟不想这么快就回到我楼上的家去。此刻我很难分辨得出,到底是我楼上的家凉爽和清静呢,还是这对夫妇居住的这个小小的家凉爽和清静?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这个由煤棚改装出来的家,这对在城市流浪打工的夫妇今晚一定会睡得安宁了。
煤棚里点着的蜡烛光线很微弱,幽幽的光泽即使普照在狭小的天地里,也显得很阴暗,远不及煤棚外熠熠的城市灯光。煤棚里的家很简陋,简陋到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张木板铺出的床,和床上很脏很旧散发出酸臭味的被盖,最值钱的东西恐怕就是女人用来挑菜卖的那对竹篮了,竹篮立在屋子的一角,占据了很大一片空间。竹篮的倒影在烛光的摇曳中从墙壁延伸出来,懒懒地横躺在窄小的地面上,在烛光里发出微微的叹息。烛光能照得见的就只有这些,没有家具,甚至于连煮饭的饮具都没有看到。这就是他们在城市寻觅到的家啊,一间早已被这个城市忽略了的小煤棚。但我感觉到了,他们对这个家很知足,对我慷慨地给予他们这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很感激,我想这种知足和感激一直会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他们懂得感恩,懂得想用出力去帮我干活来给予回报。
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从那一排排关着门的煤棚前走过,那些锈迹斑斑的铁锁,那些锁着的门把城市夜空摇曳的灯光都阻挡在了门外,把煤棚的秘密都深藏在了漆黑阴暗潮湿的狭小空间里,看上去就多了几分孤单,也多了几分冷漠。走过这些煤棚和围墙牵手形成的狭小长廊时,那对陌生的夫妇还在那间开着门的煤棚前站着,手上拿着的蜡烛在夜色中一闪一闪地亮着。我告别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向我欠身致礼,要用蜡烛给我照路。其实我就拿着应急灯,根本用不着他们的蜡烛,我还是答应了他们送我出门的请求。离开煤棚时我并没有急于开灯,而是让他们用蜡烛微弱的光亮送了我一小段。我打开灯后他们才站下来,然后就一直目送着我,到我转过墙角,走出那条黑暗的长廊。
城市的闷热在灯光摇曳中散发出烦躁的气息,在夜色中从洞开的窗子里不断侵淫着我心灵上的宁静。是一对寻觅到废弃煤棚里的陌生夫妇,用一支蜡烛的光亮照出了我要寻找的那条让自己沉静的小路。回到七楼的家中,透过城市的灯光,我只看见城市的高楼和高楼边缘深处那些朦胧的远山。楼下煤棚的烛光不见了,在强大的城市灯光面前,那点微弱的烛光肯定要被忽略掉,它无法凝聚出光的主流,甚至于连做城市灯光的点缀都谈不上。但因了这道烛光,今夜,煤棚里的陌生夫妇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我自己也能够沉静下来,踏踏实实地睡一个安稳觉了。
责任编辑 林芝
□罗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