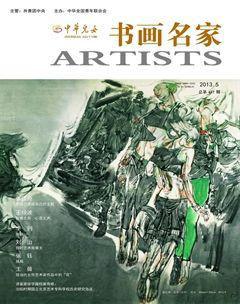列语
山己
时间:2013年4月15日
地点:李列工作室
受访人:李 列
采访人:山 己
对艺术的某一种形式钻营太精深、太透彻也是很危险的。太精深往往会陷入的很深,容易限制和失去产生其它可能性的空间,物极必反嘛。艺术本身更多是自我的省悟。
SHMJ:这是你第几个工作室?是否考虑过搬去艺术家聚居区创作和生活?
李列:这已经是我第二个工作室了,之前的工作室在马泉营那边,有二十来个艺术家,创作氛围还是不错的,至于搬离的原因,主客观的因素都有。我想,艺术家之间虽然需要交流,但我希望保持独立的状态,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主题,与艺术家们交流的时候我会有所选择。
SHMJ:看到你的这些作品,使我自然联系到你二十岁在首届中国油画静物展获奖的那幅《织物》,非常写实。你的写生作品和创作距离蛮大的,写生从题材和技法上都能给熟悉你的观者以新鲜感。
李列:从我个人喜好上来讲我喜欢具象的表现手法,但是具象概括不了我的全部,一些形式感和意象表达也始终是贯穿我作品的因素。前几天我去画了万寿寺的写生,平时写生的机会不多,我大多时间是呆在画室里面观察、创作,更多是理性的思维和表现,写生则是充满激情。画画如同生活,或者每个人的性格,不可能以单一的面来呈现。我平时的作品里多带有中国古典式的情趣与精神内涵,这种表述是不自觉的。就如同小孩子看到卡通的形象怦然心动一样。当我游走于车水马龙的都市街道,两侧高楼林立,突然一座飞檐的箭楼横在面前,古朴、肃静。对我,就有足够的震撼,停下细细端详吧。
SHMJ:万寿寺写生灵活随意,挺精彩的。这和反复制作出来的作品截然不同,具有现场感。
李列:写生考验的是画家的直觉感受,画室里的创作每幅耗时都很长,更多考验的是画家的理性与耐力。那幅万寿寺写生当时只用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是想尝试色彩和形式感,最后效果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理想的。我写生时并没有完全对照自然,也没有表现万寿寺的客观颜色,却搁置了许多的主观成份在写生里面。针对客观对象无差别的描摹当然不是绘画的主张,从这一点上来看与我平时创作的主张没有多大区别,我把写生也看成是一种创作。
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平时写生的机会不多,我个人刚开始不喜欢临摹别人的作品,以前学画的时候老师和朋友们认为临摹和写生是学习最好的途径,而我个人观点则认为对艺术的某一种形式钻营太精深、太透彻也是很危险的。太精深往往会陷入的很深,容易限制和失去产生其它可能性的空间,物极必反嘛。艺术本身更多是自我的省悟。假如画家被既定的观念、流派、审美……所左右,就丧失了自我发挥的空间。一部小说你把它过于精读了你获得的未必就是你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章节中有些讳莫如深的东西反而让人着迷。我当然不是反对临摹大师的作品,我是说要会临摹,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像书法的描红,手动了,脑子未必思考,描红的效果未必有临帖好。所以,动脑子是主导。
SHMJ:陶渊明的观点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强调个人的会意和新的体验。
李列:在前人既有的经验面前学习是前提,但未必顶礼膜拜。给予自己一点的空间,保持模糊的状态不被死的结论所左右,开放性的结论更有其自身的魅力。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或大师作品可以包罗所有艺术规律抑或完美存在,在大师的作品面前,首先剔除那些艺术理论书上过多的溢美之词所带来的光环,想象画家就住在你画室的隔壁,每天早晚见面寒暄的一个人。再分析这幅作品,可能就客观许多。假如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铺设好的就非常乏味了。
SHMJ:怎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来北京发展?
李列:我一直喜欢材料在画布上产生的肌理感,总试图把写实油画和材料、媒介等作一些尝试性的对接。2007年的时候我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材料工作室,开始非常不适应,周围的人基本都搞抽象或者表现主义,我想我还得夹缝求生吧,寻找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呵呵……学业完成之后就在北京定居下来。因为有单位,有时还要回去上课,都是阶段性教学,对创作没太大影响。期间完成了一批作品,在北京和上海做了两次展览——“列景”和“游离古典”。“列景”和“游离古典”的作品颜色均是以黑、白、灰为主,现在的画都稍微加入了色彩。
SHMJ:北京的氛围给你带来了哪些影响,对于你的创作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或者干扰?
李列:你这个后缀的“干扰”提的好。大家的直观认为北京相比较于地方城市更具丰富性,聚集许多艺术人才、很多想法观念,大家彼此间交流多了能碰撞出新的火花来……。其实,我感觉艺术本身更需要艺术家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艺术需要交流,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要有明鉴的心。至始至终我的作品都着重反应细节和自我情绪的表达,我喜欢丢勒、格列柯。应该受古典主义影响更大,喜欢只能是喜欢,我反对去模仿、被左右。是否能独立这取决于画家心智的成熟度;取决于对艺术本身的理解,这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它牵扯到画家的整体素养。
SHMJ:中国式的古典形式感成为你作品的样貌,具有明显的辨识度,在创作它们的时候你的灵感是来自那些方面?
李列:这个问题涉及到创作作品时的精神情感,我骨子里很传统,有时候很怀旧,性格内敛,比不上别的艺术家们性格张扬。我喜欢委婉、哀怨的情调,无论是写生还是创作给人的感觉都不是欢愉的,有淡淡的哀愁充斥在里边,画面所溢出的情绪让人感觉到“清冷”。每个艺术家的性情以及作品都脱离不了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时代,这牵扯到性格、兴趣、知识结构等层面。这对于艺术家的影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但要具体说出来,挺难。
SHMJ:作品的宁静、萧瑟气息与当下时代节奏产生了巨大的逆差,这般的冲突可否视作你个人与时代的摩擦呢?
李列:没错,作品如同我的个人性格一样。我是爱静的人,在人多的场合我会感觉莫名的孤独。有人告诉我,说现在的很多画看起来就象画家是被人追着画完的,你的画是你被人关起来画完的。我说,没人关我,是我把门反锁上画完的(笑)。传统的文化以及理念正在被当代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所超越,对此,我非常困顿,不愿接受却无能为力。用“践踏”这个词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一个时期以来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融合,我们能否保持自身原有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审美取向,更多是价值观的问题。
SHMJ:你是不是从宋代绘画之中获得一些启发,让画面里的景与物变得紧张、冷峻。
李列:其实每个时代的艺术都带有每个时代的烙印,近现代的艺术作品与以前不会一样的,当代画家的作品也具有时代特征,艺术家的思想、审美、情趣,意识形态都会不自觉地与时代挂钩。中世纪的绘画以现代人的意识形态当然不好去理解,必须了解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近几十年,油画的声息在西方日见微弱。相反,在中国它却找到另外一方天地。中国在接受了固有的西方油画的同时也在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我是说现在中国画家在尊重西方绘画技巧和理念的同时更多是借助油画这种材质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表达的内容包括我们理解的图式、色彩、情感因素等等。当下,常有声音妄自菲薄,说中国人不用画油画了,再画也无法超越西方的某个时期的某某某。我问他,汉代的金缕玉衣材质、工艺无与伦比,现代人还愿意做一个嘛?即使做了,有实际意义吗?所以,并不能简单说中国的油画家比不上西方的油画家。近三十年油画本土化发展趋势最明显,画家们更加自信和独立,自信非常关键。现在信息沟通也很发达,油画本身也不存在秘密可言,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油画家对于自我的管控、观念和审美诉求就浮现出来。
SHMJ:在你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图式情趣,令我想到中国的工笔画,同时它又具备西方绘画里的明暗、对比、过度。
李列:你说的作品是我2008年以后陆续完成的,将中国式造景与现代构图对接做的尝试。我放置了悲壮的情怀在作品里,有的还采用了纪念碑式的构图,我不表现小情小趣反而更喜欢冷酷直接的东西,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悲壮的东西就一定比婉约的好,这完全是个人性情所致。希望自己的作品禁得起别人琢磨、品味,去材料工作室读研修班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SHMJ:这是许多画家普遍的心理,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愿意自己拥有一套“绝活”,任由别人去模仿也模仿不像。
李列:后来就意识到过分强调“绝活”走向了极端未必是件好事,绘画毕竟不是为了技法而技法,独特的技法是绘画的一个步骤,用好了就锦上添花,前提是以作品内涵作为支撑。基弗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野性、苍茫、冷酷的气质,符合我的胃口。虽然我和他不从事同一种风格的创作,但他的精神内涵能够关照到我,南京作家苏童文学的婉约、静谧、恍惚气质也能给我以触动,他甚至让我想到苏州老城小巷里湿漉漉的青苔,有评论家说苏童的思想和文笔就像苏州的丝绸一样细腻,我赞成。
SHMJ:基弗尔和苏童,两个人的距离无比遥远仿佛是影响你艺术的两个磁极。
李列: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大,苏童和基弗尔在地里位置上相隔万里,从事的行业更不在一个领域,他们的情感貌似背向而驰,我却同时欣赏,可见人性的情感的兼容性。还有,他们似乎又有相通的地方。假如二人能有一次对话机会肯定会有碰撞,对于形式美的看法,人文情感的追求都是可以展开的点……,作为我个人是比较关注当下问题的,包括社会现象与人的思想观念等,去年全球都在讨论世界末日的话题,有的人搞的非常惊恐,我画了《2012年12月21日的预言》,算是应景而生。人生很脆弱,思想也很脆弱,自然灾难、人为污染、战争……对人形成种种冲击无法避免……。在另一幅作品《松竹梅》里我着重刻画了一个白色的治疗盘,它象征着伤害和治疗,而松、竹、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当今的中国传统文人气在弱化,更趋向于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是冲击。个别国家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自己的坚守底线,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着手值得我们学习。
SHMJ:“松、竹、梅”与“治疗盘”二者并置引申出传统文化遭遇治疗、伤害性的威胁,这样的安排有别于人们以往的经验。
李列:对于传统文化我总有种悲悯的情结,想把它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构图上怎样呈现它们我反复考虑了大概半个多月,画起来倒是挺快。这张画着重突出暗调子里的一抹亮色,松、竹、梅也罩上一层淡淡色彩。开始构思这幅画的时候,素材的选择挺费脑筋,我太太是学医的,建议亮色的地方可以摆放一个治疗盘,当时听了就很激动,结果效果还是不错,既吻合作品主题又满足了构成需要。在构思创作期间太太总会给我很大帮助。她懂画也懂我……。
作品《雨夜》的人物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他,因为他的长相很适合入画就约他给我做模特。采用了他侧面的角度,画面所传达出的气息是湿冷湿冷的,里面石头,植物,人之间形成了趋势和空间感。
SHMJ: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模特本人的时候你脑海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感?
李列:没有,在见到模特之前已经有80%的构图确定好了,人物的地方是虚位以待,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之后才起了点变化。这张画色彩控制的比较少,我始终不习惯把颜色画的很强烈,所以不停在弱化它们,你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什么颜色来。性格中对于张扬的颜色是不排斥的,可是让我尝试去驾驭未必就愿意。我喜欢中国传统的古画经过时间侵袭以后呈现出雅致、沉静、委婉的状态,我的作品就体现了类似的怀旧情怀。马远和夏圭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们的构图形式对我创作影响很大,而有的画家笔墨用的好我就会着重吸取他们的笔墨,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吸收他们作品里的营养。
我的画内容都不复杂,甚至可以用简洁来形容。处理单纯画面的时候避免简单化反而更困难,因为元素少,如果一个地方不对劲很容易破坏画面的整体感,视觉上会变得空洞。我的画面里大部分是空白,必须得有耐看的地方留住观者的目光。
SHMJ:画中的鸟栖身在生硬冰冷的环境中,这能否看作是你内心的遭遇或者只是你对于某种构图形式感的迷恋?
李列:形式感的迷恋只是一个方面,是绘画构成的需要,其背后体现的是个人的情怀。对自身情感的发现存在一点迷惑,不好用语言来表达,我画完一幅画只是把画呈现了出来而已,有的评论家们会把它解析的淋漓尽致,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连我自己看了都一头雾水。
SHMJ:一旦你和评论家之间产生不同观点的时候,你会去与他们争辩,否定他们的过度解读吗?
李列:当然不会。不用说评论家,就连普通观众怎么去看待我的作品我都不会干预的,欣赏艺术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解,艺术家创作时究竟是怎么想的艺术家自己也不容易说清楚。这绝非一种尴尬,大多绘画作品不完全是叙述性的,叙事性在作品中允许只占有很小比例,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每件作品都为观者提供发挥想象的空间,每个人最后得到的东西都基于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而不同。最怕别人问我:这幅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SHMJ:观众往往是怀着看懂、弄明白的心理去欣赏艺术品,这与艺术家观念和初衷之间形成了不同步、不对等的关系。
李列:我认为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给予观者灌输确切的“答案”是对观者的不负责任,当然,叙事性的主题创作除外。假如艺术家把一块画布涂成了红色有必要再去跟观者解释为什么涂红吗?我感觉未必!因为每个观者看到红色的感受会有差异,艺术家去解释红色就等于给观者设立“障碍和框定”,让观者钻进“套子”里面去。这样的“框定”经常会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旅游风景区里,自然天成的山峰都给取上了所谓具象的名字,这不就是牵着游客的眼睛去接受人为的“框定”吗?我想,给人们提供感受是艺术应该担任起来的任务,艺术作品只有在被观看的过程中它的外延才能被人们不断扩大。
SHMJ:因为你采取“黑、白、灰”的颜色,你画的石头仿佛是蒸腾的烟雾,既像是固态又像是气态,很有意思。
李列:石头也是文化符号,存在于中国古今的文艺作品当中,我画的石头连我自己都很难说出究竟是太湖石还是灵璧石。很多人看来了以后说是太湖石,其实真正的太湖石不具备这种形式感,太湖石讲究“皱、透、漏、瘦、丑”,我画的石头“丑”可能是有的,要是说“透”就说不通了,更谈不上“皱”。我画石头没有任何的参考,是自我的直接表达。有人反馈给我说从石头里面能看到生灵的五官模样,我自己看不出来,在画的过程里我是抽象的思维,具象的去表现。
SHMJ:《2012年12月21日的预言》和《夜雨》《新溪山行旅图》这三幅作品标志着你的人物作品的回归?
李列:我一直都在关注怎么处理人物画,近期开始尝试把人物放置在之前的场景里面。我每个时期的题材都不是预先设定好的,是跟随情感和对材料理解渐渐展开变化,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调整。
SHMJ:所有作品中你通过对传统图式的借鉴和再现像是在坚守某种价值观,反抗某种价值观……,这么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李列:坚守与反抗可能都有,意义在于我内心的挣扎,挣扎或者碰撞才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和隐忧。骨子里的东西挥之不去,无法改变,同时当下人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已与传统文化之间背离相当远了。当然我们不能用对与错的的观点去评判当下的人,人的背后是时代的大背景在支撑着,困境不只体现在艺术行业中,我想每个行业都会有类似的困境存在,作为个人你要怎么选择?能否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伴随着这样的语境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出现了,很多人对当代艺术有所微词,那大可不必。关键是要看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态度,真诚的创作总会打动人的。再一段时间,对当代艺术的评价都会客观、公正了。
当代艺术中绝大多数艺术家是报以真诚的态度去创作的,从手法到形式再到思想都是遵从于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真实感受,针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我个人而言目前的主题、技法、形式风格,我创作起来感觉很踏实,很有激情。我对于具象写实语言的追求也许会延续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