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年片
□孙春平


潘洗,本名姜鸿琦,满族,工程硕士,1969年生于辽宁岫岩。曾在国企从事过共青团、会计、宣传等工作,现供职于辽宁鞍山供电公司。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多篇,著有小说集《香味橡皮》。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北2830”召集人。
专栏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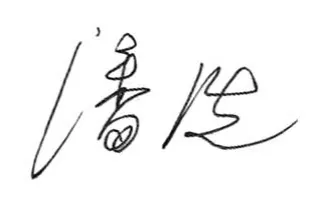
二十年前的冬天,我的老岳父携夫人兴致勃勃回河南老家省亲。岳父是抗美援朝时参的军,打败美国野心狼后,撤过鸭绿江便留在东北当了工人。数十年风风雨雨,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退休了,时间充裕了,才又有了这次返乡之旅。
小年前的一天中午,岳父突然打来电话,急慌慌地说,我们在郑州火车站呢,正准备回去,可下大客时,钱包被人摸走了,早买好的火车票和回家的盘缠都在里面。我说,能不能再回老家去,跟亲友们借点钱买车票,以后再寄回去嘛。岳父说,好几百里旱路,没钱买票,哪辆车让你白坐?为这种事回去,手心朝上的,脸上也臊得慌啊。再说,傍年根了,手上有钱想买票也难,我丢的那两张票还是我外甥求了好多人才买到的。我说,别急,遇事找警察,你去附近派出所想想办法。岳父说,我们现在就在站前派出所呢,用的就是他们的电话。我说,你把电话交给身边的警察,我跟他们说。
警察接了电话,我自报了身份,求他先借几百元钱,并信誓旦旦地保证马上就去邮局寄款。警察口气挺委婉,态度却坚决,说记者同志,你家老人所遭遇的情况,我们深表同情。可我们每天处理的此类情况真是太多太多,手上哪有那么多的资金垫付。我们要是不小心,让骗子骗到派出所来,那才叫笑话呢。况且,即使我们借了钱,怕也难保证能很快买到返程的车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送救助站了。所里的电话很忙,非常抱歉,就这样吧。我急吼吼地喊,警察同志,天黑之前,请务必留二位老人在派出所里避避寒,我们一定抓紧想办法,拜托了!
关于小心受骗的话,好似一根小棍杈支在了我的嘴巴里,让我心里再有多少话也难以倾诉。妻子已披挂起来,说这就去沈阳,坐飞机奔郑州,总不能让老爸老妈挨冻挨饿受欺负。我拦住她,说且不说你到了沈阳能不能搞到飞机票,只怕你连怎么去沈阳都是大问题。你忘了大雪封路,这几天总是有朋友求我帮买火车票啊?妻子是中学老师,正好放寒假,此时已全不顾为人师者的斯文,冲着我瞪眼睛,说平日里你不总自吹自擂记者是无冕之王吗,三个不服两个不忿的,怎么到了我爸我妈有难的时候,就变成了缩头乌龟屁点能耐也没有了!
我哪有心跟她分辩,在地中间转了一阵圈子,便将我存在家中的所有名片和通讯录都翻出来,试图能找出一两个郑州的朋友。我在报社当记者,以前也曾有过新闻稿获过省外的奖励,也算有机会去外地领奖和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同仁聚会,难免嘴上喊着久仰久仰,忙着交换名片,尤其是推杯换盏酒意正浓的时刻,掏不出名片的也要在小本本上留下彼此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不似当下,人人都有手机,问了号码,一按键,既保存,也将自己的信息发送了过去。
万幸,还真找出了两张郑州朋友的名片。我一边努力在脑海中搜寻拼凑着这两个人可能的音容笑貌,一边打着腹稿,想好电话接通后怎么有效地表达好求助于人的言辞。第一个电话打出去,接电话人说,某某已去深圳另求发展,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了。另一个电话倒是本人接的,听我报了姓名,人家说,对不起了,请原谅我这人眼浊脑昏,真是记不住你是谁了。我不甘心,再回忆可能共同出席的某次会议,人家又说,怪只怪眼下骗子太多,我的片子也撒的太滥。片子嘛,不是骗人就是被骗。当然,但愿你不是呀。
我的嘴巴再次被小棍杈撑住,没法说下去了。我放下电话,坐在那里发呆。也难怪,换了有人找我,只凭了名片上给出的信息,对方还请求立时将币子送到火车站素不相识的人手上,我又当如何?妻子又冲过来催我,说就凭酒桌上认识的几头烂蒜,也能算朋友?我气哼哼地说,再给我半个钟头,想不出办法,用不着劳你大驾,我自己去!
我所剩的办法就是扔开那堆名片,再去翻看通信簿,左一本,右一本,都是巴掌大小,便于携带。上面的信息多数由我亲笔所记,也有个别的,是陌生的笔迹。酒桌上,呼朋唤友的,一时掏不名片,便在这种小簿子上留联系方式。有人嫌哄乱喧哗,夺去笔,自己在上面写,还说这才是真迹。留在上面的信息多数只有姓名和电话。我按照郑州的区号0371一一查找,果然就找到了一个,秦国春。看笔迹,不是我的,那就是人家的,字挺大,颇显粗放。酒喝大了的人写下的字多这样。有病乱投医,我已来不及在记忆的深处还能不能筛辨得出这人的印象,急把电话打过去。有人接了,里面很乱,好像有人在嚷,还有人在抚慰。我说找秦国春,接电话人喊了声小秦,接着便是噔地一响,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了桌上。
“我是秦国春。请问哪位找我?”足有两分钟,总算有人说话了。
我的心不由刷地一凉,竟是位女士!这种事,女人往往更小心谨慎。但事已至此,只好报上姓名,还问秦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在新闻界,同仁中常以老师相称,就好比进了工厂,多喊师傅。
秦国春说:“看肇老师说的,一听声音,我就感觉到了东北人的豪放。大尾巴肇,你说十有八九是满族,对吧?我还记得你那篇获奖新闻的题目呢。肇老师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这里正乱,有人闹到报社来了,说我们的新闻歪曲了他。您大点声说,不然我听不清楚。”
我便如此这般说了,说了岳父岳母眼下的困窘,也讲了我和家人的牵挂。秦国春打断我,说我明白了。这样吧,等我处理完办公室的乱糟事,马上去火车站。如果我无力安排好伯父伯母,一定会给你回电话,莫以成败论情谊,你别怪罪就是。若是顺利,我就不回电话了,行吗?我提醒,最好是天黑前呀,不然你就难找到二位老人啦!
听声音,那边确是一片嘈杂,似乎还有人拍桌踢椅。秦国春能这般应承下来,已让我心中很是欣慰。守在电话旁的那半天加一晚,我和妻子的心很是忐忑,既盼电话响,又怕电话叫,个中的复杂滋味,一言难述。天黑之前,家里的电话共响了两次,我和妻子都惊惊的不敢接。一次是妻子的学生打来的,请教一道数学题;另个电话来自报社,部主任安排我第二天去采访一个会议。放下电话,我和妻子都长嘘了一口气,相视而笑。夜幕已经垂临,秦国春的电话没有打进来,看来形势不错,可资期待。
半夜十点多钟,电话再一次响起,是岳父打来的。岳父兴冲冲地说,我跟你妈已坐上火车了,是特快,你的朋友还给买了卧铺,你好好谢谢人家吧。我是在车上借一位咱东北老乡的“大哥大”打的,不多说了,话费挺贵的。二十年前,手机尚为奢侈之物,一声“大哥大”,足以将寻常百姓拒之千里。我和妻子自是大喜,尤其是妻子,挂在嘴上半天加一晌的揶揄挖苦之辞顿飞九天云外,说不是说河南人不好交吗,没想还真有活雷锋。又大半夜的抱住我的脑袋,非要帮我揪下她刚发现的几根白发。我岂会不懂她的心思,加上心中骤然而至的轻松,便忙着宽衣解带,报以一时的豪强。
那一番折腾,竟是罕见的酣畅。没想事毕,妻子竟幽幽地问我,你给秦国春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听好像是女声。这个秦国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说,我到现在还在想着她的模样,又是在哪个会议上认识的呢。妻子用眼角扫过来,腔调已有些酸,说不会吧?越想遮瞒越有鬼,一般关系,人家能这么帮你?睡意正浪潮一般一波一波涌过来,我懒得在这样的话题上跟她费唾沫,说了声你愿信不信,明天问你爸你妈,便翻身睡去了。
第二天的会议采访是九点。八点一过,我先给秦国春打去电话。以我的经验,新闻单位这个时刻正是人员最集中的时候。接电话的同志说,秦国春去外地采访了,过几天才回来。我问,不知她有没有“大哥大”,能把号码告诉我吗?接电话人笑了,说我们小秦记者的武器装备还没上升到这个档次吧。单位倒是给我们都配了BP机,你要是有急事,就呼她吧。我按照对方给出的号码,请接转台输去肇某某深致谢意的信息。秦国春没有回。那个时间,她或许正在采访,或许还在路上,身边没有电话或信号不在服务区内,一切皆有可能,正常,不奇怪。
那天傍晚,我将岳父岳母接到家中。饭桌上,我给二位老人敬酒,故意文绉绉地说,二老千里奔波,虽小有磨难与波折,所幸吉人天助,坦途依旧。我们迎接二老平安回府。岳父大人压下我的手,说坐下坐下,一家人少说醋酸话。什么吉人天助,要不是你的朋友帮忙,我们老两口真就得去救助站了,听说那地方吃不得吃睡不得睡,还要受人欺负,鬼知哪天才能赶回来。岳母说,你那朋友昨晚也真赶得及时。眼看着擦黑了,派出所的警察又要给救助站打电话,那小秦闺女就赶到了。先提你的名字,接着就拿出了两张车票,还说就是为搞这两张票才来晚了。人家还非拉我们去了附近的饭店,荤的素的点了好几盘,让我们慢慢吃,自己却跑出去,再回来时手上就提了一塑料袋面包水果什么的,还放到我手上二百元钱,说备着路上急需。当时我们老两口虽说正饿得肚子咕咕叫,也没敢动筷子,想等她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没想她又说明天一早要外出采访,家里有些事要安顿,就不陪了。又说二老慢慢吃,别着急,开车前半小时进候车室就行,我就不送伯父伯母上车了。哎哟哟,真没想到,人家替咱们想得这么周到。岳父对我说,你怎么感谢你的朋友,我就不说了。但头一宗,这车票钱,还有小秦同志放到你妈手上的二百元钱,总得抓紧给人家返回去。
一直没说什么话的妻子突然问,爸,这个秦国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岳父说,比你年轻,我和你妈估摸着,不会超过三十岁。人也长得端正漂亮,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挺受端详的。咦,这你还用问我呀?妻子用眼角剜了我一眼,说名记同志说,他见过的人太多,多过夜空中的繁星,这个人具体啥模样他也记不清楚了。岳母说,这闺女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有点河南人的侉味,可句句听得懂,还软软的,不像咱们东北人,开口就直门亮嗓硬邦邦的。岳父感觉到了他女儿问话里的不和谐音符,有意把话题往一旁岔,说我也是河南人,咋从没听你夸我一句说话好听?岳母说,你拉倒吧,跟你老家的那些乡亲们倒有一拼,侉得掉渣。要说不侉的时候,也就是晚上睡觉,那呼噜打的,别说跟咱们东北人一样,连猪八戒都挑不出毛病。一家人哈哈大笑,总算翻过了那一篇。
酒足饭饱之后,岳父岳母说连日奔波劳累,还是想回自己家解乏。我家的房子确是太狭窄,我和妻子也不勉强。没想把二老送上出租汽车刚回家门,妻子便如夏日里的绿头蝇,把我视为祼露了脓血的伤口,又不依不饶地扑上来,说这回不用咬紧牙关充硬汉了吧。哼,很年轻呀,很漂亮呀,还软声款语很会发嗲,行啊,名记先生口味不低嘛。老实交待,那个姓秦的跟你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看脸色,家里的这只母老虎杏眼圆瞪,柳眉倒耸,脸色跟昨晚的半是怀疑半是揶揄已全然不同。女人疑心大,好吃醋,为人师表是在校园里,回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半点也不免俗。昨日老父老母远在异地他乡,那份疑惑尚视为次要矛盾,而今日,老人平安抵家,次要矛盾便转化为主要矛盾了。我心里自是委屈和焦恼,想一想,昨天那半天加一晌,我这可为半个儿的女婿也算绞尽了脑汁,磨破了唇舌,给并不算熟悉的朋友递上了多少拜年般的好话,况且,还有多少善后的工作需要我去一一落实。平安是福,快乐是金,我本不求回报,但得到的总不该是这无端的猜忌吧?我心中的火气冲上来,冷脸回道,你说是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老相好,婚外情,正宗铁子,这回你心满意足了吧!说罢,门一摔,径回卧室,再不理她。
那一夜,妻子睡在了女儿的小房间里。放假了,读初一的女儿说想念爷爷奶奶,率先去了乡下。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或可视为客厅的门廊里的餐桌上仍是杯盘狼藉,女儿房间的房门却死死关着。哼,不收拾便不收拾,撂给谁看?张三(狼)不吃死孩子,那是活人惯的!我连早点都没吃,便去了单位。
家里纵有沟壑万千,家外仍需四通八达。我又给郑州打去了电话,问秦国春是否已回。接话人记住了我的声音,说我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嘛,她外出采访,要好几天。我再问,不知你们是哪家新闻单位?接话人听我这么问,估计猜想到了我和秦国春的关系不过平平,口气便不再那么客气,说连我们是哪家单位都不知道,就不要总打电话了嘛。然后匆匆报了一下报社的名称,便放了电话。
有了这,似乎已足够。我去了邮局,填了汇款单,准备先把秦国春垫付的款额寄回去。没想到了柜台前,邮政小姐却执拗得让我无可奈何,非让我在汇款单上写上收款人单位的街区号和邮政编码。我说你往这家报社寄就是,肯定收得到。邮政小姐说,这是规定,请先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接了没发出的汇款单在手,我心中自是郁闷。秦国春不在单位,那个电话不好再打,何苦自讨没趣。又想,这几百元钱给秦国春寄到哪儿,最好先听听她的意见,直接寄往她的报社也未必合适。我们报社以前就曾出过因一张汇款单而引出很大误会的先例。收发室收到一张汇款单,一千元,是给一位编辑的。有好事者见了,怀疑那位编辑搞有偿新闻,并把话说了出去,直引得二人公开叫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还是谨慎些为好。秦国春一片热忱,助人为乐,若是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就大不该了。
三天后,我再打电话,正好秦国春已回。我再次表达了谢意,并说了寄款的事。秦国春笑道,说肇兄,五次三番地说谢,嫌不嫌累呀?那几百元钱,也算不得什么巨资,你又何苦非得这么急着分成泾渭?我跟你说,我一直没去过东北,对白山黑水和广阔的东北大平原神往已久,正打算过了年就约朋友一起去关东大地看一看呢,老兄是不是怕我叨扰,不想尽地主之谊呀?我心中大喜,说那就盼你早点成行,出了正月,东北的很多滑雪场就关门大吉啦。秦国春说,你等我的电话吧,但愿天遂人愿。
那几天,家里的冷战却一直僵持着,妻子坚持住在女儿的房间里,我也不想委屈自己。有时下班回家,饭菜虽已做好,但很明显,在我进门前,娘娘已独自享用过了。年关已近在眼前,计划中我们要一起回乡下过年,顺便把女儿接回来,可这样的冷战情绪又怎好回老家。思之再三,我便独自去了她娘家,还提上了拜年的礼物,期盼二老侧翼迂回,给些掩护和支持。
二位老人最关心的当然还是欠着秦国春的钱款事。我如实禀告,说秦国春准备过了年就来东北。岳父大为高兴,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安排出时间,请客人来家坐一坐。面前的二老是家中那位胡搅蛮缠女皇的生身父母,我自然无须隐晦与掩饰,便讲了心中的委屈。岳母大人态度明朗,没等我说完,便喷着唾沫星子骂,说这个倔丫头,跟她的驴子爹一样,一条道跑到黑,真是咬住屎橛子不松口,给根麻花都不换!埋汰了自家的男人也就算了,你总不该再埋汰家外帮了咱们那么大忙的人呀!你等我骂她,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岳母退休前是工厂里的天车司机,地地道道的东北女人,岳父从朝鲜战场上下来进了工厂,才结下了这段姻缘。
没想岳父大人听了岳母的骂,反倒哈哈大笑,说我这驴子怎么就不知香臭一条道跑到黑了?人啊,谁没从年轻时过过,虽说我没多少文化,可什么什么情,什么什么礼的道理我老头子还是懂的。我知他说的那个词儿是“发乎情,止乎礼”,便只是笑笑,表示理解,也不打断他。岳父继续说,女孩子年轻,漂亮,爱说爱笑,男人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为了保护她,甚至可以豁出命来,这很正常嘛。当年我们在朝鲜战场,连队卫生员就是个女孩子,山东人,姓孙,大家不叫她名字,都叫她孙二妹,她也高高兴兴地应下来。《水浒传》里不是有个孙二娘嘛,也是山东的,那个孙二娘的故事就是她讲给我们的。这个孙二妹有文化,不光会给我们讲梁山好汉,讲《西游记》,给受伤的战士换药时还会轻轻哼唱沂蒙小调。可也是怪,只要听她唱,就连伤口的疼痛也好像一下轻了许多。所以我们这些战友们有事没事都好往卫生所里钻,就是听她说说话也觉心里舒服。大家在阵地看到野花,也会给她采回来。二排一班的洞庭鲤子就是因为看到战壕外的一簇野花开得漂亮,忍不住跳了出去,对面山上的枪嘎勾一响,就把我们洞庭鲤子的性命夺了去。埋葬鲤子那天,你没见孙二妹哭的呀,抱着松木板的墓碑不撒手,还郑重地对着墓碑亲了两口,看得全连战友都泪流不止。后来,朝鲜战争停战,我们退回沈阳,一边休整,一边等待分配。孙二妹是最先得到分配消息的,她想上大学,学医,组织上批准了,去了上海。战友们送她上火车那天,她泪流满面,抱着我们挨个贴脸。轮到和陕北李逵贴脸时,李逵故意用大胡子扎她,她拍拍李逵的脸说,告诉未来的嫂子,说孙二妹羡慕她。那年月,别说男人和女人贴脸,就是拉拉手,都让人脸红。可那次,大家都没觉脸上臊,只觉得很干净,很亲密,因为那是换命的交情啊!
岳父说得动了感情,连眼窝都红了。岳母塞过去毛巾,嘴巴啧啧着,说看看,老小孩了不是。这些话以前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说呀?岳父说,怎么没说,哪次战友们来信或寄来贺年片,我没给你看呀!岳母问,那孙二妹跟你贴脸时,没跟你说了什么?岳父说,说啦,当然说啦。她说倔驴子的性子只可跟美国佬撒,可千万不能跟未来的嫂子撒。你想想看,这辈子,我跟你撒过倔脾气吗?岳母笑起来,说也没少撒,只是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
岳父回忆起战火中的情谊,虽感人,却难推启我那扇还郁闷着的沉重心扉。他是在抚慰我,还是在变相地支持着他女儿的歪理邪说?他说的是“发乎情,止乎礼”,可我跟秦国春,却只是一般的相识,连模样都模糊着,哪里就到了止乎礼的地步!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连老爷子都认定我和那位乐施好善的女子有着不同凡响的情感历程,我这理还上哪儿讲去!冤比窦娥啊!
好在那天我回家门,妻子已备齐了两菜一汤,坐在桌前跟我共进晚餐,夜里,也不请自归地与我同卧一榻。我乐得借坡下驴,也就不再计较岳父或岳母跟她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了。
说话间过完了年,又过了正月。我再次给秦国春打去电话,想催她早日成行计划中的旅行。未想,接电话的人说,小秦调走了,是跟先生随军调转的。我问能否将她新的联系电话告诉我,对方说,她去的是保密单位,走时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说等她有了合适的联系方式时,自会告知昔日的朋友。
我算是她的朋友吗?如果可以滥竽充数,那调转工作这么大的事情她为什么都没告诉我一声?我心里满是失落和沮丧,再去岳父家时,便把这事说了。岳父责怪我,说那也要怪你办事拖沓。你也是有年假的,不会专程跑一趟郑州呀?心疼车脚钱,我出。我嘟哝说,哪是钱的事。别忘了,我家里还有个天下第一歪呢,谁知我一走,你们的宝贝闺女又能歪出什么花花样来。
生活中的这段插曲,有快乐和感动,也有郁结和落寞,似乎到此就可以画个休止符了。我好像白拣了个便宜,尽管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类便宜不仅一点不感兴趣,而且还只觉堵,堵得胸闷气短。我只盼着哪一天,秦国春会突然打来电话,说已在奔东北的途中,或者告知她新的联系方式。
但没有,一切都没有,宛若黄鹤凌空,一去无痕。直到又一年的岁末,我才突然收到一张贺年片,上面的所有字迹都是电脑打的,内容倒也简洁,只有“新年快乐”四字,落款则是“上海 秦国春”。原来是调到了上海,果然是保密单位,连具体名称都没留,我就是想回复一下都难了。
以后数年,每到年底,我都会收到一片那样的贺年片。小有不同的只是贺年片上的生肖邮票依年而变,由鼠而牛,再虎再兔,让我只知秦国春仍在上海,却无从觅踪。到了上世纪的最后那年,上海的秦国春变成了深圳的秦国春,仍是年复一年,一年一片。数年后,邮寄地址又变成了北京。我心里先是存着企盼,一年又一年的,后来,那份企盼便如星星之火,不熄不灭,存留着,积攒着,竟至变了熠熠欲发的窝火和怨忿。这算什么嘛,你明明知道我欠着你一份情谊和债务,就应该给我一个回报的机会,或者把通信地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起码让我先把欠下的那份钱款先寄还给你,哪怕加上通胀的因素,我十倍奉还也心甘情愿。可你这般隐身闹市,却一年又一年不厌其烦地用贺年片祝福我提醒我,这不是折磨人吗!我知道这样想有点不近情理,甚至映衬了我内心深处的灰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许,秦国春几番变动的单位真的是严格保密不可泄露,也许她确是早把那几百元钱忘在了脑后,或者一直期盼着我们还有在东北重逢的一天。我也知情义无价的道理,但凡事皆有度,物极则反,这种事放在你身上试试,换了谁,可能也免不了暗窝邪火吧?
几年前,岳母辞世,岳父由大舅哥接到了大连。大连海天开阔,冬暖夏凉,正宜颐养天年。未想,岳父大人去年也走了,走得挺急,是心梗。我和妻子赶到时,已是阴阳两世,连句话都没说上。今年入冬时,我和妻子再去大连,为老人祭周年。亲友们散去后,大舅哥对我说,老爸在世时,几次跟我提起去河南的事,念念不忘你的朋友帮忙。我在整理老爸的遗物时,看到一封信,也许跟你有关,就交你留个念想吧。
河南犟毛驴好,见字如晤!
我们都老了,有些人已去和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老战友们重聚了。正如你的来信所言,我们这些活着的老战友什么时候能再聚一聚呀,真是聚一次少一次啦。可也是怪,咱们都八十多岁了,一辈子走过那么多的地方,经历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老了老了,为什么偏偏在朝鲜战场上的那两三年间的人和事总是在梦里出现呢?
别怪我骂你,有事说事,老战友照办就是,不就是一年一张贺年片吗,还寄钱来干什么,显摆你有钱呀!可又想,寄就寄来吧,我买酒喝,你老小子结婚、生子,抱孙子重孙子,那一次又一次的喜酒可都欠着我呢,哈哈。只是,老战友的杯子要是能碰一碰,那酒喝进嘴里才更有滋有味呢。
犟毛驴所嘱之事,老战友非常理解,也完全支持。其实,在你来信之前,孙二妹已给我来过信,托嘱的也是这个事,那封信是她弥留之际让她闺女代笔写给我的。她先是在上海,后来又随女儿去了深圳,对你所托之事一直不敢有忘,临终之时再托嘱给我,我哪敢不放在心上呀。我现在是随着儿子住北京,脑子虽清醒,腿脚却一年不如一年,不然,我就去大连看望你了。我想洞庭鲤子,我想孙二妹,我想犟毛驴呀!有时想起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情景,眼泪流出来,又忍不住咧嘴笑,真是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呀。
前些天孙子从部队回家休假,张口闭口战友战友的。我撇嘴讥他,说你们那算什么战友,充其量是室友、营友。真正的战友得是一块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有着可以换命的情义,你们有吗?
祝河南犟毛驴身体康健,长命百岁!
陕北李逵
侄辈小李逵 代笔
2010年10月26日
我大惊,想起家中书橱内那厚厚一摞单独存放在一起的署名秦国春的贺年片,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似乎一切都已昭白天下,可其中的深层次意蕴却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我敬爱的老岳父通过贺年片委婉提示给我的,不会仅仅是不要忘了奉还友人的那几百元的票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