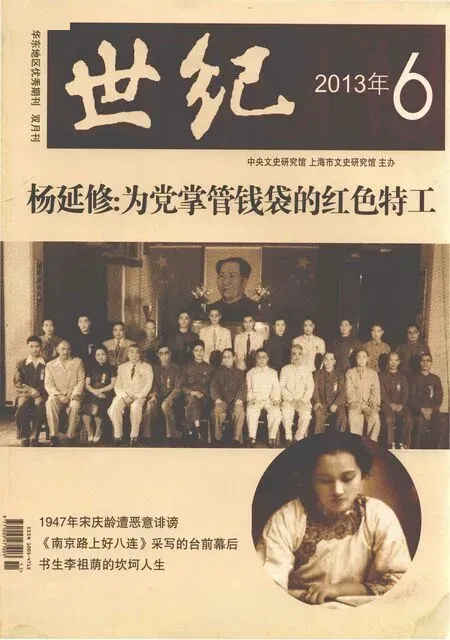“四边”方略——笑谈之十六
陈四益
按说,在大学读书时,也没少下过工厂。上钢五厂、上海柴油机厂都去过,每次不少于半个月,但都是去参加劳动,打打小工。回来需要汇报的是学到了哪些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对工厂组织、生产设备、动力系统、工艺流程以及产品销售等等,全不在意。所以,尽管耗费了不少时日,工厂内情如何,依旧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一味按报刊上的调子大唱颂歌。
到了1972年,离开干校,来到湖南省临湘县云溪镇,成了一家部队化工厂的一员,情况就不同了。当初听到关于这家工厂的介绍,说是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完全现代化,坐火车上下班,闻之神往。不料到得那里,不过是山沟一片。一条大山沟进去,又分出许多小沟岔,各条沟岔编了号,里边要建一座厂。譬如,2号沟是02厂,将来生产锦纶;三号沟是03厂,将来生产涤纶;4号沟5号沟分别是腈纶厂和橡胶厂。此外,当然还有电厂、水厂、机修厂、物资总库、运输大队以及医院、研究所等等。
这样矮而浅的山沟,于战备其实全无意义,不要说精准的制导导弹,就是普通的轰炸机,那小山沟也无能遮拦,但因为是在人迹稀少的山沟里,远离城市,所以所有公用设施都要自建,连商店、电影队、文工团、中学、小学、托儿所都得自办。耗费之大,自不待言。我去之前的两三年,一直在搞基建,别说坐火车上下班,就是挖沟、填土、扛水泥、运钢筋、埋管线,也都是人拉肩扛。
“革命”的年代,多产的是革命口号: “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流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串一串,都表现着当年的豪情。若是遇到评选标兵模范,还要替他们编织豪言壮语。据先我来到的一位朋友说,当初他们为一位劳模“编写”“讲用稿”的时候,因为这位模范讷于言也不敏于辞,竟挤不出一句闪亮发光的语言。于是,几位“秀才”只能代劳。闭门造车,想了一整天,终于有人憋出一句“活一分钟就要绕红太阳转六十秒”——脑汁绞尽的秀才们不由大喜,于是,这句话就成了这位模范“讲用稿”的“核心语言”,广为流传。
云溪是个小站,火车一到,各种器材连夜抢运。为了埋管线又突击挖沟,挖好沟又突击回填。这样赶来赶去,看起来很快,但现场不及清理,许多建材、器材就这样被填在土下。百千年后,如果从这里发掘出大批工具、不锈钢管或成袋的水泥,一定会使考古家搔首踟蹰——不知这些东西当初为什么要埋在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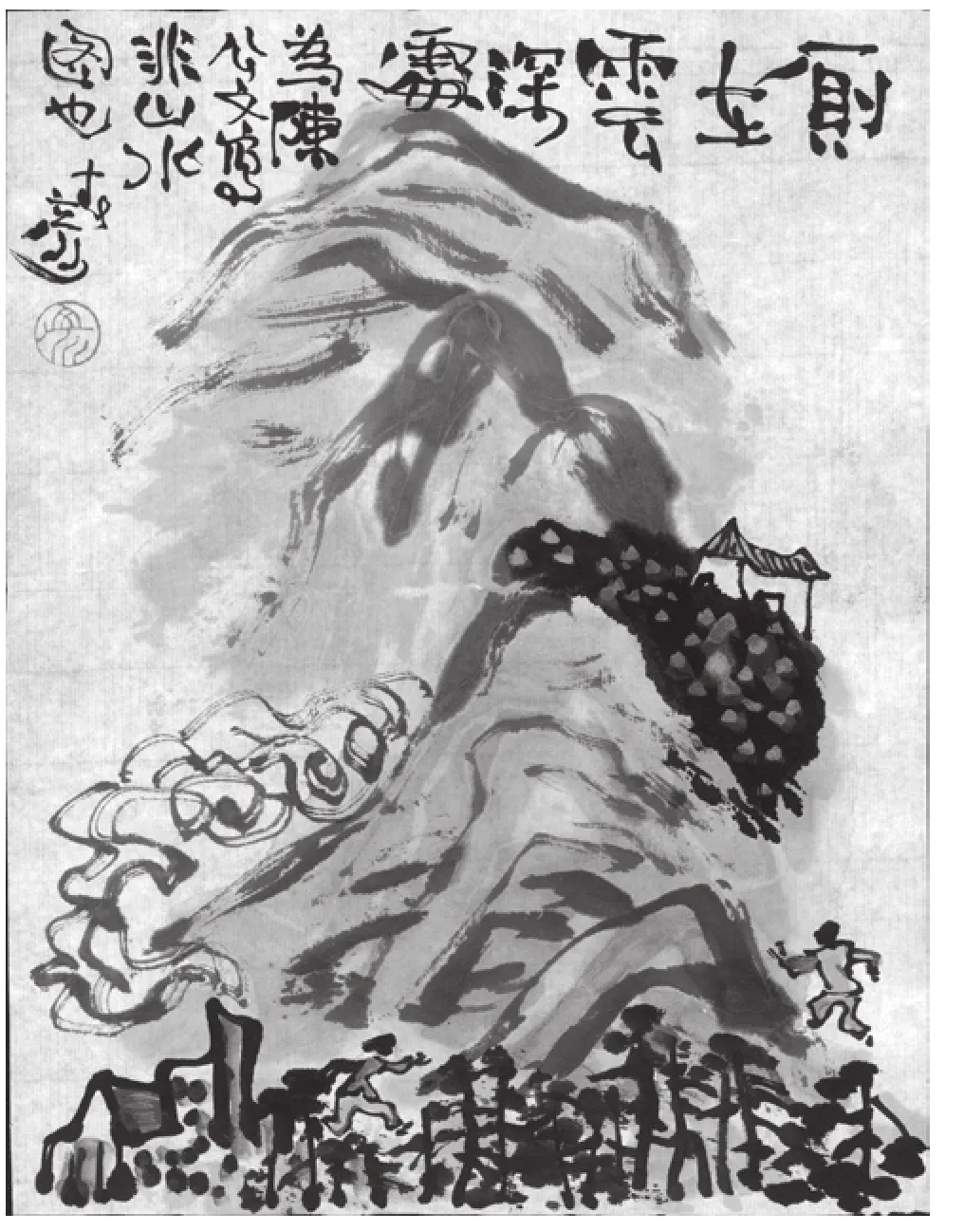
《厕在云深处》 谢春彦作
待到我去的时候,厂房已经竖起,设备也大体安装就绪,可就是无法正常运转,为了打通生产流程,就没完没了地“攻关”。起初我并不明白一个新建的厂,为什么就会问题成堆?后来渐渐明白,那时正值“革命”,什么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都要“敢想、敢说、敢干”,都要“打破常规”。前文说过炼油厂要把炼塔横过来塞进山洞里,即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一例。尽管失败了,仍旧“精神可嘉”,花点钱嘛,只当学费,不在话下。
在化工厂的建设中,也同样“豪气冲云霄”。为了争速度,抢时间,按时“让亲人解放军换装”,实行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投产”的“四边”方略。按照常规,生产工艺的设计,先要做小试,然后做放大实验,也叫中试,经过验证没有问题,才正式施工建设。所有工艺上的问题都应在前期解决,才不至造成浪费。但是这种科学的态度被当做“条条框框”,统统打破。结果,以涤纶厂为例,未经中试就直接建厂,弄得后患无穷。1972年我到这家工厂时,机器已经安装,但流程一直没有打通,不是这里堵,就是那里漏。日复一日的“攻关”弄得从厂领导到技术人员筋疲力竭,失去信心。一车间是氧化车间,车间主任是学化工的。氧化塔老是堵塞成了整个流程的第一个瓶颈,车间主任的压力当然很大。我们两家住在隔壁,看他那筋疲力尽的样子着实同情。一个个新的“攻关”方案带来希望,又带来失望。当又一个方案拿来时,这位主任丧气地说:“不管你是什么方案,反正你要留一个口,堵了我可以捅。”无奈的回答,成了失去信心的典型——自动化的生产线要靠人工来捅堵,岂非笑话!但谁也不敢明说这是前期盲目求快、不尊重科学带来的后患。这后患直到文革结束,依然不曾解决,虽也曾几次“报喜”,几番“验收”,但都是骗骗上头,通一点蒸汽,便说流程打通;把研究院实验室里做出的一点涤纶丝扎上红绸,便称献礼。到了工厂,我才开始知道许多“伟大的业绩”是怎么“造出来”的。
那是全国大学解放军的时代, 不曾料到就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工厂里,弄虚作假竟一样通行,而所谓用“革命精神”打破的条条框框,恰恰是“科学精神”。想要多,反得其少;想要快,反得其慢;想要好,反得其坏;想要省,反得其费。从这里,我开始悟到了“大跃进”、“总路线”失败的原因。“多快好省”何尝不好,但若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变定然要走向反面。及至大错铸就,又不思回到科学道路上来,反而误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愈趋愈远,终至不可收拾。
幸好后来发现,“的确良”(或称的确凉)并不适于制作军装。一来它透气不好,夏天穿,闷气。更为要命的是化纤制品一遇火星便会粘在肉上灼伤皮肤,所以后来并不催逼投产。到了1975年,这家部队企业整体交给了地方,部队干部统统撤离。以后又花了无限气力,才变成了现在的巴陵石化总厂。多少技术人员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如何让这家因“革命加拼命”弄到濒死的企业起死回生。
三处是纺织总厂,地处湖北蒲圻的山沟里。因为化工部分一直不能正常生产,依靠化工化纤原料的纺织厂自然无事可做。我曾去过那里,山下江边就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据说江边沙滩还可以捡到折戟断箭。山上的厂房虽已建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么闲置了一二十年。后来,我问起那里的情况,答曰:早已荒芜,只剩得断壁颓垣了。
荒唐的事还有许多:纺丝车间是一座7层厂房。原先设计图纸都有厕所。不知是哪一位领导在审查图纸时,大笔一挥,说车间里还修什么厕所?于是,在“革命化”的理由下,砍掉,把厕所建在了车间后面山坡上。纺丝车间大多是女工,上个厕所要从几层楼上跑下来,再跑到山坡上那个简易厕所,然后再跑下山坡,爬楼回到工岗。费工误事,遇到下雨,一路泥泞,更是苦不堪言。大家都在骂,可是谁也无法追究在“革命”旗号下的失误。
最早的一批职工宿舍,是在“学大庆”的口号下修建的。大庆的“干打垒”是学习的榜样。但大庆是在东北平原,多的是土,云溪山沟里却缺的是土。于是只好勉为其难,存其名而易其实,从山上采石建房。“石质干打垒”是建成了,石头之间用水泥灌接,结实美观,冬暖夏凉,但建造的成本比烧砖还贵。这才改弦更张,改用红砖砌房。那几栋“干打垒”成了“学大庆”的标本。
为了“学大庆”,还派出过赴大庆学习团。回来之后,台面上讲的当然都是“革命加拼命”、“三老四严”、“铁人精神”等“通用教材”,但私下里传的却是大庆的福利,多少个“不要钱”以及那时被当做“修正主义”的奖金之类“物质刺激”。于是,上面高喊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下面私议的口号却是要求“全面学大庆”。那年头,聪明的企业领导都在口头上高喊“学大庆”,而背地里却暗用奖金、福利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一味精神“挂帅”的呆子,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宣传部门总喜欢夸耀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其实离开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那些空对空的宣传全无实效。
这些笑谈在当时是不会也不能公然讲的,但却无法禁止人们的私议。我总奇怪,为什么明知假话却偏要大讲,而明知实情却偏要禁言。难道真有人以为重复假话就可以成为社会的直接现实?或许他们是太清楚社会的直接现实,因而企图用各种假话空话大话来涂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