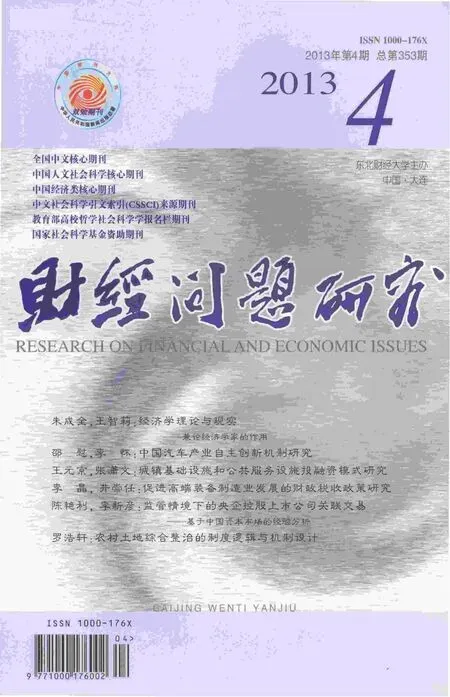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制度逻辑与机制设计
罗浩轩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各方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要对规则进行认知和内化,从而推动制度变迁[1]。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利益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和相互妥协的过程。许多已有的国外文献都论述了土地整治目标扩大的历史。如Van Huylenbroeck等指出,早期的土地整治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以整合碎片化的土地为手段来扩大农业生产。然而,这样的土地整治面临收益率低和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随着人们对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深入认识,土地整治逐渐成为包括实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多元化的工具。多元化的目的使整治规划和执行过程复杂化[2]。我国对土地整治的认识也有一个类似的认知路径。整治规划和执行过程复杂化也使得中央、地方和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一、我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
早期土地整治的主要对象是农用地、“四荒地”以及工矿废弃地,通过对它们的开发、整理和复垦,达到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土地资源利用结构、提高集约化水平和促进可持续利用的目的[3]。它内化了中央政府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粮食安全的要求,如199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中提出:“积极推进土地整理,搞好土地建设。”此时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决策的执行者。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利用计划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已经难以满足激增的土地需求。特别是2004年国家禁止了跨地区补充耕地的做法以后,各地开始通过内部的土地整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于是,土地整理的内涵已经从原来单纯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发展到对田、水、路、林和村的综合整治;其目的也由促进农业增产、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到为其他产业提供支撑;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开始从单纯的中央政府土地整理政策的执行者,向与中央政府、农民进行利益界定和协调的政策决策参与者转变。
地方政府在整治中的角色转变,源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发展战略是政府在大规模干预下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型战略[4]。自市场化和分权化以来,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目标的激励下,有着强烈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由于无法运用货币政策和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以补贴、减税等方式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这造成了长期以来以投资为主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利用计划的约束下,通过整治节约建设用地指标获取土地增值收益,除了能满足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求外,还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表1可以看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价款从2005年的0.55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1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3.8%。出让合同价款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影响出现波动,但都在30%以上,其中2010年和2011年的比重都在60%以上。

表1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价款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单位:万亿元
这里有必要指出人们观念中的误区,即政府的土地收入主要耗散于政府各个部门的福利、工资开支等纯粹的非生产性指出。周飞舟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出让金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补偿土地开发和转让成本,政府的土地净收益一般为20%左右。这部分净收益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用于弥补财政支出,以及诸如公益性用地、工业用地等难以产生收益的土地征收成本;另一个方面则是用来作为基本资产为城市建设融资[5]。赵德余也指出,土地收益并非耗散在各个部门的工资福利方面,而是政府实现其公共政策目标如公共设施建设需要的重要资源支持[6]。
二、关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选择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批评
Vitikainnen在考察欧洲国家的土地整理(Land Consolidation)时总结了土地整理的四个目标:一是通过土地集并和灌溉的改进,促进农业和林业的发展;二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三是保持动植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四是通过土地节约满足其他的用地需求[7]。我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也存在多重目标,包括促进耕地保护和集约用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时尽管都含有上述多重目标,但侧重点不同。中央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希望通过整治保护耕地的数量、确保粮食安全。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整治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开发建设的资金。农民的目标符合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首先是通过农用地整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促进自己的务农收入提高;其次是通过村庄整治为自身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最后是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的利益。
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整治应侧重哪一方的目标和利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首先,整治过程中农民利益保护是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目标,必须保障农民利益。由于农民利益保护往往集中于整治过程中的征地补偿环节,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建议。例如,周其仁认为,通过还权赋能,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真正还给农民;成都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保障了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利益,“同地同权”是未来发展趋势[8]。陈家泽将产权对价理论引入,提出农户财产性权利的相对价格形成机制是对农户的最终激励,是“唯一正确的激励机制和效率基础”[9]。王华华和王尚银提出,要将当前法定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政策转变为以“保护”为原则的“社会补偿”政策,实现公平正义和城市化的和谐发展[10]。
其次,一些官员和学者始终强调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保护粮食安全。开展土地开发整理从根本上说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吴海洋指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破解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重要手段,可以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抵御灾害能力,保障粮食安全[11]。这种观点暗示:保障农业和农村发展是首要目标;通过整治满足土地需求,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往往是附带目标;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和自身利益,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6]。
再次,一些学者强调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该更加注重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协调,特别是在征地补偿环节中的利益协调。杨涛和施国庆认为,利益分配与保障机制的残缺是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政府应从制度和政策上加以保证和引导来协调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12]。刘润秋认为,多元主体的利益既有交集又有冲突,构成了一对矛盾统一体,而当前缺乏一种能够协调和平衡流转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安排[13]。
最后,学者们对地方政府在整治中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持批评态度。批评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批评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的规定和要求进行整治,如张曙光在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土地目标矛盾和利益博弈”的论述中指出,“地方政府和官员可以采取多种办法规避中央的行政控制和计划限制,使政策实施结果向自己一方倾斜”,“一个严重后果是农地转用的规模大大超过了计划控制和实际需要的规模”[14]。第二种是批评地方政府对待农民利益态度粗暴、不走程序,如王华华和王尚银指出,地方政府在执行以“保障”为原则的土地征收政策时,倾向于采取非民主的“强征”态度[10]。第三种是批评地方政府在整治中采用各种手段为自身攫取利益,如《京华时报》曾经报道,河北廊坊香河县从2008年以来,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旗号,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大规模“圈占”耕地[15]。
综上所述,国内已有关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文献中,对农民的利益最为关注,对农业增产、粮食安全的问题的关注次之,对地方政府则大多是批评。地方政府似乎成了公然违抗中央政策、侵害农民利益的“罪魁祸首”。一方面它通过采用各种“土对策”对付中央政府的要求和监督,与中央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未批先占,多占少补,占优补劣,甚至出现刷绿漆、挂绿网以“迷惑”国土部门卫星遥感的奇怪现象[16];另一方面它又粗暴对待农民利益,在城市化进程中剥夺农民利益:逼农民“上楼”,“集中”、强拆农房、强行改村变居。此外,它还不择手段谋求自身利益,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发财致富的好工具[17]。
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政策的统一性与执行的灵活性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一味指责地方政府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容易忽视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科层制组织形式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理性目标,但也可能演化成以自我生存为目标的生命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在整治中确实出现了“目标替代”(Goal Displacement),但一个长期稳定的组织离不开持续运行的组织制度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环境。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地方政府出现的“奇怪现象”是对现有组织的理性设计,是与当前制度环境适应的必然产物。我国政府体制是具有“职责同构”特点的庞大科层组织,地方政府的行为只是中央政府意志的延续。由于组织自身也存在有限理性的约束,因而与其说地方政府在执行决策时与中央政府和农民严重对立,不如说是对地方政府行政架构的理性设计与中央政府贯彻意志的模式相对立,从而造成整治中的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只有理解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才能“对症下药”,当前学界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完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对策建议,如对征地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顶层设计”以及经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才能找到合理的路径。
(一)中央政府关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相关政策的统一性
周雪光在关于基层地方政府“共谋现象”的探讨中,提出了组织制度存在的“政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悖论,为解释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行为逻辑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框架[18]。政策的统一性源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决策集权程度的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一旦做出,便通过各种渠道自上而下地传达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通过对决策的部署实施来回应中央。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这种政策的统一性表现为中央以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推动整治。中央的整治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政策正面推动整治。早在1997年,国家就提出:“积极推进土地整理,搞好土地建设”;在199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又指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此后,国家又相继制定了《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2001—2010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2001—2010年)》和《规划(2011—2015年)》)。特别是两个整治规划,明确了整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第二个层次是与整治相关的各类具体执行细则。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土地复垦条例》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第三个层次是与整治内容有交集的各类政策。这些政策既与整治互为目的和手段,又不局限于整治,同时还规制了整治的实施。这些政策包括“十二五”规划纲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全国新增1 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等。第四个层次是中央根据整治的实际状况出台一系列约束性政策,其目的是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差进行修正。例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关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的统一性意味着中央政府实施治理能力的强化,但其内容只能是指导性的,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地区的不同差异。
(二)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整治政策过程中的灵活性
1.中央政府预留了地方政府执行整治政策的灵活空间
中央政府在做决策时就考虑到了微观层面的差异性,于是有意为政策的执行预留了灵活性的空间。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这一类灵活性可以分为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国家和地方联合起来,根据地区特点制定整治方案,推动土地整治。例如,自2008年以来,国家联合地方相继实施了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宁夏中北部、黑龙江三江平原东部以及汶川灾后重建五大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这五个重大工程建设总规模为1 970万亩,新增耕地将达到770万亩。同时,总规模达1 360万亩,新增耕地约100多万亩的青海省东部黄河谷地百万亩土地开发整理、湖南省洞庭湖区基本农田建设、云南省“兴地睦边”农田整治、湖北省南水北调汉江沿线土地开发整理和河南省南水北调及沿线土地整治这五个重大工程也在审查和实施过程中。一种是允许各地政府自主制定或调整相应土地整治的细则。如成都市针对川西平原农村林盘式居住的特点,按照“连线成片、聚点成群”的思路,修编完成《川西林盘保护利用规划》,在此基础上推动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将一个个川西林盘打造成了乡村休闲旅游场所,实现第一、三产业互动。当前学界热议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方式,也是地方灵活性的体现。根据《规划(2011—2015年)》的要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仍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给予试验区“先试先行”的权利,积极探索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新模式。天津、成都和重庆等地纷纷开始了试点,天津市于2005年开始了“宅基地换房”;成都市通过对农民还权赋能,建立了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重庆市则将建设用地“证券化”,建立起了地票交易所。同时,全国多个省市开始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直接流转上市[19]。这些创新都没有脱离“占补平衡”原则和“增减挂钩”的政策框架,并得到了中央政府不同程度的认可。
2.地方政府根据自身需要对中央政府提供的整治任务相关资源进行转移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政府部署的某项任务,通过某种手段或渠道将另一项任务的资源转移到该项任务中。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以整治为名扩大建设用地指标数量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的资源进行转移。地方政府要实现经济增长,急需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建设用地指标的出让。上文的表1也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获得、出让建设用地指标的过程,也是地方政府将土地资源货币化为城市建设资金的过程。
从地方政府对整治的态度转变,也可以看到地方是如何在中央政策统一性下为实现自身目标灵活地转移资源的:周立群和张红星发现,地方政府热切关注土地整治始于2004年国家禁止跨区补充耕地以后。由于当时各地仍有建设用地指标,但土地后备资源不足,地方政府逐渐将目光转向通过土地整治获得“占补平衡”指标。然而,由于农地整治增加耕地的单位成本小于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推进工作更为细致、繁琐的村庄整治在当时并不利于地方政府转移资源满足己用,因而导致村庄整治进程缓慢。有关课题组的报告说明了这一事实:2005—2006年,在成都市金堂县栖贤乡向前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整治的新增耕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40%。随着城镇扩张,建设用地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都开始趋于紧张,中央政府诸多约束政策迫使地方政府只能寻找其他路径,如通过村庄整理可以同时获得上述两种指标。因此,“农村的建设用地开始用于实现更高的价值,这就形成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思路”[20]。
2010年,国务院在一份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文件(国发〔2010〕47号)中提出:“要明确受益主体,规范收益用途,确保所获土地增值收益及时全部返还农村,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防止农村和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在《规划(2011—2015年)》中也提出:“确保增减挂钩所获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返还农村”。但是,2010年和2011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均高于60%,这充分说明土地财政仍然难以遏制。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三个“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①2011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用三个“最严格”强调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约束下,地方转移土地资源用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势头如此强劲,甚至冒着不惜付出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的代价?这一切都源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
Qian和Weingast将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归结于中国式分权[21],而Blanchard和Shleifer在总结俄罗斯实施分权制并未取得经济增长的教训后,提出中国式分权取得成功还需要政治集权相配合,政治集权能够提供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中央确立以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能促进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22]。根据组织行为学,一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带有情感、利益的社会人,他们在执行指令过程中必然会将自己的认知、情感因素带入。地方官员在面对由中央下达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地方经济指标增长双重目标时,往往会倾向于与自己升迁有重大关系的后者。这里可以将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提出的双因素理论(Two Factors Theory)引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来加以解释。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仅仅是保障因素(Hygiene Factor),即如果地方政府无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则会引起中央政府强烈不满,相应官员甚至会受到降职处分;但在一定程度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以后,再进一步的努力却难以获得中央政府更高程度的认可。而经济增长指标则是激励因素(Motivative Factor),地方政府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地方官员就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提拔;相反,由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因复杂,即使经济未能实现中央预期的增长率,地方政府也可以对此加以解释,不会引起因粮食安全目标无法达到而被责难。
在整治过程中将本属于农业的资源用于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是不合理的,但从执行者及其直接上级甚至社会利益角度来看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在地方政府面临燃眉之急的任务却自身资源匮乏时,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情形在现实的基层政府司空见惯。例如,某地政府计划用1 000亩土地修建学校却苦于没有资金,许多地方政府一般会将其中的200亩土地作为商住用地开发出让,这样不仅能支付学校征地、开发和建设的成本,还能有节余用于其他地方的建设。如果当地政府严格按照土地规划办事,严格处理公益性土地转为商用地的行为,那么修建学校的计划只能搁置,其他建设也难以实现。
3.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有意歪曲中央政府相关整治决策
合理的中央政策因涉及到地方政府核心利益而被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通过灵活操作加以扭曲,同时地方政府还使用各种手段来规避政策制定者的督察,以此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比较常见的地方政府歪曲中央政策的方式有:
一是将中央或上级部门制定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整治政策流程肢解。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往往需要大量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并且整治周期较长。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顾中央或上级部门制定的流程。笔者在成都市S县调研时发现,S县国土部门早在2009年6月就将该县Z镇的土地以每亩9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了成都某开发商,对此当地的农民和外来业主却毫不知情。同年8月,Z镇政府却突然发出拆迁公告,以每亩土地仅2—4万不等的补偿要求农民迅速搬迁。在这个事件中,S县将成都市规定的“由集体和农户自主持立项批复挂牌”变成了由当地政府先挂牌出让,再通知农户;农村集体土地在未经农民集体和农户的2/3同意下由当地政府自行转变用途,征求农户意见完全沦为形式。
二是利用中央或上级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对耕地实行占优补劣。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占补平衡”要数量质量并举,并特别注重提高耕地质量。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地耕地数量、质量及其分布状况的统计十分复杂。部分地方政府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大量占用土地肥沃、灌溉条件优越的“熟地”,而补充的耕地大多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差的山区,造成占优补劣、耕地质量总体下降,特别是极个别地区的耕地反而由集中、连片且优质逐步向零散、零星且劣质转变。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复垦后的土地里夹杂着碎石和砖块,部分土地的厚度不符合耕作要求,甚至立交桥下的小块土地也被开垦出来,挂上牌作为被“补”耕地。
三是以变通或灵活的方式对突破土地征用制度的行为加以解释,实现土地利用的“非农化”。地方政府即使做出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超出土地规划或计划,都能以变通或灵活的方式加以解释。因此,尽管中央采取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农用地流转后的用途不得改变,但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非农化”的趋势。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农业劳动力“空心化”已成趋势[23],但每年农民个人建房占地仍在上升。这说明,农民在宅基地上盖房多占、超占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成为农地“非农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因与中央政府发生“目标冲突”造成了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政策的统一性与执行的灵活性既是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必要制度,又为这种激励不相容提供了目标替代的可能。上述的第一种灵活性是符合中央要求的,同时也是合理的;第二种灵活性尽管在中央看来不具备合理性,但从地方政府甚至社会利益角度来看可能是合理的;第三种灵活性无论从中央还是社会利益角度来看都是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目标替代主要是通过第二、三种灵活性实现。地方政府通过“基层共谋”和显示与中央一致的虚假偏好①根据“吉巴德-萨特斯维特的操纵定理”(Gibbard-Satterthwaite Theorem),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可以操纵最后结果以使自己得利。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利益,中央则通过《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复垦条例》等规章制度和加大目标激励强度来限制地方政府超过规定的灵活性。
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合作博弈的稳定性和激励相容问题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属于合作博弈。稳定性(Stability)和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对合作博弈情景进行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的关键。
第一,稳定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是可以支出自身资源获得收益的个体,且他们获得的收益可以相互传递(Transferable)。假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集合为N,即N={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他们之间可以单独行动或任意联合,其可能的组合集合一共包括5种组合方式,设S是他们的任意一种组合方式,则S⊆N。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为获得收益支出的成本分别为x中央、x地方和x农民,让x=(x中央,x地方,x农民)表示支出向量。设v(S)为组合S的产出盈余函数,则:

如果不等式(1)成立,那么联合S能够持续生产高于支出成本的盈余v(S),这就意味着配置方式并未达到稳定性。只有当任何联合不能再改进一种配置方式了,这种配置才达到了稳定性。即:

通过成都、重庆等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创新实践来看,不等式(1)仍然成立。以成都为例,成都市自2008年以来,通过“确权颁证”、“耕保基金”、“交易平台”、“担保公司”、“联建政策”和“直接上市”[24]六大创新,提高了各方参与整治的效率,农民从中获得了更高的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用地问题和资金问题,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目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合作博弈的一个特点是,任何合作的潜在利益矛盾,都可以通过缔约方式解决。成都市的六大创新可以看成基于博弈三方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而进行的缔约。然而,成都市的制度创新仍然没有结束,不等式(2)还远未实现。就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还处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阶段,挂钩半径和整治方式仍然受到严格限制。换言之,关于整治的博弈远未达到稳定。
第二,激励相容。如果表达自身偏好是一种占优策略,以至于所有的博弈参与者都能提供自身的偏好序列,那么这个机制就能实现激励相容。一个成功的激励相容机制将对表达虚假偏好的市场操控行为者给予负激励。然而,当前无论是中央、地方还是农民,都存在着表达虚假偏好的操控策略。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对于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是工具性的,并非自己真正的目的;同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第二种执行的灵活性往往持有模糊的态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于“公共利益”长期未能给予明确的界定。地方政府的第二、三种灵活性均是虚假偏好策略。很多学者都指出,农民也存在寻租行为,比如在征地前“抢种”、“抢建”以获得更多的赔偿,以及在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后毁约等,但总体来说农民仍是弱势群体,其行为有很大的被动性。激励相容问题往往与目标冲突有关,正是目标之间的激烈冲突,才导致了虚假偏好。
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机制设计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th和Peranson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中,市场的任意一方都难以通过操纵策略获得利益[25]。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要实现良性发展,必须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消除这种操控的可能,最终达到合作博弈的稳定性。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一个良好的机制需要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和激励问题,前者的目的是使经济活动参与者较少花费维持机制运行的信息传递成本;后者的目的是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关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激励机制的问题,前文已有论述;而整治高昂的信息成本则表现在:农用地流转市场匹配困难,大多数流转仍是以农户之间自行协商流转价格为主[26];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封闭运作,交易类似于双边垄断的市场结构,缺乏竞争力,定价也缺乏效率;土地复垦监测制度尚不完善;绝大部分地区缺乏关于整治信息公示的网络平台。对此,我们分别就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出建议,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机制设计
就减少信息成本而言,一是建立关于农用土地流转的中介信息服务平台,政府对中介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并以村为单位实行会员注册制,允许价格自由浮动。二是建立农村建设用地产权交易中心,在整村整治的原则上,允许集体自行挂牌转让,这不仅有利于价格发现,也是缓解地方与农民利益冲突的缔约方式。三是加快土地整治信息化建设,建立土地复垦监测数据库和信息公示网络平台,便于群众监督。
就建设激励机制而言,一是加大对保护耕地的补贴力度,特别是要重视对耕地非商品性产出的补贴,注重耕地数量和质量并重。二是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整治。它不仅能够打破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垄断,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27]。三是修改税制,通过“赋权换税收”,使政府的土地收入由一次性出让收入转变为多年的财产税收入[28],降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政府投资的金融风险。四是前述的农村建设用地产权交易中心,也是激励农民参与整治的设计。
[1]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Van Huylenbroeck,G.,Coelho,J.C.,Pinto,P.A.Evaluation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LCPs):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6,12(3):297.
[3]鹿心社.论中国土地整理的总体方略[J].农业工程学报,2002,18(1).
[4]常志霄.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战略、增长模式与政府功能[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59.
[5]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1):62,69.
[6]赵德余.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互动[J].社会学研究,2009,(2):109,126.
[7]Vitikainen,A.An Overview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Europe[J].Nordic Journal of Surveying and Real Estate Research,2004,(1):29.
[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践的调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
[9]陈家泽.产权对价与资本形成: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以成都试验区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2011,(4):98.
[10]王华华,王尚银.中国土地征收政策社会公正化:由保障到保护[J].理论与改革,2012,(3):53,52.
[11]吴海洋.农村土地整治:助推农业现代化[J].求是,2012,(7):51.
[12]杨涛,施国庆.建设征地中相关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探析[J].农村经济,2006,(2):19.
[13]刘润秋.利益协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J].人民论坛,2012,(2):27-29.
[14]张曙光.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3.
[15]香河圈占耕地高价卖给开发商[N].京华时报,2011-05-19.
[16]陈谊娜,李松,徐旭忠.“增减挂钩”变形记[J].瞭望,2010,(11):26.
[17]吴国清.“土地财政”还能维持多久[D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4/01/c_1211807.htm,2010.4.
[18]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1-20.
[19]潘莹,刘瑶,卢炳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立法现状及展望[J].法制与社会,2012,(12):211.
[20]周立群,张红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J].南京社会科学,2011,(8):73-75.
[21]Qian,Y.,Weingast,B.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Chinese Style[J].Journal of Policy Reform,1996,1(2):149-185.
[22]Blanchard,O.,Shleifer,A.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J].IMF Staff Papers,2001,48(4):171-179.
[23]王国敏,罗浩轩.中国农业劳动力从“内卷化”向“空心化”转换研究[J].探索,2012,(2):93.
[24]黄宝连,黄祖辉,顾益康,王丽娟.产权视角下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研究——以成都为例[J].经济学家,2012,(3):70-72.
[25]Roth,A.E.,Peranson,E.The Redesign of the Matching Market for American Physicians:Some Engineering Aspects of Economic Desig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4):762-763.
[26]朱述斌,申云,石成玉.农地流转市场中介平台与定价机制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3):41.
[27]周生春,汪杰贵.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2012,(3):111-121.
[2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12,(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