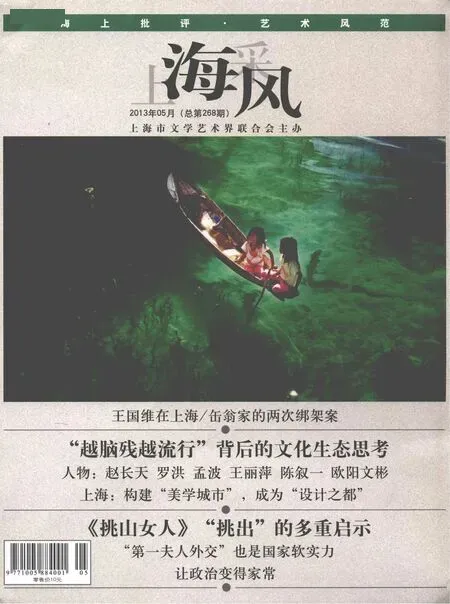春天的三个瞬间
文/影 子
壹
三月抵达了塞维利亚。拜伦勋爵说,一座有趣的城市,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没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拜伦说的乃是塞维利亚,他为这“天堂下面西班牙最辉煌”的塞维利亚创造了唐璜,也创造了他自己。
谁都会热爱塞维利亚,那是一个河岸边长着高大的棕榈树、满街挂满黄橙橙的鲜橘、有着摩尔人的宫殿、日尔曼人的教堂和罗马人巷陌的混血热情的城市。普通的市井多是些小小庭院,历经2000年斑驳侵蚀,幽深依旧是北非阿拉伯遗风。用鹅卵石和碎瓷片铺成色彩繁复的硬地面,四周是地中海日光直射下格外雪白的墙。拉丁人是那么喜欢花,天地狭小怎么办?他们把花种在陶盆里,挂在白墙上,衔在卡门的嘴角,栽在命运里。大多是些十腊红,紫丁香,粉月桂,满园红花,大丛绿叶,直白简单的表述,只浓不淡的审美,非常的卡斯蒂利亚。墙角转弯处的铸铁栏杆上随意挂着镌刻民间诗句的木牌:
卡门跳着舞,
在塞维利亚的大街上。
她已头发斑白,
但双眸明亮,
哦,孩子们,
请拉开帷幕。
塞维利亚的帷幕被拉开,在街道上走着就仿佛是在石台上起舞。阳光热辣,碧血黄沙,激情狂野,忧伤哀怨,像每一个弗拉明戈舞者,虽风情万种,媚态横生,但决不是柔和的慢板,是充满了悲情又决绝得昂然。五百年前,两百年前,许许多多的塞维利亚人就这样在街上走着,虽内心挣扎,可还是有人决定了远行,离开塞维利亚,去新大陆,或更遥远的未触摸的陆地,东方,其中就有我的祖先。
在塞维利亚老城,Manuel Rojias Marcos街3号是一座由民居改造而成的弗拉明戈舞蹈博物馆,这处我祖先出生居住的典型的安达卢西亚院落将在五月成为地球上第一个“中国友好城市”——塞维利亚的中国文化中心,开幕的第一个展览是“弗拉明戈在上海”,在塞维利亚,在上海。
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从院子的露台上都可以眺望到标志着信仰的希拉尔达塔,塔下的塞维利亚大教堂里安葬着哥伦布的棺椁,由四位大航海时代的国王的雕像抬着,代表了西班牙最早的四个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纳瓦拉和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手持一个长矛,长矛上穿着熟透的石榴,表达广袤的人类族群对哥伦布的敬意。
1492年,历经十年困战,伊莎贝拉攻克下摩尔人在西班牙最后的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她答应见一位等待了好多年的叫哥伦布的年轻人,女王听说了他与众不同的荒唐的探险计划——向西航行,到遍地黄金的亚洲去,印度,中国。女王说,人们都说西面的大海是不可逾越的。哥伦布说:“那么他们以前是怎么说格拉纳达的呢?说它是不可征服的……”一个月后哥伦布告别塞维利亚出海去。塞维利亚,哥伦布写道,是安达卢西亚的瑰宝,也将是世界的近邻。
贰
为八月初要在江滨梦工厂上演的音乐剧《彼得·潘》回到上海。季风书园已经从老地方搬走了。从前住茂名坊的时候,经常在礼拜六下午从一号线底下穿过去找店主小宝喝咖啡,顺便买书。有一次他指着店里满坑满谷的书说,这里百分之八十五的书都是垃圾,而每一次他好像都是刚刚从某个国家旅行归来,所以也常讲,别处的一切细节都是对的,哪怕是街边的垃圾桶等等,言下之意……
在季风买最后一本书是在今年二月,美国人刘香成和英国人凯伦·史密斯编的《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Shanghai: A History in Photographs),然后就去了西班牙旅行演出,最后把书留在了西班牙老城科尔多瓦Teatro Gongora的化妆间里。
印象深刻的是封面。苏珊·桑塔格说,图片的力量是你过后去看才能感觉到的。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一家人开着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微型轿车在上海街头春光明媚的下午,远处是八十年代都还常见的公交车和公交上盯着可疑小轿车的一群“蓝蚂蚁”。画面很阳光,构图很经典,但情调似乎又很荒唐,我喜欢这种纠结的场面,像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里说的,“那不仅仅是恐怖的年代,也是抒情的年代,我们应该为它作证”。
现在我从一号线陕西南路口爬出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法国梧桐,春日的阳光和即将在高楼背后展开的我熟悉却走不完的弄堂,撒落的阳光激荡着慵懒的灰尘,怀念的时光就这样奔腾而去。
上海的肖像,肯定不是一个封面,而是一个历史长卷,一个半世纪的风云光影,中国近代史的潮起潮落,国家和民众关于繁荣、先进、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努力浓缩在这座海边的壮丽大城。这座大城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时刻,战争、逃亡、投机和革命,瑰丽也阴郁。
有时你会惊觉,这座人们习惯性幻想中的欲望城市和她的上流社会是不存在的。其实天生就没有土著的贵族,没有可以求索的谱系,最大的奇迹都是外来的不知背景的,因此所有的故事都是没头没尾的,没头的故事又总是特别的刺激。
这个春天,城市失去了站在原点上的季风、汉源、会讲故事的作家、还有诗人,我的朋友们。但我们仍然阅读上海,于是,我们能看到钱钟书笔下,作为“暴发户上海的冷漠和卑俗本色”。张爱玲眼里,上海人趋炎附势,浑水摸鱼,但也可爱的真切人性,无论战争的阴霾和历史的创伤,人们看不见大历史的洪流尘烟,永不褪色的只有王安忆口中上海弄堂里的流言:“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
叁
自从Central Perk的名字被上海M5的一家咖啡馆抢占,我和三个朋友在798新开的咖啡馆就一直处在“沽名钓誉”的边缘,Miss Shanghai,你以为我会坚持这个名字,不,想一想,这可是在北京!
其实也并不在意讨好来客,此间咖啡馆的起因是四个朋友各自有一款收藏癖,A的vintage铁皮罐,B的art Deco台灯,C的Renaissance靠背椅,D的比利时虹吸壶,经年累月、丧心病狂的攒哪,吞噬掉时间与空间,茫然的生存皆指向一个无奈且氲氤的终点——咖啡馆,甚至连喝咖啡的人都不缺,这几个都是一天四杯以上的coffee worm,那就开吧,在一栋厂房的三楼。
四月,再次去博鳌亚洲论坛演出,观众席里坐着比尔·盖茨和索罗斯。坐在灯塔酒吧的阳光里翻墙爬进油管,看到的第一段视频是关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Frank Schubert,美国最后一个守灯塔的人。
他去世时93岁,守灯塔守了71年。守灯塔是多么浪漫的工作,只是没多少人真的肯做。枯燥啊,但也不见得,他守的是纽约的灯塔,见证所有轮船出入这个港口。他是个又瘦又高、面相斯文的人,当然有教养,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读了无数本书,他从来没放过一天的假,他说,“我不要退休,我太爱海了,我太爱我的工作了”。可是爱海的人可以当水手,当渔夫,这些工作都是动的;如果爱静,有什么好过守灯塔的人呢?
灯塔由燃油到用电,一切自动化了,但那耀目的灯泡坏掉了还是需要人来换。不过当今有超大的GPS导航,灯塔只是明信片里的背景。
站在舞台上,被千万盏灯光照耀和死守着一盏灯,都同样要过。人生,看你如何选择和被命运安排罢了。
Frank说:“我每天看灿烂的黎明和日落,背后还有无数曼哈顿的灯火,一生何求!”
咖啡馆于是起名作Soloist,Café Soloist,独自歌唱,那是16年前我唱过的第一首自己写的歌。《独自歌唱》的录影带在外滩滇池路一带的每个街角取景。清晨,空气中已隐约飘散着煎炸物同劣质咖啡混合的烟尘气。唱歌的女孩在薄雾中由远及近地走动,两个滑板少年在镜头里悠进荡出,等所有的音符都失了,背景由虚渐实。一艘白色的大船在两幢古老的大楼中间缓缓平移,仿佛是被装台工人推着、在中山东路上独自行驶的一件逼真的道具,而再远处的水上隐约可见的,是想象中远方的灯塔。
上海,如果你还记得,欢迎在这个春天到北京来喝一杯同这个场景和记忆相关的soloist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