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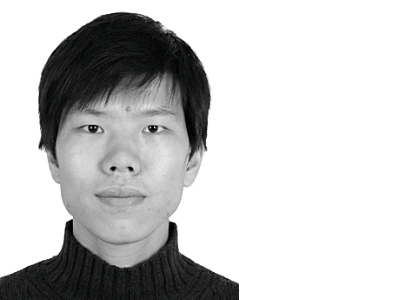
◤这座城市只比我们大十几岁,却委实衰老得太快了。
◤每当我意识到这是一颗外星球时,我就更能理解我的家乡。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发自冷水江市
坐在大巴车上,从长沙向南疾驰两百公里,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地图,当车窗外天空的颜色慢慢变灰,公路两旁房子的外墙依次变黑,树叶渐渐看不出绿色……我就知道,离家乡越来越近了。
这种气息是那么熟悉,就像你常年探望的一个重病患者,你的手搭在门把上时就能嗅到它。是的,欢迎你回来,欢迎回到冷水江星。
冷水江是湖南中部的一个县级市。看上去,它就像电影《小武》中的汾阳(更现代一点,但范儿差不多)。不过,我这说了也等于白说,因为我国大部分的小县城都长成这个德性。我真正要说的是,只有在这儿长大的人,比如我,才知道冷水江的秘密——它是一颗外星球。
每当我意识到这是一颗外星球时,我就更能理解我的家乡。我就能够顺着对它的爱与忧伤。
膨胀的城市,消失的城市
我一直担心,冷水江星有一天会突然消失。从大巴上下来,看到城市,“乌漆抹黑”的主题色保持得近乎完美,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和大部分城市的生长过程相比,冷水江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是一座小镇,本地人叫它“老鼠巷”,因为这里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又窄又短。
富饶的资源造就了冷水江。它的颜色——每一位来冷水江的外地朋友都会问我,冷水江为什么总是这么黑?因为这里产煤,每个月运煤车出城时漏下的煤灰,都以吨计。
冷水江别号“中南煤海”,城里一半土地下面都埋藏着煤炭资源。它还有一个更牛逼的标志,“世界锑都”。这里是世界上锑储量最多的城市。在过去的100年间,全世界有1/4的锑产自这里。
所以,“老鼠巷”想一直低调是不可能的。1969年,冷水江建市了。不提“工业建市”的背景,你只要玩过“帝国时代”或者“文明”之类的游戏,就能够理解在这么多资源的地方建个基地的合理性。
我的父亲原本跟随爷爷生活在隔壁新化县的另外一个镇,托冷水江发展的福气,高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冷水江市的机械分厂。要不然我和家父现在多半在乡下种田,或做着小生意吧。
高中毕业的12年来,我和一个外号“红薯”的同学,每次回到家乡,都会绕着市区走一圈。冷水江的市区不到十平方公里,比朝阳公园大不了多少,一晚上的功夫就能溜一遍。
就像一个仪式,我和红薯每次丈量这座城市,就像用手抚摸它的脸庞。这座城市只比我们大十几岁,却委实衰老得太快了。我们感受它现在的皱纹时,也追忆其过往美好的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我们的记忆里,这座城市发展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会冷水江市区虽小,但依山傍水,规划周正。图书馆、电影院、人民剧院、文化宫、青少年宫、儿童乐园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所幸拥有一个不错的童年。比如,在图书馆看《七龙珠》和《圣斗士》,在人民剧院看匹诺曹木偶戏,读小学每年六一儿童节排着队去儿童乐园坐小火车穿越假山……
那时候的冷水江颇有一种悠然的城市气度,不仅市政府会规划建造各种公共设施,各个厂矿学校里,这些公共设施也一应俱全。比如我后来所生活的钢铁总厂,厂区有文化宫,有灯光球场,有荷花池,有电影院和礼堂。我家那会就住在礼堂里的平房里,房子本身挺寒碜,可胜在礼堂景色宜人,有古树参天,有一个大操场,两个硕大无比的喷水池,夏天蝉噪时,常有附近的小孩儿扎在那儿捞蝌蚪。
这种悠然的气度是什么时候消失不见的呢?
以图书馆为例,它本来是一独栋,三层楼,每一层都有分门别类的藏书。1996年前后,我认识的字刚好够到可以去一楼的借书室借名著时,一楼被租给商户开成了一家内衣店;又过两年,二楼的阅览室成了一家网吧。不久,整栋楼给拆了,成了一家临街的商铺。
这是一个缩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有不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去处都渐渐消失了,电影院建了商品楼,人民剧院、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都建成了商铺。荷花池、球场、花园等绿化地带也甚难幸免。
现在,我和红薯年复一年绕着城市行走时,在黑夜里所经过的景色千篇一律,无非是厂房、商铺和民居的摩肩接踵。
忆及这个城市的起点,城市因为工厂的入驻和资源的开发,宛若一位瘦个姑娘得到了滋养,渐渐丰腴,出落得标致。问题在于,这姑娘的欲望没有就此停下来。她不停地饕餮了下去,吃相渐渐失态,面目也可憎起来。
“向钱看”几乎成了唯一的发展逻辑。城市创造经济利益的功能在不断强化,这几乎是它剩下的唯一功能。
在冷水江星,城市和工厂就像一对欢喜冤家。城市环绕工厂得以建立,工厂也因为城市的支持而生长。但这种发展不计后果地疯狂开展下去后,城市和工厂终于发现彼此成为了阻碍。
到了本世纪初,这种畸形的发展达到顶峰。在过去的40年间,冷水江用仅占湖南省千分之二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千分之十的经济总量。但代价是,市区内有八百多家工厂。你能想象一个朝阳公园里头塞八百多家工厂是什么概念吗?城市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
最终,城市的管理者们承认游戏玩崩了。“三废污染突出,城市功能不齐,绿化率偏低,车流拥堵,卫生难以整治……”2010年市委开会时对城市会诊后得出结论,决定推倒重来,计划在东边十公里处再造一座新的城市。
我对这座城市的现在已无多少留恋。从数据上来看,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水江便已有三十多万人口,现在仍然停留在这个数字。而每年过年聚会,老同学总是越来越少。举家迁往外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选择。冷水江星的衰竭和灭亡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
掏空的大闸蟹
如果停留在市区,你还只能看到冷水江星的表面。只有你到了“世界锑都”的所在地锡矿山,你才能见识真正的“冷水江星”。
2010年年底,我去过那儿。时值初冬,我站在山里,如同置身于外星——一个被黑乎乎的矿渣铺满的世界。
这里是比冷水江市先一步走到了尽头。民国四年(1915)冬,美国地质学家丁格兰(F.R.Tegengren)到锡矿山勘察,推算锑总储量达上百万吨。2009年时,冷水江市被国务院评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锡矿山的锑被估计仅能持续开采5年。掐指一算,今年过完,“世界锑都”就无锑可采了。
当然,它也出发得更早。早在1898年,这里就开始被大规模开采。在1914年时,由于一战爆发,锑价暴涨,“矿洞遍野,人群如蚁”。当时,锡矿山不仅有矿工十万,长沙、湘潭、益阳、邵阳等地的青楼班子也纷纷闻讯赶来这个穷乡僻壤,妓女多时达三百余名,蔚为大观。
俱往矣。现在锡矿山里,最常见到的是从漫山遍野的矿渣中钻出来的寒芒。寒芒常常被误认为是芦苇。它们看上去很像,区别在于芦苇要择水而生,寒芒则坚韧得多。除它以外,被严重污染的土壤里已经长不出任何其它的植被了。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茂密的寒芒发出灰白的光芒,层层叠叠,伴着呜咽的风声微微摆动,缓慢而不带生气。
在寒芒与矿渣之下,是进行着最后疯狂的矿洞。2010年我下井时,工人们正在开采矿柱。这是井下最后一部分锑矿,同时也像顶梁柱一样承载着地表的重量。
此时的锡矿山,就像一只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大闸蟹,从外面看挺饱满,可是里面全掏空了。矿柱越挖越细,坍塌因此常常发生。2004年4月的一个半夜,轰隆一声巨响,肖家岭附近甚至有一整座山都塌没了。而在宝大兴地区,矿洞顶板距地表最薄处仅0.6米,仿佛一块薄冰,随时有山崩地陷的危险。
政府不得不组织矿区上万居民移民,而尚未迁出的居民区也随处可见“此处沉陷,注意安全”的标识牌。
山里零星点缀着几栋房子,经年累月地被熏成了黑色。我在半山腰的一排房子前,遇见了一个正在筛矿渣的男子。他把买来的矿渣倒在筛车里,前后摇动约15次,细细的锑矿从筛网里慢慢漏下,最后他将筛车奋力向前一倾,把废渣倒掉,铲进新的矿渣。
这活计跟工地上筛沙子一模一样。我从小着迷于这道工序的韵律感,耐耐心心蹲在旁边看了一刻钟,看他重复了20遍,筛选出了有一袋大米那么多的锑矿,价值约五块钱。
他的妻子在不远的小溪边洗矿。那是对矿渣的另外一种利用方式——用水流和滤网对矿渣中的锑进行筛选。聊了一会后,他诚恳地说,老板,如果你有兴趣,投资个15万,我能帮你一年半回本。
聊天间,陆续有奔驰、宝马、保时捷等豪车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下。
近百年来,靠山吃山是这里最重要的逻辑。有钱的人开矿,有权的人入干股,普通人进厂当职工,也算有个铁饭碗。惨一点的,就只能从漏下的矿渣中讨一口饭吃了。人们不仅筛矿、洗矿,还常常在半夜挪开家里的衣柜,凿开一条坑道,去偷采国营矿井的锑矿。
民间集资潮
当冷水江星人对锡矿山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利用时,锡矿山也用另一种方式融入当地人的身体。那100万吨矿渣,在100年来融入雨水,渗进地表,进入当地人的历史和生活。
意识到锑是一种全球性的污染物与有毒金属元素,在全世界都是近几年的事。锑可以导致肝、皮肤、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方面的疾病,长期吸入锑粉和含锑烟雾,可引起“锑尘肺”和肺癌。更要命的是,锑与另外一种剧毒物质砷往往是共生关系。
大部分的当地人都不知道中科院曾于2009年在锡矿山做过一项实验。经调查,高达86.16%的当地居民体内砷含量达到了中毒标准,此外,该地居民的锑中毒、汞中毒比率也远高于正常水平。
在返乡之前,我知道家乡出了另外一件大事——近千家投资公司卷款潜逃,涉案金额近十亿,平摊下来,每个冷水江人搭进去了2000块。
这件事情和资源的衰竭互为表里。
2010年,全国科学发展与资源枯竭城市转型高峰论坛曾在冷水江召开,当着数个部委负责人的面,冷水江市政府表示要经济转型。
当时,冷水江市第二产业的比率达到70%,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大量投资煤矿、锑矿的钱进入投资公司。而这些资本经投资公司运作,大部分投向贵州的矿产开发。
这也算是靠山吃山的最终一种延续方式。而如后所示,游戏最终崩盘。
在冷水江星的衰竭故事中,我所知的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伤害。如果要问谁在这其中仍然活得滋润,我会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桌。他毕业后先是在一所学校挂职领空饷,接着去煤矿入了干股,最后开了一家投资公司,成为跑路老板中的一员。要问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本事,我只能默默地告诉你他爹是市领导。
所以,事发后,投资公司酿成危局时,政府宣布近千家投资公司“非法”,擦干净了屁股仿佛毫无干系,请原谅我无法相信。一如我无法相信政府再造一座“山水新城”的承诺,哪怕它在会议和蓝图上看起来是如此地美如画。
我曾在冷水江见过这样的一句口号——世界只有一个锑都。没错。我在这个世界也只有一个故乡。现在它们都要消失了。我不知道等到这一切真实上演时,我该去哪里凭吊我的它。我唯一的祝愿,是这个冷水江星球的故事,不要在地球上再发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