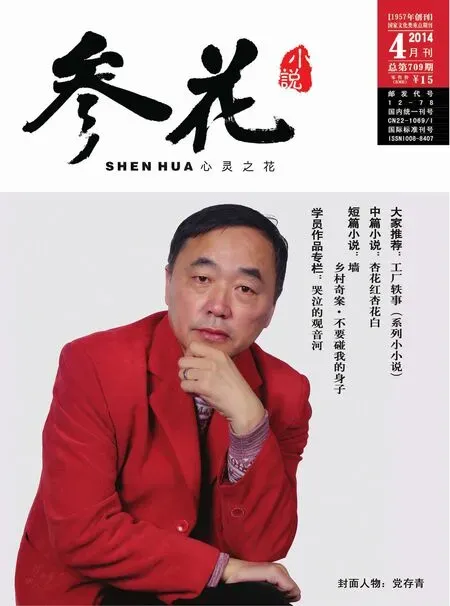乐景哀情:于永生处回望
——浅析萧红小说《小城三月》
◎孙雪松
乐景哀情:于永生处回望
——浅析萧红小说《小城三月》
◎孙雪松
短篇小说《小城三月》作为萧红最后的面世之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韵味。这位一生书写苦难的天才女作家,在她生命的绝笔处最后一次完成了对于时代症结的揭示、对于死亡的隐说、对于人性的叩问,也以宽容之心,完成了与世界的和解。
《小城三月》 萧红 小说
1941年7月1日刊于《时代文学》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是萧红得以面世的最后绝笔。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流亡香港。几经波折下萧红疾病缠身,在好友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住进玛丽医院。彼时萧红已日渐憔悴,言谈恳切,仿佛预言着不久将至的永世诀别。萧红就是在缠绵病榻之际完成了《小城三月》。虽然这并非萧红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然而却是这位笔耕十年的天才作家得以留传给世人的最后面影。而这篇已臻成熟的小说,也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韵味。
一、哀情:文化夹缝中的人之哀
《小城三月》讲述了一个简单到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故事:“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 这段“禁忌之恋”,在北国的三月里悄悄生长,又在女主人公那逃不出的心魔里,随她一同香消玉殒,郁郁而终了。这不仅仅是一出爱情的悲剧,更是一个站在新旧文化夹缝里,被时代抛弃的女人的挽歌。
女主人公翠姨是一个颇具古典气质的女子。她虽然长得并不十分漂亮,却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凤仪,待人接物又是极优雅的,而优雅之中又透露出一种闺中女子特有的娇羞与纤纤弱质。娴静、优雅、欲语还休,从外表上看,翠姨很好地诠释了东方传统女人的含蓄之美。这是与她那“大说大笑,不修边幅”的妹妹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也难怪“我”的伯父要戏称她为“林黛玉”了。翠姨不仅有黛玉的气质,也有着黛玉式的性格——含蓄矜持,自怜自卑。这样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行为方式:想求而不敢求。对于“绒绳鞋”翠姨便是如此,即使已经喜爱至极,翠姨也未告诉“我”急于上街去买的就是这“绒绳鞋”。或者是矜持使然,也或者是胆怯使然,总之翠姨从不敢说出自己对“绒绳鞋”至深的喜爱,最后只能在犹疑中痛失所爱。这何尝不是她与堂哥哥之间爱情的隐喻呢。翠姨的这种“想要而不敢”来自于与她气质一脉相承的文化牵绊。因为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女性是随意不能表达个人欲求的。这使她终生在个人欲求与怯懦自矜中困顿挣扎。
但是,这样一个继承着传统文化血脉的女子,所“求”的又恰恰是与传统文化完全背离的“新知”。翠姨没有与一味追求“现代流行”而全未开蒙的妹妹同流,也没有与彻底活在黑色的旧时代的堂妹妹为伍,而是更愿意同“我”亲近。她总是愿意问在学堂里念书的“我”的意见,羡慕着“我”的“博学”;愿意融入到“我”的维新家庭之中,与“我们”打网球、开音乐会、看花灯;喜欢穿西装的洋学生。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与这样的生活统一起来的堂哥哥。她对堂哥哥的爱恋,恰恰影射了她对于现代文明的憧憬。而这憧憬又是如此的无望。传统的思维方式、礼教、道德已经根深蒂固,破土而出,像是坚韧的藤蔓将翠姨紧紧缠绕。束缚住她的双脚让她无法逃离,捆绑住她的双手让她无法挣扎,紧掩上她的嘴让她无法呼救,只留下一双还向往着光明的双眼,要看着“哈尔滨的方向”。而那个方向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在,她只能在自卑中胆怯,唯沉默与眼泪在死亡中永生。
佛家讲究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恚、求不得。想要而得不到,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而萧红又赋予了它时空的维度,使它获得了历史的具体性。试想若翠姨是她那未经启蒙的妹妹,那也不过是在懵懂之中苟安一生;若是那早已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我”,则必然会勇敢出走追求真我。而翠姨不是妹妹,也不是“我”,她就是那一个,或者说那一群生活在时代的裂隙之中,遭受新旧文化冲击,而又被两种文化双双抛弃到边缘的女性。这又何尝不是萧红自身的写照呢。那一代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怎能不带有传统文化的旧疾。萧红成功地出逃了,但她仍逃脱不了身为女性必须要依附于男性的弱质心理。萧军是她的“拯救者”,而端木蕻良则是她的“牺牲者”。“传统文化心理不时冲破前卫思想,左右着新女性们的命运。” 这是萧红及那一代女性无法摆脱的心理症结。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挽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女性的墓志铭。
二、乐景:儿童视角下的景之乐
《小城三月》无疑是一个悲剧故事,但初读文本,却很容易在萧红营造的轻快氛围中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这不是个让人流泪的故事,却绝对是个让人掩卷怅惋的故事。
这种独特感受来自于作者独特的叙事视角的选择。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叙事,从而使文本充满作家主体声音的介入。而这个第一人称视角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便是“我”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女。这就决定了小说采用的叙述语态是天真无邪、稚气未脱的儿童口吻。儿童视角之下,明丽的色彩,轻快的节奏,真挚的感情全部跃然纸上。
小说充满了跳脱的色彩。三月的小城装满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城里人的披肩是蓝的、紫的、红的、绿的,最流行的是枣红的;盛大的婚礼上,女人们都穿着绣花大袄,有枣红的、绛色的、玫瑰紫的,上边绣着荷花、玫瑰、松竹梅,她们脸上都擦着白粉,嘴上都染得鲜红。大红、大绿、大紫造成的颜色对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了一派繁华的景象。
色之外是声的奏鸣。开在家里的音乐会时常乐声不断,笛子、箫、日本琴、风琴、月琴等等,声声不绝,就连十岁的弟弟也不成调地吹着口琴。这曲子不一定多悦耳,有时甚至多是“笛膜震抖得似乎就要爆裂了似的滋滋地叫着”的噪音,但大家都越按越快,越踏越快,直到气力没有了,大家才在大笑之中停了下来。
儿童视角为这个单色而悲伤的故事填充了轻松、明快的因子,让其缤纷、热闹起来。而翠姨正是在这一片繁华之中,在儿童懵懂的口吻中静默死去的。大喜与大悲的两级跨越,制造出一种情到极致的伤心。
然而以乐景衬哀情,绝不是萧红这样书写的唯一用意。这其中蕴含了萧红的死亡哲学。叔本华认为,苦难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生就是经历苦难的过程,而死亡将带来永生的平静。死亡不是人生之大悲痛,反而是一种结束与一种开始。就像尾声中的春天一样,它那么急匆匆地跑来,“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呵。’而后很快就跑过去了。”这样迅速而悄无声息地走过,消融的却是一整个冬天的朔方雪国。恰若死亡,轻而易举地带走人世间厚重的苦难。这其中体现的是萧红面向死亡的洒脱。
三、回顾:精神的乐土
《小城三月》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面世之作,深陷病痛的她时时预感着死亡的将至。众所周知,萧红一生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回望乡土的姿态,故乡是她精神的集散地。在萧红的人生绝笔之处,如此真实地以童年玩伴开姨作为原型创作的故事《小城三月》,成为了萧红能为人所见到的对其精神乐土的最后一次回望。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在回避痛苦。在压力之下,人们往往选择开启精神防御功能,深层潜意识里希望自己回到童年,像孩子一样生活。单纯、淳厚、倔强的萧红,在其早期创作中就已经展现出孩子般的气质。何况深陷病苦之时,更愿意逃避到那个安全温暖的精神栖居地之中。而在此时,那曾承载着萧红欢乐回忆,也勾连着萧红痛苦来源的“家”,已经渐渐褪去了冰冷的色彩。具有维新思想的父亲,宽厚而慈善的继母,家也是开明民主的所在。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萧红在人生将尽的时候,通过《小城三月》与世界彻底和解了。
而作为一个十年间都在书写苦难的作家,不可能仅赋予其作品以和解的意义。《小城三月》所承载的对于时代症结的揭示,对于死亡的隐说,对于人性的叩问或许可以算是对萧红那数十载红尘人世的不完整总结吧。
[1]萧红:《呼兰河传》,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
[2]季红真:《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1年。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雅楠)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