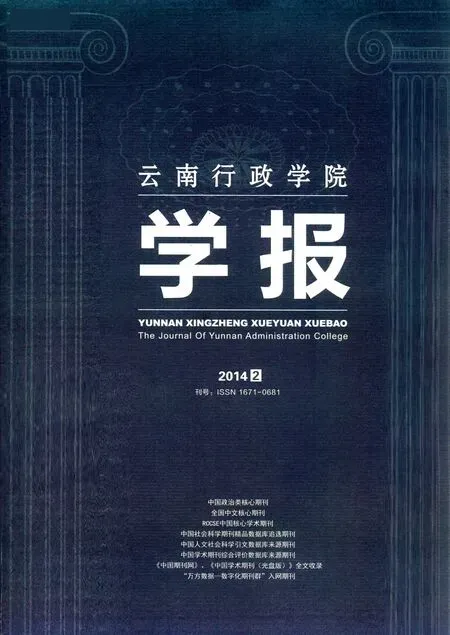康德与巴特在上帝观上的一致性
杨杰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云南昆明,650032)
康德与巴特在上帝观上的一致性
杨杰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云南昆明,650032)
康德的世界观不仅极大的影响了西方的哲学界,而且它也波及到神学界。巴特称上帝是“完全的他者”(the Wholly Other),是人所不能解释、不能跨越的客体。巴特走的是康德的“老路”——把上帝从认知领域“驱逐出境”,让上帝在道德领域“安家”。他们都相信上帝的本质具有不可知性,作为人无论透过什么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二人都把关于上帝的知识与人的认识能力割裂开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巴特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康德的“衣钵”。
康德;巴特;上帝;完全的他者;不可知性
康德(Immanuel Kant)是整个启蒙运动的高峰和发言人,他的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康德哲学的核心是自由,康德借助其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承认人的限制的同时,也宣扬人的自由意志。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人不在依赖自身以外的任何权威,乃是从自身的不成熟中释放出来。依此看来,“自主”就是启蒙的同义词,这就极大的加强了人对自主之信念的信心。康德的世界观不仅极大的影响了西方的哲学界,而且它也波及到神学界。
巴特(Karl Barth),被誉为“当代基督教之父”,他早年对《实践理性批判》充满兴趣,对巴特影响最深的神学教师,皆属于自由派神学(Liberalism)阵营。巴特因在1919年出版了他的神学宣言——《罗马书释义》从而蜚声神学界,“在基督教的神学界,掀起了有如哥白尼式的革命。”他的思想仿佛一阵旋风,极大的影响了20世纪的神学思考,承袭其思想的神学学派被称为“新正统派”(Neo—orthodoxy)。
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界,上帝经常被唯理论者“请出来”解释那些哲学里的“疑难杂症”。笛卡尔在解释天赋观念的由来和莱布尼茨在解释单子的“预定和谐”时,都“请上帝出来帮忙”。康德提出二元论的哲学之后,科学与信仰间的关系就尘埃落定了——“科学关乎知识,信仰关乎道德,两者互不搭界”的观点深入人心。人既然无法认识事物自身,所以也不可能认识上帝。康德的先验哲学已把上帝从人类中抽离出来,也把人从上帝那里抽离出来。”换言之,关于上帝的事,是无法被科学所证明的,所以是不合科学、不合理性和不合逻辑的。这就大大冲击了一些保守的基督徒的信念。
客观地说,后世的施莱尔马赫、自由派神学、巴特以及巴特主义者或多或少都受了康德二元论哲学的极大影响,不得不把传统的基督信仰一再“化妆”,以顺应理性时代的要求;可见康德哲学对现代、当代的神学思潮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康德把上帝归入本体界,上帝虽然不是完全被隔离,但康德留给上帝的空间实在是十分局促的——上帝与现象界的关系仅仅是:人在伦理世界中需要上帝。而巴特称上帝是“完全的他者”(the Wholly Other),是人所不能解释、不能跨越的客体。自康德之后,上帝在哲学界、神学界的地位都被颠覆了。康德的上帝观与巴特的上帝观,究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
一、康德:上帝是“自在之物”
要理解康德为何把上帝“放置”在本体界中,还得溯源到康德的先验哲学。其实,早在康德之前的休谟,就一针见血的提出两点批判:一是通过感觉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是或然的(经验论陷入困境);二是天赋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唯理论陷入困境)。明显地,康德受了休谟的启发,也看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各执己见”的最终结局——前者必然沦为怀疑论,后者必然导致独断论。康德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解答”休谟的疑问——其实是“把问题又丢给休谟,好像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康德的解决认识论的方式,是在近代哲学界来一场“大地震”(传统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巴特在二十世纪初也在神学界投了一枚引起轩然大波的“炸弹”一样。
康德认为,经验论忽略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唯理论与之相反,它夸大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实际上,人类的理性只是一种感性直观能力罢了,而没有理智的直观能力。这个结论让人亦喜亦忧:喜的是,经验质料进入感性直观能力时,是有秩序的,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通过知性范畴的参与就能形成知识了;忧的是,人只能认识事物对于我们的“表现”(Erscheinungen),并不能认识事物自身(或作“物自体”、“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一言以蔽之,人只能获得关于现象的知识,关于事物自身的知识,人是无法获取的。康德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的对象确定为现象,从而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接着,康德又坚持知性范畴只能在经验上使用而不能超验的用于物自体之上,这就在证明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同时,也证明了以往知识类型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
总之,康德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是没有资格成为科学的,思维与存在是截然对立的。人的认识止步于现象,至于现象之后的自在之物始终处在知识的彼岸。现象不是沟通思维与存在的桥梁,而是隔绝思维与存在的鸿沟。简言之,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能认识事物自身。
康德认为,理性的三个理念——灵魂、世界和上帝,是无法借助认识工具来认识的,毕竟知性的范畴只能限于经验界运用,若作超验的使用则不能形成科学知识。矛盾是理性的本质属性,只要理性企图去认识那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就必然会导致矛盾。人类理性穷根究底的本性,只是个“闹剧”(会导致“先验幻相”)而已,并没有什么实在意义。换言之,人的认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识理性的三个理念。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迫使知性范畴做超验的使用。因此,康德的结论是:形而上学的出路不在科学知识而在道德自由中。
二、巴特:上帝是“完全的他者”
巴特的神学是否直接深受康德的影响(巴特早年曾迷上康德),姑且不做辩解,但巴特神学初衷是对自由派的批判。大概在1911年前后,巴特开始反思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并渐渐地远离它,逐渐转移向宗教改革的神学思想,并下功夫研读圣经原典,后来他又批判了昔日他所崇敬的德国老师的思想。
巴特曾受教于哈纳克(Harnack)和何耳曼的门下,他们是当时自由派神学的砥柱中流。哈纳克否认耶稣的上帝性,而何耳曼直言圣经是有很多错误的一本书。一战时,他们摘下了神学面具,公开支持德国的侵略行动。与此同时,巴特也公开与老师们叫板,驳斥自由派神学。但有学者评论说,巴特是一种“新自由派”,他的思想内核与自由派的核心精神是如出一辙的,只是二者的表达形式不一样罢了。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十分公允的,并且自由派神学和巴特的上帝学明显有着康德世界观的“痕迹”,其表现如下:
第一,巴特对启示有了新的定义:启示是“从上垂直而下的”,是“上帝主动与人的相遇、会面和对话”,是本体界触碰到现象界,但本体界没有进入现象界。启蒙运动或者康德都呼吁人必须从任何一套权威或信仰中中解放出来,完全自主,所以人在检视历史时,也必须严守人之自主性。巴特继承了这类“历史批判法”,坚持“上帝不介入”的原则——上帝不会藉超自然的方式或启示来介入受造界。换言之,“上帝的话语”与圣经完全是两码事,即圣经不是信仰的权威,圣经是有谬误的。启示与圣经不能画上等号。“圣经是话语的见证,是记号,指引我们认识启示。上帝的话不是圣经本身,圣经的话语本身也不是启示……若将圣经等于上帝的话,就是将启示客观化、物质化。”
第二,巴特主张应当分清“历史事实”(Historie)和“历史意义”(Geschichet)。这种划分是随着不相信圣经之权威而来的,是最自然的一种过渡。康德把上帝“孤立”在本体界中,相当于区分了“现象界的耶稣”和“本体界的基督”。康德的信念与巴特的十分相似。巴特认为,“启示并没有进入到历史,启示只是触碰到历史,如同切线触及圆圈那样”。[1](p26)
换言之,巴特认为圣经记载的是否是真实发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本身对于当下的人类有何意义。与此同时,巴特也默认了圣经记载的历史事件是有错误的、无价值的,但圣经的教导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正如启蒙运运动时期的莱辛(G·E.Lessing, 1729—1871)所言:“任何宗教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历史,而在于藉着爱来改变生命的能力。”
第三,巴特宣称,上帝不是客体世界中的一位,上帝是具有“绝对超越性”的,深不可测的“完全的他者”。用巴特的话来说,“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用这个词在表达什么。谁有信仰,谁就知道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谁有信仰,谁就和约伯一样热爱位于无法探究的高处令人生畏的上帝,谁就和路德一样热爱隐形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
巴特认为,上帝永远是主体,绝不是客体,他是无限的、至高的。简言之,上帝是我们无法描述的一位上帝,上帝是“那位不可知者”(the unknown),因此,人不能直接的认识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一位……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必须对他表示敬畏。——这就是他比所有其他神祗高出一筹的地方,这就是他作为上帝、造物主和拯救者的特征。”
自由派的上帝是内涵在世界中的上帝,巴特反驳说,上帝是“完全的他者”;自由派主张把人放在上帝的地位上,巴特宣告:不要把上帝当作人,要把上帝当上帝。乍一观察,自由派与巴特的上帝观是分道扬镳的——毕竟,前者是将上帝世俗化,后者是将上帝神秘化,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其实不然,自由派与巴特都受了启蒙运动的“熏陶”,即以人本的方式来建构上帝观,而不是回归到圣经本身。因此,自由派与巴特走的是一条道。
最后,由于巴特主张上帝是“完全的他者”,就表明:人不能知道这位神是谁;又由于人类处在“有限”的范围内,所以人根本就不能得到真理或拥有真理或传递真理,充其量只能接近真理。
三、康德与巴特:上帝具有“不可知性”
下面我们有必要对康德是世界观和巴特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首先,康德的先验哲学影响其道德哲学。康德划分了现象界(Phenomenon)和本体界(Noumenon),现象界是经验之表象的总和,现象(Phaenomena)之外的不可知领域,即为本体(Noumena)。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划分,比拟为“楼下”(现象界)和“楼上”(本体界),楼下关于知识(认识领域),楼上关于道德(实践领域);前者关乎自然法则,后者关乎道德法则;前者是“知性为自然立法”,后者是“理性为自身立法”;前者关乎自然,后者关乎自由;前者是感觉世界,后者是理智世界,二者各司其职,各行其道,互不侵犯。楼上和楼下始终有着本质的不同。
康德宣称上帝“住在”楼上,所以只对人的道德领域产生影响,与人的认知无关。换言之,我们根本无法获得关于上帝的任何知识——上帝被隔离在知识之外。巴特宣称上帝具有主体性的地位,是完全超越、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言下之意是:有限的人根本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上帝——人类根本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的真貌。
康德哲学表明:不只在知识领域上上帝被隔离,就是在道德领域上帝也是悬设的。上帝被放置在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德福相配”。康德在实践领域里,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非理论性的证明,是出于“以福配德”的目的,好鼓励现世道德的需要,才假设了上帝的存在。笔者认为,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诚如康德所言“它是一种理不论证明”,因此,就理论上来说它并不可靠。“康德关于上帝的悬设,更多的不是出于自身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适应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的时代需求……自从康德进行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之后,上帝的立足之地就从外在的自然世界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世界。从此以后,上帝的存在不在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必要的;上帝存在的根据不再是理论的逻辑证明的逻辑证明,而是实践的道德要求。”
康德认为,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识水平与他的道德实践没有任何关系,把这个观点很自然的稍作升华,就得到一个结论——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无必然联系。前者关涉外在世界,后者关涉内在世界,二者是互不搭界的。信仰并不需要以认知为基础,也不可能以认知为基础。
其次,巴特的启示论也影响着他的道德观。由于巴特坚持上帝不会在历史中具体的启示自己,继而导致上帝具有完全不可知性的特性,其结果是:关于上帝的记载(即圣经)具有不真实性。换言之,上帝并不介入历史,因此圣经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不可靠,但圣经中道德教训却是弥足珍贵的。很显然,巴特走的是康德的“老路”——把上帝从认知领域“驱逐出境”,让上帝在道德领域安家。总而言之,知识上的相对性必然导致道德上的相对性,康德和巴特都面临着同样的张力。
综上所述,在上帝观上,施莱尔马赫、自由派神学家和巴特都继承了康德的世界观。巴特虽然宣称他反对自由派神学,但究其本质而言,他的上帝观与自由派神学的上帝观是无二致的。康德的上帝观与巴特的上帝观在关于如何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的层面上,也是如出一辙的,康德所宣称的正是是巴特所相信的。
巴特的上帝观与宗教改革、清教徒时期的上帝观是不一样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巴特的上帝观远远比康德的上帝观更接加近圣经中的上帝观。毕竟,巴特的上帝观具有神学性的特质,它是有一些“根”的——其中最主要的“根”就是圣经,尽管他不像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那般完全服膺于圣经的神圣权威,不过巴特也没有激进到把圣经完全抛弃。相较之下,康德的上帝观几乎可以说是“无根”的,康德的上帝观只是一个哲学上的理念罢了,几乎毫无实质内容可言,上帝根本就是被架空了。康德与巴特在上帝观上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相信上帝的本质具有不可知性,无论透过什么方式作为人,都不可能获得真正关于上帝的知识。从这个角度上讲,巴特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康德的“衣钵”。
康德与巴特,前者在哲学界,后者在神学界都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当传统的形而上学面临困境时,康德并不是“推一把”,使其尽早坍塌,而是指出形而上学的出路不在科学知识而在道德自由中;当自由派的上帝学冲击整个基督教思想界时,巴特一鸣惊人,驳斥“上帝活着世界中”的论调,提出“上帝就是上帝”的响亮宣言。
姑且勿论康德与巴特他们构建上帝观的动机如何,且就二人上帝观的思想本质而言,是相一致的——二人都把关于上帝的知识与人的认识能力割裂开了。
[1]简河培(Harvie M.Conn).认识现代神学[M].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
[2]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巴特.罗马书释义[M].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弗朗西斯·薛华.前车可鉴[M].梁祖永,梁寿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7]赵林.上帝与牛顿之间[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
[8]赵中辉.英汉神学名词词典(新增订版)[M].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0.
[9]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
(责任编辑 李保林)
D0-02
A
1671-0681(2014)02-0029-03
杨杰(1989-),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201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