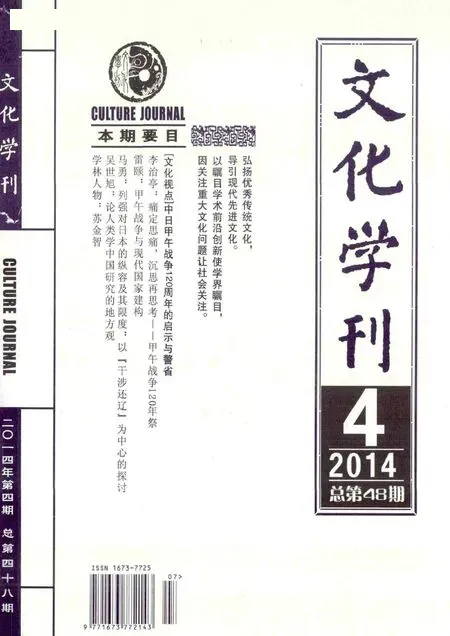傅斯年的东北研究
罗 杨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一、写作因由:书生救国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中如是开头。早在傅先生写作此书的三十年前,1901年,日本一些学者便在东京创立“黑龙会”,计划以黑龙江流域为主干,展开对中国大陆的争夺。1894年孙中山先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其创的兴中会誓词,恰为黑龙会在内的日本右翼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虽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推行“蒙、汉、满、藏、回”五族共和的新民族认同,但并未完全消除“满族中心论”,满、蒙等在日本和俄国的鼓动下,屡屡发起“复辟”和“独立”之类的行动。
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等列强为借口瓜分中国利益,发出“何谓中国 (支那)?”之问,认为中国本土和中国历史上行使宗主权的地方,应在会议决议中区别对待,日本为实现自身在东北的特权,更是鼓吹“中国疆域仅限于长①此部分写作幸得沈阳师范大学吴世旭老师推荐的叶碧苓:“九一八事迹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一文,它对我梳理傅斯年先生写作此书的背景是重要的参考材料。城以内十八省”。消息传回中国,梁启超先生随即在天津发表演说,以古代地理书籍《禹贡》中所载的“九州” “五服”等地域,力证东北自古便属中国之境。梁启超先生发表演说不久,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就在报上抛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他提出:支那不等于清,支那只等于汉民族的区域。满洲、蒙古和西藏这些边陲,是中国自古力所不逮之处;再者,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近成立了十余年的年轻国家,无权宣称继承包括蒙藏等边地在内的全部领土。矢野仁一这一主张后成为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思想基础,将满蒙视作应与中国分离,收入日本囊中的特殊区域。
1931年,日本发动傅斯年先生在引语中所谓的“沈阳之变”,即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请求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日本假意遵循国际联盟令其撤军的决议,加紧入侵中国,如傅斯年先生所言:“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1]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傅斯年先生等学者和学生在北平图书馆外集会,傅先生以“书生何以报国?”之问引起在场者共鸣。随后,傅斯年先生集合多位学者,共同撰写《东北史纲》,以驳斥日本的“满蒙非中国论”。当时预想是分别由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写作古代之东北、隋至元末之东北、明清之东北、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东北之外交。
当年底,国际联盟决定派出以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先后去往日本、上海和北平,敦促中日两国最终达成调解。当李顿调查团到达北平之后,以傅斯年、梅贻琦等学者主动出面招待调查团。当时,有三百多件关于187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调查呈交给调查团,其中便有李济先生从傅斯年、方壮猷和徐中舒先生合著的《东北史纲》中摘录并译成英文的材料Manchuria in History:A Summary。最终,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做出“满洲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满洲与中国的关系是恒久的、本质的”决议,并劝告日本将满洲归还中国。
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卷首中自叙,作此书目的有二:其一为驳日本满蒙论,他归纳了东北史上与中央王朝的四种关系,“就历史而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尊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仆臣,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2]而李顿调查团最后的决议,可谓实现了傅先生“书生救国”之志,尽管日本实质上并未就此止住侵吞东北之心。其目的二是傅先生深感国人对东北知识之寡陋。正如1937年也开始撰述《东北通史》的金毓黻在该书引言中说,“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在这个意义上,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开启了国内学者的东北研究。此外,《东北史纲》虽是傅斯年先生在“救国之志”下写就,但此书无不奠定了后来学者探究“何为中国”的眼光,如1934年顾颉刚先生创设“禹贡学会”,其学刊致力于研究中国境内中华民族之形成,可视作是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中观点的延续。
二、渤海两岸,源为一体
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共分五章,论述的历史时段从最远古至隋初,第一章对应上古时期,论渤海沿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的肇始;第二章主讲燕、秦、汉时的东北;第三章追溯两汉魏晋时期东北的郡县沿革史;第四章具体分析两汉魏晋时期东北的属部,最后一章则是汉晋间东北之大事。
为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本来之领土论”,傅斯年先生在第一章便要论证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傅先生考量上古文明之关系的眼光是以渤海黄海为中心,从而将东北与华北联系起来,说明渤海两岸,同为一家。他认为,环渤海黄海沿海,分布着几条大河,如流经河南、山东的济水与黄河,流经河北的滦河,流经辽宁和吉林的辽河、鸭绿江,朝鲜境内的大同江,乃至更北部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与嫩江。中国上古的文明正是在这些注入渤海的河流冲积地上孕育、滋长。河流窜起了它们途经的广大区域,即当时中日学者如梁启超、矢野仁一等争议的焦点地方:中国疆域的边界是否包括满、蒙等长城以外区域。傅先生此视角用以渤海为中心四散的河流,突破了长城内外的边界。他进一步推断,“大致当在夏商时,当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种族,为黄河下半淮水、济水、辽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流域之后代居民,安置一个基础的原素。”[3]为论证此“基础的原素”,傅斯年先生提出三点证据;中国东北与殷商共通的“人降论”卵生神话,箕子的故事,以及殷商与东北地名的核比。第三点傅斯年先生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夷夏东西说”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傅先生认为,神话的比较研究是厘清民族分合问题的一大利器,如犹太民族,虽然方言各异,但其创始神话相同,而古代中国东北各部落均有“卵生”神话,譬如《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骊纪》《朝鲜实录本记》中都有“朱蒙传说”,其中最重要的雷同情节之一,便是国王朱蒙的母亲河伯之女为日所照,感而受孕,生下一卵,儿子朱蒙自卵中孵化而生。
东北地区这类神话的另一种叙述则是“吞卵产子”,这记载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傅先生参考了几个版本,一是当时北平故宫博物院藏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他认为这是最初本,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满洲实录》,这个版本介于前两者之间。这则神话是关于清王室爱新觉罗的创始神话。神话开头即将长白山视作方圆千里内的中心之地,从山上流下三条河:分别是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南海的鸭绿江;从山北泻出向北注入北海的混同江;东向入东海的爱滹江。在沈阳故宫藏本中注有“满洲源流。满洲原起于长白。”[4]该神话的第二部分讲述的是“天女玄鸟”的故事:在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有一湖泊,天降三位仙女沐浴其中,浴毕上岸,有神鹊衔来一枚朱果放在第三女佛库伦的衣服上,她把朱果衔在嘴里,后入其腹中,随即感而受孕,生下一个男孩,瞬间便长大成人。佛库伦对儿子说,“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此时,长白山东南有三姓夷酋长正相互厮杀,佛库伦之子见到他们,便说,“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5]三姓人共同拥戴他为王,国定号为满洲,佛库伦之子正是满洲的始祖。
在考察东北诸部落的“朱蒙天女玄鸟”神话后,傅斯年先生从神话的一致性断定东北区域各个部族之间,尽管后来各异,但应是同源。进一步地,他指出此神话不仅限于东北,殷商、古淮夷也有类似的神话。《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腹中,她生下殷商的始祖。傅先生还引到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之先,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6]据傅先生分析,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借商人西向的势力,从岱南而出,在西北建立部落。它本身东海上的淮夷之属,所以与东北、殷商这些同在渤海沿岸的部族有相同的起源神话。
通过比较环渤海的东北部族、殷商与淮夷的卵生神话,傅斯年先生认为这实则是一个神话在这整片区域的流传,由此,不仅东北各部族上古时出自同源,更重要的是,“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族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有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7]
从地域上论证渤海两岸上古原为一体,而在时间维度上,傅先生此说亦有深意。《东北史纲》中,与天女玄鸟神话相对,傅先生梳理了东北各部族在历史上的渊源流变。他认为,东北最早的部族为肃慎朝鲜之类,时代并起于殷周之世,更进一步地,他引《左传》《周书》等文献证明,“朝鲜为殷商之后世,肃慎为诸夏之与国”,所以,东北历史与黄河流域之历史“并起而为一事”。傅先生又以《满洲源流考》中“挹娄疆域与肃慎正同”,“肃慎、挹娄、女真为一音之转”。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为清朝皇室之部族,而上述可见,清王室从源流上看并不是真正的“异族”。傅先生认为当下满清族属与汉人的差异,只因双方“基础的原素”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速度不一,或“易于因政治力量而混同”。
傅斯年先生通过“天女玄鸟”神话的比较分析揭示出环渤海岸的东北与殷商所属的东夷,其创始神话的核心便是始祖以卵生而建国立业,此论与他梳理满清王室的族属源流相应,暗指清朝的创立者东北的女真人自上古与现今长城之内的汉人同源。而继矢野仁一提出“满蒙非中国本来之领土”后,日本的关东军以此论为基础,抛出“满蒙论”: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我国密切,即使闭口不谈民族自决,满蒙是满洲人及蒙古人之领土,而满洲人、蒙古人比起汉民族,毋宁被认为与大和民族更接近。[8]日本也早策动溥仪等满清皇室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次,矢野仁一论点中重要一点便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只从辛亥革命算起,清王朝的领土虽然包含满蒙藏等,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新的、汉族建立的国家,无权继承清的领土范围。傅斯年先生结合族源进行的卵生神话分析,以满清与汉民族同源一体,表明中华民国应当继承满清的领土权①这点结论直接得益于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辉老师的启发。。
东北与殷商的关系,不仅可用卵生神话证之,傅斯年先生的第二条论据是箕子的故事,指出“中国之殷代本自东北来,其亡也向东北去。”东北,如同殷商实力的贮存器。箕子的故事,一说是身为殷商后裔的箕子见殷道衰微,于是去往朝鲜,教当地土著民礼教、耕田、蚕桑织造等;一说武王伐纣之后,放殷商后裔箕子,并把朝鲜分封给他,箕子受了周的封礼,不得不按照臣的礼节,来朝周天子。据傅先生考证,周汉时的朝鲜与现在所指地域不同,箕子所去的朝鲜为辽宁的部分及今天朝鲜的大部分。箕子后人之国的西部后被燕国吞并,秦朝承袭燕国,在当地设立郡县。到汉武帝时,以朝鲜王不恭顺为借口讨伐,设置四郡,北境的部族都臣服,南部部落向汉王朝入贡。由此,东北乃至今天朝鲜半岛全部统一于中国的版图中,或为郡县制,或是羁縻统治。
将箕子奔朝鲜的故事与《诗经》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联系,傅斯年先生推论“海外”应指渤海东岸,那么,商汤之先祖早已据东北,正因为有之前的根基,在周灭商后,箕子及其殷商遗民才能退保辽东,而周公、成王征东夷的兵力才能始终不及。其二,傅先生指出中国对四周部落多用贱词,如戎、狄之类,但惟独对“夷”尊崇有加,他引《后汉书·东夷传》中对“夷”的阐释:“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9]傅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正因为中国人自觉与东夷为一类,所以与其同情。第三,汉武帝征伐东夷后,果如上述所述般“柔顺”和“易以道御”,傅先生认为倘若不是因为此地自殷商始便属中国,汉武帝怎会如此迅速征服且持久再无叛乱。相反,其他真正的异族,哪怕汉族攻下其城池,不久也会反抗,如大宛之类。汉武帝一统东北,恰是基于殷商在此的底子,箕子东奔与武帝东征,都是一有“共同原素”的民族在渤海两岸的兴替。
三、中国失礼,求之四夷
自殷商兴自东北,到武帝东征,魏晋之时,东北之地或已为中央朝廷设置的郡县——这是傅斯年先生在本书第三章中详细梳理的县治沿革,或是朝廷分封的藩属。后者之于傅先生,需要解决的矛盾便在于“族属”或者说“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历史上在东北建立的“国家”,譬如夫余国、高句丽等,与汉人国家间的关系,进一步地,此种族与族、国与国间的历史关系导致今天该如何处理中国东北问题,这恰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争议的焦点。
为此,傅先生特意在本书第四章“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中“辩明”。他认为,在认识东北诸部之族别时,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方能廓清东北族属与疆域间的真正关系,“诸书所记东北部族,非一代事。自箕氏朝鲜至慕容氏,虽汉族及其文化之东进为一经恒之事件,然所谓夷者,历代消长不同,疆域分合乃异。如混为一世之事观之,势必失其窍要。”[10]朝代更替,疆域随族属势力变化而不同,但傅先生正是要反对矢野仁一满清是满清,民国为民国的割断历史之论调。其次,傅先生从东北自古以来便为各民族往来汇聚之说起,“东北区域,北接黑水金山,西连浣海松漠,南挟朝鲜半岛,西南与山东半岛相应,海陆皆不呈封闭之形势,故若干民族来来去去,为历史上必然之事”。那么如何处理这众多的民族与他们建立过的诸政权呢?傅先生把东北“族”与“国”的矛盾化为“阶级”的区分,“一国之内,一地之民,每非尽是纯一之部族。且同为一地之众民,亦不必尽是渊源一脉,阶级之形成为不可免者。必先看清东北诸部族中之有阶级,然后可知东北诸地之民族分配也。”[11]
按傅先生在书中的划分,东北的“族类”共有四大类:中国人 (等同于长城以内的汉人)、獩貊、挹娄和韩族;除汉族朝廷设置的郡县外,上述族属在东北建立的国或部落则有夫余、高句丽、沃沮、挹娄、三韩部落。通过用阶级的概念分析这些族与国,傅先生消解了多民族与一国、多国多民族与东北一地间的矛盾。
傅先生首先追溯了东北的中国人,他在书中对中国人的定义是“自燕齐一带而往原以汉语为母语之民族”。[12]中国人在东北可分两种:郡县之民与封建王国的统治者。汉人一直以其政治组织和文化上的优势,东向拓土,殷商时箕子奔朝鲜,秦汉承春秋战国,在此设立郡县。更重要的是,汉人除属郡县之民,直接受制于长城内政权外,而且还是夫余、高句丽、三韩等封建王国或部落的“统治阶层”。傅先生此论断有两点依据,其一依然是前文引述的“卵生神话”:《论衡·吉验篇》中记载,北夷櫜离国王的侍婢产下一卵后,孵出一名男婴名叫东明,国王见他才干出众,怕日后国家被他夺取,便想要除掉他,东明奔走,南渡虎水,“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13]《魏书·高句丽传》中说高句丽出自夫余,它的先祖名叫朱蒙,与东明的卵生神话雷同,朱蒙也是出自卵中。国中大臣为绝后患,派人谋杀他,朱蒙弃夫余国而南走,遇三姓之人,到升骨城定居,建立高句丽国。[14]傅先生认为高句丽出自夫余、夫余出自北夷櫜离,东明与朱蒙实则为一词。加之傅先生此前已经证明,根据殷商与东北乃至整个环渤海圈共有的“卵生神话”,说明殷商与东北源自一体,整个卵生神话的前后两部分——卵生与为王,说明夫余、高句丽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汉人始祖实为同一脉。
汉人为东北封建王国与部落上级阶层的证据之二,是傅先生发现在夫余、高句丽、三韩人中,存在一种自称“亡人”的人。《魏志·夫余传》里说“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今夫余库有玉璧珪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15]中国人在东北的势力不仅自西向东,更有从北往南之势,在南部的三韩部落中,也有中国人与土著混合的国家,《后书》和《魏志》都记载,南部三韩中的辰韩,国中有耆老,自称是秦之亡人,他们的言语和生活习俗都与邻国马韩不相同。那么,这些“亡人”是何时并因何事来土著异族之中的呢?傅斯年先生分析这是匈奴东进逼得东胡东退的连锁反应。“东胡在周末为强族,内容甚复杂。所谓林胡、楼烦、山戎者,亦不知其是匈奴别部,或是东胡,但知其与中国关系不少耳。秦时中国统一于南,匈奴统一于北,东胡山戎等之迁移必东其方向。”[16]当时东北的土著之民是后文将提到的獩貊之属,他们建立城郭,为定居的农耕部落,抵挡不住东胡游牧之民,因而夫余国染有一些胡风,如兄死弟妻嫂等,这并不是东夷本来的风俗。辰韩的情况类似,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部族,秦人为躲避战乱来此,成为亡人,但也因此使得辰韩在南部三韩族属之中最为开化,知晓礼俗,区别于马韩等纯粹的土著民,但与东胡游牧民族入侵夫余一样,马韩虽然粗野,但蛮力胜过辰韩,辰韩不得自立为王,必须受制于马韩人。
汉族多为东北封建王国与部族的上层,那么,这些王国的下层民众则是东北真正的土著之民——獩貊。在黄河流域的各个部族尚未混合成为统一的中国民族之前,貊人分布在整个环渤海圈内,中国民族形成之后,他们便成为东边的土著民。根据《诗经》,獩貊人在西周春秋初的时候还分布在今天的河北以及山东境内,譬如,在西周时,河北中部仍为貊人所居,周将它驱除出去,也有一部分貊人留在当地,被同化入中国人之中。傅斯年先认为这也是汉族与东北部族类同的原因之一。其次,獩貊民或许正应了傅先生“殷商兴之东北,王也东北”的推断,殷商遗民箕子退居东北后,正是凭借当地土著獩貊之民建立国家。《汉书·地理志》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17]。第三,夫余、高句丽、沃沮等地的都是獩貊人的区域,只不过统治者不是他们而已。傅先生列举相关文献,《后书》 “夫余国本獩地也”,《魏志》“夫余其印言‘獩王之印’,盖本獩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句骊一名貊耳”[18],至于沃沮,《魏志》中也记载以当地土民为县侯,一些官吏由土民獩貊人担任。因此,傅先生下结论说,“秦汉魏时,自中国人外,獩貊为东北最众之民族也”[19],根据傅先生此前的推论,此民族在殷商之际就与兴起于黄河流域的汉族有莫大渊源,它为在东北立国的夫余、高句丽等提供了被统治的底子。
东北最特殊的民族为挹娄。傅先生认为挹娄即为通古斯族,“挹娄之后为勿吉,勿吉之转音为靺鞨,靺鞨之遗而复振者为女真,女真之受中国节制者为建州,建州之改名曰满洲。”[20]而挹娄往上追溯则是古肃慎国,《左传》记载“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但傅先生就肃慎与挹娄渊源关系上前后似有不同之处,第一章本已确定肃慎-挹娄-女真一线的历史脉络,但在第四章中又将挹娄是否为古肃慎国付诸阙疑,或许是因为挹娄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满清源流,满清历史上是否与中国为同一族属或是其疆域,又与傅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息息相关,所以至为慎重。挹娄为东北最为特殊的民族,还因为它与夫余、高句丽、沃沮等国完全不同。首先,当时它是散漫的部落,没有形成同一的国家,而且“独无法俗,最无纪纲”;其次,即使夫余染上些许胡风,但它与高句丽、沃沮等国以及汉人一样,都是城郭之族、农耕之民,挹娄则是游牧民族,穴居,善于制作石镞 (这点倒是和古肃慎国相似);生活习俗方面,夫余、高句丽、沃沮、獩貊人和中国人相同,吃俎豆,只有挹娄不吃,他们只知道养猪,不骑马也不放牧牛羊。
在东北区域,族属最为复杂的是南端的三韩,即马韩、辰韩与弁韩。傅先生一是认为三韩虽然族属复杂,但有一个基本且独立的土著原素,它与獩貊一样,是东北的另一土著群体,但与獩貊的习俗等等完全不同;其次,有关这一土著群体的与其他族属的关系,联系前文,当獩貊民族遭到东胡东进时,被迫退让,这又挤压三韩土著南移。所以,三韩之中,有夫余、獩貊等人,也有秦时避难的汉亡人,又因南端近海,有来自海上的倭人。三韩之间发展不平衡,辰韩文化因受汉族影响最为开化,但最初受制于武力彪悍的马韩,后来辰韩的新罗部崛起,马韩即为百济,新罗凭借对唐朝的归顺,在百济与高丽中一支独大。
傅斯年先生逐一比较了东北这四种族类在文化上的高低,其判断标准是这些民族之间文化上的不同之处,其次是它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相似之处。整个区域按照文化高低大致可分为南北中三个部分:中部以獩貊土著为底子的夫余、高句丽这些国家,它们在文化上与中原最为接近,有城市、农耕,这是东夷与西域各族和北狄之类最大的不同,虽然历代经常把东夷和北部的这些民族相混,但它们并不是一体,东夷更近中华。夫余、句丽这些国家前文提到,尽管还沾染了一些胡风,但土著獩貊却是最为中国化者,中原的一些禁忌、生活方式,例如月历、丧礼,他们都得以保留,傅先生还特意提到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所谓土著者,谓居处生活著土为定,非迁徙之游牧民族。盖缘中国本部文化进展特速,故后代礼俗每异先世,东夷转能保存中国古代之生活状态也”。[21]南部的三韩部落没有形成国家组织,以土穴为居,但已从事农业,文化程度低,其中较为进步者都是北部避难而来的亡人。文化最低等的是北部的挹娄人,他们仍处在石器时代,相比爱好洁净的高句丽等文明之属,挹娄人最为不洁。从中国古代区分族属最重要的标准头发样式上,也可以看出这几类民族与中国不同的亲疏关系:最北面的挹娄人编发,中部的夫余、獩貊等与中原人相似,南部的韩人不编发,但也不像中原人的发式。因此,挹娄所属的通古斯种与东北本土的两大土著獩貊及韩族定不是同类。
理清了东北的族属与王国、阶级与文化等关系,傅斯年先生驳斥了日本人所谓的“古代东北及朝鲜为通古斯人所居”的言论,显然,从他上文的论证看,朝鲜古代之民即为三韩部落,这其中有中国的亡人,也有东北的土著獩貊和韩族,而北部的通古斯只不过是东北三大文化区中的一块。他也指出这之后的流变以及对中国的重大影响:“自挹娄诸部扩张疆土转号勿吉 (靺鞨)后,通古斯人始以渐雄视于东北。前此强大者,为夫余句骊之横介于中国与通古斯族间者。隋代以前,中国与代表通古斯族之挹娄勿吉往来绝少,唐代彼始与中国交兵。高句丽之亡,靺鞨之兴,可谓之东北汉族以外居住区域中最大之转变,前此为最近于中国之獩貊人世界,后此为稍远于中国之通古斯族世界矣。”[22]在傅先生看来,夫余、高句丽这些自殷商始便于中国同为一体的王国,无论其上层的汉人,还是作为王国底子的獩貊,是中国与异族通古斯间的缓冲地带,当它们灭亡后,中原王朝直面真正的“夷狄”通古斯人的转变,“其重大或不在中央亚细亚由印度日耳曼世界转入土耳其世界之下”“白山黑水之间,历世强不能驯,非复句骊獩貊时代之礼乐人文矣”。但综观全书,傅先生在处理与通古斯,即挹娄-女真-满清的相关材料时,有前后矛盾之处,其实在本书开篇,他就指出东北的民族都是“东夷”,通古斯是东夷之一,它或许正是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流民族构成之一的基本原素,而且一直南向望化,封贡不绝,城郭礼俗,最近中土。
傅先生用阶级概念处理东北族属与王国间的矛盾,是为了说明该如何认识满清帝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他列举到,外国人称“大清帝国”为中国,而中国的革命人士称它为“满清”,这实则各有所据,前者着眼于全民,后者是一统治组织为对象,清帝国便是满洲。因此,“世上甚少单纯之民族,封建时代,社会之阶级每即使民族之阶级,少数之统治者与多数之被统治者常非一事。如忘其阶级,而谓某国出于某部,必穿凿也”。[23]正如夫余、高句丽、沃沮等王国统治者与统治之民不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虽为满洲,但多数被统治之民仍为汉族,所以不能像矢野仁一所谓的中华民国应从辛亥革命算起,无权继承满清帝国对满蒙藏等边疆的统治权。更何况,根据傅先生考据的东北之初民,原本就与环渤海岸的黄河流域同属一源,如整个环渤海圈卵生及东明 (朱蒙)为王的神话。
四、结语
“何为中国”?这既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本等列强为瓜分中国利益,认为应将历史上中国直接统治与行使宗主权的地盘分而对待,而后者恰是满、蒙、藏、回等非汉族民族聚居的边疆之地;另一方面,这也是从推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满清帝国,到为领土主权抗争的中华民国转型时,国人不断调整的认同。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便是这此过程中书生救国与立国的一例。综观全书,傅先生似乎呈现出两条彼此矛盾交织的线索,一是为论证东北与汉族为同源,但又不得不处理这片区域内一直以来诸多民族及非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王国问题。
针对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的“满蒙非中国本来之领土论”及以此作为侵华政策基础的日本政府,傅先生便要证明东北在历史上属于中国,进一步地需说明,年轻的中华民国为何有权继承满清帝国的领土主权。由于时局的需要,因此傅先生这部分的立论重在同源、一体。傅先生以上古时期整个环渤海岸流传的“卵生神话”,箕子奔朝鲜,中原士人与东夷在情感上的互通等,提出东北如同是东夷的一块贮藏地,殷商兴自东北,亡也向东北去。联系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属东夷的殷商与西面的夏同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进而,东北不仅是殷商文化的保存地,当中国本部的文化发展太快而异于先世时,这里转而保存着中国古代的礼俗,即“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对于满清与民国的继承关系,傅先生给予了三方面的应对:首先分析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三个不同版本中关于满洲始祖的神话,与殷商创始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结构相似,满洲始祖的母亲佛库仑同样是吞卵产子,傅先生认为从创世神话可推知民族分合,满清与东夷同源。其次,傅先生主张要历史地看待民族东北区域上民族与疆域的消长,而不能仅凭一朝一代观之,这实则是驳日本乃至其他列强将满清与民国割裂对待的言论。面对东北历史上曾经诸多的民族与封建王国,傅先生指出要厘清统治阶级与国家的区分,不能仅以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族属代替整个国家,因为世界上很少只有一个民族的国家,此外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常不是一类。由此推知,清帝国的统治阶级虽为满族人,但不能以满清代替中国,那么,民国与清帝国只是统治阶层不同,国家的延续性仍在。
在分析东北区域内部的族属时,傅先生却勾勒出它们复杂的混同关系。他首先指出东北不是一块封闭地方,在这片四面开阔地上若干民族来来去去是常态。倘若将他描述的族属大致分为北、中、南三部分,北面为通古斯人,傅先生在书中呈现出他们既向慕华化,又在中部源自古东夷的王国灭亡后,成为中国本部直接面对的强敌;中部则是与中国关系最亲近的土著獩貊为底子的一些王国,这其中有为上层的汉族,也有的沾染上东胡的胡风;南部主要是东北的另一土著韩族,三韩部落中既有汉族的亡人,也受到海上来的倭人影响。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流动恰是形成上述混同局面的原因之一,譬如,匈奴与汉民族的东进,挤压土著獩貊,又进而迫使另一土著韩族往南迁移。在这片区域上,有从事农耕与住在城市的民族,也有在森林间游牧的部落。东北历史上纷繁复杂且充满动态的族属关系与上述重在一体的论述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矛盾是因时局影响,傅先生必须将原本处于整个天下格局中的夷夏关系,框定到有明确疆域版图内的中国,用有限制的国族去收拢并包住原本超越国族之天下时的紧张。譬如,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 ‘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为国族一统的建构解释这些“混入之迹”,所以他无不矛盾地说,“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24]
傅先生的《东北史纲》被誉为中国东北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因特定的时代使命,力证东北与长城以内省份的同源一体,但也不应忽略傅先生引述的众多历史文献中呈现出的东北之开阔和多样性。今日的民族学研究或者东北研究,不再有傅先生当时那般紧迫和现实的救国与立国需要,或许,可以以更为开放地研究态度对待傅先生书中的这两种矛盾。
——在傅炯业先生李梅英女士金婚庆典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