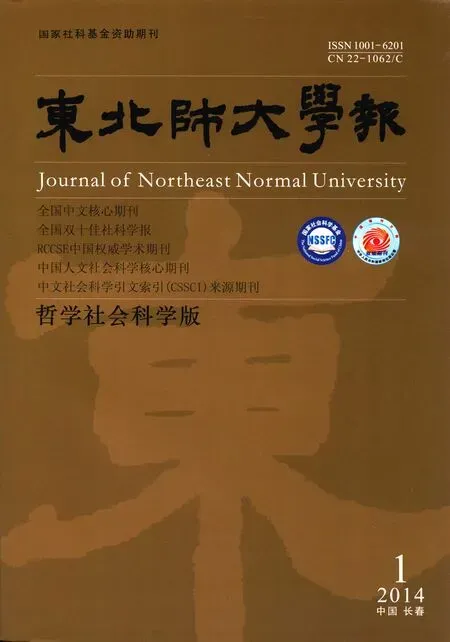试析傩礼中方相氏的地位嬗变
刘振华
试析傩礼中方相氏的地位嬗变
刘振华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吉林长春130021)
方相氏是傩礼中的主角,其主要职责是“驱疫”。但汉以后,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被弱化。方相氏职责和地位的变化,表明一直高高在上的方相氏已开始走向民间,自周以来傩仪的礼制规范已渐渐被打破,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发生改变。随着傩仪逐渐由严肃的国家礼制向娱人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傩与戏剧越走越近,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诞生。
傩礼;方相氏;职责;地位下降;戏剧
古傩的主角叫方相氏,也称方相。在殷墟发现的方相辞,各家解读不同,郭沫若等人认为其中“方相”二字是两个地名,但陈邦怀在《殷代社会史料征存》中表达了和郭老等人的不同看法,认为“方相”二字应当连读,就是周礼中的方相氏,并得出结论,这条卜辞记载的是殷商傩礼。如果此结论成立,那么关于方相氏的文字记载将大大提前。
方相氏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而对于方相之得名,郑玄注曰:“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贾公彦疏:“郑云‘方相’犹言‘放想’者,汉时有此语,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相也。”[1]831,851
一、方相氏的职责
从《周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方相氏有两项职责,一是“时傩”时“索室驱疫”,二是“大丧”时走在棺柩的前面,到了墓地之后“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在这两项职责中,方相氏最为核心的作用都是“驱鬼”,但所驱之鬼却有不同。前者的“驱疫”之“疫”当指疫鬼,但并未言明是何种疫鬼,应是广义、泛指。而后者则明确指出是“驱方良”,郑玄注曰:“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1]851可见,“方良”即“罔两”,那么“罔两”又是什么呢?
“罔两”在史料中又有“罔象”、“罔阆”、“蝄蜽”和“魍魉”的写法。
《事物纪原·石羊虎》:“《风俗通》曰:‘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脑’。”[2]485《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注曰:“罔两,水神。”孔颖达引《鲁语》贾逵注云:“罔两、罔象有夔龙之形而无实体,然则罔两、罔象皆是虚无……非神名也。”[1]1868《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郭象注曰:“罔两,景外之微阴也。”[3]110-111《淮南子·道应训》:“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高诱注曰:“罔两,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罔两恍惚之物,见景光明,以为神也。”[4]891-892《楚辞·东方朔〈七谏·哀命〉》:“哀形体之离解兮,神罔两而无舍。”王逸注曰:“罔两,无所据依貌也。”[5]137《史记·孔子世家》:“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6]1912刘勰《文心雕龙·夸饰》:“娈彼洛神,既非魍魉,惟此水怪,亦非魑魅。”[7]51
《说文》:“蝄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说:‘蝄蜽,状如三风小儿,赤黑色,赤目,长耳,美发’。”[8]672《国语·鲁语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为龙、罔象。”韦昭注曰:“木石,谓山也。……蝄蜽,山精,傚人声则迷惑人也。”[9]201张衡《南都赋》:“追水豹兮鞭蝄蜽,惮夔龙兮怖蛟螭。”[10]72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字说·集字一》:“蝄蜽,俗作魍魉。”[11]215
《孔子家语·辨物》:“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怪龙罔象。”[12]63蔡邕《独断》:“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瘧鬼;其一者,居若水,是为魍魉;其一者,居人宫室区隅,善惊小儿。于是命方相氏……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13]11。关于“颛顼时傩”的故事,《论衡》、《后汉书·礼仪志》、《搜神记》、《文选》等均有提及。《文选·班孟坚幽通赋》:“恐魍魉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李善注曰:“郭象为罔两,司马彪为罔浪。罔浪,景外重阴也。”李周翰注曰:“魍魉,影外微阴也。”[14]272
以上记载对“罔两”的解释或谓“木石之怪”,或谓“水神”,或谓“景外之微阴”、“无所据依貌”、“恍惚之物”。那么方相氏所驱之“方良”到底是什么疫鬼呢?由于方相氏是在墓穴之中驱“方良”,墓穴乃木石构成,所以“水神”恐不确切,倒是“木石之怪”极为可能。台弯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陈炜舜总结说:“罔,非也;两,二也。此义古人虽未明言,却贯穿了罔两一词的传统二义:山精水怪则非有非无,景外微阴则非明非暗。高诱谓罔两乃恍惚之物,也就是说,罔两有恍惚的特征”,“恍惚则非皦非昧,影外微阴有恍惚之状,而木石之怪一义亦自恍惚所衍生。”[15]124-125由此可见,方相所驱“方良”是一种非明非暗、若有若无、恍惚之物的没有实际形体的“木石之怪”。
所以说,方相氏在“时傩”和“大丧”时所驱鬼之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广义上泛指的各种能带来不祥的疫鬼。而后者则是特指的“方良”,即“木石之怪”,驱逐的目的显然是防止其对逝者亡灵的惊扰。
“时傩”是指每年按时节的变化而于固定时间举行的驱鬼仪式。古之先民认为鬼为阴物,阴气盛则鬼出,因而要举行仪式来驱逐疫鬼,是为“傩”。《礼记·月令》记载了三种傩仪,分别是“国难”(傩,下同)、天子难和大难。“国难”也称“国人难”,是指季春之月以天子和诸侯为主体的王城周族设置的傩礼。《礼记·月令》中说,“(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难”是指仲秋之月天子举行的傩礼。《礼记·月令》中说,“(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郑玄注说,“此难,难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阳气左行,……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之”;“大难”是季冬之月有民众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傩礼。《礼记·月令》中说,“(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难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门,磔攘也。”[1]1364,1374,1383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三种傩仪的规格是有所不同的。《周礼注疏》中贾公彦疏曰:“季春之月,命国难。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行而出,故难之。……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者,按彼郑注,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故难之,以通达秋气,此月难阳气,故惟天子得难。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故难之。”[1]808
紧接着,贾氏又曰:“命有司者,谓命方相氏,言大难者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难……此子春所引,虽引三时之难,惟即季冬大难知者,此经始难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氏亦据季冬大难而言。”按贾氏的说法,只有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季冬大傩才有方相氏出现,而春傩和秋傩则没有方相氏。此说极是,这也是宫廷傩和民间傩的区别所在。按照《礼记·月令》的记载,只有在大傩即冬傩时才有普通民众的参与,那么宫廷傩礼由方相等朝廷礼官进行的“索室驱疫”在民间只能是“沿门逐疫”,这才有孔子“朝服”立于东阶迎候乡人傩的场面。所以民间傩仪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使用专职方相的,只能是驱傩者戴着面具装扮成方相的样子进行“沿门逐疫”。
二、方相氏在傩礼中地位的下降
方相是傩礼中的主角,但方相在傩礼中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不断下降的态势。
我们知道,最早的傩仪是《周礼·夏官》中记载的“方相氏,狂夫四人”和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代驱傩,方相氏是四人,其貌是“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其动作是“执戈扬盾”,其作用是“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但到了汉代,则有所变化。《续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製,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輿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候云。”[16]3127-3128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制傩仪与周制已有所变化。周制傩仪中,方相氏是绝对主体,“帅百隶而时难”,且方相氏为“狂夫四人”。而汉制中并未明确方相氏是四人,那么就很有可能已变为一人。方相氏不再是傩仪的主导者,而是“黄门令”,即宦官,整个傩仪都是在“黄门令”的主持下完成的。而且,还出现了“十二兽”,“因作方相氏与十二兽舞”说明方相氏在傩礼中驱疫的核心职责已被“十二兽”所分担。方相氏的地位此时已比周时有所下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和玄学的兴起,一年一次的大傩已无法保证,宫廷傩礼渐成萎缩之势。但是,北齐不仅继承了东汉的傩制,而且还有创新和发展。方相氏的地位和汉时相比变化不大。
《隋书·礼仪志》记载了北齐的宫廷傩礼:“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以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閤,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17]168-169北齐宫廷傩礼基本继承了东汉末期的宫廷傩制,但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侲子的选择不再是“中黄门弟子”,而变成了“乐人子弟”,而且人数上也翻了一倍;二是出现了“舞戏”——“方相与十二兽舞戏”。
到了隋,方相氏地位进一步下降。《隋书·礼仪志》记载:“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选侲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其一人为唱师,着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方相氏执戈扬盾,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17]169从中可以看出,隋时方相地位进一步下降,已成为“工人二十二人”其中的一人。
《新唐书》记载唐时傩仪:“大傩之礼,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盾;其一人为唱师,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禳,设祭。太祝一人,斋郞三人。右校为瘗埳,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傩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近仗入陈于阶。鼓吹令帅傩者各集于宫门外。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傩者于长乐门、永安门以入,至左右上閤,鼓噪以进。方相氏执戈扬盾唱,侲子和……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趋顺天门以出,分诣诸城门,出郭而止。”[18]207-208唐时方相还是“工人二十二人”中的一人,但“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说明方相作为驱傩的主角地位比隋又有下降。
方相氏在唐时地位的进一步沦落,还体现在一向为宫傩专用的方相氏,竟然出现在了民间傩仪中。《大唐开元礼》卷九十《诸州县傩》记载:“方相四人,俱执戈盾,唱率四人。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杂职八人,四人执鼓鞉,四人执鞭。前一日之夕,所司帅领宿于州府门外。未辨色,所司白刺史请引傩者入。将辨色,宦者二人出门,各执青麾引傩者入。于是傩者击鼓鞉,俱噪呼鼓鞭,击戈扬盾而入。唱率侲子和……宦者引之,遍索诸室及门巷。”[19]424从以上记载,方相氏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可见一斑,方相氏不再作为傩仪等级区分的主要标志,一向为皇家专用的方相氏已出现在州县的傩仪之中。
“大丧”,即指天子、王后、太子、太王、太后等的葬礼。大丧时,方相氏一是要“先柩”,二是要“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宋张君房所辑的《云笈七签·轩辕本纪》:“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20]2177宋高承在《事物纪原·方相》中说“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2]481说明嫫母就是最早的方相。《续汉书·礼仪志》:“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立乘四马先驱。”[16]3144这说明直至汉代,方相氏在葬礼中的使用和在“时傩”时一样,还是有严格的等级约束的,仍只可在最高等级中应用,但这种情况在晋代发生了变化。
《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晋公卿礼秩》曰:“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车驾马。”[21]2501这说明晋代方相的使用已扩大到王公,而非仅于帝王。而到北齐时,则进一步扩大了葬礼中方相的使用范围,“后齐定令,亲王、公主、太妃、妃及从三品已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毕进输。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仆,皆听立凶门柏历。三品已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已下,达于庶人,以魌头。”[17]155到了隋代则放宽到四品,“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头。”[17]156-157晋三品以上,隋四品以上,到了唐已放宽到五品,“其方相四目,五品已上用之;魌头两目,七品以上用之,并玄衣朱裳,执戈、盾,载于车”[22]508。
宋以后,在民间葬礼中,方相氏虽还使用普遍,但逐渐演变为以纸人为之,做为葬礼的先导。
吕祖谦在《东莱别集》中曰:“古礼方相氏乃狂夫四人,世俗乃用竹结缚之,不应古制,今参定魌头,当使人服深青衣,朱裳(冠且用世俗所造方相氏之冠),戴假面(即世俗所谓面具也),执戈扬盾(近胡文定公之葬,方相用人)。”[23]65-66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宋时的方相氏已是“乃用竹结缚之”,而很少用人。而《东京梦华录》卷四的记载则更进一步:“若凶事出殡,自下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有须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24]80“方相氏”已经成为市场上可以买卖的“殡葬用品”,原本“高高在上”的方相氏,逐步深入民间,成为民间葬礼中不可或缺的神祇。
三、方相氏地位的下降与傩礼的世俗化、娱乐化
方相氏在傩礼中地位的变化,表明自周以来的礼制规范已渐渐被打破,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被弱化,具有规范礼仪的傩仪自汉以后更具“歌舞表演”的性质。
东汉末期的“方相与十二兽舞”的出现,是宫廷傩礼世俗化、娱乐化的里程碑式的标志[25]223。一方面说明方相氏在傩礼中“驱疫”的核心职责已由“十二兽”分担,更重要的是在傩礼的开始阶段,中黄门领倡、侲子们附和“十二兽吃鬼歌”,“倡”其实就是一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的“艺术形式”。倡过之后,就是舞——“方相与十二兽舞”。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说,“汉制大傩,以方相四,斗十二兽,兽各有衣、毛、角,由中黄门行之,以斗始却以舞终。”[26]1221这一“倡”一“舞”,实际上标志着傩礼中已出现具有情节的艺术形式,这和先秦原始的傩仪已有本质上的区别,也显露出些许傩戏的端倪。到了北齐,“方相与十二兽舞”已演变为“方相与十二兽舞戏”,说明傩礼的世俗化、娱乐化的成分进一步加大,此时的驱傩的仪式性已向观赏性过度。隋时,方相氏已成为“工人二十二人”中的一人,“工人”属乐官一类,傩礼的娱乐化成分进一步加强。唐时,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曾命四人装扮成方相氏,一人扮兰陵王,演出“方相伴兰陵王舞”,后人称之为“跳兰陵王”,说明此时方相氏“驱疫”的职责已越来越背离原始的初衷,娱乐性已成为驱傩的目的之一。而方相氏出现在民间傩仪中,表明其已不再是皇家专用。到了宋代,“方相氏”更是成为民间的殡葬用品。方相氏在傩礼中的地位变化说明,做为“通神”主导者的方相氏已从“神坛”上走了下来,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向“娱人”方面转变,这就为傩仪的不断世俗化、娱乐化打下了基础,也表明傩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已和戏剧越走越近了。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郭庆潘.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王逸.楚辞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司马迁著,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孙奕.履斋示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王肃.孔子家语[M].上海:广益书局,1937.
[13]蔡邕.独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陈炜舜.释罔两[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16]司马彪.续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8]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中敕.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0]张君房.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1]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2]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3]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M].永康胡氏梦选廔刻本,1924.
[2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5]刘振华.先秦两汉宫廷傩礼世俗化演变探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26]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Change of the Mage in Plague-dislodging Ritual
LIU Zhen-hua
(Jilin College Of The Arts,Changchun 130021,China)
The mage is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uo ritual,whose main duty is to dislodge the plague.However,after Han Dynasty,the predominant status of the mage has been weakened.The declination of its duty and status shows that the mage,belonging to the upper class in the past,now has become popular among civilians.Since the etiquette patterns of Nuo ritual has gradually been broken in Zhou Dynasty,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is changing.The Nuo ritual is developing from solemn national liturgy to entertainment and secularization;as a result,the ritual is approaching drama and contributes to the birth of Nuo drama.
Nuo Ritual;the Mage;Duty;Declination of Status;Drama
K234
A
1001-6201(2014)01-0076-05
[责任编辑:赵 红]
2013-11-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23);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研究项目(2014192)。
刘振华(1970-),男,吉林长春人,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