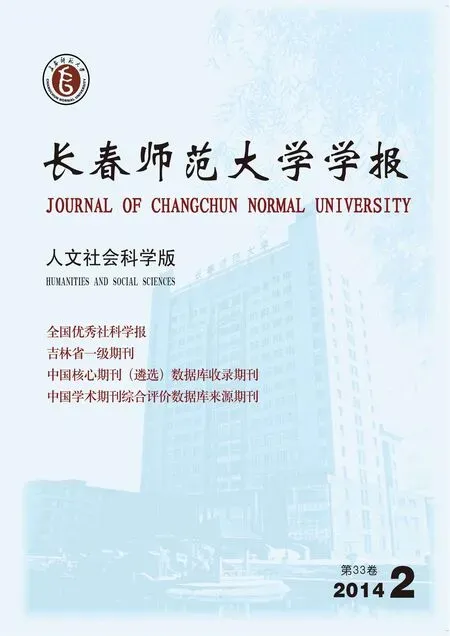论张晓风散文语言的动感艺术
詹秀华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论张晓风散文语言的动感艺术
詹秀华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作为台湾著名的散文大家,张晓风是一位“以动写静,化美为媚的能手”,其散文语言不仅富有古典美、色彩美、音乐美,而且充满强烈鲜明的动感,形成一种扑面而来、让人印象至深的动态美。她特别讲究动词的运用,其动词不仅用得精、巧,并且动量足、气势丰沛。此外,她大量运用拟喻,并配合通感、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展示的不仅是自然景观的静态的外在之形,更令自然之物充满张扬饱满的生命精神,散发出独特的动感魅力。
动感;拟人;通感
张晓风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大家,她的散文不仅有着独特的诗性感悟[1]、极高的文化艺术素养,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富有创造性。其散文语言不仅富有古典美、色彩美、音乐美,而且充满强烈鲜明的动感,形成一种扑面而来、让人印象至深的动态美。其散文中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无不充满丰沛的生命活力。正如学者楼肇明所说,“她是一位以动写静,化美为媚的能手,她笔下的自然美,几乎无不具有一种气势逼人眼目,感知‘入侵人的肌体’的‘挑衅性’和‘侵略性’”[2]。她散文中的写景状物,非表面空泛的形容,非静态的临摹,非平凡客观的写实,而是深入传神的刻画,是灵动新奇、动态十足的表现,凸现了自然景物张扬饱满的生命精神,散发出独特的动感魅力。
为表现事物的动态美,张晓风灵活调动了多种语言表现手段。其化静为动、以动写静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妙用动词,化静为动
要表现事物的动态,最关键的莫过于动词的运用,正如余光中所说,“景有静有动,即使描写静景,也要把它写动,才算高手……只会用形容词的人,其实不懂写景。形容词是化妆师,动词才是演员。”[3]张晓风在描写自然山水时,总是把焦点放在动词身上,通过动词的妙用来营造景物的动态感觉。晓风妙用动词的艺术手法主要有:
首先,发挥中国古典文学以动写静的艺术精髓,化叙为摹,化静态的描写为动态的叙事。这不仅可使静景动化,且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使一般动词在表现上艺术化、陌生化。
(1)我转身离去,落日在我身后画着红艳的圆。(《画晴》)
(2)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其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撒在花架上的,哗哗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花之笔记》)
(3)小草莓包括多少神迹啊!如何棕黑色的泥土竟长了灰褐色的枝子,如何灰褐色的枝子会溢出深绿色的叶子,如何深绿色的叶间会沁出珠白的花朵,又如何珠白的花朵已锤炼为一块碧涩的祖母绿,而那颗祖母绿又如何终于兑换成浑圆甜蜜的红宝石。(《咏物篇》)
例(1)中,个“画”字把落日写动了,普通的一个字让整个句子活了起来;例(2)中一连用了“开”、“泼撒”、“流下”、“淌”、“爬上”等动词,爬藤花开的各种姿态写得活泼灵动、生机勃勃;例(3)在顶真的句式里,连续变换运用“长”、“溢出”、“沁出”、“锤炼”、“兑换”等动词,将枝而叶、由叶而花、由花而果的整个成长过程以及其间不同颜色的更迭写得精确入微。
其次,大量选用幅度大、气势猛、量能十足的动词,有意识地从速度、力度、气势等方面加大动量。这不仅强化了动态事物的动作感,也使张的散文在秀媚之中透出刚健猛劲,正如余光中所赞,“张晓风不愧是台湾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
(4)春柳的柔条上暗藏着无数叫做“青眼”的叶蕾,那些眼随兴一张,便喷出几脉绿叶。(《咏物篇》)
通过一个“喷”字,本是缓慢而不显眼的植物成长过程被强化为具体可见、速度飞快的动作,动感效果格外显著。
(5)满山的牵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秋天 秋天》)
(6)疾劲的山风推着我,我被浮在稀薄的青烟里。(《归去》)
“冲击”一词不仅化静为动,并且使本是柔美的花儿具有了如海浪一样的强大力度。“推”写出了山风的力度之强,“浮”则从反面衬托了劲风疾吹的效果。
(7)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疏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情怀》)
(8)梅叶已凋尽,梅花尚未剪裁,我只能伫立细赏梅树清奇磊落的骨格。不可想象的是,这样寂然不动的岩石里,怎能迸出花来呢?(《常常,我想起那道山》)
“扑”强调了花香之浓郁和传递速度之快捷,“迸”字突出了梅花盛开的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强。动词的精心选用使上述二例气势磅礴,动感十足。
二、且拟且喻,生发动感
张晓风的语言运用技巧超乎常人,在她的散文中几乎所有常用的汉语修辞手法都有所涉及,但她最偏爱的手法莫过于比拟。她文中比拟之繁密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以致有学者命名为“艺术仿生学”[4]。它们或单用,或拟喻合用;或赋予自然生物以人的喜怒哀乐,或为无生命现象注入生机。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说:“诗人的声音不是发自自然,而是给自然以呼吸,让自然表达他的思想”,晓风正是这样一位给自然以呼吸、与自然同呼吸的深情“诗人”。以诗为文是她散文最大的特点,在她看来,“烟岚是山的呼吸”,“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扬起来的一声欢呼”,“土地一定是有生命的”,“颜色也是有欲望,有性格甚至有语言有欢呼的”,她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节逼得雨中行人连魂梦都走投无路的杏花,那些各式各流的日本花道纳不进去的,市价标不出来的,不肯许身就范于园艺杂志的那一种未经世故的花”。整个天地自然在她笔下被饱注了精、气、神,万物在悠然自得地轻舞飞扬,充满了勃勃的生命律动感。
(9)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春之怀古》)
(10)那时候,是五月,桐花在一夜之间,攻占了所有的山头。(《花朝手记》)
雷可以惹哭云,花与鸟争斗不休,桐花的盛开是对山头的攻占……在晓风的笔下,触目所及皆是生命的活泼与张扬,比拟的运用让其文字充满了强烈的动感。
除了单用拟人之外,晓风更多的是喻拟合用,二者的结合更增添了文字的威力。经济简短的文字迅猛出击,“把对象彻里彻外地写透写足”乃至“写到十二分”,让人在感受其想象的奇特之外更感悟其强烈鲜活的动感。
(11)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春之怀古》)
(12)荒旱的沙碛上,因为一阵偶雨,遍地野花猛然争放,错觉里几乎能听到轰然一响,所有颜色便一刹间窜上地面,像什么壕沟里埋伏着的万千勇士奇袭而至。(《矛盾篇之三》)
在这里,春天如被企盼多时的王师,所向披靡,赶走了肆虐多时的风雪,而桃花正是它的先头部队;沙碛野花的争放有如伏兵瞬间奇袭而来,本是风花雪月的景致在晓风的笔下硬是写出了“刀光剑影”,显得“杀气腾腾”。
三、巧写幻觉,动化感觉
1.运用通感
人的心理感觉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当人们感知某一客观事物时,不仅引发相应的感觉,大脑中原先贮存的来自其他感官的感知信息、经验、记忆,经过想象和联想,会自动对此感觉进行补充,并把一些没有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赋予它。这种基于经验和习惯而产生的不同感官之间在心理上的相互勾通即为通感[5]。它不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往往呈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幻觉,但这种幻觉有助于更真实生动地表达人们对客体的直觉和体验。晓风在写作中常利用通感,将视觉感受转化为听觉、味觉、嗅觉、压力等多种感受,将个人的感觉经验动态化,增强了写景的动感效果。
(13)残霞仍在燃烧着,那样生动,叫人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听到火星子的劈拍声了。(《归去》)
(14)对了,就是这灿白,闭着眼睛也能感到的。在云里,在芦苇上,在满山的翠竹上,在满谷的长风里,这样乱扑扑地压了下来。(《秋天.秋天》)
(15)阳光的酒调得很淡,却很醇,浅浅地斟在每一个杯形的小野花里。(《魔季》)
例(13)中用“燃烧”把视觉感受转化为触觉体验,并幻化成听觉感受;例(14)中的“压”字,让本是视觉感受的灿白仿佛有了沉甸甸的压力感;例(15)中的阳光如酒一样淡却醇香,将视觉形象幻变为味觉和嗅觉。多种感觉的并现带来了表达上的生动鲜活。
2.变换视点,倒置主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本是动态的审美主体,山水是静态的被审美的客体。但晓风在写景时,有意变换视点,倒置主客关系,写出了一种奇妙的幻觉——自然幻化成主体,成了动作的主动发出者,人则退居成被动的客体,转为静态的动作的承受者,由此巧妙地将静态的景物动态化了。
(16)而方才幻灯片上的山水忽然之间都遥远了,那些绢,那些画纸的颜色都暗淡如一盒久置的香,只有眼前的景致那样真切地逼来,真把我逼到一棵开满小白花的树前。(《咏物篇》)
(17)船在长江上走,两岸风景逼人而来简直是一场美的夹杀。(《同色》)
(18)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的,简直是绿色的花瓣……(《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例(16)中本是人走近花树,却变成景致把人逼向树前;例(17)中,两岸风景不仅逼人而来,且可以对人形成“一场美的夹杀”,两个“逼”字具有同等的动感催化作用;例(18)中本是船动人动山不动,但用“叠”字却写出了人不动而山动如花盛放的美妙幻觉。
四、对比夸张,强化动感
对比和夸张乃是不同的修辞手法,对比涉及对照和比较的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夸张只关涉被夸大的单一事物,但二者在表达效果上具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对事物进行了强调和突出,通过加大其某一特性的程度使事物更加鲜明。晓风在写景时,常对事物进行对比或夸张,有意加大动感的强度,予读者更深刻的印象。如:
(19)有些美,如山间月色,不知为什么美得那样无情,那样冷绝白绝,触手成冰。无月之夜的那种浑厚温暖的黑色此刻已扯开。(《春俎》)
(20)两侧的山又黑又坚实,有如一锭古老的徽墨,而徵墨最浑凝的上方却被一点灼然的光突破。(《春俎》)
(21)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雨之调》)
同样是写黑夜中的光亮,例(19)中在通感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比,“触手成冰”“冷绝白绝”的月光硬生生地把温暖的黑色“扯开”,生动地展示了月光进入夜色的力度和冷暖的对碰;例(20)中则比喻、对比兼用。夜幕下,如古老黑墨的山被“一点灼然的光突破”,在展现山色的厚重无边与亮光的凝练耀眼的同时,强调了亮光切割夜色的艰难;例(21)中用“广不可及”的灰来烘托一株莲花的红,用雨的“漠然”的来反衬红莲如“即将燃起的火”一般的热烈,莲花的卓尔不群跃然纸上。
(22)少年游狮头山,站在庵前看晚霞落日,只觉如万艳争流竞渡,一片西天华美到几乎受伤的地步。(《花朝手记》)
(23)那年春天,波斯菊开得特别放浪,我站在花园中间,四望皆花,真怕自己会被那些美所击昏。(《初绽的诗篇》)
(24)真的,山月如雨,隔着长窗,隔着纱帘,一样淋得人兜头兜脸,眉发滴水,连寒衾也淋湿了,一间屋子竟无一处可着脚,整栋别墅都漂浮起来,晃漾起来,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惊惶。(《春俎》)
落日晚霞可以美到让人“受伤”,花儿的美可以把人“击昏”,山月如雨,可以把人连同屋子里的一切彻夜“淋湿”,以至让人产生“绝望的惊惶”。如此极致的自然之美在敏感热烈的晓风心里引起的强烈震撼,非夸张难以尽言。
五、活用词性,表现动感
晓风不仅深谙动词增动之效,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她还晓知词性活用之妙。她曾经举例分析过余光中散文中词性代换的惊人之笔,对于余光中散文语言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性的变化与互用,给予极力赞赏。在写景中,她自己亦擅长词性的活用,利用特定的语境将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藉此手法来表现事物的动感。如:
(25)那一树桅子花复瓣的白和复瓣的香都留在不知名的篱落间,径自白着香着。(《咏物篇》)
(26)典型的台湾乡间的景色,秧针绿在水田里,鹭鸳白在田埂上,小小的四合院隐在山阿里,青苔覆瓦,杜鹃踯躅在在山边水湄。(《中庭兰桂》)
例(25)中,“白”、“香”活用为动词,并与名词化的白与香相搭配,使得花儿的色与香浓郁袭人;例(26)中,“绿”、“白”活用为动词,与下文的“隐”、“覆”、“踯躅”等动词相呼应,一串漂亮的排比句让台湾乡间景致跃然纸上。
(27)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一珠红莲!(《雨之调》)
(28)有时,一夜之间,花拆了,有时,半个上午,花胖了。(《咏物篇》)
例(27)中的形容词“红”与“香”活用为动词,用“将红未红”、“待香未香”写出了一种美在揭晓之前令人向往的神秘和夺目;例(28)中,一个“胖”字,形容词用为动词,幽默感十足地浓缩并动化了花开的过程。
综上所述,强烈的动感是张晓风散文的突出特点,其散文以用好、用精动词为核心,并调动起多种修辞手法,展示的不仅是自然景观的静态的外在之形,更发掘出自然之物内在的生命精神,充满生命的动感。她的文字不是纯客观的外在景观的描述,还是作者主体精神的观照和外在投射。不仅用眼睛观察、发现自然,更以心灵的直觉和想象去重组和再造自然,是晓风“以眼观物”到“以心观物”的自然结果,这使得晓风笔下之景,已非如实呈现的自然之景和一般的经验感受,而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对自然之景的变形,充分体现了文学语言的变异美。
[1]徐光萍.生命的笺注—张晓风诗性解释散文解读[J].江苏大学学报,2003(12):79-82.
[2]楼肇明.张晓风散文论[J].文学评论,1994(1):106-117.
[3]李军.语用修辞探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248.
[4]楼肇明.星约·情象·诗课[M]∥张晓风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371-397.
[5]李荣启.文学语言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7.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Zhang Xiao-feng Essay’s Language
ZHAN Xiu-hua
(Zhongshan College UEST of China,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02, China)
As a famous essay writer from Taiwan, Zhang Xiao-feng is an expert at converting static state into dynamic state. Her essay’s language not only embodies classical beauty,polychrome beauty and musical quality, but also is full of impressive emotions. She express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verb, and utilizes plenty of rhetoric skills such as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synaesthesia and exaggeration. Her essay’s language not only shows the static state of nature, but also infuses new life and energy into natural things, so it is full of especially dynamic enchantment.
dynamic; personification; synaesthesia
2013-10-17
詹秀华(1969- ),女,江西婺源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硕士,从事语言学研究。
I207.6
A
2095-7602(2014)02-0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