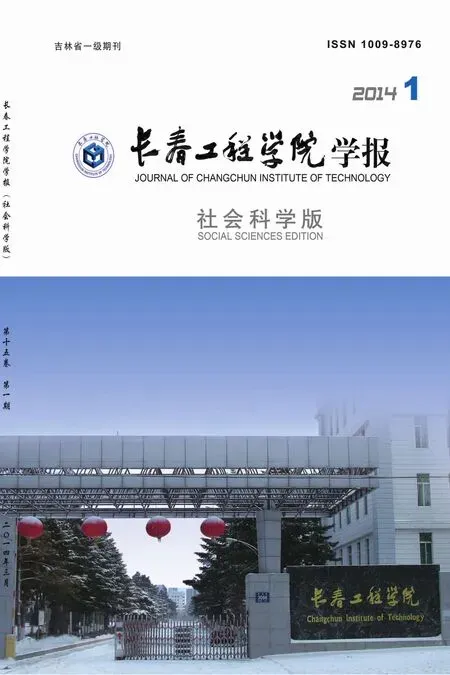浅析六朝诗歌中的江南意象
李纯海,韩小婷
(西华师范大学,南充 637000)
文学的地域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六朝时偏安一隅的南方政权,使得江南地区得到长期的发展。由此衍生出来的江南意象便成为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产物。江南意象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所必须重视的方面。江南意象是从江南特有的地域地貌及其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它兼有空间地域与文化特质的内涵。六朝时,南方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江南意象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自六朝伊始,历代诗人创作中对江南风物诗化的努力,则为江南意象的形成提供了主观的条件。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籖》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可见诗歌各体,各有所重。与近体诗相区别的古诗则强调了“求意象”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
一、江南意象的定义
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心理嗜好:喜好江南。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化中强化着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对江南的认同感。江南,又称江东、江左,作为地域名称历史悠久。但关于江南的范围,长期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的《史记》中说:“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道出了他笔下的江南区域。随着历代对南方的开发与拓殖,江南概念也越来越延伸。广义之江南多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狭义之江南特指吴越之地。随着晋室南渡,荆、扬二州逐渐成为南朝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发展极快。六朝都城,均立于建康。最终形成了一个与北方相区别的独特文化区域。司马迁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长久以来江南以地域蛮荒,物质丰饶而著称,秀美的自然地貌,也多令人神往。江南以一种特有的神秘感,一直萦绕在我们眼前。纵观历史,“南方的发展由点到面,由经济的繁荣到政治中心的形成,由偏安一隅到变为正朔所在,政治的正统吸引着士人们,文化中心的形成也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了”[1]。
由此可见,江南起初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但随着历史发展,范围不断外延,最终演变成为一个独具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地理文化概念。本文对江南概念的选择,主要是选择狭义范畴上的江南,来进行表述。
对于何谓意象,简而言之,意象就是创作主体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将客观物象融入其主观情感而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克罗齐在《美学》中曾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2]由此可知,意象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是自然的外在景象与作者的内在情意的统一。意源于作者的内心世界,象是意的载体,诗人们通过借助物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赋有了某些特殊含义和文学韵味的一种有意义的具体形象。
所谓江南意象,就是指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将涉及到江南地区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地理名称以及人物形象等意象群用来反映其主体情感。这些意象总的特点就是带有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等显著特点。六朝诗人们将自身的主观情感和人生感悟,融汇于秀丽的江南美景中,或者是通过借助这些意象来反映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意念情愫,以期提升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内涵。
二、江南意象的分类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会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江南是一个宽泛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文化的核心区。由于地形使然,主体创造视角的不同,因此六朝诗人们笔下描绘的具有江南特色的意象渐显多样化趋势,可谓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六朝诗中描述的江南意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自然意象、人物意象、地名意象。下面本文分别加以举例说明:
(一)自然意象
六朝人对山水自然景物的热衷,可以折射出时代的背景。六朝政权,偏安南方,加之政治黑暗,政权更迭频繁。士子忧生惧祸、儒家入世主张不再那么吸引人,“而他们纷纷云集于川泽成网、雨水充沛、林木蓊郁、山峦苍翠的江南水乡,在此开始了他们吟赏山水的生涯。谢灵运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3]诗人们经常流连于此等地理环境之中,自然而然地增强了对自然景观的发现与欣赏。
六朝人对山水自然的喜好情怀,虽有纵情山水、明哲保身的政治因素,但对于江南山水自然的热衷,确实是发自内心,他们对自然山水都有其浓厚的审美兴趣。无论是庙堂士大夫、还是林间古处士,无不情牵于此。因此,江南在众多的诗文作品中,在六朝诗人们的生花妙笔下,形成了的绮丽、秀美的典型自然意象。六朝时期大量的诗歌描写到了江南的秀美风景。归纳以来,涉及自然意象的主要包括描写时节、青山、绿水、树、花草等。
时节:暮春、三春、“暮春春服美,游驾凌丹梯。”(谢朓《登山曲》)、“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三》
山:南山、“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况复南山曲,何异幽栖时。”(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南国多异山。杂树共冬荣。”(江淹《渡西塞望江上诸山诗》)
水:春水,绿水“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顾恺之《神情诗》)、“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刘孝绰《赋得始归雁诗》)、“绿水溅长袖,浮苔染轻楫。”(梁简文帝《北渚》)
树:梅、芳树、修竹、柳。“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西洲曲》)、“芳树归飞聚俦匹,犹有残光半山日。”(萧子显《乌栖曲》)、“风荡飘莺乱,云行芳树低。”(谢朓《登山曲》)、“上林杂嘉树,江潭间修竹。”(徐陵《咏柑》)、“丝条变柳色,香气动兰心。”(庾信《咏春近余雪应诏》)
花草:江南莲、江南草、蔓草。“江南莲花开,红花覆碧水。”(梁武帝萧衍《四时子夜歌·夏歌》)、“山中工杜绿。江南莲叶紫。”(谢跳《往敬亭路上》)、“沙棠作船桂为楫,夜渡江南采莲叶。”(梁元帝萧绎《乌栖曲》)、“汉渚水初渌,江南草复黄。”(梁简文帝萧纲《从顿还城诗》)、“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陶渊明《乙酉岁九月九日》)、“蔓草缘高隅,修杨夹广津。”(鲍照《行药至城东桥》)
(二)人物意象
《绀珠集》记载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而少刚,笮之则服。”独特的自然地貌造就了江南地区的人文风俗,其诗风自然就会绮艳清丽、明快自然了。屈原在《离骚》中以美人自喻,“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采莲可能从那时起就与美人有了关联,一提起采莲,似乎就看见了美丽动人的采莲女。一提起江南,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了。六朝时期的采莲女形象如出水清莲,鲜活动人。吴均诗“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诗中的采莲女锦带罗衣,额前还贴有动人的花钿”。梁武帝诗中的采莲女“江花玉面两相似”及梁元帝诗中采莲女的“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荷叶和罗裙,荷花和面庞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将一个美丽动人的采莲女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人物意象主要包括:越女、采莲女等。
越女:“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莲曲》)
采莲女:“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西洲曲》)、“晚日照空矶,采莲承晚晖。”(梁简文帝萧纲《采莲曲》)、“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梁元帝萧绎《采莲曲》)、“涉江竟何望,留滞空采莲。”(江淹《贻袁常侍》)、“舆童唱秉椒,棹女歌采莲。”(鲍照《拟青青陵上柏》)
(三)地名意象
南朝诗人谢朓,在其诗歌《入朝曲》中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赞美江南风景秀美,金陵具有王者之气。“江南佳丽地”用以描绘江南地区的秀丽繁华,盛赞金陵帝王之都的辉煌景象,在诗人的描绘中尽显江南特色,又在词句的对偶中使地域特征意象化。
地理环境的制约与规定,风俗习惯的影响与渗透,能够使文学的传统得以长时期的保留。六朝时,由于富有江南城市生活色彩的诗歌的流行,在诗歌中就出现了一些经常被诗人们吟咏的典型江南城市,如“扬州、金陵”,它们成为了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城市意象群,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扬州这个地名意象。由于建康是六朝扬州州治所在地,因此六朝时期建康一般也称为扬州,治所兼具中心城市的特点,扬州自然就成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心城市、中心区与边缘区域构成了一系列特殊的文化景观,与其他文化区域互相区别,显示出本区域的独立品质,这也是“扬州”作为语象总是出现于诗歌中的原因之一。
由于江南地区河港交叉,水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可谓是“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与人文地理优势相叠加,经济与文化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使其更容易成为在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地名意象。总之,地名意象包括:吴江、长江、五湖、扬州、金陵等。
吴江:“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妒鱼肥。”(张翰《思吴江歌》)“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江淹《赤亭渚诗》)
长江:“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陶渊明《拟古诗》)、“种莲长江边,藕生黄蘖浦。”(《读曲歌》)(萧衍《采莲曲》)
五湖:“妾家五湖口。采菱五湖侧。”(费农《采菱曲》)
扬州:“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臧质《莫愁乐》)、“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释宝月《估客乐》)、“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刘诞《襄阳乐》)
金陵:“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
四、江南意象的影响
江南意象在六朝诗歌中的频繁出现,使得江南地域的文学审美性得到充分发掘。江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普遍走入人们的关注视野,由此而引发了历代士子文人对江南意象的不断探索与挖掘,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对唐诗影响最大。六朝诗歌的发展,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江南意象的出现,为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及后世山水作品,提供了摹仿和借鉴的范式。在艺术表现方面,六朝诗人们作了不懈的努力与多方的探索。因此在语言选择运用、审美风格取向、意象生成与构造等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唐诗的发展与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后世诗人在选择诗歌语言上,往往偏好于富有江南特色的意象化诗歌语言,江南意象为其创作诗歌语象提供了参照与依据。一系列清新、绮丽的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成为诗人们倍受青睐的选择对象。所谓“江北、江南,诗家常用”。唐诗中就有“江南好、忆江南、望江南”等诗句。唐代也有很多的《采莲曲》,如王昌龄、白居易等人的作品,都由最初的模拟六朝而愈见清丽工整。后世还有众多美妙的叙事、典故、诗章、名句、意象以及逸事集中浓缩于“江南”一语,而且诗人文学家,心心相印,文脉相承,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意象诗歌语言的传统。
其次,是意象审美风格的影响。六朝诗歌不仅生成了很多的江南意象,而且还奠定了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就表现出江南地域特有的审美风格。以及后世江南意象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辞章,已成为中国永远的抒情性审美经典。江南寒山寺的钟声、“家在江南黄叶村”的画意,亦已远播异邦,泽及全球华人文化圈。
第三,意象生成与构造方式的影响。六朝时生成了明丽清新、清巧多姿、语象丰富的江南意象,这都与诗歌的意象构造方式有关。六朝诗人开始重视诗歌的形式美,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开始注重诗词的格律,同时运用对偶与双关的修辞手法。唐人对于六朝诗歌的接受与继承是深入而广泛的现象。而后世诗歌创作又多师法于唐代。由于唐人对六朝诗歌持有一种积极、创造性地吸收态度,才迎来了唐诗的发展的全面繁荣,才达到了古代诗歌艺术创作的最高峰。而在汉魏六朝诗歌在诗歌史上也圆满地完成了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
“江南”所指涉的空间,与其说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不妨说是由具有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的特定人物和地点、象征与意象等,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六朝时江南由地理区域名称转化为诗歌意象,由此产生的独具一格的江南意象,使得江南地域自然和人文的审美价值被发现。六朝诗人们沉浸其中,反复吟咏,他们把对自然山水的热衷和欣赏融入到作品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清新自然的诗歌语言风格。随着六朝诗歌的传播与影响,江南意象也逐渐深入到后世诗人的创作意识中。江南意象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地域特色的审美意象。
[1]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
[2]朱光潜.诗论[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47.
[3]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80.
[4]郑华萍.论陆游词中的江南意象[J].文教资料,2012,(32):49-52.
[5]张凤.六朝诗歌中江南意象的生成与构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0:1-68.
[6]左鹏.论唐诗中的江南意象[J].江汉论坛,2004(3):95-98.
[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詹英.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