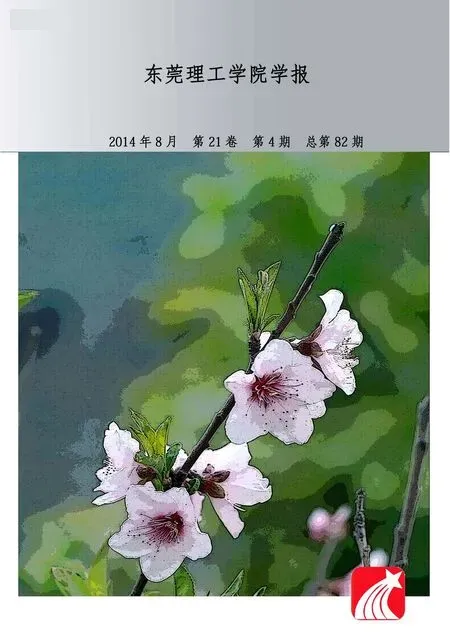语言体验性及其象似性研究
冯建明
(广东医学院 外语部,广东东莞 523808)
人类语言源起何处?这是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千百年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无论是西方宗教神话中的“语言神授”说还是现代语言学中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似乎都未能揭示语言起源的真相,但“语言体验”观的提出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该观点认为语言源自人类与世界的互动和体验,是客观世界经由认知世界投向语言世界的结果。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构成了象似性的生存基础和存在价值[1]406。语言体验观的提出不仅真正解开了语言的本源之谜,而且对于语言学中的老问题“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之争”而言是一个终止符——体验性和象似性一脉相承,承认语言的体验性,必然可以得出象似性的结论。本文拟从体验性探究入手,旨在论证和强调象似性存在的合理性,并以语言中大量的象似性语言事实进行证实。
一、体验性——语言的始源
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中国古代学者早就提出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体验性观点。成书于商末周初的《周易·系辞下传》明确阐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先民们通过各种感官去感知和认识自身以及周围事物,借以生成最基本的象征符号“八卦”,体现了语言体验性的基本思想。战国末年的荀子在《正名篇》里提出“待天官之当簿其类”、“心有征知”、“然后随而命之”等重要观点来论述词语产生的过程。人类借助“天官”(即五官)与客观世界接触,形成感性认识,然后依赖“心”(即天君)对五官感觉到的各种材料进行理性辨析和验证(即征知),从而形成概念,“然后随而命之”,给这个概念进行“制名”。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闪烁着语言体验性的思想: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心声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的活动和体验是概念形成的关键因素,语言的产生离不开“人”这一万物之灵,强调了语言生成过程中的人本性和人类中心思想。
西方语言学者就语言的起源问题也提出过种种观点和假设。Herder[2]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并以人类对“羊”的取名为例,详细阐释了语言起源的心理过程。Jespersen[3]对语言的起源概括出了四种假说:摹声说、感叹说、本能说和喘息说,而另一位语言学家Aitchison[4]105则归纳出三种可能:对自然界(首先是动物)声音的模仿,由于口唇喉舌的自然动作而发出的声音和原始的歌声,并认为人类语言的起源是这些因素相互促进的结果。远古人类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体验和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独特的身体构造和感觉器官去感知周围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感觉;体验的结果经过组织分类和岁月沉淀,固化成某种心理印象,于是诞生了语言的内在形式——概念。“语言体验说”否定了语言的天赋观和先验论,强调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体认”特征。既然认知是体验的,那么认知的结果——语言自然也具体验性。
语言体验性在当代语言学领域中的显贵——认知语言学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领军人物Lakoff 和Johnson 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 Johnson,1980)、《火、女人和危险事物》(Lakoff,1987)、《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Lakoff & Johnson,1999)中着力阐述了贯穿始终的语言体验性思想。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先祖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心,天生就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这种与生俱来的“体认”思维本能地以各种经验作为认识和衡量外部世界的标准和参照点,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理解,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身体各部位和区别这些部位的功能以及我们身体与外部世界的空间联系。”[5]体验的结果就是概念的形成,故而Lakoff和Johnson[6]497强调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抽象的概念被物化成外部的显性形式,于是产生了语言符号。因此认知语言学认为,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心智是体验的,意义是体验的,思维也是体验的,这是体验哲学的核心[7]249。体验主义成为语言生成原始动力的这一假说也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如Berlin 和Kay(1969)对颜色词的研究,Rosch(1978)关于基本层次范畴的确定,Stern(1985)有关婴儿身体性逻辑的实验,以及大量的概念隐喻研究,它们从实证的角度有力论证了体验性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自然世界是包括人类语言在内一切非物质形态生发繁衍的根基和本源,但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及其行为活动,仅凭客观世界自身是无法创制语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体验性才是语言萌芽和成长的真正始源。语言的体验性始源特征为解决语言符号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语言象似性研究提供了认知基础和理论支撑。
二、象似性——语言的本质
《周易》、《正名篇》、《文心雕龙》等中国典籍关于语言体验性思想的阐述,以及西方关于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说,已经蕴含了语言—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样的观点。事实上,语言象似性研究历史久远,造字圣人仓颉模仿万物之状创造了古代象形文字;作为中国哲学和文化之源的《易经》明确提出了象似性的观点:“是故《易》者,像也;象也者,像也。”八卦依据“观物取像”和“寻像归意”而得以形成,直接体现了象似性思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基于取像构字的造字原则,提出“文者,物象之本”的观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自然的联系,名称必然对应于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本质,语言结构映现了世界结构。近代普通语言学创始人洪堡特[8]70指出“(大自然中)这一切我们都在语言的种种相似之处中一再见到,并且语言能体现出这一切。因为在我们借助语言进入一个语音世界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语言的结构规律与大自然的规律近似”,从而提出了“语言与世界同构”的观点。现代语言哲学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9]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表示:“……然而这些符号语言却表明,即使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它们也是其所表现的东西的图像”,“命题是实在的一幅图像”,这些思想被概括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理论,成为象似性理论的重要源头。
中西方学者早就意识到,语言——通过人类体验这一手段和媒介——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因而具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符号总是天然地代表着它所指称的那个对象,都是象似的,但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语言研究传统,尤其是近代索绪尔结构主义的盛行,语言象似性思想一直未占主流地位。
20 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的认知语言学使得符号象似性研究重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虽然与索绪尔同时代的另一位符号学大师皮尔斯[10]106提出的“每种语言的句法结构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观点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但他关于符号的理论构成了其后认知语言学中象似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遵循“世界—认知—语言”这一原则,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人对世界的体验认知,才使得语言和世界的联系成为可能,具有某种相似关系。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对象似性现象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Haiman 将象似性分为动因和同构两种,前者指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外部象似性,后者指语言内部符号之间的内部象似性。Newmeyer[11]认为语言符号的外形、长度、复杂性及其构件之间的关系总是平行于被其所编码的概念、经验和交际策略。Dirven[12]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象似性是认知语言学突破传统语言思想的五大创造性思想之一”。
三、象似性在语言中的表征
象声(拟声)、象形(拟形)是语言符号最基本、最古老、最自然的产生方式,从语言起源的角度看, “象声和象形是人类所具有的符号化认知能力的两大渊源。”[13]65自然语言中大量的象似象征现象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语音象似是语言象似性最为本质的特征。上古时期人类先祖借助其独有的发音器官模拟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声音和动物的声音以及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每一个音(元音和辅音)在形成之初都与人类的感觉印象存有某种联系。音义学家研究发现,单个的辅音或元音都可能带有意义;持“存在普遍论”观点的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皆有“声”(能的一种形式),且凡“声”皆传义,只不过我们暂时不能全部解码其互相传递的物理的、生物的或心理的信息罢了[14]158。例如音素“i”在发音时开口度小,声音小,因此表示“小、少、弱”等,如英语中little,mini,kid,teeny 等,以及汉字粒(li)、细(xi)等;而音素“a”,口型大,声音大,故使人联想到“大、重、远”等,如vast,sharp,far,以及大(da)、炸(zha)、哗啦(hua la)等。英语中圆唇辅音“r”代表圆形,如ring,round 等,汉语则用圆唇元音“ü”来表示,如“卷”“圈”等。再如齿龈擦音“s”常与蛇的“咝咝声”、风的“飕飕声”相联系,鼻音“m”发音低沉不清晰,常表示“咕哝”、 “嗡嗡声”等。语言中还存在语音联觉现象,即一些音的组合也能传递固定的语义联想,如“gr-”带来的心理特征是“沉闷而令人不快的声音”,如grumble,groan; “-ump”有“沉重下坠”之感觉,如dump,stump。音义之间的象似性和人类天生具有的通感联觉在许多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如心理学家克勒的“圆-尖角星效应”实验(1929),额斯泰尔与多斯特的“情感词辨析”实验(1965)等。从根本上讲,音义结合本是有理据的,只不过后来的语言使用者更关注语言的工具性而疏忽了其背后的象似本源性。
语言中不仅存在音义象似,也存在形义象似,即所谓象形、拟形。根据图画或图形创造文字表达意义是全世界文字起源的共同基本特征。人类文字,不管是表意文字还是拼音文字,如果追根溯源,都脱胎于图形,最初都经历过图画文字阶段和象形文字阶段。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具有最鲜明的象形特征,虽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简化,至今已失去了最初直观的象似特征,但仍可依稀辨析其图象痕迹。其他如古埃及圣书字、古印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美玛雅文字等也都源于图画文字。事实上,不仅表意文字具有形义象似关系,拼音文字也是如此。研究表明,英文26 个字母最初也是起源于象形,描摹动物或事物的形状。这些图画文字历经多次辗转借用,演变成今天广为流通的抽象符号,其演变路径大致可回溯为“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希腊字母→腓尼基字母→塞母字母→楔形文字+ 圣书字”,其源头发端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所使用的象形文字。比如英文字母“A”,其最初的形状在一千多年前的腓尼基字母表中为“V”,中间加一横,形似牛头或牛角。这是因为“牛”这个动物在古代腓尼基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象征着财富,因此被置于字母表中第一位。后来希腊人将它倒过来书写,沿用至今。英语单词的首字母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整个词,因此“wave”之意来自形似水波的“W”; “H”貌似两根树枝搭成的篱笆,因而许多以它为首字母的单词常常具有“房子、保护、阻碍”等义,如hedge,helmet,hinder,hut。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的“以形求义”(以及“因声求义”)等传统研究方法也适用于表音文字系统。
象似现象也大量体现在语言的句法层面和语用层面。沈家煊[15]2认为,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据的,也就是说,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关系。认知语言学概括出三类主要的象似性原则:顺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原则指的是句子成分的线性排列顺序与其所要表达的实际事件或状态的先后时间顺序相一致,如凯撒名言“Vedi,Vidi,Vici.”(I came,I saw,I conquered.)“He opened the door and came in.”“毕业之后,我要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一个可爱的孩子。”距离象似性原则指句子成分之间形式上的间隔距离与其所表达的事物距离或概念距离相一致,语符距离越近意味着概念也越接近,反之亦然。例如“the handsome young Chinese sportsman”、“数十座漂亮的老石头房屋”中多个修饰语的不同排序反映了它们与中心词的概念距离:距离越近则表明与中心词的关系越密切,越体现中心词的概念内涵,距离越远则越来越指向它的概念外延;又如在“I don’t think Tom can win in the game.”“I think Tom can not win in the game.”
两个表示否定概念的句子中,后句中否定词not离情态动词can 的距离较之于前句中的距离更近,因此后句的否定力度更大。数量象似性原则指语言形式或结构的复杂性反映了概念结构的复杂性,语符数量与所传达的信息量以及概念复杂程度呈正比关系。例如“He is short. He is very short. He is very very short.”中的第三句以及李清照词《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通过词汇重叠现象传递出更多的信息量,表达了言者(作者)某种强烈的态度和情感。Greenberg[16]曾指出,世界上有复数形式比单数形式长的语言,却没有单数形式比复数形式长的语言。至于语用层面的象似性现象就更多了,例如在人际交往中,关系越亲密语言越简单,关系越疏远语言则越复杂。以“开门”这一动作为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形式:“开门!” “开下门吧!”“能否开下门?” “劳驾开下门好吗?”随着语言形式的逐渐冗长则透露出越来越远的社会距离,语气也显得越来越有礼貌。同样情况英语中亦是如此。
四、结语
语言体验性揭示了语言的本源,强调语言的体验性是为了论证象似性这一语言的根本属性,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象似性是对索绪尔任意性的彻底反动,它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揭示语言、认知和现实的必然联系。象似现象普遍存在于语言中,支配人类语言的是象似性,而非任意性,推动语言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象似性认知机制。语言的体验性和象似性研究对语言教学极具指导意义,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体验展开积极联想,思索语言形式背后的象似关系和认知机制,解读基于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形式本体观教学法”所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从而实现语言体验性和象似性理论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1]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Herder J G. Abhandlung 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Jespersen Otto. 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M].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413-416.
[4]Aitchison Jean. The Seeds of Speech: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96-98.
[5]Ungerer F,Schi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6]Lakoff G,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Basic Books,1999.
[7]Johnson Mark,George Lakoff.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J]. Cognitive Linguistics,2002,13(1):245-263.
[8]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70.
[9]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3-34.
[10]Peirce C S.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 Buchler[M].NY:Harcourt,Brace,1940.
[11]Newmeyer F J. Language Form and Language Function[M].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114-115.
[12]Dirven Ren. In search of conceptual structure:Five milestones in the work of Gunter Radden[M]//Hubert Cuyckens,Thomas Berg,Ren Dirven. Motivation in Language,viii-xxvii.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3.
[13]李葆嘉. 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63-66.
[14]Agrawal P L. Theory of phonosemantics[M]. Jaipur:Universal Theory Research Center,2010.
[15]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2-8.
[16]Greenberg J H. Universals of Language[M]. Cambridge MIT Press,1966:7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