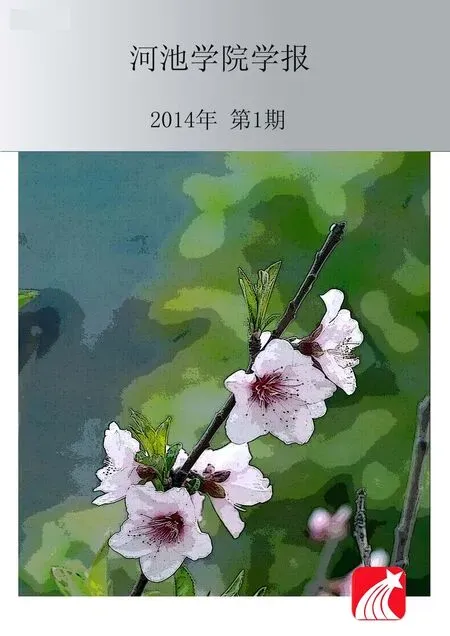1949~1966:广西当代文学体制的建构与《广西文艺》的变迁
陈代云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新中国的文学体制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确立起来的:它把文学看成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并将工农兵想象成隐含的读者,重视民族民间文学在建构“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反对除此之外的个人的文学品味和艺术旨趣,将“人民”看成是一切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一次文代会还有另一个重要成果,即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协),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扬以中宣部副部长之身份兼任文联副主席,具体阐释党的文艺政策、部署文艺运动、开展思想斗争。就这样,通过中宣部、文联和作协,党对全国的文艺活动进行指导和指挥,同样,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文艺机构,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开展文学活动,维护新中国的文学体制。
广西当代文学体制当然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但因为有边缘和民族的双重“身份”,所以广西力图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和民族的“自我意识”中间寻求一条“本土”的当代文学体制的建构路径。然而,对于如何掌控两者的尺度,广西作家显然没有直接的经验,尤其是在广西作家文学蓬勃发展的解放初期,他们总是在党和国家的“规定”、民众的“需求”和自我的“文学想象”中不断徘徊,不断地调适,不断修正,也正因为如此,广西在建构文学体制的过程中才显示出特殊的意义。
刊物是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往往能体现文艺政策的“风向”,从中也可以“捕捉”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基本态度。1950年2月,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6月,经周钢鸣、陆地、冯培澜、胡明树、苗延秀等人的共同努力,广西召开了全省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以周钢鸣为主任、陆地为副主任、冯培澜为秘书长的广西省文联筹委会,代行文联工作,负责组织文艺队伍、创办文艺刊物,开展文艺创作。1950年10月,《广西日报》开辟《文艺》旬刊,1951年6月,《广西文艺》创刊,1957年1月停刊,另办《漓江》,《漓江》1958年1月停刊,3月,广西省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同月,《红水河》创刊,1960年,《红水河》停刊,《广西文学》出版,同时又另创《广西艺术》杂志,1961年,《广西文学》和《广西艺术》、《群众艺术》合刊,《广西文艺》再度面世,直至1966年因文革而停刊。可以看到,1957年至1961年短短数年间,《广西文艺》多次易名,曾依次改为《漓江》、《红水河》、《广西文学》,最后依然以《广西文艺》为刊名出版。这一频繁更名现象背后不仅包含着广西文艺界对国家文艺政策的应激性反应,同是也包含了广西作家对民族性、地方性文学发展的思考。
早在创刊之初,《广西文艺》就确立了基本的编辑方针,即把《广西文艺》办成“地方性的、群众性的、通俗性的文艺刊物”,“本刊的读者对象不能是包罗各阶层群众兼而有之的一般性群众,而应该是工农兵群众,最低限度通过工农兵干部而能为工农兵群众所接受,因此在作品内容上不能像过去一般文艺杂志那样以占大量篇幅的小说、剧本、诗歌为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以短小精悍的易为工农兵接受的通俗的民间形式的作品为主。”[1]正是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之下,新生的《广西文艺》发表作家文学作品的比例并不大,故事、寓言、童话、山歌、地方戏等民间文学作品是其主要内容,有时候还会穿插歌曲、连环画、版画等其他艺术形式。标举与“一般文艺杂志”的区别,固然是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学创作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但至少还隐含着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工农兵”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他们更乐于接受(或者只能接受)通俗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第二,在现代文学史上,广西的作家文学并不发达,在解放初期还形不成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因此,直接从作家文学的角度去构建广西新文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1952年5月,广西文联筹委会举办了“红五月”工人文艺创作征文比赛,先后来稿30篇,获得一二三等奖的4篇作品,其题材分别是鼓词、报告、方言剧、诗歌。由此可见,在刚刚解放的时候,广西的群众文学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50年代中期以后,广西的作家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摆脱民间文学的“限制”常常是广西作家努力的目标之一。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双百方针”,接着,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藉此时机,《广西文艺》更名为《漓江》,树立起作家文学的标准,展开了文学本土化的想象。时任主编的胡明树以散文的笔调创作了创刊词,在该文中,他写道:“广西的自然景色就是一个大公园”,“在广西,民族民间文艺有着丰富的遗产”,“广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些特产,都是和广西农民生活分不开的”,“广西正在发展着新的工业”,“到处都是新的生活,新的面貌”,“凡这些,都将成为构成以反映广西各族人民生活为中心的刊物的特色,刊物的风格。”[2]胡明树将广西的自然风光、民族传统、革命历史以及工农业生产等都纳入“各族人民的生活”,对广西文学的“多样性”充满了热情的期望,同时,在创刊号上,《漓江》还将所发作品主要分为“诗歌”、“小说、特写”、“杂文、小品、随笔”等三个板块,暗合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传统“四分法”,由此表明与《广西文艺》的差别。
《漓江》虽然沿用了《广西文艺》“地方性”、“通俗性”、“群众性”的办刊方针,其实以“编辑部”为代表的作家们早就意识到了广西作家文学的兴起和人们群众对文化艺术生活的多样性需求,所以在1956年《广西文艺》停刊时,编辑部就假定即将面世的《漓江》的读者群,“包括工农兵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文艺爱好者、青年文艺写作者和爱好者、国家干部、教员、学生等等。”[3]强调读者应有一定的文学水平或许符合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但这一要求在本质上和延安文学是相左的。早在1949年,茅盾就意识到,“文学和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说:诗歌、戏剧、小说、绘画、音乐等,要描写工农兵,以及工农兵的干部,要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4]无论题材、主题还是言说方式,艺术都应以工农兵为准则,但五四新文学传统是以“西方”为资源,“启蒙”和“救亡”为目标的作家文学,所以常常被批评为西化、知识分子化和脱离群众,《漓江》对“文学性”的要求一旦放在为“工农兵”的天平上,便很容易倒向“错误”的一边。
1957年6月,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8月,《漓江》编辑部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对第六、第七两期刊物进行自我批评,12月,又不得不再发表《对错误的再认识》,不仅对胡明树进行了公开批评,而且还做了自我反省。文章说,“很显然,胡明树是利用了主编的职权,篡改了党所规定的——也是本刊编委会所通过的——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的根本方针,公开地宣传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自我批评中,文章写道,“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虽然没有以这个代创刊词为依据,(因为胡明树对党交给他的工作采取抗拒态度,没有负起主编的实际责任。)但我们为什么没能发现这个代创刊词的谬误,竟让它代表自己说话?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同志都为它的文体‘新颖’喝过采?道理很简单:我们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5]这表明,虽然“我们”划清了和右派分子胡明树的界限,但“我们”也或明或暗地“背离”了1951年《广西文艺》的编辑方针,这暗示着,经过数年的发展,广西作家文学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1951年提出的主要发表“通俗的民间形式的作品”的编辑方针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现实,所以作家们身在其间而不自觉,只有外界的政治提醒,即“‘人民日报’给我们吹起了响亮的号角”时,“我们”才“醒悟”过来。
1958年,借广西省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之机,《红水河》创刊,“这个刊物是在经过反右派斗争,检查并批判了‘漓江’所犯的错误的基础上诞生的。”“刊物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次是部分的革命知识分子。刊物的内容和形式,将尽力逐步做到适合刊物主要对象的需要和他们的阅读水平。”在服务对象上,《红水河》介于《广西文艺》和《漓江》之间,对《广西文艺》的“服从”显然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而对《漓江》的“靠近”又是文学内部发展的结果。所以,编辑部认为,“根据上述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红水河’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6]《红水河》虽然未能像《漓江》一样办成比较“纯粹”的文学杂志,但依然强调“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这表明,广西的文学刊物有了比较稳定的作家队伍,文学作品质量也较高,比如《红水河》后来发表的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苗延秀的《元宵夜曲》、黄飞卿的《五伯娘和新儿媳》等都是广西文坛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就全国的文学形势来说,50年代末正是轰轰烈烈的文艺“大跃进”时期,在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时为广西文学界领导人之一的苗延秀却公开批评了这种创作“不从可能、自愿、需要出发”“有一个乡布置群众一个晚上完成一万多首的民歌创作任务,群众虽然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夜之内完成了这个任务,但却找不出几首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民歌来。”[7]这种对“文学性”的要求和全国的诗歌气候比较起来,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发展趋势。[8]对于在民歌的海洋里浸淫千年的广西来说,对作家文学的“渴望”显然甚于耳熟能详的“新民歌”,1960年,将《广西文学》从《广西文艺》中“分离”出来,就可以看成是广西力求区分文学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尝试与努力。
从1951年创刊到1966年停刊,《广西文艺》所刊发的作品从倾向于“艺”逐渐向倾向于“文”发展,这是广西作家文学迅速成长的反映,也是文学内部运动的结果,但是,特殊的政治气候却不断地“修正”广西文学的“发展道路”,所以,广西文学界不得不频繁地更换刊物名称以“适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对曾海君等人创办同仁刊物的批评可以看成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也是一个有启示意义的插曲:文学青年曾海君和朋友们决定创办《民族诗刊》,但是“领导上”决定“公办”时,他退了出来,并秘密另办《诗与散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是觉得同仁刊物纵有困难,但也有许多优越性,这就是:1.为将来我们想过渡来搞专业创作,做了准备,架了桥梁;2.让大家去担一担风险,受些锻炼,会有好处;3.容易办出风格来,我们有充分的选稿自由;4.大家既是同仁,当然就会热爱它,从而忠于它,如果公办,情况当然不同,其好处是经济困难没有了,不怕失本,坏处是,刊物编辑机关化,则没有了上述四大好处。这就是我之所以坚持私人办的理由。”[9]曾海君、唐剑文、王成等都不是专业作家,但在办刊物的时候,他们想到了文学的“专业创作”和“风格”,这种“文学性”诉求实际上也是“民间”对作家文学需要的婉转表达。
新中国的文艺体制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它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它服务于全体人民,但不承认人们在艺术方面的多样性需求,因此拒绝少数人的“纯粹”的文学趣味。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考察1949~1966年的文学创作,会发现,广西当代作家不仅人数增长快速,而且不断地谋求“民族”文学经验的现代表达,力图将广西文学从民间文学的传统和藩篱中“抽离”出来,走进作家文学的序列。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广西文学的“兴盛”是相对的,第一是和它的历史比较,广西的作家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对于表达民族民间文学经验来说,广西作家找到了“有效的办法”。但是和大多数省份比较,广西的作家文学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有部分作家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如陆地、苗延秀、黄青、韦其麟、包玉堂等,但他们往往是以民族作家的身份出现的,难以跻身汉语文学世界之前列。或者说,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谈论这一时期文学的时候,常常将他们忽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林白、杨克、东西、鬼子、刘春、盘妙彬等才“来到”以汉族文学观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1980年1月,陆地在广西第三次文代会的工作报告中说,“解放初期广西文学艺术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在省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学艺术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支包括各文艺部门的,专业和业余的,老中青结合的,多民族的革命文艺队伍。”[10]“比较薄弱”和“蓬勃发展”是理解建国初期广西文学的关键词,当然,这里的“蓬勃发展”只适宜放在“民族文学”的范畴里来看。
1971年,广西革委会以《广西文艺》为基础,创办了《革命文艺》,1972年又恢复《广西文艺》之名继续出版,直到1980年,《广西文艺》才改名为《广西文学》,正式成为一本纯文学杂志。不过,广西当代文学早期的“民族”身份并没有给自己带来足够的信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篇小说的“软肋”,因为“长篇小说以其大气、厚重和对历史文化与时代思想的承载,成为文学创作中具有最高美学含量和艺术技能的尖端产品,是衡量作家的思想力度、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的文本标志。”[11]314广西一直没有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文革前值得提及的仅有陆地1960年出版的土改小说《美丽的南方》和刘玉峰1964年出版的剿匪小说《山村复仇记》。虽然广西文学内部曾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的快速发展称为“文学桂军的崛起”,但在“崛起”面前,“我们客观地看到,文学桂军尽管已有了不小的成绩,但跟文学陕军、文学湘军、文学晋军等作家群体以及全国一些‘文化强省’相比,文学桂军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为“长篇乏力”、“大师空缺”、“产业自觉有待深化”,[11]314-322显然,广西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了,不过想要在整个汉语文学世界里跻身前列显然还有很长的文学之路要走。
彼得·比格尔说,“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12]一旦“完整的社会系统”出现“缝隙”,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多样性需求就会快速地呈现出来,文革结束后,广西文学的发展路径再次成为作家们关注的话题。1985年,梅帅元、杨克在《广西文学》撰文,提出了旨在建立有广西本土气质的文学写作新向度——“百越境界”,1988年,借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机,广西文艺界全面展开“88新反思”,思考广西文学的“出路”。1996年,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讨论繁荣广西文艺的具体办法,1997年,在全国率先签约作家,此后,区党委还实施了“213工程”和文艺创作“精品工程”,由此吹响了包括政府和作家在内的广西文学集体冲锋的号角,以大踏步的方式走在汉语文学的世界之中。
[1]编者的话[J].广西文艺,1951,(创刊号).
[2]胡明树.漓江也是一朵花(代创刊词)[J].漓江,1957,(创刊号).
[3]编辑部.终刊与改刊[J].广西文艺,1956,(12).
[4]茅盾.为工农兵[J].文艺报,1949,(11).
[5]编辑部.对错误的再认识[J].漓江,1957,(12).
[6]本刊编辑部.致读者[J].红水河,1958,(创刊号).
[7]苗延秀.为创作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而努力——在区文联及作协广西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工作报告[Z].红水河,1959,(6).
[8]陈代云·“写歌人”与诗人的诞生——论十七年时期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观念[J].民族文学研究,2011,(1).
[9]短剑.曾海君办“同人刊物”的隐私[J].漓江,1957,(11).
[10]陆地.解放思想 加强团结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工作报告[M]//广西通志(文学艺术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11]李建平,黄伟林.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J].周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