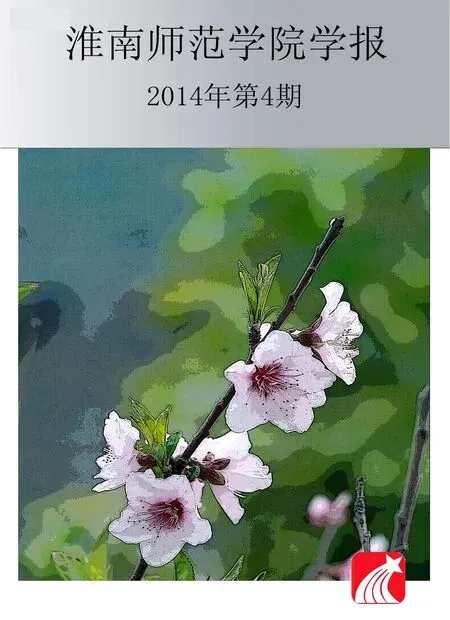论豫让在《淮南子》、《史记》、《战国策》中的形象差异
余杭,程水龙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论豫让在《淮南子》、《史记》、《战国策》中的形象差异
余杭,程水龙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淮南子》、《史记》、《战国策》三部著述中都有豫让为智伯报仇一事的描述,却各有旨趣。在对三者描述文字的细微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后,笔者发现作者或编者所处时代背景、个人身世遭遇对三部著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才使得豫让这个刺客形象蕴藏着迥异的情愫。从中又揭示出史学著述或诸子著作如文学一般,也蕴藏着编著者的运思构想与其思想情感的复杂因素。
豫让;《淮南子》;《史记》;《战国策》
豫让,战国时晋国人,出身侠士之家,祖上毕万、毕阳都是晋国家喻户晓的侠士。作为侠士家族的一员,豫让的行事风范与后世对其人生评判不无关联。在现存文献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战国策》、《说苑》和《丽泽论说集録》等著作中都有记载,相较而言,《淮南子》、《史记》、《战国策》三书中描述豫让的文字为多。并且《淮南子》中的文字材料有很多取自《史记》和《战国策》,这在尊师程水龙先生的文章:《〈淮南子>引〈战国策>用意之深析》中详细地论述了,故此文不加赘述。这里仅以此三书为例,试论异同。然而三者同中有异,这些微异之处潜藏着怎样的运思构想?包蕴着何种情怀?笔者不揣孤陋试作探究,敬请方家指教!
一、豫让离开范中行氏而臣事智伯行为的描述文字
关于豫让离开范中行氏而臣事智伯一事,《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曰:“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①陈广忠:《淮南子斠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豫让原为晋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的臣子,在智伯伐中行氏之后改事智伯。关于此事,刘安用“背”、“臣”这两个动词描述,明显带有贬斥意味,将其行为定性为背叛。臣主间的微妙关系是身处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刘安极为关注的,此处名言“豫让背其主”,一“主”字意在强调臣下对主上当保持忠心。
对豫让该行为,《史记》卷八十六曰:“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处,司马迁对豫让未表露明显的评判,用“无所知名”来概括豫让离开范中行氏的原因。这一“名”字虽不同于刘安的批判指责,可还是显现太史公另一衡定标准,“名”有名声之意,若说战国时刺客不重名声,则恐司马迁不会赞成,因为在他看来,豫让是因为“名”而去。
至于刘向整理的《战国策》卷十八,则云:“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③缪文远,缪伟:《战国策》,罗永莲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战国策》“知伯”,同“智伯”。)这里说豫让因“不悦”而离开,可是对为何不悦却只字未提。或许刘向整理这段史料时以为侠士行踪不定,随性而往,“不悦”二字似乎更符合豫让的身份与性格。
上述三家均记载了豫让离开中行氏转事智伯的行为,对其动机各家判断有异。他们的遣词造句既是对豫让的评判,也流露出编撰者人生心路历程的不同意蕴。而关于主上与臣仆的关系,此处三家观念大体一致,刘安有意突出“忠”,正如他后文所言,使豫让背主的并不是“趋舍厚薄之势异”,而是“人之恩泽使之然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①陈广忠:《淮南子斠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因而,司马迁和刘向皆云智伯“宠之”,即智伯给了豫让所需要的一种尊重与爱惜。
二、豫让为智伯报仇的行为、心理的描述文字
三家对豫让为智伯报仇的行为和心理的文字描述也有着详略的差异,各有旨趣。《淮南子·主术训》云:“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他只用简洁的十二个字描述了豫让为报仇而自残的过程。这是一位忠臣对主上的最佳“忠”态,即自残甚至不惜一切去报其主。关于豫让的心理,刘安在《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中用一段揣度性文字进行了陈述:“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他认为豫让报主之心是极真挚的,不带一丝功利,不苟安偷生,定要以死相报,关键仍是基于一个“忠”字。
司马迁和刘向较之于刘安的简略,则是对豫让报仇的经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司马迁所撰与刘向的整理相比较,《战国策》描述更为精彩恰当,《战国策》卷十八载:“豫让遁逃山中,……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②缪文远,缪伟:《战国策》,罗永莲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史记》与《战国策》之间也存有差异,司马迁在述说漆身为厉之后,没有交代下一次自残的原因,只是在豫让两次自残之后,云“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③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至于其友如何识别残身者是豫让,却不得而知。
豫让漆身是为改变外貌,变哑则为变其音色,撰写者要表明这一次更胜上一次自残的情理,就需要前后文的紧密衔接。而《战国策》为了使得豫让前后两次的自残,符合事理,情节紧凑,在“漆身为厉”之后,特意交代“其妻不识”其形,但还是识破豫让的伪装,那就是“其音何类吾夫之甚”,关于声音这一环节的处理,《战国策》明显高过《史记》,因为有了这一环节的铺设,豫让随后的“吞炭变音”则符合逻辑。
关于豫让报仇的内心世界描写,《史记》、《战国策》比《淮南子》要细腻得多。豫让得知智伯被杀后,《史记》描写了豫让表决:“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豫让报仇是为灵魂“不愧”,一则不愧于智伯,二则为知己之名。而当他两次行刺失败后,在回答赵襄子为何要刺杀之问时,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随后又言:“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言为心声,豫让为主报仇,在出于知遇之恩外,亦有为“名”而死的心理,作为死士、作为忠臣,怎样去显示一位侠士应有的名义,坦然而死,“虽死不恨”,这才是豫让的心愿,赵襄子考虑到豫让此时“名既成矣”,故而成全了豫让美名。司马迁的描述,字里行间都有很明确的对“名”的强调。
上述言行心理的描述,《战国策》与《史记》略同,但在一些细微之处,《战国策》又有自己的特色,如赵襄子为成全豫让最后的要求答应刺衣时,《史记》云:“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战国策》云:“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用“呼天”二字来描写豫让的绝唱,极为精彩,很好地凸显豫让内心的纠结之情。
三、豫让报仇结果的评述文字
《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说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④同①。,而刘安则认为他们只是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罢了。豫让不留恋家庭、妻小,以实际行动为主献身,展示了自己的一种信仰,并不是为了名利。豫让之所以与前贤们一样,不同于世俗,则是“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那么在刘安眼里,豫让以死报主,理所应当。而且,《淮南子·道应训》中又通过魏文侯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魏文侯在听了大夫蹇重强国君应掌握大道、有没有豫让那样的臣子不重要的言论后,说:“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刘安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另一见解,作为国君更应选用贤良,不可一味苛求豫让那样的忠臣之士。《主术训》直言:“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司马迁与刘安观点稍异,他在《史记》卷八十六的结尾云:“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①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在司马迁看来,做为臣下只要最终“名垂后世”,就是不枉生,其自残行为也不为妄。而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于豫让自杀之后,继续云“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②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借赵国之士的涕泣,表露了自己的怜悯之心,也从侧面赞赏了豫让之“义”举。而且据《说苑》襄子“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③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四、三家文字描述不同的深层原因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的题材是人,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史学著作、百家著述,著者或编者在关于故事主人翁的描述上常常带有个人人生境遇的感慨,往往蕴藏着自己思想情感的复杂因素。《淮南子》、《史记》、《战国策》的著编者也如是。
刘安、司马迁和刘向三人志不得伸而彼此命运迥异,这对各自著述的编撰有着深刻影响。淮南王刘安虽是汉高祖刘邦之孙,但身世坎坷,身负两代冤屈:其祖母赵姬因赵相“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而受牵连入狱,于狱中生下刘安之父刘长后自杀;其父刘长在汉文帝继位后,“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椎辟阳侯,最终在文帝六年以谋反罪被废徙蜀,途中绝食而死。其后文帝“追尊淮南王为厉王”,其子皆封侯,刘安最长,袭封淮南王。两代人都屈死,刘安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但淮南相“不听王而听汉”。然刘安仍不忘两代冤屈,“时欲衅逆,未有因也”,听信武安侯私言“非大王当立者谁”,后更因郎中雷被与太子刘迁比剑之事激发了刘安谋反之心,但密谋被淮南相、其孙刘建及辟阳侯孙审卿揭发,终导致“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刘安谋反一事是一步步升级的,由刚开始的对两代冤屈的积忿,到对朝廷安排淮南相监督封国事务的不满,再到朝廷要问罪太子的不安而欲谋反。
刘安代表的地方王权和朝廷代表的皇权之间始终处于如箭在弦,满弦欲发的紧张状态。在皇帝对自己处处戒备的情况下又不敢声张,满腹怨恨只有述诸笔端,组织门客著书。“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④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汉武帝很关注这位淮南王。刘安的曲折身世和尴尬处境对他主持编纂《淮南子》有深刻影响。作为皇亲贵族的他,有治国的宏才大略,却不能过多干预朝政,必须避嫌。《淮南子》末卷“要略”篇云:“纪纲道德,经纬人事”,“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⑤陈广忠:《淮南子斠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就显示了刘安治国理念和开阔胸襟,可其境遇与宏大抱负相抵触,所以身为人臣要常常表示忠君之意,以期脱谋反之嫌,这在《淮南子》中显露加多。
因此对于豫让的行为刘安为何始终着眼于“忠”,就不难理解,也寄予了他对地方王权和中央皇权之间矛盾冲突的和解之愿。批判豫让“背其主”,意在表明自己对汉朝统治者的忠心。当他转而弃旧主投奔智伯,则是因为“人之恩泽使之然”,刘安如此描述也从侧面提示汉皇帝应施恩与臣民,这才是维持一份忠心的关键。刘安对豫让自残报主的行为的描述,也可显示他为社稷献身的一腔热血,死而后已。
刘安认为是不能用世俗的名利眼光来看待豫让自始至终都不动摇和放弃为智伯报仇的信念。豫让始终坚守忠心,体现的是“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这是在暗暗告诫汉武帝,不要将自己为朝廷效力看成是别有企图,进而劝谏汉武帝当专心于政事,使能臣志士踵武相承,辅佐大业,而非处处见疑,忠而被谤。君主须善于任用“管仲、鲍叔”这样的贤臣,而非等到社稷倾危之时才求“豫让”之类的忠臣义士。正如明代文学家方孝孺的名篇《豫让论》所言:“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世乱而忧国忧民之忠臣出,身处盛世,忠心不当体现在为国死而后已,而是用智慧与能力为人主尽心尽力。然这两类臣的角色转换与主上相关,君德澄明则臣下竭忠尽智,君德昏聩则臣下只能报主于国家既亡之后了。刘安的意思很明确,自己是贤臣或忠臣或反臣,关键就在于君德。这在对豫让相关人物智伯一事的描述中有所体现。《淮南子·人间训》里的一段文字中具体描述了智伯向韩赵魏三家求土地时三家的态度,其中重点叙述了魏宣子的态度和谋臣任登的建议,魏宣子“弗欲与之”,而任登认为“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此言耐人寻味,如果智伯一味地向诸侯要土地,必然会构怨于诸侯,到时群起而攻之,总好过去做第一个箭靶吧!众所周知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实施“推恩令”,大势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想以此弱化地方王权而加强中央集权。刘安重点论述任登的话,首先申明自己不会当第一个“箭靶”,其次想告诉汉武帝刘彻:物极则反,过度的压制可能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七国之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事出必有因,无风不起浪,只有在上者仁德,诸侯国才会归服。以武力夺取不如以德行收服,不然只会导致“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的局面。
《淮南子》一书中对豫让、智伯、赵襄子之事多次提及,常常在文字表述中以“忠”字来诠释豫让的言行。然而淮南王刘安最终因谋反事发自杀身亡,后世关于淮南王谋反一事有很多争议,或批判,或鸣不平,在此不作赘述。但我们知道,刘安编撰《淮南子》的方法是不同于《史记》和《战国策》的。他是依杂家论述的方法,“事”、“理”并重,云:“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则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他欲用大量历史故事来充实其著述,豫让、智伯、赵襄子及众谋臣的形象就是他选取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非作为主体进行详细论述,所以《淮南子》中关于豫让的事散见于不同的篇章,且每次都是概要述说。
与刘安同处武帝朝代的司马迁,却因个人遭遇而与刘安著述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创作《史记》与两件事情息息相关,其直接动机是父亲司马谈的临终托付。司马谈是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迁子承父业,将墨笔书史实当做自己的使命。然而太史令在朝堂上的地位并不高,《报任安书》云:“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①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史记·封禅书》礼有:“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飧。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②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可见其主要职责只是沟通天神,解释阴阳灾异,和祠官一起负责祭祀等事宜。尽管如此,他仍决心继续父亲著史的志愿,其父尝云:“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所以《汉书·司马迁传》云其创作宗旨为:“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史记》中浓郁的悲剧情怀则是受李陵之祸带来的灾难影响。李陵于“天汉二年秋”与匈奴大战,兵败后投降。当时朝中众臣都说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希望能帮他脱罪。因此惹怒武帝刘彻,“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身体上受辱,使司马迁心灵蒙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和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忍辱负重,并将满腔悲愤之情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其中有不得志的委屈,遭受奇耻大辱的愤慨,对有冤不能鸣的悲叹和对武帝刘彻的专制的反抗。
正是有这诸多的情绪,所以司马迁笔下的豫让与刘安笔下的形象有较多差异。司马迁因为自己抱负不能伸,名声不能成;不能为李陵洗刷冤屈,残败的身躯给祖上蒙羞,不能给后代子孙添光,所以他笔下对“名”才会高度重视:豫让因“无所知名”而离开范中行氏;为智伯报仇的动机是因为智伯“知己”,给了他符合身份的名。由于司马迁自始至终对自己的残败之躯心怀芥蒂,所以他笔下的豫让自残程度明显不像刘安那样夸饰严重,而是有意对豫让自残行为进行淡化,这从《史记·吕后本纪》里仅用十字描写吕后将戚夫人做成人彘的过程也可探知一二:“断……手足,去眼,辉耳,饮暗药”。他人生的后期唯希望《史记》能扬名后世,以弥补自己心灵上的这片空白。父司马谈临终遗言是他念念不忘的,《太史公自序》载父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而且,司马迁为李陵辩争就是为了给他正名,这也涉及到为名所困的战国策士或侠士命运问题。关于豫让从二主之事,司马迁并没有做出评价,这暗合了他认为李陵投降有自己的立场和苦衷,不能简单将其定为不忠。在第二次复仇行动中豫让友人感慨:“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必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比《战国策》多了一句“何必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联系到祸及自身的李陵事件,这两句话似乎可以理解成为李陵抱冤,即降敌定有难言之隐。“委质而臣事”匈奴,或许是权宜之计,以待日后报国君之恩。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这样的作法不但不能实行而且会被定作叛臣。司马迁对此也无能为力,故而有后面豫让的答复之语,揭示出其内心的矛盾:虽然知道刺杀赵襄子很难,但还是要去做,只为了“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而且“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①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这正是为名所累者的处境:不遇时汲汲以求名,知遇后又为名所累,必须互为恩报,否则必被视为不忠。
这些地方也潜藏着太史公内心的矛盾: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以待时机,但臣事二主还是不当有的行为。司马迁所造明主赵襄子的形象则是汉武帝效仿的典范:在豫让要行刺他的时候,赏识他的义“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并且在豫让二次行刺时满足了他击衣的愿望,成就了豫让报主之心,同时豫让也成就了赵襄子贤君之名。太史公希望刘彻也能如此贤明,不计臣子的过错,而成就他们的名声。但最终汉武帝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史记》著成之后也只得“藏之名山”,只因其中有论及汉武帝的诸多专制之处,易招致更大灾难。
刘向编撰《战国策》是西汉末年,此时汉初的强盛一去不复返,朝廷宦官、外戚专权,皇帝形同虚设,朝政腐败,不再有汉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同为皇室宗亲,刘向此时比武帝时的刘安要幸运得多,最坏的情形不过是不得重用,而不会像淮南王刘安那样常常受到猜忌。实际上刘向有心匡扶汉室却一再被排挤,在与宦官、外戚的一次次斗争中,刘向为汉宗室竭尽忠诚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过,不仅在思想上表现出和汉王朝同心,而且还将自己的进谏之言融入著作之中,如《列女传》、《新序》、《说苑》。
《战国策》是刘向整理的,其动机在《战国策书录》中说的很清楚。他认为造成战国纷争攻伐局面的原因是“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君德浅薄”。主张德治,赞赏纵横策士“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②严可均辑,任雪芳审定:《全汉文》(卷三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意在提醒雅好儒术的成帝对策士的权谋之术多加留意,以资现实政治之需。
基于对朝政的忧戚,刘向希望皇上能够重用有志之士,因而在对豫让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对帝王的劝诫主张,提出德治的途径:君臣之“义”和维持君臣之“义”的方法。在《赵策》的《知伯从汉魏兵以攻赵》、《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中介绍了豫让同时期的两位谋臣郗疵和知过。由于知伯不听二人的谏言,刚愎自用,导致最终的失败。但是汉成帝沉迷于赵氏姐妹的美色,此时朝政落于王氏外戚手中。刘向主张如果有忠心于汉室的谋臣拱卫于皇帝左右,与汉室共存亡,就不会导致外戚专权的局面了。而且他还希望借智伯不听谏导致灭亡的教训来警醒汉成帝:不要沉醉女色,而应广纳谏言,收服贤才,振作起来,拯救国家于累卵之势。
《赵策·晋毕阳之孙豫让》重点诠释的是“君臣之义”和如何维持君臣之义。豫让离开范中行氏是因为他“不说”,从前后文内容推测很可能是对自己所得的不满,豫让秉持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理念,“知己”者是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范中行氏和豫让的君臣之义之所以薄弱,是因为“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而智伯和豫让的君臣之义如此笃厚,则是因为“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并非刘安一“背”字可以言尽,所以刘向整理这段文字,想表达的是:国君要想得到贤士就要待他如“知己”,了解他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知道他的需求;要维持“君臣之义”就要给予贤臣“国士”待遇,这样才能让贤士为你尽忠。刘向塑造的赵襄子的明君形象也是为了给汉成帝立一个模范:他欣赏豫让,某种意义上也是豫让的知己,理解他的内心需求,故让他“击衣”复仇。或许刘向坚信,只要汉成帝能惜才、爱才,有志之士就能助其重振汉室。
综上所述,对于同一事件,三部著述有着不同的描述,各有侧重,旨趣有别。既带有时代的烙印,又有著者、编者思想的影子。刘安、司马迁、刘向的人生境遇不同,也赋予了豫让不同的时代色彩、深邃的思想情感,使得豫让这个刺客形象有着细微差异,并蕴藏着迥异的情愫。《淮南子》重在说理,而《史记》、《战国策》则重在叙事。《史记》和《战国策》作为两部内容宏富的史料著述,对史料的剪裁、使用自然不同于《淮南子》。《淮南子》依据论证观点需要而辑取史事,篇幅或长或短,如描写豫让的文字比较零碎,散见于不同的篇章;而《史记》和《战国策》出于笔录史实的需要,常常将相关史料集中编撰。并且同为史学家,司马迁在描述史实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刘向的整理则显得客观。
On the image difference of Yu Rang in Huainanzi,Shiji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cheme
YU Hang,CHENG Shuilong
We can find the description words about Yu Rang revenge for Zhi Bo in three works:Huainanzi,Shijiand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cheme,but each has its strong point.Because the author or editor of three books has different era background,and personal experiences,so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depiction of Yu rang image text,the deep emotional imprinting make the assassin image of Yu Rang contains different feelings.It also reveals the historical works or works of philosophers contain complex thinking ideas and emotions of the editors,just the same as literature works.
Yu Rang;Huainanzi;Shiji;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cheme
I206.2
A
1009-9530(2014)04-0058-06
2014-02-06
余杭(1990-),女,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程水龙,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教学等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