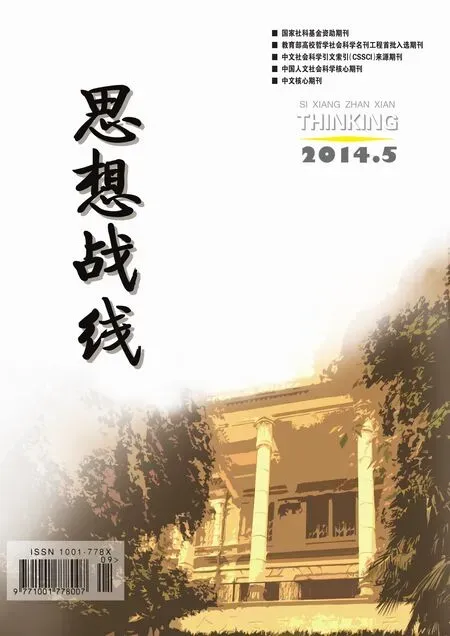“思想中国”:17世纪法国宗教背景下的“哲学注释”
——拉莫特·勒瓦耶和帕斯卡尔对中国的思考和描述
钱林森
一、引 言
16世纪欧洲人“登陆”中国,进而发现中国,使“中—欧”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彼此不相识的两大文明开始在1600年间首次接触”,[注]Jacques Gernet,Chine et christianisme, La première confrontation,Préface à la nouvelle édition, Paris:Gallimard,1991.中译本参见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耿 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开辟了中欧(中法)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相遇、交流、碰撞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来华的欧洲游历家、商人、使节、三次“造访”的传教士的纷至沓来,[注]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使者的传教士,第一批来华造访的是8世纪唐朝的景教,第二批是13世纪元朝方济各派修士,第三批是16~17世纪明清之际,罗马天主教廷的耶稣会修士。参见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页。及其在中国的游记、对东方世界的报道,尤其是耶稣会士所记载的中国书简、游记以及著述中所传播的中国知识和中国形象在欧洲广泛传播,一个全新的文化中国、思想中国的形象,[注]即以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1585年)所开创的文明中国——“大中华帝国”形象,完成并流行于1450~1650年间;以基歇尔神甫《中国图志》(1667年)所标示的思想中国——“孔夫子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650~1750年间。参见周 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卷,第一编第四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第75页。走进了17世纪法国和欧洲知识精英的视野,使他们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东方“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故乡,全然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球”,不同于新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它是“充盈的,它的文明令人吃惊”;也不同于欧洲本身,它是一个跟欧洲世界“‘可比较’的世界”: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传统、深厚的文化智慧、特异的伦理风俗……都令世人惊异!于是,“这个中国”的发现,便在17世纪法国(欧洲)思想文化界引起了“震撼”与“躁动”,其强烈之程度,以至“使整个古典时代‘为之不安’”。[注]Voir François Jullien, Thierry Marchaisse, 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Paris:Editions du Seuil,2000,pp.211~213.参见[法]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张 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40~142页。事实上,17世纪,在“至高无双的天主教国王”路易十四治下,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思想家、神学家、乃至宫廷的传道士,凡是阅读过盛传于当时的中国读物,[注]如金尼阁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卫匡国神甫的《中国历史》(1658年),基歇尔神甫《中国图志》(1667年),柏应理神甫《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年),等等。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在华耶稣会士传来的中国报道、中国信息者,无不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陌生、特异的“文化中国”、“思想中国”而“震撼”、“惊疑”与“不安”,无一例外地从各自的理念、信仰、需要和立场出发,对中国进行思考、判断、质疑与争辩,并率先在欧洲作出了法国的回应,从而掀起了全欧洲关于中国的首次大辩论,即爆发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震动欧洲的“中国礼仪之争”。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思想家对中国的思考、辩论,上承16世纪人文主义巨擘蒙田对中国智慧的反应,下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对中国文化的采集、利用,为18世纪中法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交流、碰撞,构筑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铺垫了丰腴的文化土壤。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便以17世纪法国自由思想家拉莫特·勒瓦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的著作为切入口,来考察彼时处于宗教语境下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们对中国的思考与描述,并从而返观全新的“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对欧洲基督教文化所起到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注释”作用。
二、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道德》中的中国思考
在17世纪,最先继蒙田对中国制度文明、道德智慧进行思考的,是“怀疑论者”、自由思想家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oyer,1588~1672年),他在1641年发表的《论异教徒的道德》(La vertu des païens)著作中,立专章《孔夫子》(Confucius),首次将孔子和苏格拉底放在同等位置,两者齐名,并列于天堂,引向人类智慧,哲学从天上降临人间。当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于1600年间开始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时,蒙田已经去世8个年头,他不可能读到这一时期传教士相关的中国读物、接触不到孔夫子与儒家文化的相关知识,在生前《随笔集》中也未提及孔夫子的名字,否则,他必定“免不了要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做一番比较”。[注]Voir R.Etiemble,L'Europe chinoise,1,Paris:Gallimard,1988,p.258.中译本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而蒙田逝世10年后出生的拉莫特·勒瓦耶,却十分熟谙流传甚广的、在华耶稣会士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注]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甫(P.Nicolas Trigault)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l'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enterprise par les P.P.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comprise en cinq livres),共5卷,取自利玛窦的评论,原书为拉丁文,由利克布尔神甫(P.Riquebourg)译成法文,1615年在里昂出版,1617年里尔重印,1618年巴黎再版,本节引文,依据1618年巴黎版,均转引自艾田蒲《中国之欧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所塑造的“万世圣哲”孔夫子形象,[注]参见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61页。这位法国王爷的“导师”、上流社会的雅士,毫不犹豫地运用金尼阁神甫所提供的材料和知识,在其《论异教徒的道德》中,“以某种全新的思想研究了拯救不信教者的问题”,[注]法国史学家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称:“这种新思想是发现美洲和中国的结果。”参见[法]维吉尔·毕诺《中国与法国哲学精神的形成》(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 Paris, Reprints, 1971.),耿昇译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9页)。在17世纪法国神学界、思想界,率先将孔夫子引来与苏格拉底做比较,法国和欧洲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探索与认识,由此被推进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拉莫特·勒瓦耶在《论异教徒的道德》“孔夫子”专章中,大量采用了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对孔子描述的材料,[注]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道德》如何征引金尼阁神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对孔子描述的材料,艾田蒲有详尽的论述。Voir R.Etiemble,L'Europe chinoise,1,Paris:Gallimard,1988,pp.273~278.中译本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2~267页。本节《论异教徒的道德》引文依据《拉莫特·勒瓦耶著作》卷5,1757年(Le tome V des Oeuvres de La Mothe Le Voyer, Dresde:Groell, 1757.),均转引自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2~267页,不再另注。凡涉及到“孔圣人”及其伦理和门生在历代所起的作用时,拉莫特·勒瓦耶都无一例外地步金尼阁神甫的后尘,他认为“那是当时关于中国的‘最美的’论述。”拉莫特·勒瓦耶在这部著作中,赞扬孔老夫子的德行,肯定孔子与人为善的基督箴言;赞扬孔子信徒不是偶像崇拜者,只崇尚一个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只承认他们称之为天主的唯一上帝”等等,在这些方面,他都无保留地借鉴了金尼阁神甫的观点。与在华传教士利马窦、金尼阁等采取同一步调,似可见出作者反击冉森派、维护耶稣会士东方传教事业的创作旨意,但该著深层的意义远不在此。如文化史家艾田蒲所指出的,只要人们结合拉莫特·勒瓦耶“怀疑论”的思想背景,更深入地研读他这部“异教徒德行论”,就不难发现作者对耶稣会士和东方孔圣人这些赞语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思想”,亦即上述毕诺先生所言的“某种全新的思想”。
从中法文化和思想相遇、交流的历史看,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道德》之“深层思想”或开拓意义首先在于,作者力图以基督教的怀疑论,替代基督教唯理论,不以神学家,而以哲学家身份,开创了孔子和苏格拉底平行比较的第一例。他根据东西方这两位“圣哲”差不多处于类似的生活时代、相同的哲思趋向和高洁的德行,称孔子堪为“中国的苏格拉底”,他大胆地提出:孔子与苏格拉底是“异教世界中最具美德的两位”,孔子的戒条和箴言,“始终贯穿于中国的伦理思想”,孔子同苏格拉底一样,“运用他们在伦理方面的权威,使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如此果敢的并行对比,便引领读者走向蒙田,而非圣依纳爵(saint Ignace),走向智慧,而非宗教教条。当时正是17世纪,正值传教士就中国人究竟是唯灵论还是唯物论,孔夫子究竟是人间哲人还是神性“先知”争论不休之际,拉莫特深刻的思想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从他开始,这一对比便成为后继者一种广为采用的哲学注释,或哲学工具。
拉莫特在《孔夫子》章节中引述金尼阁神甫的观点,以“哲学”的名义揭示了儒教培育下的中国文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占据的无可取代的位置和影响,继蒙田之后,作哲学的追问,触及到中国制度文明的思想内核,为下世纪启蒙作家追寻“哲人国王”的理想,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他这么写道:“理所当然,把王权交付于哲学家,让暴力乖乖归顺于理性,这之于孔子不是一种小荣誉。除了哲学王子和哲学家们治理国家以外,人们还能希求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呢?此种罕见的精神影响力促成中国实现了两种值得庆幸的事业:由于孔子的崇高美德,君王甚至不会发出不符合孔子戒律的命令;朝廷文武百官必然是孔子的信徒,换句话说,是哲学家们在统治着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哲学家治国”这一人文主义思想,在17世纪法国君权神授的专制政体的文化语境下,显然获得了“离经叛道”的思想意义。
拉摸特·勒瓦耶巧妙地接过金尼阁赞美孔子美德和圣洁的话语,层层递进,不断追问,注进了自己的“新思想”。在他看来,孔子在对万物起源的认识和道德智慧方面,毫不逊于西方圣哲苏格拉底他们,至于孔子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箴言,更是作为自然伦理的准则,始终贯穿于中国人伦理思想之中。因此他断言:“对待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像对待曾经的那些伟大哲人一样给予其同样的荣誉,如果我们只对苏格拉底、毕达哥(Pythagore)表达敬意,而对拥有同样美德的孔子不敬,那么,我们将是极其不公道且是极其冒昧的。”依据拉莫特的推论,如此“圣洁”的孔圣人,不能不受到上帝的“圣宠”与“惠顾”,异教徒的孔子灵魂因而得到上帝的拯救。别具反讽意味的是,《孔夫子》的作者拉摸特,一切入论题不忘提醒读者:这位被他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孔子,比上帝早生501年!这就给当时一切稍有一点理性思考的读者不禁自问:既然东去的基督教使徒们自以为带给人间的训诫,孔子在500年前就已经提出,那么他们为何还要这位早于上帝而生的德行高洁、智慧充盈、且得“圣宠”而自救的东方孔圣人皈依改宗呢?机敏的拉莫特就这样和神学家金尼阁联手,不顾整个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神权主义的威压,在17世纪上半叶,力举孔夫子的儒学文化精神,张扬中国的自然神论、道德哲学,率先以法国“哲人”的名义,赞美“异教徒的美德”,演练出令世人惊异的历史场面:“神圣的孔夫子,为我们祈祷吧!”拉莫特就这样悄然无声地“将人文主义引向摆脱宗教束缚的自由思想,或者至少是引向一种较为自由的思想”,从而使“‘哲学家’这个词重新获得了大胆的革命性的意义”。[注]Voir R.Etiemble,L’Europe chinoise,1,Paris:Gallimard,1988,p.267.中译本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三、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书简》和《思想录》中的中国描述
帕斯卡尔(Balaise Pascal, 1623~1662年),17世纪杰出的数理科学家、哲学家、前期古典主义著名的散文家,代表之作为《致外省人书简》(Les Provinciales, 1656~1657年)和《思想录》(Pensées, 1670年),这两部作品,“以其论战的锋芒和思想的深邃以及文笔的流畅隽永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史上的古典著作”。[注]何兆武:《帕斯卡尔的生平和科学贡献》,载[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5页。
《致外省人书简》是一部宗教论战作品,产生于17世纪中叶耶稣会与冉森派冲突日趋尖锐的时代。[注]冉森教派,17世纪40年代传入法国,由冉森(Jansenius, 1585~1638年)创立,接近加尔文教义的教派,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吸引了拉辛、帕斯卡尔这样的作家、思想家的追捧。其作者帕斯卡尔,身为冉森派教义的信徒和该教派反抗耶稣会理论斗争中的主要辩护人,在1656~1657年间,应冉森教派领袖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年)之邀,曾以世俗“哲人”的身份,接连发表了18封致外省人的信札,[注]参见何兆武《帕斯卡尔的生平和著作年表》,载[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4~505页。为冉森教派辩护,抨击耶稣会士道德败坏,结集成书,匿名印行,而引发出冉森派与耶稣会之间一场激烈的神学论争,这是17世纪法国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尖锐斗争。帕斯卡尔作为这场论争前沿的不妥协的“斗士”,他在论战中写出的这些信札,展现出“某些光辉的近代思想内容和近代思想方法,却超出神学范围之外而为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注]何兆武:《帕斯卡尔的生平和著作年表》,载[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6页。令中法文化关系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是作者在这部宗教论战的书简中,为反击他的敌手,而征引中国例证,使人们从其神学论争的“夹缝中”,不仅窥见到这位天才思想家吉光片羽的思想火花,而且也能从中看到这位英年早逝的“哲人”兼作家,在17世纪中叶思考、探索中国的历史身影。
17世纪中叶是法国对中国加深认识和了解的时代,也是宗教论争不断加剧的时代,东征来华的传教士因布教方法的分歧与争斗而酿成的“礼仪之争”正待爆发。《致外省人书简》正是这个时代特点的反映和产物,帕斯卡尔对中国例证的征引和思考,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1656年,正当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一方,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为另一方)对中国礼仪事件,争吵不休,呈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刻,帕斯卡尔利用傅泛济神父的《宗教信仰的崇拜者》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帕斯卡尔写了《一位友人致外省人第五封信》,闪烁其词地提到Keum-facum(孔夫子)的名字,首次征引中国例证。不同于先前的拉莫特,援引在华耶稣会士颂扬“孔圣人”的赞词,巧妙地注入其“自由的思想”,也不同于后来的培尔,借用中国例证,引向对基督文化本身的批判,帕斯卡尔在这封书简中征引中国的例证,为的是谴责耶稣会士们放纵的道德行为:据说,耶稣会士在东征时,“在他们所置身的国度里,人们对于一个在十字架上殉难的神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他们取消了让人愤慨的十字架,只宣扬荣耀光辉的耶稣—基督,而不再宣扬殉难的耶稣—基督。这就好像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行为:他们允许基督徒进行偶像崇拜,并且想出了绝妙的点子——把耶稣—基督的像藏在衣服下面,当他们公开拜偶像(Chacim-coan)和孔夫子(Keum-facum)时,心里想着耶稣……”。[注]参见[法]帕斯卡尔《外省人信札》,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7页。帕斯卡尔援引礼仪之争中这段材料充满讽刺意味,目的在于攻击、批判耶稣会士亵渎神圣基督的放荡行为,这就将本属于传教士圈内神学家间的礼仪之争,首次披露于法国公众,使耶稣会士传播福音的方法变成了冉森派指控耶稣会的一份诉状。在书简里,他虽然援引了傅泛济所描述的孔子形象,但却没有明确说明那位Keum-facum(孔夫子)是谁,他传授了什么以及人们对他抱有何种形式的崇拜,另外,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混淆”手法,把孔子和偶像(Chacim-coan)等同起来,进行排斥,以传达他的护教立场,也清楚地表明,这位冉森派思想家与儒家文化擦身而过的“相逢”,陷入了一种模糊暧昧、模棱两可的难解境地,而没有进入对“他者”明确的理解、接近和接纳。而陷入一种模棱两可、模糊难解的境地,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还处于一种犹疑、选择和“寻找”阶段。
《思想录》是一部杂感、笔记之类的作品,本是帕斯卡尔生前尚未完成的笔录手稿,始作于1656年9月,其中有些部分已大致成章者,“斐然可读,文思流畅,清明如水”,[注][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序。本拟《为基督教辩护》为题发表,作者辞世后,全稿经亲友整理,于1670年以《思想录》为名问世。[注]1670年首版全名为《帕斯卡尔先生对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考》(Pensées de Monsieur Pascal sur la religion 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参见何兆武《帕斯卡尔生平和著作年表》,载[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11页。帕斯卡尔在这部遗作中,留下了一段关于“中国的历史”的简短而令人足思的文字与话题,是这位思想家思考中国最著名的例证。中国古老历史的话题之引发,起始于卫匡国神父(le père Martini)所著《中国上古史》(1658年)一书。卫匡国神父在这部著作中,根据中国人甲子生肖纪年法,把中国古代纪年上溯到伏羲时代,即公元前2952年,伏羲以后的事迹皆为信史。这一时间要比希伯莱文献确定诺亚洪水的时间早600年。卫神父依据中国编年表毫不犹豫地把诺亚洪水年代上溯到基督时代以前3 000年,这显然与《圣经》和当时法国权威史学家博絮埃(Bossuet)的《世界史论》所载不合。卫匡国神父崇拜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天文学,他证明并确信中国纪年的可靠性,却不料向他所隶属的基督文明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如果“接受中国古老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世界史。从此,再也不可能如同博絮埃那样把世界史只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诸民族的范畴内,必须从中加入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亚洲和远东诸民族的历史”。基督文明作为人类文化惟一源头,东西文化关系中的欧洲中心论都会受到彻底的置疑。同时,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中国纪年的古老性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疑问:人类的摇篮应该归于何处?文明的发祥地究竟在哪”?[注]参见[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 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1页。这在当时法国神学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帕斯卡尔参与了辩论,在其代表作《思想录》中留下了“中国个案”的独特思考和描述。
古老的中国历史年表与圣经年表不合,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但是哪一个呢?显然,这对帕斯卡尔这样一位具有严谨科学精神同时又是忠实信徒的思想家来说,不能不感到震惊和“不安”。在基督文明中心论看来,如果可以怀疑圣经有计算错误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没有错误呢?这正是“中国的历史”年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哲学、甚或认识论的全部意义所在。以一句充满护教论色彩的名言作为他思辨的开场,申言:“只有那些见证者拼死证明的历史,我才愿意相信。”[注]Voir Pascal,Pensées,Oeuvres Complètes,II.éd.de Michel Le Guern,Paris:Gallimard, 2000, p.819.以下所引帕斯卡尔谈论中国的文字,均据此,不再另注。暗示圣经年表见证者们为了他们所相信的真实和公正的事业而殉难。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到帕氏这句话,一如有些法国批评家所言,“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真理的证明,不如说是一种狂热的标志”。[注]法国《思想》杂志施莱尔先生(M. Jean-Louis Schlegel)1996年南京大学国际跨文化对话论坛发言。Voir Qian Linsen & Alain Le Pichon,Culture: Diversité et coexistence dans le dialogue Chine-Occident,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Nanjing,1996,Nanjing:Editions Yilin,1998,pp.138~140.中译本可参见钱林森等《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刘 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150页。这种狂热,似乎是伴随着17世纪法国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和争论而打上时代印记。帕斯卡尔接着用充满怀疑的口吻提出:“两者之中哪一个更可信?摩西,还是中国?”显然这个疑问不单单属于帕斯卡尔,它同样属于17世纪法国那些因为卫匡国神父对中国文明古老性的确证而变得惊诧、怀疑和不安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疑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如果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西方征服者的暴行,虽然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带有西方意识或许是基督教的批判性的沉思,提出了“你把你的兄弟怎么啦?”这样一个“圣经式”的问题,但是,对西班牙基督教徒将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提出疑义(当然蒙田除外),那么,东征的西方耶稣会士发现了中国,提到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这就产生了疑惑,提出了问题。中国以其古老悠久的文明历史、丰富精致的文化和高度的智慧,向基督教及其文化价值、普世性和优越性提出了质疑,反之,欧洲也对不很了解的中国文明提出疑问,于是,“摩西或中国”的问题就这样摆到了当时法国人和欧洲人的面前,帕斯卡尔的疑问具有普遍意义,是17世纪中法文化史、思想史中的经典性的“发问”:“是摩西?还是中国?”这个问题强调的是一个特殊方面,哪一个是最可信的,是摩西(《圣经》)的启示还是中国的智慧?在基督文化视野下,中国的出现,无疑是“另一个世界”、是不能归类的“另类”。在帕斯卡尔护教论的眼光里,中国已不只是在起颠覆作用的另类巨人,中国在进入他的思想的同时,已经“展现出一种选择”。他提出“是摩西还是中国”的疑惑,表明他已进入了选择而又难以抉择的境地,这毕竟首先属于他本人的问题,因为他参与这一辩论的时候,正游移于“怀疑论者和相对论者”(比如蒙田)而不知所措。况且,“摩西或中国”这句发问是“瘸腿的”,[注]François Jullien, Thierry Marchaisse,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Paris:Editions du Seuil, 2000,p.51.法国当代思想家于连认为,“摩西或中国”这句名言是“瘸腿”的。此论有理。这句发问的选择里,一方面是一神教的创始人摩西,而另一方面,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对称人物,比方说孔子,却是“中国”——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人们毫无所知的文化空间,“帕斯卡尔确实感觉到找到一个对立面的可能,但是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对立面是什么样子”。如其《一位友人致外省人第五封信》所明示的,帕氏不大了解孔夫子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他把孔子看作是一种人们崇拜的偶像。他确实缺乏足够的中国知识支撑,以便能够从中国方面对照摩西,提出“确证”。因此,帕斯卡尔如果提出年表问题作为“证据”,总是觉得可疑而不可靠,其原因在于他不知道中国年表是以可核查的科学文献,特别是以天文观察(月蚀观察)为依据的。幸好,他清醒地预感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完全无知。他这样回答卫匡国神父,以及读过卫神父著作的自由思想论者:
这是不可笼统看待的问题。我对你们说,既有让人目眩难辨的东西,又有照亮人的东西。仅此一句话,我就推翻你们的所有推理。你们说:“可是中国让人模糊难懂;”而我的回答是:“中国虽然让人模糊难懂,却有光明的启示可以追寻,努力去追寻吧!”[注]Voir Pascal,Pensées,Oeuvres complètes,II.éd.de Michel Le Guern,Paris:Gallimard, 2000, p.819.
这是帕斯卡尔思考中国留给后世的经典性命题,法国思想界称之为“帕斯卡式的公案(koan)”,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探讨、长思。有批评家认为,帕斯卡尔其实给出了一个能够让我们在今天仍然兴奋不已的答案:将“中国”和“基督教”或“西方”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坚持不懈的考察 、寻找。帕斯卡尔在这里运用“中国使人模糊难解”(La Chine obscurcit)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形式,其中包含了认识他者过程中所涉及的模糊和明晰的辩证法,显示出帕斯卡尔特有的哲学才气。可以这样理解他的上述这段话:是的,与中国接触——真正的接触中——确实存在模糊、混乱,以及一种关于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的标准和我的智慧的重新探讨。对此,有人会犹疑。可是对于那些持之以恒甚至走得更远的人来说,这种模糊只是暂时性的,抑或是只代表事物的某一面:它是关于他者、关于自己的一种明晰,一种新认识的反面。因此,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找它们。抛开惰性,因为这些惰性仅仅满足于表象,满足于“粗略”的观察,满足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印象。[注]Voir Qian Linsen & Alain Le Pichon,Culture: Diversité et coexistence dans le dialogue Chine-Occident,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Nanjing, 1996, Nanjing:Editions Yilin, 1998,pp.139~140.这就是说,克服懈怠,坚持“寻找”这是帕斯卡尔的“公案”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
坚持“寻找”之路,是帕斯卡尔作为一名冉森派思想家关于“摩西与中国”发问的终极思考。他没有说“中国算不了什么”或者“如果它模糊困扰你,就避开它”!恰恰相反,他激励、敦促人们去追寻,以便求得更多、更好地理解。这位思想家坚信“寻求光明的启示”的信念。他责备动摇论者轻易放弃阵地,放弃“寻找”。这在17世纪中欧(中法)接触初始阶段,实属难能可贵。那么,如何寻找?怎样辨明真相或真理呢?帕斯卡尔在其思考中国这段简短文字中最后一句话,给出了答案:“必须去仔细观察它,应该把文献摆到桌子上。”
必须就近去考察,把中心问题摆到桌面上,作一番精细的考索研究。帕斯卡尔这个结语,不断给后世思想探求者们以巨大启示。著名的法国当代思想家于连重读帕氏这段文字,就这样说过:“我觉得帕斯卡尔关于中国所说的一切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强调‘中国个案’构成的反对力量,也强调这样的事实:为了正确理解中国个案,必须深入到细节——‘把文献摆到桌子上’……当然了,对帕斯卡尔而言,中国这个反对力量限制在神学范围里;但他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即‘这个不可归类的理论的丰富性。’”[注]François Jullien, Thierry Marchaisse,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 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Paris:Editions du Seuil,2000,p.218.于连的哲学探索,比如,利用中国进行廓清——廓清新的思维可能性,就是在帕斯卡尔的“中国公案”、中国命题启发下进行的。我们曾经指出过,[注]参见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16、17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向外扩张,与异质文化相遇阶段,不外存在这么两种态势:一是不为任何发现的异质文化的相异性所迷惑,而一并加以摧毁,就像西班牙基督徒发现美洲“新大陆”,对印第安人文明一样;一是发现异质文化的相异性就迷目昏眩,不愿超越这种差异,而以自我为中心,比个高下,正像17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发现中国文化所作的那样。帕斯卡尔留给我们的启示是,超越差异和徒劳无益的比较,不是对抗或摧毁,再往前一步,继续“寻找”,就能重新发现共同的人性,这也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相似性。这是帕斯卡尔作为哲学家和作家,从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哲学高度”,从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最初接触中,所得到的思考和结论,它接近于我们的思考和结论。虽然帕斯卡尔的“哲思”仍然无法超越基督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藩篱,但他对中国的征引和思考,在17世纪中法文化、思想相遇的历史进程中,却留下明亮的印记。
四、结 语
至此,我们通过对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道德》及帕斯卡尔《致外省人书简》和《思想录》中对中国之思考、描述的考察,看到了作为全新的“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其对17世纪法国(欧洲)基督教文化所起到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注释”、“哲学工具”作用。拉莫特不顾彼时神权主义的威压,开拓性地将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平行比较,力举儒学文化精神、张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和道德哲学,其不仅力图以基督教怀疑论替代原先的唯理论,更以“哲学”的名义触及了中国文明的思想内核,为之后启蒙作家追寻“哲人国王”的理想开辟了路径。帕斯卡尔则在“礼仪之争”正待爆发的时代背景下,秉持历史批评的原则,将“自由的思想”巧妙地注入在华耶稣会士颂扬“孔圣人”的赞词之中,以达到谴责耶稣会士道德行为放纵的目的,并通过“摩西与中国”问题的思考,将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融通定位于通过不懈地“寻找”和“观察”来发现共同人性,从而给予了彼时的欧洲人高度的哲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