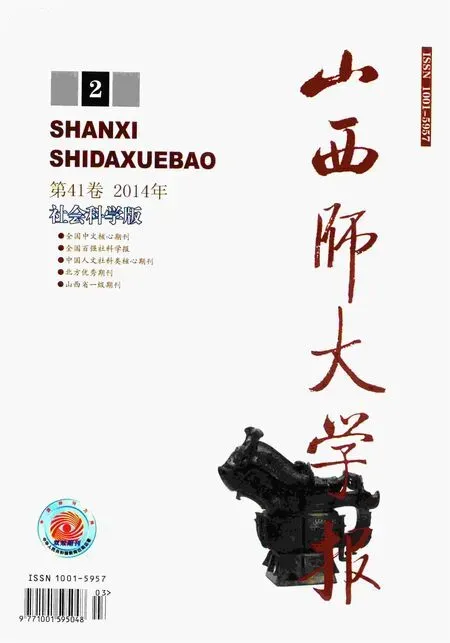死亡的文化呈现及意义阐释
黄达安,苏 静
(1.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南宁 530004;2.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即面临着死亡,死亡为生命设置了限度,却也为生命的展开和意义的追寻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人对于死亡的追问亘古未变,正如叔本华所说:“死亡是真正激励哲学、给哲学以灵感的守护神。”[1]204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死亡和生育构成了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社会的世代交迭,以及文化的“薪火相传”。死亡固然意味着个体自然生命的终结,却是整个人类生命延续和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试想没有死亡,人类生命的更新和突破也将难以实现。
那么,何谓死亡文化?死亡文化不仅指行为层面的丧葬文化、碑刻文化、祭祀文化、吊唁文化等,还包括在观念层面的人对死亡的态度和意识,或者说,死亡文化包括显性直观的器物层面(如棺椁,坟茔,墓碑等)和隐性的具有解释作用的观念层面(包括死亡意识和死亡观念,以及相关的习俗制度等)。总体而言,“所谓死亡文化,就是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以及由此体现于死亡的操作形态和实物形态之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其习俗、规范之总和。”[2]13
死亡是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归宿,也是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的永恒主题,人对于死亡的思考和追问发展出来的文化即为死亡文化,文化意义上的死亡与人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与人类的历史活动纽结在一起,对死亡的追问和思考伴随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已经深入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意识之中。死亡作为最为强烈的否定力量,引发人们对于生命的反思,激发起深层次的艺魂和诗情。“对于人来说,没有像死那样使人思考虚无的场所了。对自我说来,死是虚无的最强烈的现象。正如虚无曾经使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所惊惧的那样,死在他们那里,不,自古以来,就是一般哲学最正统的课题。思索存在的人,而且思索人的人,不能不思索死。”[3]70“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将生命自身的意义建立在更为崇高的价值目标上,使人们能够理性地看待生命的流逝和生存的价值,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和死亡。
一、死亡之意识呈现
死亡总是令人畏惧的,但正是出于对死的恐惧,才激发了人们对于永恒生命的追寻。长沙马王堆帛画中墓主升天的图景,《山海经》中关于 “不死树”、“不死泉”、“不死民”、“不死之旧乡”、“不死国”的记载,以及信徒对于基督复活的信仰,都表明着一直以来人类对死亡的抗争和对永生的渴求。然而,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无可避免地向死亡逼近,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终点,所谓“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列子·杨朱》)。死亡抹杀了一切的差别和自然存在,也激发起人们对于死亡和生存这一对立关系的思考。死亡意识即“关于死亡的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个体关于死亡的感觉、情感、愿望、意志、思想,也包括社会关于死亡的观念、心理及思想体系”[4]2。
死亡意识首先是对作为事件发生的死亡本身的认识。由于死亡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验和亲历,对于人们的知识世界而言,死亡意味着未知的深渊和黑暗地带。人们有关死亡的认知和感悟也往往从恐惧开始,正如古希腊哲人爱比克泰德所说:“可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死亡意识首先在于如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对永生的向往和不死的执迷就是这一死亡意识的产物,即在意识层面上尽可能抹煞、遮蔽、延迟死亡的确定性。其次是对死亡自身的否定所引起的人们有关死亡形式和死亡世界的想象。许多民族的神话和宗教对灵魂不朽的坚信,以及对于乐土、天堂、冥界、地狱等世界的想象性构筑,在某种程度都是由对死亡恐惧的情感体验而来的死亡意识的发展。再次,死亡的无可避免促使人们审视和反思生命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是以“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的方式存在,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紧随死亡而来的虚无,促使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并且认识到对死亡的逃避只会使人无法面对本真的生活。相对于宗教信仰通过创造彼岸世界来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向死而生”实则是对庸常生活“沉沦”(Verfallen)的否定,或者说,死亡赋予了此在以积极的意义。
中西方的死亡意识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死亡文化。钱穆先生就认为东西方人生态度的不同在于,西方以宗教人生为首座,中国则是以道德人生为首座。西方死亡文化受到宗教的影响,对于死亡的拒斥表现为借助宗教的力量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宗教观念将灵魂与肉体区分开来,肉体终会腐朽、消散,灵魂的不朽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死亡只是生命存在方式的转化,生命仍然以灵魂的形式在彼岸世界继续存留。
相比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克服则是通过对现世人生积极肯定来实现的。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儒家重视的是当下生命和现世人生,《荀子·大略》中记载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孔子提出人依据“礼”而生活,纵然艰难,却是人应尽的义务,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做到勉力而为,躬行不悖,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离世,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谓“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并且人应当追求在生命和死亡之上更为重要的价值和目标,既然生命短暂,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如何使得有限的人生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就需要生命意义的延伸和附加,孔子感慨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更有甚者,为了仁、义等价值可以牺牲生命本身,“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秦伯》)儒家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使人们认识到肉体生命的消逝不足为惧,文化、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延续更值得去追求。相较于儒家现实功利的生命追求和道德境界,道家的方式则主张取消生死之间的界限,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既然生与死齐一,为死亡而忧心忡忡就未免杞人忧天之讥了,而只有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脱,才能最终获得生命的真正自由。
二、临终文化:活着体验死亡与生命意义之生成
即使人具备了“先行到死中去”的自觉和勇气,当死神真正来临时,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情绪,甚至可能引发人的消极应对。“威胁人们最大的不幸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死亡,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人的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什么比别人正遭受生命危险更能激起我们最强烈的关注;也没有什么比被判以死刑更加可怕。”[1]207说到底,即使人们相信人的生命形式在死亡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如灵魂、超脱、升仙等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但仍然无法阻止人们对于死亡的根本恐惧。因为死亡充其量只是他人的经历,我们只能见证他人之死,并从中推断、想象,对每个活着的个体而言,死亡是在自身的主观体验之外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我们不会活着体验死亡。”对于死亡的先验恐惧是临终文化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临终文化正是对临终阶段的人群及其亲属的支持和特殊照顾,目的在于缓解死亡造成的恐惧和忧虑,提升生命的质量,体现人道关怀。临终文化表现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前者的代表是临终关怀,后者的代表是安乐死问题。
临终关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英国的桑德斯护士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发展到现在,临终关怀已经成为照亮人生最后旅途的灯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与临终关怀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机构是建立于1988年的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临终关怀”(hospice care)一词从拉丁文“hospes”发展而来,意指相互照顾,具有较为强烈的宗教慈善意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视,使得临终关怀和临终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临终关怀的文化意义在于主张生命应当获得同样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特别是在对待老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态度上。在生产经验之于生产活动重要性较低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功利性的社会发展要求往往漠视老年人口的存在价值,常有遗弃、限制、资源不等分配等变相剥夺老年人生存权利的状况。临终关怀的提出是对这种功利性人口观念的纠偏。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迅速,预测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近14%的人口是老年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临终关怀的研究和发展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逼近死亡给临终者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恐惧和焦虑,还有肉体上的折磨和苦痛。在后者大大超过前者时,对于生命的绝望也会让部分临终者选择自主死亡,或者是当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识已然不复存在,肉体的存留是否还有意义成为疑问时,由他人做出终止其生命活动的抉择,就涉及到安乐死的问题。长期以来安乐死一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死亡是否是人的权利的一种,是否有必要从伦理道德上谴责由自己或他人做出对生命的决断,以及应当由个体自身还是由个体之外的宗教、集体利益等外在力量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成了安乐死广受争议的诸多原因。
安乐死主要针对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征的个体,以及不可逆的器质性垂死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等,其形式包括医生在规定范围内对病患者的无痛致死,病患者的自杀和拒绝治疗,以及亲属或他人的不作为等。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思想家赞同以自杀来解除病痛折磨的做法,主张应当“任其死亡”。中世纪时,基督教宣扬生命是天赐,认为结束他人包括病人的生命是绝对罪恶的。17世纪,培根将“euthanasia”一词用于指公民自愿基础上的安乐死,并认为安乐死的研究是医学技术的重要领域。19世纪中叶,蒙克(W. Munk)把安乐死看作是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但反对加速死亡。20世纪30年代,英国上议院和法国参议院曾讨论过安乐死的法案。1936年英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协会。然而安乐死的讨论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极端,赫克尔甚至主张要毒死“千千万万无用的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安乐死的名义杀害慢性病人、残疾人、精神病人和所谓的劣等民族达数百万人,大屠杀将安乐死当作杀人的藉口和手段。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安乐死避之不谈,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于重病患者的安乐死问题才再一次被提出。
反对安乐死的多为持生命神圣论者,对他人或自身生命的自行终止或加速终止被视为违反了传统的道德原则和宗教观念,胡弗兰德的《医德十二箴言》中即规定了:“即使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治时,你该维持他的生命,解除当时的痛苦而尽你的义务,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不人道。当你不能救他时,也应该安慰他,要争取延长他的生命,哪怕是很短的时间。”[5]144目前对于安乐死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尽管荷兰为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将安乐死视为合法行为,但安乐死的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以美国为例,不同州的法律对安乐死的规定是不同的,医生因为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而被指控谋杀的报道仍见诸报端,我国的法律也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主张安乐死观念的人认为生命权利属于个体本身,这里所说的生命权利包括了生存的权利和死亡的权利。特别是后者,认为人们有权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处置,包括终止其存在的权利。1976年举办的东京安乐死国际会议的宣言中就提出了应当尊重“生的意义”和“死的庄严”。
三、丧葬文化: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性建构
死亡对于亡者而言是生命的结束和永久的休息,而对于生者而言除了直面死亡过程的发生,亡者的故去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结束,丧葬才是死亡过程的真正句点。丧葬作为死亡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性建构,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死关系的本质理解。
首先,由于坚信存在着死后的世界,人们通过丧葬仪式将死者送入比照现世生活所构想出的死后世界。作为礼制性建筑的陵墓就是这一死后世界的重要部分。在墓葬中不仅要按照日常宫殿房屋的样式建造地宫阴宅,还要在墓穴中保存亡者生前的摆设和日常用具,使之看起来与死前生活并无二致,甚至用活人殉葬,就是因为相信死者将以另外的形式继续生存和生活。秦始皇的陵墓建造“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连自然万物也通过象征的方式纳入到陵墓的设计中。荀子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篇》)正是基于此念。不独中国如此,这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民族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某种死亡的祭礼。生者的最高的宗教义务之一就是在父亲或母亲死后给他供奉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供死者在新国度中生活下去。”[6]132—133也就是说,灵魂不死是此种丧葬文化产生的起源。受“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观念的影响,丧葬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将死亡看作个体生命存在形式的转变。
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除了以此标识亡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炫耀财富之外,还因为人们相信亡者对于生者的现实生活能够起到威胁或是荫庇的作用,这也是丧葬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尊敬、恐惧,甚至包含厌恶的复杂情感的缘由。“对原始人来说,没有不可逾越的深渊把死人与活人隔开。相反的,活人经常与死人接触。死人能够使活人得福或受祸,活人也可以给死人善待或恶报”。[7]294对于死亡的未知使原始人相信死者的力量与神灵或其他神秘力量的能力可以相提并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鬼与神本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因此侍奉死者甚至比对待生者的态度更要谨慎和拘束。在加拿大,“当村里发生火灾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把死人转移到安全地点,如果村里有死人的话,活人们从自己身上解下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来打扮死人;他们时常启开死人的坟墓,给死人换衣服;他们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食物送到死人的坟上和他们想象的死人的灵魂游荡的地方……他们把死尸埋在坟墓里时十分小心谨慎,要使尸体绝对不接触泥土:死者躺在那里,就像躺在围满了兽皮的小小密室里,这密室比活人的茅屋要富丽堂皇得多。”[7]293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指出丧葬仪式在原始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基于此形成了一系列与死亡有关的风俗、禁忌和仪式等。
其次,丧葬是对亡者评价的完成和哀思的寄托。俗语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又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也同样意味着生命的完成。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亡故者的一生和品行予以总结。古代贵族死亡后需在祖庙前举行丧葬祭奠仪式,宣读诔词和确定谥号,意味着由生者对亡者做出评价。所谓“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周礼》郑玄注)。丧葬仪式宣告人的现世生命的结束,并对人的生命和人格有一确定的反映,才是人生的真正完结。评价亡者或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对于生者也是示范和警诫,具有教育后人的文化功用。另外,丧葬仪式还具有通过集体性活动将由于死亡造成的恐惧、郁结、忧虑、遗憾等负面情绪释放和宣泄出来的作用。“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第三》)死亡给生者带来的震撼和痛苦不仅在于死亡的不可避免所引起的悲哀、恐惧、无奈和缺憾,更在于亲人的离世对情感所造成的创伤。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悼亡的诗词文章,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袁枚的《祭妹文》、《红楼梦》中贾宝玉祭奠晴雯所作的《芙蓉女儿诔》等都是祭文的名篇,其中最直指人心的莫过于诗人炙热而真挚的情感。
再次,丧葬和祭祀仪式对于“活者的世界”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丧葬文化和祭祀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构建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宗庙是古代帝王和贵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不仅如此,宗庙在社会生活中还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保障,丧葬仪式以及之后定期举行的祭祀仪式将同宗族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举行集体性的活动,对于增强宗族观念和群体情感具有特殊的意义。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卷下《宗族》释为:“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所尊也。”宗法制即脱胎于父系氏族家长制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宗庙是丧葬仪式和祭祀仪式的重要场所和载体,由于祭祀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宗庙也被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宗庙的覆灭一般被看作是王朝覆亡的标志。儒家尤为重视丧葬文化和祭祀文化,儒家倡导慎终追远的孝文化,孔子向樊迟解释何为“孝”时即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二》)。《礼记·祭统》亦云:“孝子之事亲,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可见丧葬文化和祭祀文化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孝道文化的集中体现,甚至于将之视作孝道的头等大事,“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者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章句下》)。
尽管孔子曾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然而对丧葬仪式和祭祀仪式的重视,以及将丧葬和祭祀的执行程度和情感投入作为衡量是否尽了孝道的标准,仍然助长了社会上“隆丧厚葬”的风气,以致到了“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盐铁论·散不足》)的程度。即使在现代社会,“厚葬以明孝”和“富不富,看坟墓”等畸形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仍然存在,人们把大办丧事作为向旁人展示“尽孝”和家族势力、财富的手段,即使经济状况困难的家庭,也会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操办丧事,以至于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死人无知,厚葬无益”,“简丧薄葬”无疑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1] (德)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王夫子.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3] (日)今道友信,等.存在主义美学[M].崔相录,王生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 孙利天.死亡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5] 汪松葆.中医学导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
[6]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 (法)列维5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