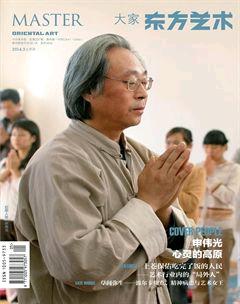电影不死是为娼
晓白

现在的人,对电影要求都很高,既要有娱乐性,又要有故事性,两性缺一不可。往前推个几十年,在我童年的时候,电视机还是一个稀罕玩意儿。城市里的人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看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跟去公园遛弯、菜市场买菜、澡堂子泡澡一样稀松平常。农村的人就看露天电影,各种婚丧嫁娶、百岁满月都会请村里的电影放映员去城里租赁胶片,天一黑,双片联映就开始了。小孩们会跑到荧幕后面去看,一边看一边嬉闹,荧幕的正面坐满了人,盛况空前,史无前例。当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一百亿的时候,这种景象已经绝迹了。
娱乐性不同于观赏性,观赏性包括了娱乐性,娱乐性仅强调娱乐。娱乐和故事是美国电影横行霸道、夜郎自大、张扬跋扈的秘籍。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大制片厂体系建立以来,这种所谓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有可口可乐的地方就有好莱坞大片。2013年,有三十四部分账大片进入了中国的电影院,其中三十部为美国电影。今年国产电影年产五百多部,进入电影院的有二百五十部左右,强调娱乐性和故事性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另外百分之五只强调故事性。这个数据说明,我们的电影跟好莱坞电影没什么本质区别,若有区别,那就是好莱坞电影很烂,中国的跟风片更烂。
跟风片的势头愈演愈烈,电影投资人的算盘打的丁零咣当的响,电影院的荧幕以每天2.5块疯狂增长。仿佛,冷静的人才在旁边冷眼旁观,热闹的人都在拼命赚钱。这是中国电影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电影最为悲哀的时期。
跟风片强调的娱乐和故事并不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惯用的伎俩,而是近几年,国产电影“假象繁荣背后投入和产出不协调造成的失控现象”。中国电影的上一个繁荣还要追溯到解放前的二、三十年代,当时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电影制片公司,如明星电影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国光影片公司等,仅1922-1926年间,单上海一地就先后开办了145家电影公司。这些电影公司,时至今日都在影响着华语片的进程。在当时,国语片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水平之高,令人咋舌。就拿1936年,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程步高导演的《新旧上海》举例。这部影片在艺术成就上并不高,严格意义上讲,跟今天的商业片别无二致。影片讲述的是几个租户在一个弄堂里,楼上楼下,几户人家,房东太太整日闲坐于大厅,从早到晚,跟租户打招呼。一部典型的合家欢喜剧。“幸福人家彼此都很类似,可是不幸人家的苦难却各不相同。”编剧正是紧扣这样的主题,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为戏剧冲突,张弛有度地叙述了生活的不易、战争的苦难和家庭存在的必要。导演程步高在影片的节奏上也延续了剧本散发出来的戏剧叙述,一以贯之、酣畅淋漓,细微处有真情,明处有暗线,悲处有喜剧。
我称这种电影叙述为“文学叙述”,区别于“故事叙述”。《新旧上海》属于文学叙述中的戏剧叙述,整个影片以戏剧的平铺直叙展开,以戏剧的冲突和矛盾做衔接纽带,这种电影很难控制,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戏剧,而不是戏剧电影(1982年,谢添导演的《茶馆》,即为稍有不慎者)。故事叙述的主要问题是它只讲故事,讲明白一件事、讲清楚一件事、讲透彻一件事为首要目的。整个影片则需要为这种所谓的“故事”牺牲原因的电影魅力,镜头也将失去本身的叙述性,来服务于“故事”。而文学叙述的好处是电影可以是小说式的叙述,也可以是戏剧式的叙述,又可以是散文式的叙述,更可以是诗歌式的叙述。而电影叙述中最为高明的叙述是定义不了的,也可以理解为“不存在叙述”,而叙述只局限于观看式电影,即“大众电影”。
《新旧上海》不管是编剧洪深对于剧情戏剧叙述上的完美,还是导演程步高在影片调度中的严谨,或是摄影及其他工种表现出来的专业性和出色,都足以使我们大为惊叹。而且观赏性和喜剧效果极佳。
为什么提《新旧上海》,是因为我想拿它和另一部喜剧片作比较,那就是2012年底上映,由光线出品,徐铮导演的《泰囧》。从片名上看,它和《新旧上海》一样的让人一头雾水。我想探究的是,中国喜剧电影经过七八十年的演变,是变的越来越开放了还是越来越封闭了?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不存在可比性。
首先,《泰囧》通过商业炒作和噱头力挽狂澜、以小搏大,创造华语片票房新高,这件事情本身是可喜可贺的。这是中国电影票房潜力最大化的一次体现。其次,本片为什么要拿来和《新旧上海》作比较。《新旧上海》的优秀体现在两个方面,叙述和技术。洪深的叙述是有功底的,若没有满腹经纶,出来的味道肯定会走样儿。《新旧上海》的制作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每个技术工种都出类拔萃。而《泰囧》在这两方面严重缺失,甚至可以用“浑水摸鱼、滥竽充数”来形容。《泰囧》的叙述延续跟风片的“故事”叙述铺展,自始至终,节奏凌乱,东拼西凑,苍白无力。如此这般并不甘休,又高举“拿来主义”,跟他的圈中好友宁浩学了一把,喜欢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宁浩的“拿来主义”也很没品。若他仅仅抄袭美国电影也就算了,它连香港电影的桥段也不肯放过,这就有点可悲了。整个电影下来,你会觉得,这个片子的编剧并非舞文弄墨出身,而是江湖游士,众所周知,江湖游士也有才华横溢旷世之才,用江湖游士来称呼他们也有点儿言过其实,高看了。电影从发明之初,就跟美术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相辅相成唇亡齿寒。但《泰囧》却实现了电影的另一种可能,不存在美术,不需要文学。若一部电影,一不实验,二不艺术,三不传统,四不美术,五不文学,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观看它的理由。我对电影的认识向来狭隘,很多人会反驳我说“好看不就成了?”好看是观赏性,娱乐是喜剧张力,两者《泰囧》也不具备。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导演的艺术,上梁不正下梁歪,把问题和走样儿归咎于技术工种显然有点儿吹毛求疵不合时宜。第三,《泰囧》的问题出在哪儿?烂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么烂,大家还振臂高呼其为“佳作”,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高票房不等于观众爱看,高票房只代表很多观众看过。在中国,票房的二分之一长期被美国大片占据,喜爱看美国大片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也会喜欢看《泰囧》,因为它们同样的烂。对于烂的欣赏,中国观众向来独具匠心。中国观众对烂的通胀消费,并不是中国的电影观众审美出现了问题,而是市场运作出现了问题。无论美国大片如何嚣张,在法国都会受到冷遇,这跟法国人的观影传统和独立的电影意识有关,而这两点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一直停顿在“好”和“不好”上,不存在两极中间的数值。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观众的选择权受到集权筛选和分配的严格限制,中国观众只能在一堆烂片里寻找“佳片”,在鸡蛋里挑骨头,在死鱼堆里挑鸡肋,可想而知,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何其的困难。从“焚书坑儒”之后,中国思想的多样性随着利于帝王统治的教育延续下来,这种局面直到“五四运动”才稍有改观。但从整体上讲,这种民族的危机感和侵略性始终停留在久远的过去。正如我们在小学时上的地理课,老师会问中国的版图像什么?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公鸡”,而异口同声的回答并不是我们的“聪明”,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这种思想移植于“第七艺术”,同样会限制到它的创作和发展。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电视节目同病相怜,一流的电影院里放着三流的电影,一流的电视机里放着三流的电视节目;而法国是三流的电影院里放着一流的电影。第四,《泰囧》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真正影评人”的重要性。没有高水平、高智商、有胆识、有见识、有学识、有独立电影观的影评人的电影国度是不存在真正电影繁荣的。
中国电影向来注重西游神话,认为向西方取经就能获得大乘佛法;其实不然,很多时候,佛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脚下。电影的出路也是如此,对电影多样性的认同,对“焚书坑儒”思想偏见的摈弃,对民族本身人文价值的自信,是中国电影的“终南捷径”,背道而驰则会“万劫不复”。不过,那种真正的电影天才是任何枷锁和限制都阻拦不了的,他们正隐藏在那些手持DV的电影爱好者之中。毕竟,电影的未来是大众的。
在过去的一年(2013)里,有两部华语片不得不提,若没有他们,我们的电影将不堪入目。一部是贾樟柯的《天注定》,另一部是蔡明亮的《郊游》,悲哀的是,它们都无法在影院与我们相见。这不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诚然如此,那些勇敢的电影斗士并不气馁,因为他们比这个时代更清楚:我们迷失在了哪里?
2014年1月25日